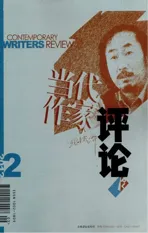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学的真正传统是先锋精神*
2012-12-18高晖
高 晖
能有机会与各位探讨当代文学与传统的问题,这对我也是一个梳理思想的机会。汪曾祺说:“只要用母语写作,就离不开传统”——的确是这样: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染缸中浸泡,从开始用汉语阅读,我们就接受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簇拥,这些都已形成常态。如果没有这次会议的提醒,我甚至从来没有正式地思考过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内在关系。从会议开始到现在,我的大脑里始终由一系列关键词组成,其中有上述各位的发言给我提供的一些新鲜词语,还有自己随兴而来的词语,而且这些词语始终在相互撞击,我甚至可以听见它们撞击时发出的声音。其中,处在高音区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就是刚才张清华教授传递给我的一个词汇,我将它转换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还有几个词语就是自己刚刚想到的——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文化参与、个人勇气、精神出路。
其实,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就开始探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相关话题,也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又提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新世纪以来,主流文学继续将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书写中华民族性格作为叙事文学的期待——甚至是焦虑地期待那些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的文本。那么,这样的文本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真的可以融东方式的空谷幽兰和西方式的理想国于一体吗?我觉得——我们至今并没有看到过,其实也从没有哪一部经典会这样周全,特别是在当时代遇到这样完美的评价。我认为,讨论问题应该集中在:我们是否真的熟悉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到底在什么部位?它对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激活它?这些问题,我一时无力回答清楚。我也许只能涉及一些与上述关键词语相关的话题。
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忽略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从来也没有讴歌过、攀附过当时代,也没有赞扬过当时代人民的什么伟大性格,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时代精神的指向,以追求真正的现实为动机,始终成为时代的叛逆者。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到屈原的《离骚》与《天问》、庄子的散文、李白诗歌,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一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当我们只是简单地考察成书的时间、当时代的背景,再传播时间、被阐释的时期、被经典化的时代对比,就会发现上述问题真切存在。
此外,在上述中国文学经典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绚丽、最生动的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阐释为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古典文学,而中国古典文学补充、反哺、激活、牵动着中国文化的筋骨,形成特殊的对立统一状态。我认为,《史记》、《离骚》、《天问》、《三国演义》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强烈的批判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而不是审美意趣、写实性和道德色彩,恰恰是这些作品对儒家的积极入世、孔子的圣人人格以及仁义精神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审视和追问。从庄子散文、李白诗歌、《红楼梦》、《人间词话》、《西游记》里面,我们除了看到浪漫主义情怀、感伤色彩,也能看到它们对道家形而上哲学、终极追问以及宁静守雌观念的文化承袭、批判、补充和激活。特别是从《金瓶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儒释道的通融,兰陵笑笑生写出了真正的佛性。我始终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先锋文学的真正鼻祖。昨晚聊天的时候,格非对我说,他读了四五遍《金瓶梅》,我感觉比较震惊。
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突出体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始终站在当时代的精神前列并已找到自身赖以存活的精神资源或者靶向——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儒释道以及由此展开的阐释、批判、超拔、补充、激活。也许,就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特有的文化哲学精神,也恰恰是我们后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阵痛点,这也是我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先天性的革命精神,即先锋特质。当然,这种先锋特质的形成、作用过程极其复杂,甚至包括当时代统治阶级的阐释误读、曲解、话语争夺和篡改。
前段时间,我看过一本法国人布尔迪厄写的书——《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书里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一个事实,即改变词语……早已是改变事物的一个方法。”①〔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第136-1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别样意义:一是文学所制造的话语系统及其话语关系,一直与社会文化关系相互勾稽并呈现出相对独立性,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始终游离于当时代意识形态之外,处于民间立场并在内部隐藏着理性精神、反叛精神与文化诉求。二是社会文化参与文学构建时呈现出自身的内在逻辑。比如,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从匿名、具名到经典命名,无疑是一种传统和现实的文化释放过程,同时经典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也无疑是政治、学术话语权的争夺过程。
我觉得,近三十年以来,无论中国当代文学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其基本形态就是颠覆和破坏,并在废墟中与世界文学再高效接轨。那时,我们从学习西方各种文本开始,曾给当代文学带来崭新气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最大贡献就是研习西方美学感知经验及其表达技术,特别是表达样式和形式感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西方叙事美学的掌握已近乎西化,中国作家已经不再缺少世界文学的表达技术,只是缺乏对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总体把握,这样,怎样续接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神,的确应该成为我们着力考虑的问题。今天,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以改革求新的姿态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真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伪命题。比如此时,我们从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转换和变革角度,探讨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就显得较为庄重。近年来,中国作家已经着手对接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此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艰辛以及成果。具体说来,中国作家已经开始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独特文化逻辑,其指向是不是色和空,是不是聚和散,是不是盛和衰……这些,都显得较为重要。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是拯救与逍遥,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应该是载道与性灵。即使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重叠表述空间,那就是悲悯——这是一个作家的心胸所在。其实,中国当代作家已有不少作品开始展现这种悲悯,关键是怎么样将这种悲悯切入中国的文化逻辑,这应该是一个问题。当我们考察新时期作家的近期作品时,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寻找属于中国的文化逻辑,并业已在此背景下建立起自身的文学话语系统。
至于当代中国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产生距离的原因,这里既有宿命、遭遇、学养,也有历史、心理、时代等相关因素,其中均可以囊括在中国经济生活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关系里,但集中体现只有在一点:那就是当代作家本人的人格问题。刚才,王光东教授提出的一个现象值得仔细考察,就是现在能继承传统并能确切表达传统的,恰恰是中国的新时期的先锋作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而且有趣味的现象,其实也是符合文化逻辑的现象,我认为,真正的先锋恰恰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真正的传统:中国当代作家,从先锋,到传统,再到先锋,这是一条成熟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作为从事写作的个体,面对这些繁多的概念,我的唯一策略就是忽略。我的意思是说,以上我所陈述的这些概念都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认为,自己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已经接受四十多年的中国文化浸淫,其传统已进入我的血液。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愿意将很多概念处理得比较模糊。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找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真正根脉。其实,写作的这么多年,我始终在想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样从一个农村孩子变成这样?从一个生下来三点三公斤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中年男人。在肉体形态变化中,我的内心生活发生哪些变化?到底是什么使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我的灵魂深处是受哪些东西的牵动——是受欲望牵动吗?受传统牵动吗?受情爱牵动吗?这些可能都不是,我认为始终有一种非常单纯的东西在推动着我。我总能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家伙从青春期怀疑、背叛信仰,到后来将自己遗失,最后重拾信仰——将个体的有限生命附着在上帝的永恒精神上。我的想法是,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走出一条寻找的道路,也许现在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其实,我近年来一直将自己当作体验的器皿,我在这个器皿里尽可能地盛装、呈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我时刻看着它们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如果说,我将这个器皿做成并且描述出来,并且始终在中国的文化逻辑上描述这个问题,虽然规模较小,也会有其自身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逻辑是否还要依赖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经验和表达,这也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昨天来到这里,①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的主会场,设在沈阳城区南端的明清册,一座体现江南式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别墅群。突然大门一关,我就觉得自己与现实有被瞬间切断的感觉,自己被笼罩在中国明清时代的建筑氛围中,至于明清的建筑味道是否表达得完全我搞不清楚,但我还是觉得此刻和当代现实生活具有很大的差异——整体建筑氛围传达着很多具有流动性的东西,比如,那些陌生离间效果、那种排延关系,还有那种远与近的关系的表达,都呈现着某种特定的流动性、空灵性,在这里我甚至想到了叙事文学本身。我觉得,这座建筑物所呈现的叙事效应,集中体现在叙事结构方式上,在这里,整座建筑物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的美学经验。如果上述美学经验体现在中国的小说里面,是否就意味者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就是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如果是这样,应该类似于《红楼梦》和《金瓶梅》吗?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表达还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我前面说过,新时期先锋作家的革命性贡献在于颠覆、破坏中国小说美学经验,并建立起新的形式感。那么,当中国当代作家建立起这些以后,还应该如何表达呢?是回归到中国传统的美学元素表达还是采用更新的方式表达,这是另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自己的问题只是——怎样重塑一种针对心灵的表达方式,是与一种内心的硬度、厚度、弹性、生成、变化有关的表达方式。刚才,张清华教授说,贾平凹的《废都》的文学想象、文学形象、结构、神韵和中国的传统有一种隐秘的沟通和回应,在二十年前所预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在今天已变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那么,我的问题是:像贾平凹这种《废都》式的沟通和回应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那怎样才能超越中国传统的美学经验?
我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真正传统就是先锋精神。从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提出回归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不应该是回归文学传统的形式逻辑,而应该是回归到以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始终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基本根脉的革命化传统体系中来,包括对现实的反叛、个体生命勇气的呼唤、精神出口的找寻、生命信仰的重塑。我觉得,这些才应该是我们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根脉所在,而不应该单单指那些所谓重构传统的宏大叙事之类的巨型概念。所有的经典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体系、没有表象的传承、甚至没有相同的文化符号,它自身就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从操作层面上说,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继承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力量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美学经验的再度创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