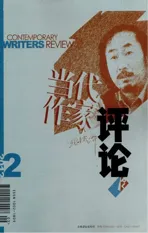文学青年加西亚·马尔克斯①
2012-12-18依兰斯塔文斯史国强
〔美〕依兰·斯塔文斯 著 史国强 译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来到巴兰基亚——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重要的工业港城,人口二十五万左右,当时他的父母还在这里生活——来此地与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的妹妹玛格特相见。他比妹妹仅年长两年零八个月,但他还依稀记得信号灯变来变去的色彩。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外祖母领他再次来到巴兰基亚,他在这里见到了第二个妹妹艾达·罗莎,又赶上巴兰基亚纪念西蒙·玻利瓦尔逝世一百周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看见一队飞机在空中翻筋斗,尤其是一架又小又黑的飞机“como un gallinazo enorme”,宛如硕大的老鹰在空中画圈。
一九三四年父母从巴兰基亚返回阿拉卡塔卡与外祖父他们一同生活。与他们一同回来的又多了两个孩子,玛格丽塔和利奇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母担心镇上学校是教会办的,怕对孩子有所限制。他读过蒙台利梭小学,那里的教员很是投入,他也喜欢阅读。但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读更好的学校,将来让孩子们在苏克雷有个立足之地。最后这家人又搬到了巴兰基亚的另一座小镇,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他们始终没有离开。
入学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爱上了画画。他总把涂鸭式的作品送与成人过目。此时他喜欢的读物是《一千零一夜》。安格里塔神父怕他们在乏味的阅读中虚度时光,所以总要考考他们,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告诉神父,《一千零一夜》百读不厌。他手里有一版未经删节的小说,“粗俗的故事”还在里面。他日后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部重要作品,因为我总以为严肃的成年人不会相信精灵能从瓶子里出来,或者一念咒语门就能打开。”①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ving to Tell the Tale:136.
这部波斯人的经典著作在他作品里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这部民间传说和故事集与《百年孤独》之间有着众多的关联。《一千零一夜》里的叙述人 Scheherazade——在波斯语里指“镇上的女人”——每晚入夜之后都要给国王丈夫讲个故事,不然就被处死。国王喜欢杀妻,凡是夜里不能让他高兴的妻子几乎无一幸免。在Scheherazade与梅尔卡迪斯之间有着共同的地方,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里的这位贝都因人要大于现实生活,如同幽灵一般,他死掉之后再度现身,而且还为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拉出了大纲。他能未卜先知,为一百年左右的家族史诗定下调子。梅尔卡迪斯和流浪的犹太人原来是神话里的人物,被加西亚·马尔克斯信手拈来,写进小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了民间故事手册。随着一个个故事不停地展开,不同的次要情节也在要求自己的生命,但这些情节都是通过人物与布恩迪亚家族的关系联系起来的。
当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巨大的另一部作品是《圣经》。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未亲口坦白,因为他对教会持有批评态度。在哥伦比亚等天主教大行其道的国家——虽然哥伦比亚对非洲文化的接触在十六世纪为加勒比沿海送来了奴隶贸易——圣经式的叙述不仅要出现在礼拜日的布道上,而且在大众文化及其他论坛上也是无处不在。音乐、报纸及其他媒体总要提到《圣经》。当地的出版物为了引人注意也要借用《圣经》里的人物。这一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百年孤独》的写作如同《圣经》里的故事,其结尾出现的都是饥馑和战争,布恩迪亚诅咒的核心也是乱伦。诅咒跟在选民这一概念之后:如同《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二节里亚伯拉罕之后的以色列人,上帝令他们离开家园,外出寻找新的土地,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将成为一个大国的族长,但又不能事事顺心如意,与此相同,布恩迪亚家族必然能够见到荣耀,但又少不了被诅咒。
这一时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发现了其他儿童读物,都是小书虫和青年人喜欢阅读的:格林兄弟讲述的民间故事、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朱尔斯·沃恩的《环球航行八十天》和《地心之旅》、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艾米利奥·萨尔格利的《黑海盗》、《神秘的黑丛林》、《萨姆达卡大地》、《蒙普拉希姆的老虎》及《马来西亚海盗》。阿尔瓦洛·马特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他们一九四九年在巴兰基亚相见,他就说自己小说里那个无所不能的人物瞭望员马克罗尔的创作灵感来自沃恩和萨尔格利的那些历险小说,这些作品是他青年时阅读的。萨尔格利对其他拉美作家也有启发,从博尔赫斯到富恩斯特,都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他的反帝倾向更容易在西班牙语作家那里找到知音,因为后者十分警惕美国在南半球的影响。萨尔格利又与沃恩不同,前者在美国几乎没人知道。②我1995年为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撰写“The First Book”(文章收入 Art and Anger〔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6〕),与报社的编辑人员据理力争,他说没有Emilio Salgari(萨尔格利)这个人,因为国会图书馆目录册里没有他的名字.我又亲自查了一遍,果然如他所说,这件事很是扫兴。不知何故,如此重要的作家在英语世界里连提也不提?
当然还要提到《堂吉诃德》,总有人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作与这部经典作品相提并论,这不是因为两部作品在情节或角色或人物上有相似之处,而是因为每部作品都在西班牙语世界里经历了时间的锤炼。塞万提斯的两卷小说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出版,现实与虚构平行推进是这部作品的精髓所在,《堂吉诃德》比《百年孤独》早了三百五十几年。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来说,“最好是阅读另外一章”。他在骨子里不喜欢这部小说,他对此也不讳言。“骑士扈从的话没完没了,又文绉绉的,令我感到无比乏味,我并没发现侍从的愚蠢行为有逗人的地方,我甚至在想我读的这部作品和大家好评连连的作品未必是一部。”
但他的初中教员梅斯特洛·胡安·卡萨林斯强烈推荐《堂吉诃德》,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听老师的话,所以他还要再读一遍。他开始了二次阅读,但他感到如同吞下“好几汤勺的泻药”。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说:“我读初中之后又试了几次,因为这是一定要研读的作品,但我的厌恶仍然没有改变,后来朋友才建议我把小说放在坐便后边,等如厕之后再取出来阅读。通过这种办法我才发现了《堂吉诃德》,宛如火焰,之后我反复咀嚼,最后小说里的不少故事都能默念出来。”①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ving to Tell the Tale:137.
一九三九年,一家人搬到苏克雷。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在圣约瑟中学读初中。这所中学位于城内,毗邻教堂。他最早的八年没在父母身旁度过,等他读高中之后又与父母很少见面。根据妹妹们对他的回忆,他的兴趣所在,谁是他的朋友,这些都是他们听来的消息。疏远是他与家人的一大特点。妹妹们总是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惊喜,有几次他的消息变成了动力,还有几次变成了妒嫉。等他成名之后,他又成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有时为这个家人买一个公寓或为那个家人支付医疗费。
孩提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充满了好奇心。他从小学到初中的成绩证明,他是上进心强的学生,门门功课都不马虎。他腼腆,不喜欢说话。据说他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入读圣约瑟中学之后,他遇见了胡安·B.斐南德斯·利诺维特斯基,此人后来成为著名记者和《先驱报》的编辑。一九四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健康的原因返回苏克雷。等他再次回到圣约瑟中学后,他为学校办的杂志《青春》投出第一个故事,这份杂志是耶稣会士为提高学生素质创办的。
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产阶级身份开始面临威胁。此时他的家庭已经陷入金融危机。加布列尔·艾里奇奥几乎入不敷出,为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九四三年一月再次回家。他面对两个选择:或是与他的六个弟妹留在家里或是想办法读完高中。他决定前往波哥大,怀里揣上几封推荐信,到教育部申请奖学金。他要在首都完成中学必修课程。他感到要有更大的空间才行,还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从地理上说,波哥大位于哥伦比亚的中央,他对那里既感到紧张又充满期待。他在波哥大得到奖学金,入读著名的奇帕科利亚男生高中;这说明他作为学生的地位有所提高。
奇帕科利亚距离波哥大约三十英里,如今已经是首都特区的一部分,当时因盐场和大教堂而著称。(奇帕科利亚是当地的印第安语,指国王奇帕的领地。)入读这所高中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开始思考政治问题。多年之后他回忆说:“这里有不少教员在教师进修学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所学院是三十年代阿尔方索·洛佩斯左派政府创办的。代数教员在课间为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化学教员把列宁的著作借给我们,历史教员告诉我们何谓阶级斗争。等我离开那座冷冰冰的监狱之后,我不知道哪里是南,哪里是北,但我确实有两个强烈的信念:一,好的小说一定要通过文学来再现现实;二,人类的未来在社会主义。”①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96.
这一时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了一批西班牙黄金世纪的作家,菲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伊·卡尔皮奥、弗朗西斯科·德·科维多·伊·维利格斯、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格特、皮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伊·赫诺和特尔索·迪·默里纳。数百年来以上文学大家对西班牙语作家发生过重要影响,以巴罗克式的、自我意识明显的风格确立了诗歌写作的形式。他发现了他们的十四行诗、民歌和四行诗,而且开始写作诗歌。但他早期的文学作品没有留存下来。
在他读高中时(他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九岁高中毕业),②Registered at the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in Folio 345,Libro18.在苏克雷的一次舞会上,爱神降临,他遇见了十三岁的梅赛德斯。梅赛德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马甘格,是家里的长女,地中海移民的后代。她的曾祖父是叙利亚人,她的祖父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她父亲是阿拉伯商人,经营药店和杂货店。舞会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请梅赛德斯嫁给他,其实他们的结合十二年之后才成为可能,那时的他不仅在哥伦比亚的其他城市生活过,而且还到过罗马、巴黎和伦敦,足迹遍及欧洲。多年之后他对朋友曼多萨说:“如今回想起来,我认为求婚是个比喻的说法,在那些日子里找女友,求婚能使你摆脱所有的麻烦。”③Pete Hamil,l“Love and Solitude”:130.
爱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里是不可缺少的佐料,可能从那时开始,不到二十岁的他才初次发现爱情的深度与宽度。几十年之后他在哈瓦那对记者说:“有一件事我是相信的,我一生是个浪漫的人。但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但青春不再,你就被迫相信浪漫的情感是反动的,落伍的。时光流逝,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才发现这些情感,这些感情,是何等的原始。”④Pete Hamil,l“Love and Solitude”:130.
梅赛德斯来自玻利瓦尔区,那里属于罗马天主教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在那边做过电报员。女孩地中海人的美丽强烈地吸引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没法不想她。她使他联想到一个埃及女神,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百年孤独》第十八章里,作家间接地提到了梅赛德斯。经过漫长的隐居之后,最后一个奥雷良诺再次离开老宅。在他二次外出时,“他仅仅走了几个街区就来到一家小药店,药店窗户上满是灰尘,瓷瓶上贴着拉丁语,一个尼罗蛇般的美人将药递给他,药名是何塞·阿卡迪奥事先写在纸上的”。⑤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379.
根据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成绩报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入读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学。他读大学主要是为了讨父母高兴。他来自人口不足二万的小镇,首都对他来说似乎太大了。但面积未必等于深度。他感觉波哥大是“一座遥远的、阴郁的城市,从十六世纪开始,无情的毛毛雨就在这里下个不停”。他告诉朋友曼多萨,“这里有太多步履匆匆的男人,黑衣服,黑帽子,与我身上的装束相同,惟独一个女人也看不见,这是昏暗的首都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我注意到法国大洋马在雨水里拉着啤酒车,有轨电车在雨中拐弯时闪出焰火般的火花,长长的送葬队伍没完没了地阻断交通。这些葬礼是世界上最做作的,灵车点缀着光鲜的饰品,黑马身上披着天鹅绒,鼻羁上插着黑羽毛,死者必是名门望族,他们以为死亡是他们的发明。”⑥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39.在《百年孤独》第七节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队身着黑衣的律师,他们能做的不过是维护现状。
加西亚·马尔克斯能成为律师吗?他投入的程度如何,对此还不好妄下断言。那些课目把他烦死了。他在《活着为了讲故事》里借用萧伯纳的话说:“为了上学我没必要打断自己的教育。”从他弟妹们的回忆判断,研究严谨的学科不是他的长项。①如 Silvia Galvis,The García Márquez:73-106 and 133-156.另见 Dasso Saldívar,El viaje a la semilla:75-128.
根据同一份成绩报告,大学一年,在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之外,其他各科成绩都很好。但最终无聊乏味还是占了上风。他第二年的成绩证明他经常旷课,结果好几门课程不及格。②Jacques Gilard,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vol.1Textos costeños.Barcelona:Editorial Bruguera,1982:7-8.多年之后他说自己不上课读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教育制度使他感到失望;但他对知识的兴趣——尤其是文学——依然强烈。
他对文学的激情(他将此称为sarampión literario文学的麻疹)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他阅读欧洲经典作品,他告诉记者:“(此后),我的文学教育开始了。一方面我阅读二流诗歌,另一方面我阅读历史教师暗地里借给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到星期日我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排遣无聊。所以说我是先读的二流诗歌,后来才发现好诗。里姆鲍德、瓦列霍……”③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48.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流行诗歌,就是印在日历上、一张一张卖的那种。我发现我对诗歌的喜欢不在我对西班牙语法的痛恨之下,当年为了初中毕业,我不得不钻研语法。我喜欢西班牙浪漫主义——努涅斯·德·阿卡,埃斯普隆赛达”。④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48.
虽然诗歌是他早年文学的重要成分,但在他的作品里却很少见到诗歌。有几次——如《霍乱时期的爱情》、《爱与其他魔鬼》和他的自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故事里引用了大师们的文学作品,这些诗人都是他年轻时读过并喜欢的。数十年之后,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国际文坛上已经成名,他与超现实主义画家罗伯托·玛塔合作,在古巴出版日历,上面就有他为水果创作的谜语。在此之外很少见到他与诗歌的证据。不过,他能发现诗歌,这是一大幸事。“(当时)我的一大乐事就是一个周日接着一个周日坐在那些蓝玻璃电车里,花上五分钱,从玻利瓦尔广场坐到智利大道,然后再坐回去——那些孤寂的下午似乎一点希望也没有,有的不过是没完没了的空虚的礼拜天。在这个怪圈式的旅行里,我无时不在阅读诗歌,诗歌,还是诗歌。电车驶过一个街区,我大概就能读完不厚的一册,到第一盏街灯在永不停歇的小雨中闪亮为止。然后我再光顾老城那些默默的咖啡馆,寻找可怜我的人,和我讨论刚刚读完的诗歌,诗歌,还是诗歌。”⑤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41.如曼多萨所说,那些诗歌的作者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希望创作出对“普通群众”来说通俗易懂的文学。他们中就有鲁文·达里奥、胡安·拉蒙·基米尼斯和帕布洛·聂鲁达。
在很大的程度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文学的理解是在他发现卡夫卡作品之后才形成的。
一九八二年他回忆说:“我读《变形记》一定是在十九岁左右(还有几次他说是十七岁)。格里高里·萨姆沙的变形使他大为震惊。他还一字不落地记得小说的第一行:‘一天早上格里高里·萨姆沙从不安的梦里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好大的昆虫。’当时我想:‘见鬼啦!我外婆就是这么讲故事的。’我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手,你要是能行的话,我对写作当然感兴趣。’”他决定阅读那些史上最重要的小说。①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30,49.在《百年孤独》里乌苏拉·伊瓜兰也说过“见鬼啦”,如她在儿子何塞·阿卡迪奥和丽贝卡的房子里发现儿子的尸体后。
卡夫卡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代人影响巨大,但这位一九二四年死于肺结核的捷克犹太作家要在拉美争取到足够的读者,那还是以后的事。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的《变形记》译作在当地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连数年没有停止。据说小说是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翻译的,一九三八年以来,博尔赫斯就对卡夫卡着迷。他为刊物《家》翻译了寓言《法律面前》,如批评家伊夫兰·克里斯特尔在其著作《隐形的作品:博尔赫斯与翻译》里所指出的,这个阿根廷人还在他著名的《幻想文学选集》里收入了几部卡夫卡的作品,选集是博尔赫斯与朋友阿道弗·卡萨利斯和希尔维娜·奥卡姆波一同编辑的。②Efraín Kristal,Invisible Work:Borges and Translation.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2:186.然而,博尔赫斯自己并没说他翻译了《变形记》。《变形记》一九二五年首次译成西班牙文,此前一年卡夫卡逝世,译文发表在《西方评论》上,这是一份在马德里出版的知识分子刊物,编者是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格·伊·格希特。译者大概是格洛·萨伊斯,不过也有人说是玛利格塔·尼尔金。一九四五年,译文以书的形式经西方评论出版社推出,同时出版的还有被称为志怪小说的其他著作。据说博尔赫斯一九三八年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沙达出版社翻译了《变形记》,这次推出的系列取名“La pajaarita de papel”(《纸鸟》)。③Cristina Pestaña Castro,“¿Quién tradujo por primera vez‘La metamorfosis’de Franz Kafka al castellano?”Espéculo:Revista de estudios literarios〔Madrid〕,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1999.
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的是哪一版?要弄清楚是不可能的。但这次阅读是诱因,这是毫无疑问的。多年之后他说,如果没读卡夫卡的小说,他就写不出早期的故事“La tercera resignación”(《无奈再三》)——故事写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最先发表在英语杂志《纽约客》上,当时他二十岁,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我意识最强。故事里写的是一位无名叙述人的印象,这一点很像格里高里·萨姆沙。叙述人躺在棺材里,“等着被埋掉,但他知道自己还没死。他要是想起来的话,一点也不困难”。④Gabriel García Márquez,“The Third Resignation,”Collected Stories,Gregory Rabassa译.New York:Harper& Row,1984:5.中产阶级的焦虑和叙述人身在其中的离奇环境似乎就是在追念卡夫卡的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宣称“卡夫卡在德国讲故事的方式与我外祖母如出一辙”。⑤Eligio García Márquez,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Historia de“Cien años de soledad.”Bogotá:Editorial Norma,2001:96.虽然卡夫卡的荒诞主义与欧洲的不少读者一拍即合,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他最初在西班牙语世界却是褒贬不一——虽然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几位作家对卡夫卡极为推崇。卡夫卡在美洲有着执著的追随者(如卡尔沃特·卡塞),但他们人数有限。此外还有一些作者,如乌拉圭的埃尔南德斯(一九○二-一九六四),他们按卡夫卡的风格写作,但未必是卡夫卡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欠了人家《城堡》作者一笔债,然而,他们的传承关系是明显的。⑥见Ilan Stavans的“Buffoonery of the Mundane,”The Nation(September 19,2002).以“Felisberto is an Imbecile”为题,在A Critic’s Journey里再次出版.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虽然原因刚好相反,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的关系。《环形废墟》、《小径分叉的花园》、《好记性福恩斯》及其他小说的作者博尔赫斯,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身上有英国人和阿根廷人的血统,是位欧化的诗人和散文家,在五十年代末之前,仅有少数知识分子崇拜者才知道他。博尔赫斯博览群书,胸怀世界主义,蔑视政治,这些特点使他经常与拉丁美洲的左派发生龃龉。博尔赫斯对待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一方面他反对,甚至讽刺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多米尼戈·贝隆,一方面他又是奥斯卡·王尔德传统的知识型花花公子。他对土著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他那里,世界建立在哲学论文和玄学构建之上。
乌拉圭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艾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这位学者是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的朋友,还为他们两人写了传记(水平一般,充满了心理分析式的阐释),一次在七十年代问博尔赫斯,听没听说《百年孤独》,那部大家都在谈论的著作。聪明的博尔赫斯说他从未听说此书。不过,在博尔赫斯的问题上,一般很难判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假设这部小说的作者不是左倾知识分子,假设这部作品不是在拉美写出来的,哪怕是十九世纪的作品,那马孔多世家传奇就很可能迷倒这位阿根廷的文学家。但是,作为探索世界的艺术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代表的作家样板,与博尔赫斯是对立的。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权力与光荣》、《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其他著作的作者——也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重要影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格林才学会了理解他身处其中的环境。“格林教会我如何破解热带的问题,一点不少。这个环境是你所熟知的,将诗意合成物里面的重要成分从这一环境里分离出来,极为困难。这个环境你太熟悉了,所以不知从何下手,你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结果是一无所知。这就是我在热带碰到的问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安东尼奥·毕加菲塔和其他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我还阅读埃米里奥·萨尔格里和约瑟夫·康拉德及二十世纪初通过现代主义视角审视周围万物的‘热带作家’,及众多其他作家,但总是在他们的想象与现实之间发现严重的矛盾。他们中的一些人落入了排列事实的陷阱,令人感到荒唐的是,他们列出的东西越多,目光似乎越短。另外一些人,如我们所知,在文字上又繁复杂芜。格雷厄姆·格林以极为准确的方式解决了这一文学问题——通过内部的连贯性将几个不对等的因素连接起来,这里既有隐性的因素,又有真实的因素。通过这一方法你可以把热带这个谜缩减成一枚熟石榴的芳香。”①Plinio Apuleyo Mendoza,The Fragrance of Guava:32.
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重要的文学影响来自美国的三个作家,这至少是一些批评家的判断: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福克纳。他崇拜这三位作家,但原因又大不相同。多斯·帕索斯研究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所有极端的特点。海明威拥有一种简洁的、几乎是电文式的风格。他的语言不复杂但却有文采。然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留下最深的、最鲜明印迹的还是福克纳。《萨托里斯》、《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等小说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这一写作形式能够再现历史,通过历史再现整个社会。马孔多作为自给自足的现实,那里的地理界限、植被和家族谱系,是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汲取了创作灵感,这个小镇又取材于密西西比州的拉法耶镇。
毫无疑问,在福克纳老家密西西比州和普通的大南方之间,在马孔多和哥伦比亚之间,一定有着相似的地方。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经历的损失和无数伤亡留下的又深又宽的伤口与哥伦比亚千日战争及一次次内战造成的恶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可比性。一九四九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一年自由派领袖盖坦在波哥大遇刺身亡。福克纳小说的西班牙语译文出现在文学杂志和文化副刊上,三十年代末又推出西班牙语译著(博尔赫斯译出《棕榈树》)。①见 Ilan Stavans,“Beyond Translation:Faulkner and Borges,”in Look Away!:The U.S.South in New World Studies,Jon Smith and Deborah Cohn编辑并序.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始终怀着一股崇敬感阅读福克纳。
深受福克纳影响的胡安·卡洛斯·奥尼蒂描述了他是如何发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
下面的回忆写的不仅是奥尼蒂一个人,还有整整一代崇拜福克纳的拉美读者。
一天下午,我离开办公室之后。在一家书店停了下来,要来最后一期的《南方》,这份杂志是维克托利亚·奥卡姆波一手创办的……我还记得当年站在大街上把杂志打开,那是我一生第一次读到威廉·福克纳的名字。先是哪个不知名的作家写的序,接下来是译成西班牙文的小说,但译文蹩脚极了。我边走边读,全然不顾身旁的行人和车辆,后来我钻进一家咖啡店,索性把故事读完,结果把等我的人忘到了脑后。我又读了一遍,魔力不减,这魔力越来越强,批评家们众口一词,说这魔力永不消退。②Juan Carlos Onetti,Confesiones de un lector.Madrid:Alfaguara,1995:20-21.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无奈再三》,这家报纸是波哥大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小说发在第八版《周末》一栏里,编辑是埃多瓦多·波尔达。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枯枝败叶》之前,《无奈再三》是他此后创作的十八个故事里的第一篇。才过了一个月,他的第二和第三篇小说“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爱娃钻进她的猫》)和“Tubal Caín forja una estrella”(《托布尔·坎塑造一颗星》)先后在《周末》副刊上发表。
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坐在打字机前一写就是几小时。在“El amargo encanto de la máquina de escribir”(《有苦有乐打字机》)一文里,他说手写和打字有所不同,前者有神秘的光环,后者是现代生活的必然结果。“人人有自己的写字方式,这是事实,因为在写作这件苦差事里,最棘手的不是选择哪件工具,是如何才能把字一个一个地写出来。”③Gabriel García Márquez,“El amargo encanto de la máquina de escribir,”in Notas de prensa:1980.虽然译著的价值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教育里很重要,但不能就此推断他作品所受的所有影响都来自国外。所有作家都是所在环境塑造出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不例外。哥伦比亚其他作家作品对他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哪怕仅仅从美学上的连贯性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未忘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小说,但他要创作出新鲜的、不同的作品,要让哥伦比亚文学以另一张面孔走出地域藩篱,进入国际文学社会。
哥伦比亚小说是因其地理定义的。《百年孤独》以加勒比海为依托,继承这一传统的还有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被拿来与巴洛克作家如阿列霍·卡彭铁尔和何塞·利马进行比较,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这一加勒比传统的代表作就是胡安·何塞·尼耶托的长篇小说《英格尔米娜》(Ingermina,一八四四)。如哥伦比亚小说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就这一传统所勾画的线索,其他民族传统还有建立在内陆高原之上的文学作品,如尤金尼奥·迪亚斯的《曼纽伊拉》(Manuela,一八五八)和伊达尔多·卡尔德隆的《高尚的野蛮人》(El buen salvaje,一九六三);安蒂奥基亚的传统,其继承者是托马斯·卡拉斯奇里亚的《大地果实》(Frutos de mi tierra,一八九六)和曼纽伊尔·瓦列霍的《褪色的时光》(El día señalado,一九六四);还有考卡的传统,其代表作品从豪尔赫·艾萨克的《玛丽亚》(Maria,一八六七)到格斯塔夫·加尔迪萨贝尔的《白痴集市》(El bazar de los idiotas,一九七四),为数众多。①见 Raymond Leslie Williams,Ideology and the Novel in the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olombia:The Colombian Novel,1844-1987.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1:20-51.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国立大学钻研法律时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此事对他的写作来说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骚乱中盖坦遇刺身亡。盖坦是民粹主义者,很有人格魅力,是自由派极受欢迎的领袖,而且还是总统候选人,那一年盖坦五十周岁。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盖坦遇刺那一天当成一生的分水岭。
盖坦在国立大学读的法律,当过波哥大市长和教育部长。盖坦在骚乱时期遇刺身亡,这一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加剧,暴力冲突不断,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盖坦遇刺那一年,他发表演说,宣称:“如果他们杀了我,为我报仇!”
盖坦遇刺发生在四月九日。波哥大正召开泛美大会,讨论贸易问题,虽然政治依然是大会上重要的话题。总统马里亚诺·佩雷斯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出席大会。
下午一点零五分左右,盖坦与几个同事离开办公室。目击者听见三声枪响,然后又传来第四声。盖坦背部中弹,一颗子弹打穿肺部,另一颗子弹打进后脑。他在地上至少躺了十分钟才被一辆黑色出租车送到五个街区之外的中心诊所。午后一点三十分左右盖坦被送进诊所,下面是历史学家的描述:“发生的事件已然无法挽回,对所有目击枪击事件的人来说,领袖已经走了。他被匆匆送进诊所,医生试图拯救他,但这已不再重要。这次凶杀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这次事件也在意料之中。他的死是必然的。他太危险了,两党领袖都怕他。”②Herbert Braun,The Assassination of Gaitán:135.
在现代哥伦比亚历史上,这次暗杀事件构成了转折点。消息马上在波哥大传开,愤怒的人们高呼:“盖坦!盖坦!”他们走上大街。广播电台警告波哥大人不要出门。内务部长发表广播讲话,否认盖坦遇害,但人们并不听从劝告。他们扑向里尔大道的政府大楼。革命就要发生,但没人站出来掌舵。一群工人和中产者抢走了据说是刺客的尸体,至于刺客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说法不一。
媒体的角色至为重要。盖坦支持者掌握的最新消息电台在他遇刺几分钟后发布通告:“这里是最新消息电台。保守派和佩雷斯政府刚刚刺杀盖坦博士,他被一个警察开枪击中,倒在办公室外面。人民,拿起武器来!准备战斗!到大街上去,带上棍子、石头、砍刀,凡是顺手找到的东西都行。抢夺五金店,取走店内的炸药、枪药、工具和砍刀。”
广播还指示人民制造燃烧弹。涌入里尔大道的人群已经组织起来,但城内其他地方还是一片混乱。人们高呼:“打倒保守政府!”在玻利瓦尔广场上,公共汽车被人们点燃。佩雷斯总统相信,“大众必然要被骚乱分子操纵,这些骚乱分子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国家政府”。③Herbert Braun,The Assassination of Gaitán:149.
盖坦遇刺也被称为波哥大事件,这次事件之前是所谓的共存期,政治见解不同的人们——自由派和保守派——还能相互容忍。波哥大事件造成此后没完没了的骚乱。历史学家指出:“盖坦率领追随者们走出了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就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也不让他们染指,然后他们进入了另一种生活,他们这才感到自己是生活的参与者。盖坦的死又将他们抛入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的底层。大众与保守派失去联系之后,那个陈旧的世界又与疏远的、零散的领袖人物浮出水面。四月九日下午人群在波哥大采取的行动说明,他们拒绝返回过去,拒绝倒退。但没有盖坦存在,大众又无法走完剩下的路程。如何夺取权力?对此谁也没有想过。既不想后退,又无法前行,骚乱者的愤怒和压抑仅有一个出口:破坏他们无法生存的社会。盖坦死后其追随者被压抑的情感、盖坦向他们灌输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以及盖坦对保守派所表示的仇恨,所有这些都成了人群大搞破坏的动因。”①Herbert Braun,The Assassination of Gaitán:203.
波哥大事件引发的骚乱持续十个小时。骚乱从波哥大开始,很快传遍全国。有人趁机抢劫商店,有人盗窃财物,然后贱卖。死亡人数达到二十万,伤者大约百万。这次骚乱先后十年,一九五八年才停歇。冈萨洛·马拉里诺著有《乱民:波哥大人的历史》一书,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这部著作撰文《波哥大一九四七》。他在文中提到初次踏上波哥大的那一天,当年他十三岁:“……那是一月份里一个阴郁的下午,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接下来他说一生中和他那代人一生中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就是当时在波哥大的年青时光。周日他跳上电车,从玻利瓦尔大道坐到智利大道。有时他能遇见一个人,一般是男人,他们一同喝咖啡,闲聊到深夜。②Gabriel García Márquez,“Bogotá1947,”on October 21,1981出版,收入 Notas de prensa:1980-1984.Bogotá:Grupo Editorial Norma,1991:218-220.发生骚乱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宿舍发生火灾,国立大学关闭。他的成绩里有一份证明,说明他已经转入卡塔赫纳大学。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发现文学与生活有着我的短篇小说没有的关系。之后发生了一个事件,对上述态度极为重要。这就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的波哥大事件,政治领袖盖坦遇刺身亡,愤怒的波哥大人民扑上大街。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宿舍里要吃午饭。我跑到事发地,但盖坦已被出租车拉走,正被送进医院。在我返回宿舍的道上,人民已经占领街道,他们示威,抢商店,烧房子。我走入示威人群,就在那天下午和傍晚,我才意识到是在哪种国度里生活,我的短篇小说与这些几乎毫不相关。”③Peter H.Stone,Paris Review:185.
此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进入新闻业。在目睹了骚乱之后,他决定离开波哥大,他能理解人民大众造反的原因,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令他感到震惊和害怕。他要离开首都,从远处选择一个分析事物的角度。他决定先到巴兰基亚,但那里的大学已经关闭。后来他赶到卡塔赫纳,这是一座正在兴起的沿海城市,周围有着深厚的殖民传统,流行的是非洲-哥伦比亚文化。这是大胆的决定。波哥大和卡塔赫纳这两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大不相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也不相同,但这两座城市将允许他发现自己的写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