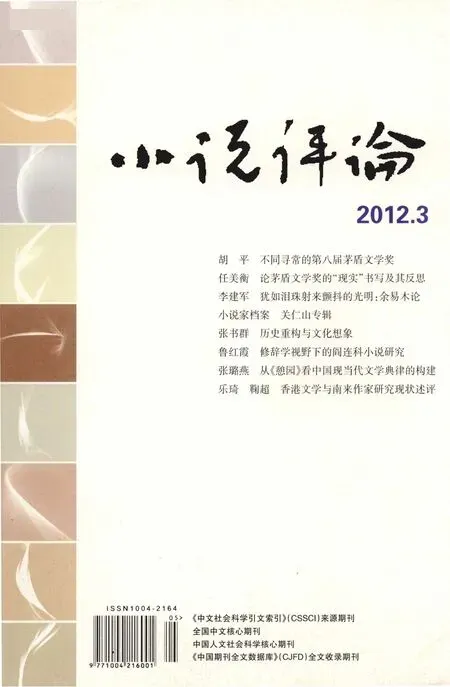词语陌生化和莫言小说语言的弹性美
2012-12-18周晓静
周晓静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把人类的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从言语中抽象归纳出来的一套符号系统、一套规则;言语是人们对语言规则的实践。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都会自觉地遵循这套规则,它是约定俗成的,是社会的;但同时,言语行为又是个人的,只要对方能意会,说话者可以在语言的大框架下肆意发挥,实现自己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更是如此。文学是作家思想感情的流泄,作家渴望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超敏感觉、独特感受用富有个性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但现有的语言框定着他们,使他们常常有“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的感慨,于是作家们开始尝试着突破语言的樊笼,“用语言挑战语言”,①希望找到一种“基本驯化”的“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②汉语的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正如申小龙所说:“一个个语词就像一个个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只要凑在一起就能‘意合’,不搞形式主义。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种特点使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有可能更多地从语言艺术角度考虑。同时,这也使得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能够容忍对语义内容作不合理的句法编码。”③作家们抓住汉语的这种“得意忘形”的特点,遵循自己情感表达的需要,打破语言的常规,努力挖掘语言深层的内在语义联系,不仅拓展了汉语言的语法弹性,更拓展了读者想象的弹性空间。
莫言是一个有着超敏感觉的作家,他在语言的规则和言语的个性表达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尊重自己的感觉,依据感觉找语言,对那些陈旧的、已经调动不起人们好奇心的组合,打破常规重新组合并赋予新义,用特殊的语言使感觉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他对现成词语的陌生化使用乍看不可思议,细品却又妙不可言、耐人寻味,扩大了语言想象的弹性空间,增加了语言审美的弹性。
一、词语变形
词语变形是指作家为了表达的需要对固有的词形进行改造。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由于情感的驱动,情之所至,某个带着作者一时一地感觉的词语会自然而然地从作者的脑海中涌出来。尽管它可能已经变形,甚至违背常规,但是正是这种“形”赋予了词语新意:一方面符合了作者描摹情态神态声态的需要,另一方面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扩大了语言的张力和弹性。《红高粱家族》中最主要的词形变化是AB——AABB。现代汉语的形态变化不多,AABB式是其中之一,一般适用于拟声词、形容词,通过音节的重叠增进语感的繁复,这样既可以增强音乐美,又可以加强语意,能够传神地描写出人物音、形、情、态,增加语言的形象性,增强感染力。如:
(1)(我奶奶喝醉了酒)奶奶倚在草垛上,搂住罗汉大爷的肩,呢呢喃喃地说:“大叔……你别走,……留下吧,你要我……我也给你……你就像我的爹一样……”
(2)河水在呜呜咽咽地悲泣。
(3)这时,单家一个小伙子惊惊诧诧地打门报案:“庄长!庄长!了不得啦,杀人啦!”④
(1)句中的“呢呢喃喃”是由拟声词“呢喃”重叠来的。“呢喃”是摹拟小声说话的声音,重叠后的“呢呢喃喃”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说话者的情态:我奶奶在我爷爷出轨后万分痛苦,以至于酒后醉醺醺地对罗汉大爷说出了这样的醉话。“呢呢喃喃”不仅表现了我奶奶的醉态,还表现了声音的唠唠叨叨、模糊不清、断断续续,以及我奶奶对罗汉大爷别样的温情。(2)句中的“呜呜咽咽”是对“呜咽”的重叠变形。莫言习惯于物我不分,他笔下的很多非人类都有着人的特性。“呜呜咽咽地悲泣”赋予墨水河以人的情感,有音,有情,有态,它表现的是伏击战惨败后我爷爷的悲凉的心态。“呜咽”是一个动词,由于突破常规地使用了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所以变形后有了形容词的特性,词意也相应地有了一些变化。(3)中的“惊惊诧诧”最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尽管AABB是形容词的扩展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适合这样的扩展,比如“勇敢”就不能重叠为“勇勇敢敢”,同样,“惊诧”一般也不适合重叠为“惊惊诧诧”。但是正如老舍所说,文学语言“不是由字句的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作家需要表达自己的感受时,某个词会自然而然地蹦进作者的脑海,而这个词语往往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作者的情感和感受。“惊惊诧诧”虽然是从“惊诧”重叠来的,但是在这个语境中,它的理性义和色彩义随着音节的重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只是“惊讶、诧异”的意思,更加强调的是“惊”,表现的是单家小伙计突遇掌柜家的灾祸,精神受到刺激而害怕、紧张不安,而“诧”含有出乎意料的意思。“惊惊诧诧”合在一起,音节重叠,语感繁复,让我们仿佛既看到了单家小伙计的惊恐状态,又仿佛听到了他因惊吓紧张而发出的急促的、咋咋呼呼的喊叫。对“惊惊诧诧”的创造性使用,增加了读者想象的弹性空间。
二、词语重组
语言中词语的组合搭配是约定俗成的,但是这种固有的、大众化的组合已经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不能很好地唤起读者的想象和共鸣,更不能满足作家要传递自己超敏感觉的要求,于是,他们尊重自己的感觉,突破语言在语法规律、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和习惯搭配上的常规,将词语凭自己的感觉重新组配,以此扩张语言的表现力,充分满足传递情感信息、美学信息的需要,增加作品语言的张力和弹性。莫言一直在追求一种“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词语重组是他实现理想的主要途径。
(一)改变词性的词语重组
改变词性的词语重组是指在特定的语境中,临时改变词性的一种用法,在艺术语言学中也叫做转品。这种超常搭配能够增加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实现简洁的修辞。如:
(4)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④
(5)围子里围子外狼籍着英勇抵抗者和疯狂进攻者的尸体。④
例(4)中“鱼贯”本是一个副词,在这里带上动态助词“着”,显然是当做动词来使用了。“鱼贯而入”是个固定组合,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使用,甚至都不会考虑“鱼贯”的词性。而当“鱼贯”被单独拿出来使用时,尽管我们还能有“像游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接连着”的直觉映像,但是陌生化的用法及超常规的语感,不由得使我们驻下眼光,细细品味——子弹穿过树冠的动态效果画面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例(5)是把形容词“狼籍”临时变性为动词,在形容词乱七八糟、杂乱不堪的语义基础上增加了画面的动态效果,展现出日本鬼子血洗村庄后的惨状。
(二)改变理性义的词语重组
词义分为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词的理性意义是人们对所指对象的区别性特征的概括认识,是词义的主干。一个词的理性义往往有多个义项,都是从词语常出现的语境(即组合)中概括归纳出来的。这些常用的组合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思维定势,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莫言有意识地对这种“约定俗成”进行重组造成陌生化,抗争日常规范和思维定势,使我们在思想及语感受阻的同时,回到起点,从另一个角度客观地重新认识这个词语,发现词语原初的灵性。如:
(6)a。父亲眉毛短促,嘴唇单薄,他觉得自己很丑。④
b。他抬头看到,吼叫的人三十出头,面孔像刀削的一样,皮肤焦黄,下巴漫长,头戴一顶香色呢礼帽,手里持着一支乌黑的短枪。④
(7)a。出殡那天,任副官黑衣挺括,毛发灿烂。④
b。狐狸的皮毛灿烂极了。④
例(6)中的“短促”和“漫长”都有自己固有的理性义。前者一般指时间短且急促,后者常指时间、道路等长得看不见尽头。它们的理性义是从常用的搭配如“生命短促”、“声音短促”、“短促的访问”及“漫长的岁月”、“漫长的河流”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其实,这两个词语主要意思是“短”和“长”,“促”和“漫”是加强说明或描述有多短,有多长。所以,莫言凭感觉,抓住它们的根本,有意打破常规,分别用这两个词来描绘人的容貌,“父亲”眉毛的异乎寻常的短,“吼叫的人”的下巴的超乎想象的长,在这两个词的统领下凸显在我们眼前。例(7)的“灿烂”常出现的语境是“星光灿烂、灿烂辉煌、灿烂的笑容”等,意思是形容光彩鲜明耀眼。莫言把它和任副官的毛发及狐狸的皮毛组合在一起,轻轻松松地把任副官的精神气儿和狐狸皮毛的质感及这只非同一般的狐狸的灵性表现了出来。
(三)改变感情色彩的词语重组
词的感情色彩是色彩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附加义,是人们在长期使用某个词的过程中加入的主观态度,大体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这种态度是约定俗成具有全民性的,它凝定在词义上,以至于人们都忽略了词义的核心——理性义。莫言故意地无视词的感情色彩,客观地使用它们,在超常规的组合中,使它们“返璞归真”,一方面唤起人们对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的回忆,另一方面,陌生化的用法达到了一种特定的修辞效果。如:
(8)一时间鸦雀无声,听得清那条大狼狗哈达哈达的喘气声,那个牵狼狗的日本官儿放了一个嘹亮的屁。④
例(8)中用“嘹亮”这个褒义的词来形容“屁”的声音,违背常规,让人不能接受。事实上莫言在这里使用了“嘹亮”的理性义——声音响亮。全村的人被日本鬼子驱赶到堤外的高粱地里看罗汉大爷遭受刑罚,作者以“我父亲”这个儿童的视角描述了当时紧张恐怖的气氛。当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形怪物”出现时,“人群悄悄地聚缩”,“父亲感到奶奶的手牢牢捏住他的肩膀”,“一时间鸦雀无声”,甚至听得清狗喘息的声音。就在这极端寂静中,人已经紧张得要崩溃了,读者的心也被绷得紧紧的,这时,“嘹亮的屁”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超常组合的突兀出现使我们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一方面有用响亮的声音来衬托无声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莫言惯用的反讽和调侃的手段,他习惯于写到最惨烈处,笔锋一转,让读者的心一紧一松,在复杂的感觉中打开了想象的大门。
三、词义别解
词义别解,就是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在同一个词形下,作者有意偷换了语素的义项,从而使词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语义也有了模糊性,增加了语言的弹性。如:
(9)马肚子上浓烈的尿臊和汗酸味被马身带起的旋风漫卷着,沉重地糊涂在父亲的头上和身上脸上,久久拂不去。④
“糊涂”这个词形,我们第一反应是把它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单纯词,念作hútu,是个形容词,表示“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如果在这个语境中认同了这个意思,那么作者是把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了。联系上下文语境,这种理解似乎行得通——我父亲小小的年纪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的洗礼,看到父老乡亲在自己身边悲惨地死去,精神麻木几近崩溃,甚至对杀害了自己无数亲人的日本鬼子产生了同情心,真是“昏头”(我爷爷语)了。但是细品之后,我们似乎也可以把这个词形看作是由两个动语素组成的动词性联合短语,读作hútú。因为“糊”和“涂”还是两个成词语素,“糊”的意思是“用黏性物把纸、布等粘起来或粘在别的器物上”;“涂”是“使油漆、颜色、脂粉、药物等附着在物体上”。动词“糊涂”给语句增添了通感的效果——只能用鼻子闻到的气味,好像可以看到或者感觉到一样被涂在了身上,拂也拂不去。在同一语境中,对两个同形的词语模棱两可地使用和理解,增加了语义的模糊性,使读者有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的弹性想象空间。
四、结语
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语言是受阻碍的、扭曲的语言”,就是因为作家感到日常语言循规蹈矩,既没新意又不能完全表达自己超敏的感觉,所以对语言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对语言规则的突破,使我们认识到了语言规则的弹性,另一方面,在“扭曲的语言”“阻碍”我们的思维和语感时,我们不得不驻下眼光调动自己的经验去品味作者的言语,捕捉言语隐含的意象和情韵,在这个延长的过程中,又体现了语言审美的灵动和弹性。当然,对语言的扭曲要有一个度,正像莫言所说“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这样的文学语言是每一个作家用毕生去苦苦探索和追求的。
注释:
①张均、韩少功: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06),第16—21页。
②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代序言,红高粱家族。
③申小龙: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0),第8页。
④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