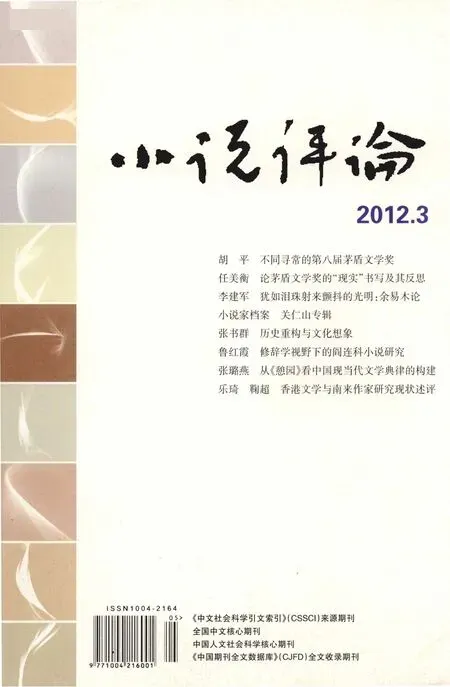传奇: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三
2012-12-18张清华
张清华
范例:裴铏【唐】:《传奇》——张爱玲:《传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网络小说:注册洗碗师:《我们是传奇》——紫火赤焰:《酒神传奇》——gqcctv:《传奇》……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传奇者流,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真趣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①
古希腊罗马的第一种小说类型,我们姑且叫它“传奇教谕小说”……它形成于公元二至六世纪。
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发现了一种运用得巧妙精细的传奇时间……这一传奇时间的把握,以及在小说中运用的技巧,已经达到了如此高超和全面的程度。体形式》②
——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
一、“传奇”及“传奇性”的概念
汉语中“传奇”一词,最早大约见于唐代小说家裴铏所辑录的小说集《传奇》。明胡应麟说,“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见《少室山房笔丛》)裴铏为中唐人,官至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所编撰的小说作品甚多。《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载有裴铏所编《传奇》三卷。这一称谓后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小说和其它艺术作品的一种泛指或者别称。
认为“传奇”即“小说”,也是胡应麟的说法:“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在《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中,胡应麟将小说类型分为六大类,即“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这大约也是“传奇”之所以成为文人小说之别称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讨论唐代小说时,所采用的称谓也即是“唐之传奇文”,并认为“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实唐代特绝之作也。”同时他还对传奇文体及源流做了精当评点,“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而无涉于传奇。”又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为之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着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可见,“传奇”与很多文学史上的命名一样,起始也含有贬抑之意,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作为一个小说体式或类型术语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美学术语。不但“宋元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等也有称为传奇的”(《见《辞海》,商务印书馆2006年两册版),明代的南曲脚本也称为“传奇”,明代中国典范的长篇小说亦称为“奇书”。“奇”可见是中国小说乃至文学的一个核心特质与要素。
在西方,一种“传奇型”的小说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出现了,“希腊罗马小说中的第一种,我们姑且叫它‘传奇教谕小说’”。③巴赫金在其小说诗学理论中,关于传奇叙事结构有精细的探讨,他甚至以此为例分析了叙事中一种“传奇时间”模型的构成方式。
中世纪欧洲小说中传奇性的文体类型十分丰富,流行于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的骑士小说中的“罗曼司(romance)”,所含也有浪漫传奇之意。在英语中“传奇”一词的对应词语“saga”,起源于北欧文学中的一个种类,可能与“萨迦”意近,牛津英汉词典对“saga”的解释有三个,一是来自古挪威语,意思为“英雄故事”,常特指北欧的英雄传奇;二是有关家族历史的故事,尤指长篇的“家世(族)小说”;其三是“有重要经历的记叙”。此外,“传奇”对应的英语词汇还有“legend”,也常用于指不同寻常的冒险与浪漫故事。
《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国文学》卷在解释“北欧传说”词条时说:
“萨迦”一词,源出德语,本意为“短故事”。它是13世纪前后冰岛和挪威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居民的口头创作,包括神话和英雄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萨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精神面貌,兼有人物传记、族谱和地方志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进行文字加工的艺术技巧。它在故事题材和创作风格上对北欧文学的影响颇深,因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学著作。
流传至今的“萨迦”不下于150种,大致分为“史传萨迦”和“神话萨迦”两大类。④
二、“传奇”的结构属性与类型
显然,北欧的“传奇”叙事同希腊小说中更加世俗化的故事有很大差异。不过作为文学传统,来自南欧和东方的古希腊罗马小说,以及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与罗曼司,则无疑影响更为深远。巴赫金在关于欧洲小说传统中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的研究中,所采用的例证即是来自希腊罗马的小说。他发现这些小说中有大量共同的结构要素,特别是在叙事的“时间修辞”中有一种刻意的含混:
一对婚龄男女,出身不详,带点神秘(不总是如此,如塔提俄斯作品中就没有这一点)。两个人都美貌异常,又纯洁异常。他们不期而遇,一般是在喜庆佳节。两人一见钟情,势不可遏,如同命运,如同不治之症。可是他们不能马上完婚。男青年遇到了障碍,只得延缓婚期。一对恋人各自东西,互相寻找,终于重逢。而后又失散,再相聚。恋人们常见的障碍和奇遇有:结婚前夜新娘被抢,双亲(如果有的话)不同意婚事,而给相爱之人另择配偶(虚设的对偶),恋人双双出逃。他们启程旅行。海上起浪,船舶遇险。人奇迹般得救,复遇海盗,被虏关入囚室。男女主人公的童贞遭到侵犯。女主角经受战争和战斗作为赎罪的牺牲。被卖做奴隶。假死。换装。认出或认不出……横加罪名。法庭审理。法庭查验恋人的纯洁和忠诚。主人公们找到自己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未出场)。同突如其来的朋友或敌人相遇、占卜、预言、梦魇、预感、催眠草药。小说以恋人完婚的圆满结局告终。⑤
巴赫金随后颇为风趣地指出了这些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主人公是在年轻貌美的时候一见钟情的,又是在同样年轻貌美的时候终成眷属的,中间经过的无数磨难,在时间上是没有计算的”。对照这些分析不难看出,古希腊罗马的小说其实与中国晚明时代开始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惜巴赫金没有读它们,假如他像歌德一样也读到了《玉娇梨》或者《好逑传》,他的例子定然要多出数倍。然而奇怪的是,与歌德读到《玉娇梨》或者《好逑传》时给予的很高评价不同⑥,历来中国的作家和研究者对这类作品很少给予重视,在谈到它们的时候总是抱以一种轻蔑或者戏谑的态度。不过,即便如此,在这些批判性的谈论中,我们仍可以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意义上看出它们与巴赫金谈论的希腊小说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比如鲁迅是这样说的,“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中间要经历诸多的磨难,或“途次遇盗”、“避祸远徙”(《玉娇梨》),或“被怨”获“诬”,遭到“拘讯”(《平山冷燕》),或因“梗直得祸”、而遭权贵“逼婚”(《好逑传》),或遇天灾离乱,“中途舟破”(《铁花仙史》)……但最后结局却无不皆大欢喜,奉旨“成婚之日,凡事无不美满”。至于小说的题旨,则无非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有的或也“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只是又套路化地设计成“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更有甚者,“事状纷繁,又混入战争及仙妖异事……”⑦虽然鲁迅从未在思想和艺术的意义上给这些“才子佳人”小说以正面评价,但可以看出,他对其叙事元素与基本构造的谈论,同巴赫金式的“结构主义”分析是十分近似的。
无独有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关于“才子佳人”一类小说的精彩而戏谑的批评,也同样可以见出这类小说的“结构要素”与特点:
这一段故事……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历来野史,皆蹈一辙……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
或许从严肃文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完全赞同曹雪芹和鲁迅的判断,他们对这类作品的各种叙事元素与特性的分析,也显示了非凡的透视力,他们几乎可以看做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之中国学派”的鼻祖了。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结构主义叙事学也完全可以是一门“中性的学问”,它的核心并不在于对作品的优劣做出判断,而是要寻找叙事中的各种规律所在。归纳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古代,都大量地存在着一种近似“传奇的叙事”,它们在故事内容、结构特性、叙事要素以及美感风格上,有着高度的类型化特点,即在内容方面多是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故事;其次,这些故事的叙述结构大都有着近似的规律可循,即男女主人公正处于美妙的情窦初开的年龄,不期而遇,一见钟情,相约终身。随后又突遭变故,意外离散,或有小人拨乱其间,不得相见,或者因误会而生仇恨,最后终于因为某个关键契机,拨云见日或冰释前嫌,于是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三,结构的要素,用巴赫金的说法,无非是“命运的马大哈”、“突然间”、“无巧不成书”等等续接或陡转的因素,帮助作者刻意延宕或者拉长了离散的过程,由此造就悬念,吸引读者;第四,由于最后结局的皆大欢喜,所以在美感风格上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喜剧性特征。这同戏剧与电影艺术中大量类型化的作品一样,虽然“俗”了一些,但却是可以“重复制作”且“最具消费价值”的作品,因为它不只是由意图牟利的写作者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一般读者和受众的接受心理所决定的。
由此我们也大致可以划定“传奇小说”的边界了,综合各种古代的传奇叙事传统,可以认定它主要的几种类型,即,除了中国式的具有寓意色彩的神魔志怪,西方式的古代英雄叙事、中世纪的冒险与浪漫叙事,也还包括了中外皆有的历史小说、世情与家族题材的小说,包括了某些世俗与消费性明显的男女爱情故事,等等。假如从基本的“美学属性”上看,它们大致也可以这样划分:一是具有刺激与消费趣味的鬼怪与冒险叙事,这类小说以惊悚和猎奇为基本特点;二是作为“喜剧”的“才子佳人小说”与浪漫爱情小说,这类以终成眷属皆大欢喜为结局,带有很强的娱乐与消费性;三是作为“悲剧”的中国式“奇书”叙事,这类作品因为描写了盛极而衰、分久必合、色欲而空等等有“完整时间长度”的故事,而常常最具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或天上人间的悲剧震撼力。
从这个角度上说,传奇小说实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十分多杂、近乎无所不包的。
此外,歌德对“中国式才子佳人小说”的“过高评价的嫌疑”,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看得还少,只是读了一部,因而觉得新鲜,还没有意识到其“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毛病;假如他读了三部以上,可能结论就全然变了。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世界文学”这个词语的发明,却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三、“传奇”叙事的美学边界与现代变迁
对于“传奇叙事”的类型边界与美学属性,我们似乎还要从更宽泛和深入的意义上来予以探讨。因为无论从中外小说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小说诗学与美学的角度看,“传奇”或“传奇性”几乎随处可见。从中国小说历史看,尽管“传奇”一词的出现晚至唐代,但早在汉魏六朝时的小说雏形中就已经有了《神异经》(汉,东方朔)、《神仙传》(汉,佚名)、《列异传》(汉,传为曹丕撰)、《神异传》(三国,佚名)、《神异记》(晋,王浮)、《神仙传》(晋,葛洪)、《搜神记》(晋,干宝)、《志怪记》(晋,殖氏)、《志怪集》(晋,佚名)、《怪异志》(晋,佚名)、《录异传》(东晋至南朝,佚名)、《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南朝宋,刘义庆)、《述异记》(南朝齐,祖冲之)、《梦记》(南朝齐,陶弘景)等著作⑧,在这些早期的志怪小说名称中,充斥了“神异”、“怪异”、“神仙”、“志怪”、“世说”、“梦”等说法,这既表明了此类作品的内容是充满奇闻异录的,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风格属性上的幻异与奇诡。这些“幻”、“奇”、“怪”、“异”的特点,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小说在内容与艺术上的倾向。
源于这种传统,中国历代小说常用超越于世俗常规和世俗伦理的传奇事件、传奇人物来构想世俗生活中所不能的景观;或是以讽喻寓言式的手法,来传达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令人警醒或感慨的命运逻辑。所以,无论是六朝“志怪”,唐代“传奇”,还是出自明清的大量笔记小说中的“异史”与“志异”,其内容与写法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以怪诞奇幻和诡异惊悚等为特征,以警世劝喻与闲暇消遣为宗旨。不止文言小说传统,明代的长篇白话叙事也不叫“长篇小说”,而叫做“奇书”;同时期的话本白话小说则称作“拍案惊奇”或“今古奇观”,并且标明其“警世”、“醒世”、“喻世”等等之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传奇”在小说史中有专指和特指之意,但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整个中国传统小说的泛指与总称,是其美学特征中最核心的一面。
传奇叙事也有很强的“寓言性”,即便是《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小说,《水浒传》式的绿林传奇,《西游记》式的神魔故事,《金瓶梅》式的市井奇谈,都同时被汇称为“四大奇书”。这表明,“奇书”叙事既是在内容上无所不包的,历史、侠盗、神鬼、世情都可以成为传奇对象;同时在美学上也是形态各异的,无论是实还是虚,真还是幻,赞誉还是讽喻,激扬还是劝诱,都可以当作“寓言”——即寄寓人心、寓世道情理于故事之中的“警醒之言”来读。如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开头一段话所说: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⑨
这段话不止可以作为《金瓶梅》这部书的解读的钥匙,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古典小说之理解的入口。它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中,“传奇”总是带有很强的“寓言”与“寓意性”的,而“寓言”也常常是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来实现的。
这就给我们理解“传奇”叙事的基本功能与美学属性提供了更宽的理路:第一、从内容上说,传奇不只是“谈神论鬼”与“英雄侠客”的专利,更是对历史沧桑与世态人情的真实演绎;第二、在写法上,不论是何种风格与手段的叙事,都可以作为讽喻现实与寄寓人心的寓言来读,因此上述两点,它几乎涵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所有叙事类型;第三、在美学上,它既包含了“才子佳人式”的喜剧形态,也包含了“奇书”叙事的悲剧形态,因此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风格与神韵的一个总称。
显然,新文学的诞生几乎终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些属性,自梁启超把小说当作“改良群治”和“新民”工具始,小说的社会认识、思想启蒙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五四”以后现代中国的小说叙事,大都采用了西方近代以来小说模式,而对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奇书”叙事、“话本”白话小说的要素,则几乎逐一清除干净。不要说“异闻野史”的功能被取消,连“浮生笔记”的俗趣也洗刷殆尽。想在现代小说中寻找具有传统气息与中国神韵的范例,除了张爱玲这样作家,几乎再难找出别的例子。虽然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兴起后,传统和民间的东西曾被重新定义为应该汲取的资源,但从实际的创作看,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与中国传统叙事在美学上却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不过,传统叙事在许多时候作为一种“潜文本”或者“集体无意识结构”,却也支持了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文学性。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虽然笔法稍嫌粗糙,主题也只在于传达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激进信息,但无意中却是中国传统式的家族叙事结构在暗中支持了它,使之在大量粗糙的新文学作品中能够赫然而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家》便是“《红楼梦》式的叙事”,是中国式的传奇确立了它在结构上的美感与深度。很显然,这部小说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描写了觉慧式的“新人”,以及透示出了时代风云的激变;而是在于真实地书写了觉新这样的“旧人”的命运,并且传达出了“封建家族”衰败中的悲情与伤怀。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作品在新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由于中断了与中国小说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缺少成熟的叙事构造、美感范型的支持,所以拉开距离来看,新文学中的真正具有美学的经典意味的作品并不多见。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张爱玲一类作家的意义就得以更强烈地显现出来,说她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中国小说的叙事与美感神韵也不过分。很明显,她使得小说再度偏离了“新文学”的道路与方向,找回了通向古老叙事传统的隐秘路径;她使小说与主流的社会生活拉开了距离,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情态恢复了关系;她使小说再度变成了世俗与人心的镜子,变成了尘世与浮生的古老“传奇”——她之所以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并非只是一个偶得,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记,标明了她小说的一种根基与血脉,气息与类型。她在小说的名字下面写下的“题记”——“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或许显得含混和低调,但恰好显现了她与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之间相似的趣味。细读她在《传奇》增订本里的短文《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还有作为“跋”的随记《中国的日夜》,就会看到她存心对于这个年代“鬼魂”般的“窥探”⑩,而这正是她小说中“既新且旧”的一个颇具神韵的描述。她以一种合适的距离,给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找到了一个观照的角度,这角度仿佛是“隔世”的景象,散发着历史的古旧与熟谙,同时也以深沉的悲情发着节制的伤怀与慨叹。总之正是某种“传统的鬼魂”在她身上的“附体”,才使她的小说在历史的局外获得了长久的重生。
作为仅有的孤例,现代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罕见的存在,张爱玲的意义也许应该是在这里——她从另一方面反证了整个新文学之质地粗糙与美感匮乏的原因,正是源于其对古典传统的偏离和废弃,源于其作为“浮生传奇”的品质的丧失。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社会斗争的工具,虽然张爱玲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看做是“旧”的甚至有问题的小说家,但她却也是新文学的“激流”之下暗自通向中国传统气脉的一个关键的纽带。仅就这点而言,她也比许多“新”的小说家更具有传之久远的可能。
四、当代传奇性小说的踪迹与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看,“传奇”的某些要素却是以“潜文本”的形式,借助当代中国的“革命文艺”环境更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由于对“创造历史”、书写英雄谱系,传奇事迹的需要,早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就显示出了对“传奇性”小说传统的借重。比张爱玲的小说稍晚,在解放区就出现了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小说,这些作品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讲史”和“侠义”小说的写法,人物比较接近类型化的“扁平人物”,故事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也收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和革命文艺的要求有不合拍处,所以大都评价不高。
出于同样原因,至五十年代,又出现了一批更具有传奇意味的长篇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至的《敌后武工队》,甚至梁斌的《红旗谱》的“前半部”,等等,这些作品如果要给它们一个共同名称的话,我以为可以称之为“类传奇叙事”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与传统的绿林侠义小说有着近似的叙事风格,故事离奇曲折,情节跌宕引人,人物类型化和传奇意味浓厚,叙述风格鲜明夸张。从大众接受的角度看,这些作品要远比主流的《创业史》一类小说受欢迎,虽然它们中的多数同样没有得到较高的评价,但“革命历史主题”本身却使它们获得了先在的合法性,因而也就难以给予压制和过分的贬抑。
这涉及到了一个关于当代革命文学的整体评价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革命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从叙事的基本构造看,上述作品因为有意无意地传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某些叙述手法,所以形成了许多复杂的“潜结构”,诸如《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之间类似“才子佳人”与“英雄美人”的叙事;《铁道游击队》中酷似林冲、鲁智深等人物的林忠、鲁汉,《烈火金钢》中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史更新、肖飞等人物;还有它们通常采用的“评书式”和“单元化”叙事结构,都增加了这些作品的传统色调,因而也就使之增加了“文学性”的含量,而有别于一般的“革命历史斗争故事”。简言之,它们是由于对古典小说的学习而变成了具有一定“文学性”、“传奇色彩”和“美学意味”的作品。否则,以这些作品笔法的粗糙与幼稚,技术的简陋与拙劣,只能沦为垃圾。而事实上,它们却得以成为了一个匮乏时代特殊的文学经典,其中的奥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本结构”作为一个“无意识系统”支持的结果。
这种情形在另一些较为主流的作品中也相类似:《青春之歌》中假如没有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没有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类似“英雄美人”和“婚外情”式的故事,也会索然无味;《红岩》中假如没有对“中美合作所”的“魔窟”与“匪类世界”的夸诞式描写,也不会使这部小说一度占据当代小说销售榜的顶端;甚至《红旗谱》,这部作品之所以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它书写了“半部传奇”。显然,前半部中朱老忠这个人物是按照“传奇”笔法书写的——他几乎已是一个“完人”,出身农民英雄之家,苦大仇深,有闯荡江湖三十余年的履历,成熟而老练,富有斗争智慧,是锁井镇百姓的主心骨。作为一个“完成性”的“性格化人物”,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古代民间英雄和侠客的化身了,正是这个人物使得小说前半部的叙事相当成功;然而在遇到“党”之后,他却不得不变成了一个必须要“成长”的人物,一个地位尴尬的“被领导者”。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性格魅力尽行丧失,小说不得不将主人公置换为了下一代人,尽管这是作品在政治上的一个需要,但是很显然,它也毁掉了作品在结构上的统一性,削弱了它的文学性。
总体上,在当代的革命文学中,“传奇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参与因素,没有稀薄的传奇性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大量“潜文本”的存在;没有“潜文本”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使这些作品保有一定的“文学性”。
传奇性在当代的“复活”还有更新的例证,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潮与先锋小说中可以看到这种复活的迹象。不过,由于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明显的西化倾向,它们在美学上也更为复杂,因此这一点似乎很难厘清。从基本经验上来说,莫言早期的《红高粱家族》,稍后的许多“新历史叙事”,都接近于一种“新式的历史传奇”,因为它们大都以嵌入或交杂的形式加入了许多民间文化与民俗元素,加入了常态下很难见到的“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传奇人格。到九十年代,英雄式的叙事逐渐被世俗讽喻的主题所取代,比如贾平凹的《废都》便是以“寓言”的方式预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颓败,以及读书人全面的精神溃败,带有强烈的类似《金瓶梅》式的寓意色彩。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更是从叙事与美感神韵上承续接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传统,用了“张爱玲式”的世俗传奇和浮生笔记的方式,展现了现代中国城市的悲剧故事,一个美丽女性的命运传奇。
可以举出的接近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些主要是靠体味与直觉,而很难从理论上说清它们的传奇性质。比如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类,也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或小人物的传奇”;莫言世纪之交以来的多部长篇《檀香刑》与《生死疲劳》等,也都可以看做是富有传奇意味的现代历史寓言;不止这两位,在阎连科、刘震云、张炜等作家的笔下,也有类似的历史寓言,如《受活》、《一句顶一万句》、《丑行或浪漫》等,也都有夸诞或传奇性的人物与故事。但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详细展开了。
总体上可以说,当代中国小说的复兴,小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的成熟,其文化含量与美学神韵的日益凸显,都与古典小说中的“传奇传统”的恢复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还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九卷,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⑤巴赫金:《小说理论》,第276—277页,第276页,第277—278页,白仁春、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Ι》,第1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⑥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的说法即与他读到中国的小说有关,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谈到一部中国小说(应指清初张匀的《玉娇梨》,当时有德文译本的中国小说还有署名“名教中人编次”的《好逑传》)时,曾以十分激赏的口气谈到,“中国人的思维,行动,感觉,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平易而质朴的,没有强烈的热情和诗意的激昂,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和理查逊的英国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随后他感慨地说:“民族文学在今天毋宁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世界文学的时代已不远了。”见《歌德与艾克曼的谈话》,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68—4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下)》,《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9—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参见朱一玄等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
⑩张爱玲:《传奇》,上海杂志社1944年版;引自《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⑪参见张清华:《“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中国当代革命叙事的三种模式及其叙事美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