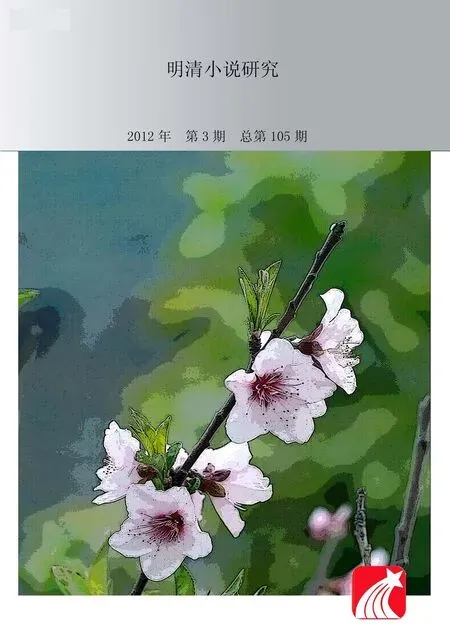明清小说的伦理观与和谐文化
2012-12-17··
· ·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伦理道德的民族,伦理道德的观念贯穿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优良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这种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而作为文学之一的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由于其文体的优势,因而它体现或传播这种文化精神就显得更为广阔和深刻。本文拟从家庭伦理与和谐文化、社会伦理与和谐文化、政治伦理与和谐文化,以及明清小说伦理观的现代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家庭伦理与和谐文化
传统的“伦理”与“道德”,在今人看来,似乎是一对名异而实同的概念,往往二词连用,即为“伦理道德”。即使单称“伦理”,人们习惯上包含了“道德”在内,反之亦然。事实上,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如“伦理”有上下尊卑的区分,侧重于“关系”,如荀子云:“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①讲的是各种社会关系。此中除“朋友”关系属平等的外,其他关系都明显带有上下等级的性质。而“道德”则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分,侧重于“标准”,作为概念或行为上的“标准”,“道德”具有恒久、稳固的性质。若将“伦理”、“道德”分别与其它的词汇组成新词,其具体含义的区别则更为明显,如“伦理”可以组成“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等等;而“道德”则可组成或“传统道德”、“现代道德”;或“人际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作为“标准”的道德,虽然没有尊卑之分,却有高下之别,如“基本道德”与“高尚道德”。
所谓“家庭伦理”,是指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是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定的社会性、时代性;其内涵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又具有一定的因承性和稳定性。在中国古代“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就属于家庭伦理范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无数家庭构成的。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人生奋斗历程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他们的奋斗目标,而“修身”则是实现这三大目标所必备的前提条件。何谓“齐家”?“齐家”,就是使家齐,语出《礼记》,意思是把家庭和家族关系处理得融洽和谐,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三大目标的第一步就是“齐家”,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也。可见这“齐家”对于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兴旺、天下的和平是多么的重要!
怎样做才能齐家呢?虽然说“修身”是担当大任的君子所必备的前提条件,但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所以古人又建立一系列的家庭秩序,亦即家庭伦理,在古代统称之为“礼”。率先倡导这种伦理秩序的是儒家学派,儒家学说开创者孔子在《礼记》中强调“礼”的重要时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②此其中的“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讲的就是家庭必须有的秩序规范。这种家庭秩序或观念,在“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文革”结束之前这个时段,人们总喜欢冠以“封建”的帽子加以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批判似乎有些偏激;其实这些伦常秩序自古至今,一直不同程度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况且原始儒学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关系是对等且双向互动的,不是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诸如“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③之类的说法即为明证;否则,即如孟子告齐宣王所说的那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可见它们都是对等互动的。由于这些伦常秩序和社会道德标准代代相传,并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当今称之为“和谐文化”。
毋庸讳言,原始儒学对等互动的伦常秩序发展到汉代董仲舒那里就有些变味,再到宋代理学家那里就彻底变质。董仲舒虽然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他已暗暗篡改了儒家学说,以其“贵阳而贱阴”理论,发展韩非“三纲”之说,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宋代朱熹再将“三纲五常”联用,并将这些“纲常”升格为“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后世批判“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明清时代的学术没有多少新的创获,大多是围绕“程朱理学”的“知”“行”“性”“智”等概念兜圈子、做文章,其中讨论较多且比较激烈的话题是“天理”与“人欲”之辩。由于原始儒学对等的伦常秩序到此期已变成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其中妇女所受到的禁锢更为严酷,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守节”观念成为灭绝妇女天性的桎梏和牢笼,于是激起人们的反抗,像李贽、黄宗羲等一批学人纷纷起来质疑和批判,人欲满足、人性解放的呼声四起。
矫枉总难免不过正。在明末清初“人欲满足”、“人性解放”的一片呼吁声中,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欲满足开始走向极端,于是乱伦无忌、烂淫烂欲现象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清初以至清中叶的思想家又开始对“理”“欲”关系作哲理反思,其中戴震的理论影响更大。戴震曾把人的情欲概括为欲、情、知三个层面,他说:“唯有欲、有情、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但戴震所主张的“遂欲”并不是纵欲,而是肯定情欲,反对滥欲;否则,贪邪、乖戾、差谬随之而至,如说“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⑤,可见戴震既反对抑欲、灭欲,又反对纵欲、滥欲。
长于综合反映社会生活的明清小说,它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着中国的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和谐文化走向现代。以家庭伦理观念而言,明代出现的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对象的长篇世情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为家庭伦理,如潘金莲勾引叔叔武松,西门庆纵欲滥淫等情节以及他们最终的悲剧结局,都从反面证明了蔑视纲常、乱伦无忌、纵欲无度都必无好下场的道理。
然而明清小说更多的是从正面倡导家庭伦理,而“和为贵”是其核心思想,所谓“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就是维系家庭伦常秩序得以顺畅和睦的法宝。正面描写旧式大家庭日常生活的小说,朱剑芒选编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最为典型,所选皆为传统家庭伦理小说。书中通过对一群富有勤俭、朴实、温厚、善良、宽容品性的女子作细致入微的描写,再现了一个个旧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肯定了女主人公不怕牺牲与乐于奉献的精神,奏响了一曲曲家庭和谐美的颂歌。
如果说《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诸篇中能维系家庭“和美”的关键在于女性的宽容与奉献,其精神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那么李渔《十二楼》诸楼故事能感化人的关键在于书中人物的“哲理思辨”,其智慧给读者以无穷的生活或生命的启迪。作者李渔的人生哲学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折衷主义,他既不满禁欲,又反对纵欲,在“理”与“欲”,“情”与“色”等方面,李渔都从哲学层面把握得恰到好处,譬如《合影楼》最终推倒那座墙,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李渔给情欲受压男女提供“遂欲”举措的一个典型例子;而《鹤归楼》中段玉初和郁自昌的感情婚姻故事以及二人相反的结局,则是作者给离乱忧患背景中的人们所开的“维欲”良方。李渔及其笔下的人物,基本上是“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钟伦外之情”,体现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观念。相反,像《水浒传》《金瓶梅》中关于潘金莲、西门庆之间种种情节,均属“桑间之色”、“伦外之情”,必然受到人们的唾弃。
二、社会伦理与和谐文化
人皆具有社会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是由无数个按一定利益和秩序构成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所组成,它需要一定的公共秩序、准则来规范、约束和维系,因而所有社会团体或阶层中的任何成员所遵守的社会共同准则或规范,就被称之为社会伦理。换言之,社会伦理即伦理道德的社会性,亦即人与人之间符合民俗道德准则和文明规范的关系范畴,是家庭伦理的延伸和拓展。
社会伦理既是制度的,也是精神的。由于社会的丰富性和人类的复杂性,社会伦理更加崇尚某种道义和精神的提炼。而中华民族从先秦诸子那里提炼出来的道德精神,无不成为历代国人的行动准则和精神追求,诸如敦实诚信,宽容谦和,仁爱互助,与人为善,成人之美,责任感、使命感和事业心……等等,都是今人所公认的传统美德。具体来说,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论,即为人际伦理,它特别讲求诚信与谦和,崇尚“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的大爱与包容;从人所从事的事业论,即为职业伦理,它讲求责任感和事业心,崇尚胸襟与情怀,顽强与执着;从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尊严的角度论,即为社会伦理的最高层面,它讲求正义感和使命感,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牺牲与奉献。……明清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是文言还是白话,都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和传播着这些道德和精神。
古代中国虽然以农耕为本,商贾为末,但商业活动自先秦直至明清绵延不绝,而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则更加频繁,形成了晋商、徽商、浙商、赣商等一系列商帮,经商地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同时也扩大了中华民族在国际的影响。然而商人趋利是职业的要求,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哪种“利”该得,哪种“利”不该得?这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伦理问题。中华民族是个“尚义”的民族,自先秦孔子及其弟子所倡导的商业道德,诸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富而好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取与义”等等,经一代又一代商人的践行和社会的提倡,已凝成后世所崇奉的“儒商精神”,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白圭,汉代的桑弘羊,直至清代晋商巨贾的常氏、乔氏、曹氏等等,都是中国儒商的典范,为时人以及后世人们所景仰。
文学反映生活,而小说戏曲是古代文学综合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佳形式。明清时代以小说戏曲反映社会生活成为该时代文学的主流,商贾活动则自然成为小说戏曲作家笔下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小说而言,像冯梦龙、凌初、李渔等一批受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小说家,他们同时又受到当时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小说有大量关于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的描写,或抨击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奸诈小人,或歌颂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都生动地诠释了儒家的“义利”之辩及其取舍。以正面形象而言,如冯梦龙笔下的吕大郎(《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施复(《施润泽滩阙遇友》)、阿寄(徐老仆义愤成家)等,李渔笔下的秦世良和秦世芳(《无声戏》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祸至》),其具体情节虽然不同,但他们利以义制、以义取财、重情重义的儒商品格是一致的。作者始终以极为欣赏的笔致,大量描写和热情歌颂这些正面的商人形象,目的是要用儒商故事来弘扬儒家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以“有益于生人之道”。
社会的和谐应以社会的安定为前提,安定是任何社会历史阶段压倒一切的前提条件。明清小说涉及社会内容、社会伦理最突出、最典型、也最具综合性的小说类型莫过于公案小说,因为社会所有可能出现的案情无不包罗在公案小说中,诸如婚姻伦理、商业伦理、日常行为伦理等等,像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影响较大的公案小说。公案小说大多是以抑豪猾、除暴乱、平反刑狱为主要内容敷衍故事,带有一定的侠义色彩,意在扶持弱势群体,并替他们洗刷冤屈、伸张正义和主持公道,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宁,并促使社会最终走向文明。
公案小说在分析案情和判案时,虽然离不开法制手段,但更多的情节是在倡导德治,即以道德感化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进行正面教育。此类内容的小说以李渔白话短篇最为突出,如骗子、偷儿的改邪归正,强盗、土匪的弃恶从善,移情别恋男女的回心转意,说长道短者的最终收敛……如此种种人心向善的情形,作者都归结为道德感化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作者崇尚和向往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德治理想。
爱心和宽容之心是道德昌明、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一个没有爱心、没有宽容之心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学派否认爱心和宽容之心的社会意义。如儒家提倡“仁爱”,道家提倡“慈爱”,墨家提倡“兼爱”,基督教提倡“博爱”,佛教肯定“慈心”,提倡“放生”……尽管他们各自的具体见解和实施方法不尽相同,但都包含共同的“爱”和“宽容”在内。
“爱”无差等,在明清文言小说中多有体现,如明·黎澄《南翁梦录》中的《医善用心》条,记“既有善艺又有仁心”的“良医”范彬在一平民妇女和宫中贵人同时求医时,不以社会地位而以病情缓急为先后,使二妇人的病均得到医愈而终得王者的嘉奖。这种“爱”不仅体现了公平,而且还是一种智慧。“爱”在明清小说中更多地体现为“善”,爱心即善心,多以“善有善报”来鼓励人们为善,引导人心向善,如《祖灵定命》、《妇德贞明》、《夫妻死节》等,均以传统观念实践者获善报的故事,宣扬和歌颂传统的伦理道德。
事实上,爱心与宽容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彼此互见。一个人如果其性格豁达,心胸开阔,且富于爱心,一定会有宽容之心;相反,性情乖戾,心胸狭窄,又缺乏爱心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有宽容之心。然而“宽容”比之于“爱心”,其实践起来似乎难度更大。因为“爱心”虽然也有心理活动,但其表达形式更多的体现为物质的“赐予”或“施与”,侧重于外在行为;而“宽容”虽然也见之于外在,但更多的体现为心理让步,侧重于内在的心理活动,所以“宽容”是需要气度,需要胸怀,需要爱心,还需要智慧。在人类各种情欲中,最难突破的恐怕是男女间的“私情”,因为什么都可以让人,唯独老婆或丈夫不可以让人,这差不多是世人公认的事实。明清小说一方面反对违背社会道德的“第三者”,提倡“贞节”;同时又能理解在特殊背景中的“男女过失”,特别是能理解女性的过失。这种理解和宽容,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和伦理观念的极大进步,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和那个县令是为典型。
明清小说反映爱心和宽容主题的故事,并不专主某家某派,而是综合众家之说,体现了明清小说那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其中文言小说以爱心和宽容之心感化人类的故事占相当的比重。如《乔王二姬合传》中的乔王二姬故事、《香畹楼忆语》中汪允莊与紫湘的故事、《影梅庵忆语》中的董小宛故事,都是以爱心和宽容的品德而影响读者。再如《与物传》中许多动物故事也极为感人,其中一篇说的是大庾岭李氏家养了两只母猫,它们各产四子,交相为哺。后来一猫为犬伤至死,另一猫衔死者众子置己窠与己子合养。这个故事与唐宋时期江洲聚族同居“义门陈”家的“百犬同槽”颇为相似,其文化渊源可上溯到先秦的儒家和墨家。如孔子主张人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墨子倡导“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等等,表述不同,其实一也,即要求人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广施“仁爱”。其爱心甚至超越人类,扩充到万事万物,达到《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尚仁义、尚宽容、尚和平的社会伦理还表现在民族矛盾方面。尽管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频繁不断,但从社会伦理观念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则非常注重“平等”与“和平”。如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体现的是一种跨国境的“爱”;儒家“尚辞让,去争夺”、“讲信修睦”,体现的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平等愿望;道家的“无为”与“不争”,体现的是顺天应人、明天道行人道的德治理想。明清小说涉及战争题材的篇目不少,如《三国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都有大量战争场面的描写。这些作品,一方面通过歌颂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或爱国将领,来表达作者和时人强烈的爱国感情和深沉的民族思想;同时也深寓着作者以及时人厌恶战争、渴求和平的愿望。以《杨家府演义》为例,如“十二寡妇破阵”、“穆桂英挂帅”、“佘太君点将”等情节,不仅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能力、作用的肯定和歌颂,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战争本身的批判,因为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让男人们纷纷战死,哪里用得着妇女们去面对刀剑与血光?可见此期有关战争题材作品的出现,其客观意义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说的那样,是在“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消灭战争”。
三、政治伦理与和谐文化
所谓政治伦理是指为政者必须遵循的行政道德准则,它特别强调为政者自身的道德素养、历史责任和社会作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所遵循的道德准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体现为政者的君子人格。
那么儒家所推崇的政治是怎样的呢?简言之,即为仁政,或称之为德政。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仁政就是人道主义政治。儒家认为实施仁政最理想的办法是“德化”而不是“法制”,但也不排斥法治手段;事实上,在整个古代中国施政的历史过程中,也没有少用法治手段。为什么说实施仁政最理想的办法是德化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心服胜过威服,用道德感化的办法更容易使人心悦诚服,德感心服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刑逼威服的作用,即如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⑥。当然孔子在强调道德感化的同时,还强调了礼的作用,“礼”也是儒家倡导其道德伦理的重要内容。
古代政治伦理约束的对象是为政者,今天称之为各级领导干部。古代社会对为政者道德修养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其政德的培养则是从孝亲开始的。孝亲是任何层级的人必须遵循的首要之义、起码之行、诸德之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是也。孝亲如何?即要求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⑦。否则,“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再由孝亲推而广之,则要求事君忠、教民爱,进而显亲扬名以立身,即如孔子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概括起来就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人君若能治天下以孝,便可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以孝,便可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以孝,便可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如此,则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便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以养斯民,以和万国。
古代不同层级的执政者,其孝义各有侧重。具体来说,天子之孝:“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而诸侯之孝:“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士之孝即为“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仰不负于天,俯不愧于民。庶人之孝则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其孝义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爱、敬、谦、和的表现和榜样的力量是一致的。
由始于“孝亲”,进而扩充到“忠君”“爱国”,再渐进到“民胞物与”的儒家伦理道德,经一代又一代君子的践行和传承,终于形成了今所谓儒家文化的完整体系。其涉及政治伦理的部分,诸如为政者的孝亲、忠君、爱民以至齐家、国治、天下平的奋斗目标,逐渐内化为强烈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凝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比如一种担当精神,一种仁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外化为一种行为准则,并在履职实践中表现为忠于职守、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古代中国尽管也曾出现过一些有悖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各级官吏,像《儒林外史》中的王惠、张静斋之流,就是典型的违背儒家政治伦理的代表人物,其追慕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物欲,为当时以及后世君子所不齿;但恪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道德准则的官员却也大有人在,自汉至清,如赵广汉、黄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王安石、海瑞、况钟、施世纶、汤斌、张鹏翮等一大批能臣要吏,他们始终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信条,勤政清廉,执法如山,宽宏大度,爱民如子,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成为儒家仁义道德的自觉守护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名字成为后世“清官”“廉吏”的代名词,他们的故事,不仅在正史中有客观的记载,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亦有许多生动的描述。现以明清小说为例略作分析。
明清小说特别是公案小说有大量清官形象,那些清官普遍具有这些共同特点: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睿智;爱民如子、清正廉明的仁德;锄奸除暴、嫉恶如仇的忠勇,是古代理想的仕人风范,成为历代民间所崇拜的各级领袖人物。如《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世纶,他折狱缉盗、惩恶扬善、惠政于民的故事,在当时影响巨大,在民间广为传颂,有“施青天”的美称,康熙皇帝曾赞之为“江南第一清官”。再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小说和《海青天》评书,都是以海瑞为描写对象,现代著名学者吴晗又将它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作品中的海瑞,他为人正直,直言敢谏,是当时被压抑、遭欺负、受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为政清廉,公正为官,明断公案,美政多多,是今人尤其是当今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另外还有一些名士加清官的形象,在当时乃至后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如《窃闻》的作者兼作品主人公的叶绍袁是个典型的名士兼清官。他曾任工部主事,还督理过盔甲厂,以及修葺城池、开浚九门河等浩大工程。后来告老还家,他家庭的经济已很拮据。《窃闻》“考”的作者朱剑芒于此异常感叹地说:“假使会捞摸的,那便是个发财的机会。可怜他(叶绍袁)本是个名士,又要做清官,甚至把家产变卖了,作为京中的旅费!……家产方面既入不敷出,自然要越闹越穷了。”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夸张,如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的汤斌,他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其所执掌差务本当都是些肥缺,但由于他要做清官,所以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由此可见,那些文学家、史学家笔下的名士、清官,都是些事功、节行、道德、文章兼具的领导者。
作者极写那些名士、清官文行并重、政绩与节操俱显的特点,除了客观上所流露出的个人观点、态度和政治见解外,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推进儒家政治伦理建设,弘扬儒家道德精神,以促进社会、国家、民族更加和谐;即使像《儒林外史》中那些反面的官场人物,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如高要县的贡生严致中、监生严致和兄弟,他俩一个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严致中)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时竟行凶打人;另一个(严致和)则是家财万贯却吝啬成性的守财奴。作者竟然给他俩取名为“致中”、“致和”,一般人看到的恐怕只是讽刺的一面,其实此中也暗寓了作者对官场人物恪守道德的迫切希望和对社会政清人和的理想追求。
四、明清小说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伦理观念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很突出的观念,并成为小说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以“孝悌”、“忠勇”、“仁爱”等为其关键词而频频出现。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以往人们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认识还不够全面的情况下,古代小说中的伦理观念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从而客观上影响了学界对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合理公正的评价。记得在三十年前,我们上大学的那会,由于十年浩劫的“文革”才刚刚结束,文革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讲古代小说的老师对明清小说的评价,形成一个习惯的程式:总是先肯定小说中“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部分,然后话锋一转,又给古代小说戴上“封建”的帽子。究其“封建”何在,大多落在“孝悌”、“忠义”的伦理观念上。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古代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已走上了正轨,文艺创作与研究真正体现了我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与研究成果异常丰硕,优良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但就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研究来说,似乎还有不少空间,比方说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中伦理观念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被正确区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部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优良传统文化的作用在当今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进一步发挥。
就“孝”字而言,作为经典之一的《孝经》,则囊括了儒家所主张的伦理体系的全部内容,如始于孝亲的家庭伦理,逐渐发展到诚信、友善的社会伦理,再进一步发展到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终至天下、万物的宇宙伦理,都是用一个“孝”字来概括,可见《孝经》中的“孝”,不是狭义的孝而是广义的孝,所以《孝经》中又有《广要道》《广至德》《广扬名》等章节。当然,以往对古代小说“忠孝”观念的批判,并不包括其中好的一面,而是批判其愚忠、愚孝的一面。但由于人们在表述习惯上喜欢在儒家“忠孝观念”前冠以“封建”二字,所以听众或读者对“封建”二字,有谈“封”色变的紧张,于是自然产生一种错误的逻辑联系,即儒家的就是封建的,封建的忠孝就是“愚忠”“愚孝”,于是得出儒家的忠孝即为“愚忠”“愚孝”的结论。实际并非如此。请看《孝经·谏诤章》里孔子与曾子的一段对话: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可见,孔子是不赞成无原则、无是非的“从父之令”;不讲原则,不讲是非的“从父之令”,在孔子看来才是真正的“不孝”。以此类推,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君父,若当不义,必争之;否则,就是不忠或不孝。如此看来,儒家的君臣、父子间的忠孝观念始终是双向互动的,何“愚”之有!
笔者在上文将明清小说的伦理观念分成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完全是出于表述的方便,其实他们之间又是互相渗透,彼此纠结在一起的,不能绝然分开。因为这三个层面的伦理,实则贯穿在儒家的五伦之中,而五伦中处核心或首要地位的当为夫妇,如《周易·序卦传》在解释恒卦时所列举的三种人伦关系就是以夫妇为中心展开的。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此三种人伦关系又构成了一个逻辑链:即从家庭(夫妇、父子,实际上还应包含“兄弟”在内),到社会(君臣,实际也应包含“朋友”在内,即更大的家庭)或政治(君臣关系体现为政治,亦可指国家)。要使得这个链条中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安宁,就得有一种秩序来规范,一种规范来约束,而这种秩序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就是双向互动的上下尊卑的人伦关系。如果这链条中各个环节都井然有序,那么乱象就无从产生,家庭从此安宁,社会从此稳定,国家从此太平。
孔子所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中的秩序和规范,虽然不见用于当时,却能教化于后世,其积极的教育意义,是通过戏曲小说的广泛传播来体现的,并在当今仍然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崇尚宽容与自信,促进人格不断完善;崇尚道义与责任,促进当今政治文明;传播民族先进文化,促进当代精神文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们要对富于儒家文化精神的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发掘其中的进步思想以指导当今的道德建设,为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民族兴旺、国家繁荣创造和谐的环境,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的亲和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
① 《荀子·非十二子》,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② 《礼记·曲礼》,见《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礼记·礼运》,见《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 杨伯峻《孟子导读》,巴蜀出版社1987年版。
⑤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⑥ 《论语·为政第二》,张燕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⑦ 《孝经·纪孝行》,见《孝经名家讲解》,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