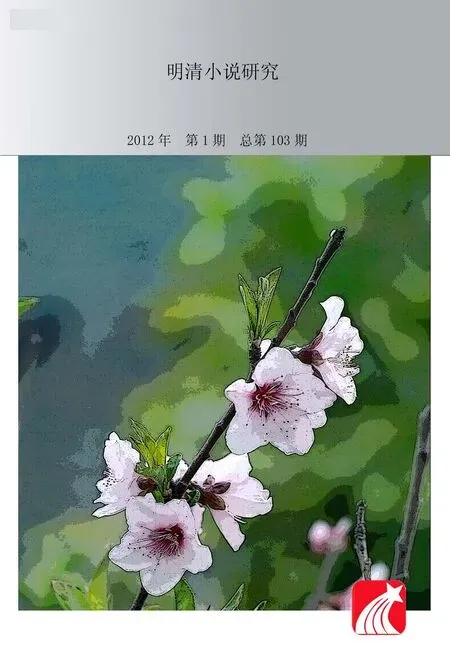论《说岳全传》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
2012-12-17··
··
《说岳全传》是岳飞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在民间传播非常广泛,在民众中的影响很大,不只这部小说文本曾畅销一时,而且还被改编成戏曲、说唱、电影等形式,在舞台上盛演不衰。但作为民间系统的通俗小说,很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似乎都忽略或误解了这本小说,很少有正式论文谈到它,某些小文章提到它时,也多是简短的杂谈。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对它才能采取较宽广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之后随着文学理论视野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多方面角度去评析这部小说,对他的评价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客观,它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肯定。总体而言,在《说岳全传》的传播接受史上,由于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的变化及传播者、接受者知识结构、道德观等的不同,对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较多的论者和读者肯定了它的审美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方面。也有部分论者持否定的态度,否定其价值主要是着眼于其封建忠君思想及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描写等方面。本文拟对《说岳全传》的价值取向进行归纳总结并初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期更好地把握和实现《说岳全传》的多重价值。
一、审美艺术价值
《说岳全传》的审美艺术价值主要包括虚实关系、人物刻画、叙事结构、悲剧价值等方面。最早肯定《说岳全传》审美艺术价值的当属郑振铎。1929年郑振铎于《文学周报》发表《岳传的演化》①一文,文中认为《说岳》是所有早期岳传的总结束,也是一部最完善的精忠传,又引金丰的序“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认为“直是道破了一切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的关键”,《说岳全传》比之前熊大木的《武穆演义》、于华玉的《尽忠报国传》更为“荒诞”,“这乃是自然的进展”、“民间的需要”,“一切传奇都不能不走到这条路上去。不荒诞便不成其为‘传奇’,不荒诞便不能为民间读者所深喜”,肯定了《说岳全传》虚构情节、加强传奇色彩的写法,同时认为其内容也自有其好处,比前几部小说叙述更详尽深入,描写更生动活泼,格外动人,尽管文章最后郑振铎把《说岳》与其它小说作比较,认为《说岳》的文字“颇平庸,不大耐得吟味,与诸本《说岳传》较之,固然是高出,若置之于《水浒》、《红楼》之列,却颇有些‘自惭形秽’”。只就文字技巧评论《说岳全传》的地位并不能提供一个明确而公允的论定,但郑振铎这篇文章首次探讨并肯定了《说岳全传》的审美艺术价值,向人们介绍了《说岳全传》是一本值得重视的通俗小说。
1956年李厚基在《文学遗产》发表《读〈说岳全传〉》②一文,详细分析了《说岳全传》中的人物形象。李厚基认为“对于岳飞,作者自己除了表示惊奇、崇敬和赞叹以外就没有别的,他努力通过艺术上所特有的夸张手法把内心中对于这样一个巍峨的英雄形象的感情,全部表达出来”,把岳飞塑造成“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正是由于作者对岳飞的“过分神化”以及“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英雄人物在所难免的”原因,使得岳飞的形象也“不是完整无缺的”。而牛皋,李厚基认为作者没有抽象地加以夸张,“这倒反使他自然可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李厚基也指出《说岳全传》塑造人物的缺点:“《说岳》仍不能摆脱普通章回小说的窠臼:它着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忽略人物性格的描写;因此,其它人物(即岳飞、牛皋、王佐、兀术、张邦昌、秦桧等除外的次要角色)就显得一般化。这正是比《三国》、《水浒》、《西游》颇为逊色的地方。”李厚基的这篇文章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对《说岳全传》的艺术价值进行了适度客观的评定。
除李厚基的《读〈说岳全传〉》之外,五六十年代还有不少文学史、小说史及专论谈到《说岳全传》,这一时期由于时代的原因在论述《说岳全传》时,重点都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也多强调其爱国主义方面。但这时学者对《说岳全传》已较能采取宽广的角度探讨,对其审美艺术价值也多有肯定。如北京大学编撰的《中国小说史》,以专论的方式详析了《说岳全传》中某些重要的情节内容,最后总括地评论云:“在艺术上,它克服了明代说岳演义普遍存在的生搬历史事实的毛病,本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态度,广泛汲取元明戏曲小说与民间说唱中的故事,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小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作者吸收了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大量运用‘市语’,语言通俗晓畅而又鲜明生动”③。从《说岳》的写作态度、方法、语言等方面肯定了其艺术价值。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说岳全传》研究的角度与内容呈现多元化倾向,对其价值的评判也趋向理性客观。1983年李时人的《关于〈说岳全传〉》④一文从内容结构、创作方法、形象塑造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说岳全传》的审美艺术价值。李时人说“《说岳》以岳飞的一生经历为线索,以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乱世为背景,谱写出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对于《说岳全传》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李时人说:“历史文学作品都是根据作家的某种认识去再现历史生活的,渗透着作家对历史生活的理解,寄寓着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因此,所有的改编加工和虚构都是艺术手段,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塑造人物、突出主题。”他认为《说岳全传》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具体细节,注意艺术创造加工,使岳飞抗金故事完整生动,使岳飞由一个历史人物上升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整个作品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十分引人入胜,艺术上颇有一些特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李时人认为“《说岳》比较善于写人物。作品着力塑造英雄岳飞,既使用神话、传奇的手法,又注意现实和具体的描写……多方面揭示他的高贵品质和内心世界”。另外牛皋、王佐、岳云以及秦桧、金兀术等反面形象也写得比较生动。在语言运用方面,李时人也加以肯定:“《说岳》采用的是民间说书用的通俗艺术语言,这种语言,既适合浓墨巨笔的粗线条勾勒,又适合细腻委婉的细节刻画,使作品通畅流走,明白如话。”李时人还肯定了《说岳全传》善于描写战争,“能因时因地写出每场战斗的特色”。对于《说岳全传》善于写战争,陈维仁在《漫评<说岳全传>》中也加以肯定:“书里正面描写战争的情节占了大半篇章……都写得十分精彩。有大的战争场面的勾勒,也有在激战中的许多细节刻划,既波澜壮阔、热闹纷繁,又形象生动、妙趣横生。”⑤
1992年出版的顾歆艺的《杨家将与岳家军系列小说》也对《说岳全传》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探讨了其多方面的价值。顾歆艺认为《说岳全传》脉络清晰、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同时又情节曲折,故事性很强,很多情节写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人物形象典型生动,特别是英雄形象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语言相当纯熟流畅,且新鲜活泼,具有民间传说的神奇色彩。顾歆艺还运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理论肯定了《说岳全传》虚实相生的创作方法,认为艺术真实不同于历史真实,只要有利于主题思想的表达都是可以虚构的,“《说岳全传》是将史实传奇化了”⑥。顾歆艺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说岳全传》的审美艺术价值,认为《说岳全传》在英雄传奇小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许多论者注意到牛皋的喜剧形象及反面人物金兀术,从多方面探讨了他们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罗书华的《中国传奇喜剧英雄生成考辨》⑦认为《说岳全传》成功地把牛皋从之前说岳故事里一员没有突出特点的将领改造或者创造成了一个生气盎然、人皆喜爱的喜剧英雄。赵文光在《古典历史小说“鲁莽”英雄形象特征及美学意蕴》⑧中更是认为《说岳全传》之所以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和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中所具有的“喜剧容量”。而牛皋的“鲁莽”英雄形象正是这喜剧容量的载体。牛皋是小说中最为活跃的人物,而且更符合普通劳动人民的审美心理和趣味,所以深得人们的喜欢。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包括牛皋在内的“鲁莽”英雄形象所蕴含的丰富的美学意蕴:“率直、真诚的人生追求,扶危救困的侠义精神、乐观忘忧的人生理念、威武刚直的英雄理想。”孙长明、许海丽的《牛皋福将形象的成因初探》⑨中认为牛皋的形象“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具有一定的反叛性”,“在民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牛皋的形象,“不仅活跃了情节,而且丰富了人物的类型,因此对小说结构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提高了小说的欣赏价值,从而使读者获得全方位的审美乐趣”。王立、冯立嵩在《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⑩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金兀术的“侠义”性格,认为“金兀术具有既令人憎又有令人敬的矛盾性,充满了多样性的魅力”,“金兀术身上灵活多样地寄托了各阶层人们对忠、对奸、对敌、对友的正确评判的道德理想”。
也有许多论者专门从《说岳全传》蕴含的悲剧意蕴方面揭示其审美价值,李长江的《浅析〈说岳全传〉中岳飞的悲剧形象》认为“《说岳全传》塑造的岳飞形象,以其刚烈执直的个性付出了英年早逝的代价,演出了一幕震撼人心的千古悲剧”。强金国在《论〈说岳全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忠奸斗争主题》中认为岳飞的愚忠“使忠奸斗争以忠的一方彻底失败而告终,从而给他精忠报国的一生涂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以大鹏与女士蝠、蛟精的故事来解释岳飞和秦桧之间的斗争,末回以大鹏归位来结束全文的安排,曲折地表达了作者以及读者的一种无法释怀的情结,借用因果关系,将历史和人生化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模式,透露出一定的悲剧气氛”。
二、思想价值
《说岳全传》的思想价值是研究者和读者讨论最多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论者在谈到《说岳全传》时特别强调其思想价值。复旦大学中文系1959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样写到“《说岳全传》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部作品,通过民族英雄岳飞率兵抗敌,树立战功一直到风波亭被害、伸冤雪恨的故事,歌颂了坚决抗战、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同时也严厉的抨击了妥协退让、卖国求荣的赵宋统治阶级和汉奸”,“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真实情况,以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在分析岳飞形象时特别强调:“作者突出了岳飞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了体现在岳飞身上的中国人民抵抗侵略者的坚强信心与英雄气概。”最后总结到《说岳全传》在“人民文学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2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作者的创作指导思想时说“《说岳全传》在表现爱国主义的民族思想方面,较之《水浒后传》更加集中和突出”,“这在清朝统治极端严酷的时期,编者勇敢地刊布这种高度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是值得赞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小说史》:“小说以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的奋战为中心,写出了赵宋统治阶级腐朽媚敌,外族统治者屡犯中原,人民英勇抵抗,这就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在谈到岳飞时也是强调其爱国主义方面,“他的反抗侵略的一生,他的精忠报国的精神,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岳飞在人民中间也就成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类似的论述在当时还有许多,如成柏泉的《谈谈〈说岳全传〉》、海燕的《对〈谈谈说岳全传〉的意见》、王延龄的《怎样评价〈说岳全传〉》等,这些文章大都篇幅短小,多为随笔性的读书札记,论述的重点都是《说岳全传》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尽管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时在肯定《说岳全传》的思想价值时观点有时不免偏激,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比较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说岳全传》,并进而采取较宽广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
李时人的《关于〈说岳全传〉》在详细分析其审美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它的思想价值:“《说岳全传》有明显的民族意识,有悼念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卖国贼的用意”,“作者所要表彰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所要鞭挞的是秦桧的奸佞卖国,所要揭露的是兀术的横暴侵略,而在这其中,小说又重点突出了对岳飞精忠报国的歌颂”,“《说岳》的思想内容,虽然包含一定的封建因素,但其主要倾向是爱国主义的,有历史的积极意义”。
1980年冯英子在《重读〈说岳全传〉》一文中更是着重强调其思想价值:“宣传了爱国主义精神,描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侵略者面前百折不挠,九死靡悔的斗争史实,使人感动,使人振奋,使人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甚至认为“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比有些理论文章更有说服力,更能收到效果”。陈维仁在《漫评〈说岳全传〉》中也认为《说岳全传》是“形象化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并进一步分析岳飞的形象:“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岳飞,是以爱国主义情操构成他灵魂的核心和精神的基石的”,“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一面,永远放射着熠熠异彩,光耀人间”。
顾歆艺在《杨家将及岳家军系列小说》中对《说岳全传》的思想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说岳全传》之所以在小说史上有一席之地,“主要还在于其感人的思想性”;“其中寄托着人民群众对历史是非曲直的公断和火热的情感”,“是借民族英雄的事迹,歌颂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人民抗敌御侮、保卫家园的美好愿望”,同时“将忠与奸的斗争紧密联系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来写,以卖国投降派作为民族英雄的反衬,以激烈的忠奸斗争作为民族斗争的一个侧面,与之相辅相承,在鞭挞汉奸卖国贼的同时,突出抗战的艰难及英雄精神的可贵”。
齐裕焜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英雄传奇小说”部分中总结概括的《说岳全传》的思想价值最具有代表性:“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样就使全书爱憎强烈、营垒分明,突出了‘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歌颂爱国、抗战的民族英雄,鞭挞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揭露了侵略者的横暴残酷,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说岳全传》成书后被改编为大量的戏曲、民间说唱等文艺形式,在民众中间广泛传播,在历代《说岳全传》的戏曲、说唱改编中,表达的最明确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反抗侵略、鞭挞权奸、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舞台上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有《挑滑车》、《八大锤》、《朱仙镇》、《枪挑小梁王》、《潞安州》、《战金山》、《疯僧扫秦》、《胡迪骂阎》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戏曲工作者更是根据抗战形势改编了许多宣扬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岳飞戏。《说岳全传》所表达的这种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其数百年来激励、教育民众,在民间盛行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三、关于负面价值问题
对《说岳全传》负面价值的认定,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岳飞的忠君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二是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描写。复旦大学中文系1959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析了《说岳全传》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之后指出:“在岳飞身上也体现了忠君甚于忠国的迂腐观念”,“把封建意识与爱国思想的矛盾,用忠孝不能两全的荒谬论调做了歪曲性的解释”,“这些都严重的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岳飞“思想中还存在着封建道德和忠君思想”,这使岳飞形象的塑造“不能够获得更高更典型的意义”,“因果报应的思想,使作者把宋、金斗争,岳飞、秦桧的斗争看成是冤冤相报,前生注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蔽了外族侵略者的凶残本质,开脱了宋朝统治者的罪行”。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在分析岳飞形象时说“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作者把岳飞与权奸强寇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士蝠之间的冤冤相报,这不仅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这些都是首先肯定了《说岳全传》的爱国主义的主题及其价值,然后指出其负面价值方面。
1983年李时人的《读〈说岳全传〉》在肯定了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之后又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岳飞的忠君:“《说岳》写岳飞之忠,又特别强调了岳飞的忠君,岳飞的忠君几乎达到了愚忠的地步。书中又多次大谈‘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这些都严重的削弱了全书的进步思想倾向”,“正因为他既要实行和赵构妥协苟安相对立的抗战路线,又要完全效忠于皇帝,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终于不免以悲剧结局”。同时李时人又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在封建社会,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一般是不敢怀疑皇权的,甚至往往把君王看成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当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忠君和忠于民族又会暂时一致起来。作者强调宋朝皇帝的正统地位,是在明亡不久的历史条件下,又寓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因此《说岳》赞扬岳飞的忠君和全书爱国主义思想倾向又有一定的历史一致性。”李时人对《说岳全传》的评价甚高,认为《说岳》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尽管他也指出了岳飞的“愚忠”,但同时认为岳飞的忠君与小说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历史一致性。
顾歆艺则明确指出岳飞的“愚忠”是《说岳全传》的一大缺陷,降低了小说的价值:“其愚忠思想十分突出,小说甚至成为封建说教的工具,这是它的一大缺陷”;“分析忠君思想,一方面,当然是历史的局限,因为作者是把皇帝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思想是与反对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论是非、过分强调忠君思想,那么则会冲淡爱国主义的主题,同时也降低了小说的价值”。另外顾歆艺认为书中的封建迷信描写也削弱了小说的价值:“迷信斗法在小说中屡屡出现,牛皋曾跟鲍方老祖学道,岳雷靠诸葛锦的神机妙算取胜等等”,“以因果报应统贯全书,成为小说的内在结构。将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南宋偏安、秦桧擅权、岳飞屈死等等,统统归之于天数,以佛家因果、冤冤相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这类描写,不仅荒唐可笑,更严重的是削弱和损害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并遮掩了民族斗争的锋芒”。
齐裕焜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分析岳飞形象时也提到了岳飞的愚忠:“作者写岳飞的精忠报国,主要方面应予肯定,但是,岳飞的忠,有时达到‘愚忠’的地步”,“作者也客观地写出了由于岳飞的愚忠而造成的悲剧,但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思想又像魔影一样控制着作者,传统的心理定势使他无法完全按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如实地去描写,最终只能用‘天命’、‘气数’的因果报应之说,为岳飞因愚忠而造成的悲剧寻求解脱”。这是从作者的创作心态分析了岳飞“愚忠”的原因。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首先肯定了《说岳全传》的价值,认为《说岳全传》写岳飞的精忠报国,其主要方面是爱国主义,由于历史和作者本身的原因,岳飞的忠又有“忠君”甚至是“愚忠”的一面。但也有少数论者持不同的观点。1982年第1期《社会科学辑刊》刊登李忠昌的《〈说岳全传〉主题思想评价》一文,认为《说岳全传》“从作者的整个创作倾向、谋篇布局、结构安排、细节描绘、人物塑造、版本演变上看,无一不是在刻意宣扬忠君思想”;作者“就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宣扬忠君思想,为岳飞(文学形象)的‘精忠’立传,或者说是让岳飞用自己的一生行为谱写的一曲忠君的赞歌”;“在《说岳全传》里,既没有写出这位民族英雄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没有把岳飞作为爱国的英雄形象来塑造”,“而是满怀对忠臣孝子的崇敬之情,以忠君思想为轴心组织矛盾冲突和展开情节”。《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英雄形象,而这一形象也得到了民众的欢迎,李忠昌认为他们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塑造一个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做人的楷模”,甚至“成为愚弄、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这显然过于偏激。对于《说岳全传》的查禁和流行,李忠昌这样认为:“清乾隆年间此书遭禁,其原因也并非是宣扬了忠君,而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和偏见。后来又开禁流行,也正在于它的忠君主题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使然。”笔者对这一观点不能认同,《说岳全传》曾两次遭清政府查禁,统治阶级并没有认为此书利于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其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也不是统治阶级推行的结果,从《说岳全传》的传播接受来看,人们喜欢它更多的是因为其体现出来的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清末这样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人们渴盼英雄出现,也尤为喜欢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借以鼓舞士气、表达抗战的决心,也是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安慰和扬眉吐气的机会。
曾良在《是爱国还是忠君——评〈说岳全传〉的主题思想》一文中表达了与李忠昌相似的观点,认为“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宣扬忠孝节义思想,而其核心是忠君思想”;《说岳全传》“并非歌颂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而是竭力宣扬忠君思想”。李忠昌和曾良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说岳全传》的负面价值上,这种评价显然有过激之嫌了。但同时曾良也承认“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宣扬岳飞的忠君思想,但客观上《说岳全传》流传很广,民众多是从小说中了解岳飞的,并且更多地把他作为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来歌颂,其愚忠思想反而降为次要地位”。
《说岳全传》中大鹏鸟转世、铁背虬、女土蝠报冤、赤须龙临凡的神话设置所涉及的因果报应,学术界历来是持批判态度,如上文所述,即使对《说岳全传》整体艺术水平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对这一点也颇有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说岳全传·前言》对此的论述更具代表性:“……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以因果报应之说统贯全书……不仅荒唐可笑,更严重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意义。编定者用宿命论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其目的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世情纷乱,起因结果,冥冥中自有安排,只要安于现状,不怒不争,静候命运的摆布就是,书中这些明显的糟粕,是应予以严肃批判的。”其它类似的论述尚有许多。但胡胜的《〈说岳全传〉中的“因果报应”辨析》一文却独辟蹊径,从民间果报观念、艺术建构等方面揭示了此段因果报应设置背后值得深思的内蕴。胡胜首先分析了民间果报观念:面对现实世界中诸多令人迷惑的不公现象,人们无法给自己满意的答复,只好转寄希望于自己创立的神,试图通过神这一超自然的力量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并借此以调整自己失控的心理天平,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式的道德劝戒具有震撼人心的威慑力。胡胜认为:“《说岳全传》可以说是这种果报观念的最好衍绎,书第八十回开篇诗‘世间缺陷乱纷纭,懊恨风波屈不伸。最是公道人心在,幻将奇语慰忠魂。’道出了果报设置乃在于昭示公道人心,弥补人世间的缺憾,为岳王伸冤。小说第七十三回写秦桧、王氏及两代奸相同党在阴司中受苦,而岳王等忠臣义士都在仙府自在逍遥,表达了民众鲜明的爱憎”;“《说岳全传》中因果报应的实质,与其说是一种望梅止渴式的自慰,毋宁说是现实伦理世界的折光”。另外胡胜还认为从艺术建构上讲,这段因果报应贯穿全书,使得整部小说的意境奇幻相生,扑朔迷离,也起到了动人视听的效果。胡胜着眼于《说岳全传》体现出来的普通民众的朴素的情感与善恶观念,对读者理解其中的因果报应、宿命等设置颇具启发意义。
注:
① 郑振铎《岳传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② 李厚基《读〈说岳全传〉》,《光明日报》1956年4月22日第1版。
③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0页。
⑦ 罗书华《中国传奇喜剧英雄生成考辨——牛皋、程咬金、焦廷贵》,《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⑧ 赵文光《古典历史小说“鲁莽”英雄形象特征及美学意蕴》,《美与时代》2003年第5期。
⑨ 孙长明、许海丽《牛皋福将形象的成因初探》,《语文学刊》2007年第17期。
⑩ 王立、冯立嵩《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