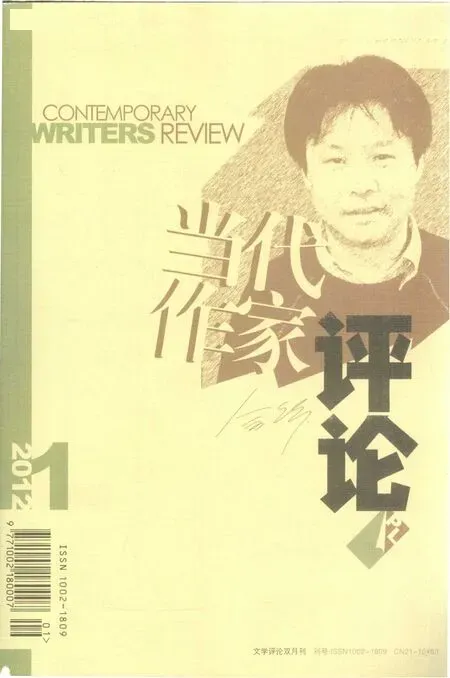“二十一世纪的先锋派”——蒋一谈短篇小说三人谈
2012-12-17杨庆祥
杨庆祥 刘 涛 徐 刚
“二十一世纪的先锋派”
——蒋一谈短篇小说三人谈
杨庆祥 刘 涛 徐 刚
一、如何界定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创作
杨庆祥:在短篇小说集《鲁迅的胡子》和《赫本啊赫本》出版以后,蒋一谈成为当下文坛被广泛关注的一位“黑马”式作家。蒋一谈的出现带有传奇色彩,九十年代初,他写完三部长篇小说(其中《北京情人》非常畅销),之后有长达十五年的时间远离所谓的“文学圈”。但与此同时,他却在默默地积攒小说创作的素材,这种积累终于在这两年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二○一○年出版的《鲁迅的胡子》出手不凡,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再版数次,二○一一年的《赫本啊赫本》也赢得了高度的肯定。在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蒋一谈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家之一,即使一些批评家对他还不是太熟悉。
很显然,蒋一谈为中国当下文学提出了新问题,如何界定蒋一谈甚至是“蒋一谈写作现象”将会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蒋一谈出生于一九六九年,但在我看来,批评家惯常使用的所谓“六○后”、“七○后”这种作家代际划分在他这里是无效的。在蒋一谈的作品中,有显著的“先锋性”特质。在我看来,这种“先锋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界定,一个是历时性的角度,一个是共时性的角度。
从历时性看,蒋一谈的写作美学和写作姿态是对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超越,这一点我在后面再详细陈述;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蒋一谈作品的“先锋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第一,他的写作规划和作品传播方式。据我所知,蒋一谈的每一部小说集,甚至是每一个单篇作品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写作规划”,大到故事的创意,小到用词遣句,这可以称之“写作的发生学”。在传播方式上,蒋一谈没有按照惯常的“期刊发表——批评家认可——读者接受”这种套路,而走的“读者认同——圈内热议——期刊发表”这样一个完全“逆转”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第二,与蒋一谈的写作规划相联系的,是他鲜明的“文体”意识——即通过不同的故事创意和写作技巧将每一篇作品构建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并在这一世界里寄托与众不同的寓意。这是蒋一谈超出其同代作家最重要的地方,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这种“文体创新意识”,在短篇小说界尤甚。从这些方面看,我愿意将蒋一谈命名为“二十一世纪的先锋派作家”。
刘涛:迄今蒋一谈的生命轨迹有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由文学转入出版,最近则是由出版复入文学,而且较短的时间即已成绩卓著。蒋一谈的第一次转变,由文学而入出版,或许迫于经济压力,是为了解决其身体和经济问题;蒋一谈的第二次转变,由出版复入文学,这是主动的选择,是为了解决灵魂问题。
徐刚:实事求是地讲,之前我对蒋一谈不是太了解。这次读到他的两本小说集《赫本啊赫本》和《鲁迅的胡子》,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庆祥刚才的概括很有道理,结合蒋一谈的个人经历,他确实是“一匹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坛黑马”。蒋一谈本人早在九十年代曾经出版过比较畅销的长篇小说,可以非常轻易地成为一位商业写作者,但他显然志不在此。选择短篇小说这道“更窄的文学之门”,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年少时未竟的艺术理想,用刘涛的话说,是“为了解决灵魂问题”。他绕开传统文学发表模式,在“纯文学”的“场域”之外,建立新的“纯文学领域”,这对于当代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蒋一谈做到了心无旁骛的写作,真正的“自由的写作”。
杨庆祥:蒋一谈的身份是复杂的,李敬泽曾说:蒋一谈在写作和出版上都完成了一个欧美作家能完成的事情。蒋一谈的这种“复杂性”必须依赖于两个前提,一是个人对文学市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并能进行资本运作;第二是,他对有形资本运作的目的并非获利,而是为了获得“象征资本”(文学价值)。也就是说,“独立出版”虽然借助于资本化的经营和运作模式,却是为了产生一个“反资本”的审美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既创造了作品,也创造了新的写作姿态和美学观念。
据我的观察,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因为对个人情感和经验的过度依赖而导致了一种“自恋”和“憎恨”式写作,并由此呈现为一种极端的美学形态(血腥、暴力和阴暗心理)。从这一点来说,蒋一谈的写作是另外一个开端,这一开端开辟了在体制和商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刘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确立之后,全民皆商,读书人都往商走,但是商不往读书人走,往而不返,但商人难以担当领导社会之责任。蒋一谈开始是读书人往商走,走得差不多了,又由商往读书人走。就其目前的写作状态来看,蒋一谈的写作不再是为了谋生,他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再回过头来写作反而显得更为纯粹。有了经济的基础,安顿好了身体,那么才有闲暇,才有可能去思考更为深入的问题。
徐刚:杨庆祥刚才说的利用资本“反资本”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一位“六○后”的作家,蒋一谈的小说里有着明显的八十年代文学的余脉,他本人也深谙那种现代主义的技巧和对人性深度的体察,但他又全然没有八十年代文学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凌空蹈虚;另外,作为一位在九十年代商业化气息中走上创作之路的作家,他又自觉拒绝作为职业作家的商业化写作。蒋一谈的小说更多的是在流行的中产阶级写作中加入现代派技巧,或者是八十年代“诗化哲学”的“通俗化”,这无疑是一种双重的“逃脱”,既逃脱一种学院体制,又逃脱那种商业体制。至于这种“逃脱”是不是一种“第三条道路”,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讨论。
“第三条道路”也让我想到未来纯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们一般会将纯文学从商业写作中抽离出来,来讨论它的纯粹性。但实际上,像卡佛、麦克尤恩这样的作家,我们很难说他们到底是纯文学作家还是商业作家。因为他们虽然并不以大众阅读为目标,但其实也有着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也就是说,他们是瞄准固定消费群体的“商业化写作”,尽管这个读者群的数量不大,但也足够“供养”他们的写作。
我想蒋一谈的小说一定也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体,或者说正在培育更多的阅读群体。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个固定的读者群体也将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市场。
二、故事之“实”和文体之“虚”
杨庆祥:蒋一谈的每篇作品几乎都像一个浓缩了的取景器。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Chinastory》,这个故事取材于最普通的父子关系,却把这一父子关系置于“城乡区隔”的背景中,朴素的故事中蕴藏着切肤之痛。这是蒋一谈小说非常有魅力的地方,任何一个年代出生的人,都能联想,都能读出“现实生活的实感”。我曾经让一个本科生在课堂上分析《Chinastory》,她毫不讳言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多位学生也告诉我了相同的感受。
蒋一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我看来,这里涉及到“故事”和“文体”的辩证关系。蒋一谈作品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与大多数人的距离很近,但另外一方面,他的故事创意和讲述故事的方式变化多端,更有戏剧化的效果,这种把“生活的实感”与“高度的形式化”结合起来的小说作品,我认为达到了当前短篇小说写作非常高的境界。我在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芭比娃娃》、《七个你》、《赫本啊赫本》等短篇里面都读到了这种惊喜,也看到了他不重复自己的努力。
刘涛:杨庆祥拈出“实”与“虚”两字,我觉得是理解蒋一谈的关键词。蒋一谈迄今的三个短篇,分别名为《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这是三个短篇小说,只是蒋一谈以这三个短篇的名字命名了整部集子。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是旧人,于现在而言是虚,然而三篇小说皆是写实。
蒋一谈擅长借气,他借了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之气,可是他未停留于此,而是以虚写实,写了当下。譬如《赫本啊赫本》写了父女之间的关系,写了参与越战老兵的心态等等;《鲁迅的胡子》则写了城市中产阶级或学者的生活状态等,也带出了时代的巨变。建筑中有一个术语叫“借景”,譬如在一座园林,周边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小山隐隐约约的,既是园林的一部分,又不是。园林因为小山而活泼起来,小山也因为园林鲜明起来,两者彼此借气,彼此衬托。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之于蒋一谈的小说,就如同那座小山之于园林,似是而非,似非又是。蒋一谈能虚能实,以虚写实,又能以实见虚,因此蒋一谈的作品才能够立起来。
蒋一谈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他要为其好奇的人物各写一篇短篇小说,这个谱系是:“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孔子、苏菲·玛索……还有孙悟空”。解析蒋一谈所喜欢的这个谱系,大体上能够见出其志向与抱负。这些人在不同的层面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伊斯特伍德、赫本、苏菲·玛索是影视演员,这与时尚有关,这些人不复杂,能够一眼看穿;鲁迅再进一步,更为深厚;孔子则更进、更进很多步,他与天地齐寿,日月同辉。蒋一谈希望能够从他们之中取得气息,一方面可见其希望在空间中胜出,成为时尚(伊斯特伍德、赫本、苏菲·玛索);另一方面也可见其希望在时间中胜出,可以成为经典(鲁迅、孔子)。时尚与经典其实可以不矛盾,只是时尚的力量不够,往往只能流行一时,但经典则会长盛不衰,流行于时间之中。
徐刚:乍一看这几个标题,《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还以为蒋一谈要重写历史人物的故事。读起来才知道,历史人物只是“引子”,一个别开生面的“噱头”,他写的还是寻常人物,是包含着“生活实感”的“朴素故事”。刘涛用“借气”和“借景”谈论蒋一谈小说中的“虚与实”,我觉得很有意思。鲁迅也好,赫本也罢,他们如同《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小点心”,能够让人回想起某些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人生充满苦痛,我们有幸来过”,这是小说集《赫本啊赫本》扉页上的一行文字,小说本身也确实在“朴素的故事中蕴藏着切肤之痛”。刚才庆祥谈到“生活的实感”和“高度的形式化”,这是对蒋一谈小说内容和形式的一个概括,这让我想起鲁迅对自己小说的一个判断,用在这里也是合适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蒋一谈的小说写城市情绪,写移民问题,写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都是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却也有着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比如《中国鲤》写移民问题,却是用一个包含着“套层结构”的故事框架来表现;再比如《芭比娃娃》这个小说,单从故事层面来看,这是绝好的有关“底层文学”的素材,毕竟,“苦难”与“性”是这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文学话题。然而小说却并不瞩目于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人物苦难的煽动性,而是处处表现出平实和内敛,避“实”就“虚”,抓住故事本身的抒情性。小说结尾,两个顽强的小女孩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彼此温暖的契机,“小小的身影在北京郊外昏黄的小街上越拖越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杨庆祥:谈到小说的文体问题,我在蒋一谈的作品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它的小说文体实际上是具有“综合性”的,也就是借鉴了其他艺术的形式。《鲁迅的胡子》的开头非常有镜头感,我最早在“二○一○年文学高端论坛”上已经谈到这个问题,《鲁迅的胡子》有很多话剧的元素,比如“道具化”,我觉得《鲁迅的胡子》如果改编成话剧将会很成功。《赫本啊赫本》通过“信件”的方式展开叙述,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剧本。《中国鲤》是篇非虚构作品,很多人知道这个美国人追杀中国鲤鱼的真实新闻事件。《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创意点直接取材于吴冠中的传记作品《我负丹心》。
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文体在蒋一谈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一切都可以成为小说,就像博尔赫斯所言“诗歌可以是一切形式”。
刘涛:文体问题并非纯粹的形式问题,透过蒋一谈短篇小说中“综合性”元素,可以追溯其思想资源。庆祥发现蒋一谈小说中的镜头感,这或许是因为蒋一谈曾看过大量的电影,电影或许就不自觉地进入其小说创作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公共体裁,现在影视蒸蒸日上,小说日薄西山,很多作家谋求将小说改编为影视,这是希望从过气的体裁转为时尚的体裁,背后的动力恐怕还是出于经济原因。
徐刚:小说的形式感,是现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问题。我注意到蒋一谈还写作过许多篇幅极短的小品文,《骑者,且赶路》、《一只会说话的狗》等篇什,如散文诗一般,韵味无穷。他本身还是诗人,小说中包含着诗歌的韵味,很有嚼头。《鲁迅的胡子》中包含有很多话剧的元素,包括其小说文体的“综合性”,我也非常认同。蒋一谈写人物对话特别多,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对话,但大都非常简洁,让人想起从海明威到雷蒙德·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他整个故事的处理,情感的把握,有着非常浓厚的卡佛的味道。我相信,蒋一谈如果写剧本,又会是一个很好的剧作家。
杨庆祥:刚才我们谈到蒋一谈短篇小说与电影、话剧甚至与散文诗的关系。我突然想到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综合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文体的“通约性”。今天小说改编成电影和话剧似乎越来越容易,这一方面固然是刘涛所谓的“时尚体裁”对于传统文学体裁的“侵略”;但另外一方面,这是否也是一种新的写作的开始?
这种写作,不再固守某一种“体裁”的边界,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各种体裁的元素熔铸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这一文体,已经无法用“体裁”来涵括,而只能以作者来命名。这可能是蒋一谈努力的一个方向,在蒋一谈认同的那些短篇小说大家那里,如卡佛、耶茨、汪曾祺等,似乎也有这种倾向。
刘涛:文体的文体不是文体问题本身,这里涉及到名与实的问题,但关键还是看作者能量的大小。若作者能量足够大,知道“实”,且能于各种文体娴熟,当然就可以随物赋形,当语则语,当默则默,当散文即散文,当小说即小说,当戏剧即戏剧,当诗歌即诗歌。
大作家可以在诸多文体中出入无疾。但是若无实与物,只玩所谓体裁、跨界云云,则会流于空洞,弄巧成拙。庆祥注意到蒋一谈文体的“综合性问题”,这是一个信号,一方面可以见其知识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一谈未来的文学世界足够大。
徐刚:我注意到汪曾祺是蒋一谈所提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汪曾祺是不折不扣的“文体家”,他的小说曾经让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蒋一谈的小说也给人不拘一格的感受。像《七个你》这样的“实验性”写法,既时尚,又先锋,确实形成了一种独特文体。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影响的焦虑”的问题。在当今之时,流派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已经没有了,转而成为文学的基本技巧和表达。甚而至于,连传统意义上的“体裁”也界限模糊了。“跨界”也好,“综合”也罢,都是缘于一种创新的冲动。
三、“我手写他心”
杨庆祥:在《赫本啊赫本》的后记中,蒋一谈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写作观:我手写我心,是写作的一个层面;我手写他心,是写作的更高层面。我记得在《赫本啊赫本》的首发现场,有作家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更高的层面还应该是“我手写我心”。
我赞同蒋一谈的写作观。在我的观察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很多作家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经验型”的写作,这种写作在八十年代一度因为对于意识形态和集体经验的抵抗而获得了有效性。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经验”被高度“私人化”,写作的格局越来越小,气度越来越封闭,这实际上就是“我手写我心”的一个局限。要跳出一己的经验,写“他心”,这“他心”实际上就是他者,就是写一种关系——历史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文学观念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所谓的“纯文学”的一个“超克”。①“超克”这一概念来自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书,所谓“超克”是超越、克服的意思,指的是日本(东亚)对欧洲近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抗。我在这里使用“超克”是为了强调蒋一谈的写作与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写作之间构成的某种紧张的富有张力的关系——杨庆祥注。
刘涛:蒋一谈提出“我手写他心”,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观念,也能见其境界。“我手写他心”以佛学言之就是“他心通”,但是能做到“他心通”颇难。一般人只关注自己,很难放掉一点自己去关心别人。
《金刚经》有所谓“我相”,孔子有所谓“毋我”,“我相”减少一些,“毋我”持续时间长一些,这个人的程度就会高一些。杨庆祥说蒋一谈这样的文学观念是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超克”,我觉得很好。八十年代承续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而来,此前因为中国一直处于颇为危险的境地,外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又有苏联的压力,内有台湾的压力等等,其时大家惟有大公无私,摒除私心,团结一致,这个国家才有向心力,才能同心同德,如此才有生存的可能。因此,那个时候讲“我们”多一些,讲“我”少一些,关注集体多,关注个人少,但是一般人就是只关心“我”,生硬地让他们舍弃“我”,去关注“我们”,这势必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八十年代之后社会风气一变,“私”的地位确立了起来。
在文学领域,纯文学、先锋文学等等思潮都强调“我”,“我”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关键词之一。在起初,这样的文学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展现了新时代的风气与特征,可是时间长了,这种“恋人絮语”、这种窃窃私语会让人烦,而且屡屡言“我”如何如何,境界也不高。就是点个人的伤痕,个人的喜怒哀乐,个人的小情调,这些能算得了什么呢?比如北岛,这个一度以写“我”而声名鹊起的作家,直到现在还沉浸在八十年代的氛围中难以自拔,他最近的《城门开》还是写自己的那点经验和感伤。
蒋一谈提出“我手写他心”可以纠正一下八十年代文学之偏,因为“我”之所知与所得终究有限,除了看看“我”之外,更应该看看“他”,看看别人的处境与社会的问题。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代也过去了,新世纪来了。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涌现出非常多的问题。作家们不能还沉浸在八十年代,而对九十年代之后的诸多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一个作家若能触到这个中心问题,那么这个作家起码在这个时间段内会繁荣昌盛。
蒋一谈这几年写下的很多短篇小说,确实实践了“我手写他心”的观念,他写了很多不同人的处境,触及到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比如“八○后”在城市中的困境(《Chinastory》),比如移民问题(《中国鲤》),比如底层问题(《芭比娃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问题(《夏末秋初》),夫妻关系问题(《清明》),传统失落的问题(《刀宴》),青年身份迷惘的问题(《七个你》)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蒋一谈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一把钥匙,他要由这把钥匙打开中国的大门,打开现实的锁,让我们知道现在时代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徐刚:“我手写他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大概有一个简单的脉络:从“集体的故事”,到“个人的故事”,然后再到“他人的故事”。
“集体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所预设的神话机制;“个人的故事”又有着梦呓般的私语,个人的小情调,格局太小;也许只有到了“他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才是更为“纯粹”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我手写他心”比“我手写我心”有着更高的层次,同时也是如两位所说的,这也是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超克”,“纠正一下八十年代文学之偏”。只有从八十年代文学那种“自我”的小天地中走出来,才能迎来一片开阔的天地,进而探索文学无限的可能,书写“历史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他人的故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对时代转型中小说家位置的判断。用卢卡奇的话说:“在这孤立而抽象的观察中,生活仿佛是一道一直向前流去的水流,仿佛是一个单调、平滑、没有结构层次的平面。”在这种“千篇一律”中,“艺术表现堕落为浮世绘”。每一位作家都“堕落”成这个时代的观察者,而非历史的参与者,写作也开始趋向于迷恋“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在此之中,叙事被处理得像绸缎一样光滑,阅读的快感在于一种“平庸的快乐”。于是,在这个叙事泛滥的年代,以自我约束的方式“写他心”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蒋一谈写的是现实,写的是“他人的故事”,以其小说才能和独有的素材来看,完全可以将现实的“浮世绘”描写得比他人更加精彩,为这个热闹的文坛增添更多的“平庸的快乐”,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我手写他心”,其小说直指的是当下中国的“世道人心”。像《Chinastory》、《金鱼的旅行》、《公羊》、《枯树会说话》等,这样的故事对心灵的探索是极为深入的。包括那篇《赫本啊赫本》,虽说“移植”了美式越战文学的悲情,但对人情、人心的开掘显示出了不俗的艺术功力,堪称“中国式越战小说”的奇葩。
杨庆祥:诚如两位所言,蒋一谈的“我手写他心”像是一位智慧作家的禅宗式顿悟,其背后饶有深意。刚才谈到这一写作观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超克”,实际上是把蒋一谈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谱系中来讨论的。我还想补充的是,如果蒋一谈有这种“历史意识”,则是与他强烈的“当下感”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于当下中国发生着的一切近乎偏执的热爱和观察,才有了蒋一谈这种具有“历史意识”和“现实感”的写作。
他人的故事归根结底是自己的故事,这个自己,不是蒋一谈本人,也不仅仅是你我。这个“他者”,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其实是一群“沉默的灵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蒋一谈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对话很多,但是却都面目含糊——他们是一群缺少清晰面孔的中国人。蒋一谈通过他的短篇小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当此时代,如何来书写中国人的故事,给这些没有灵魂的人画出灵魂,从“无”中召唤出“有”?
刘涛:一般而言,大部分作家的作品皆是自传。写“我”一般是作家的首选,关键的是不要“自恋”,陷入自己的小经历和小悲欢之中,若能“切问而近思”,由“我”亦能见出时代的消息,也能走上去,走出去。“仁”字还有一种写法,上面一个“身”字,下面一个“心”字,这涉及到个人的身心问题,若能走通也可以成“仁”。
蒋一谈的小说人物“面目模糊”,庆祥的这一发现非常精彩。蒋一谈的“他心”是我心、你心、他心,但又不仅是这些。因为蒋一谈抓住了当下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有关,与你、我、他都息息相关。
徐刚:确实如刘涛刚才所说的,蒋一谈抓住了当下的一些问题,他的小说极具“当下性”。他甚至以近乎玩笑般的戏谑口吻写到了当下中国发生的一些焦点事件,比如“三峡移民”、比如“微博事件”等等。当然,这都不是最关键的。在我看来,他所重建的“当下性”恰恰在于写出当下中国人的情感诉求,这里面涉及到移民问题、城乡问题,家庭伦理问题,等等。李敬泽在评价蒋一谈的小说时曾谈到,当代作家写不清楚二○一一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又让我不得不谈到莫言的创作。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莫言体”的小说形式,即所谓的“当代史”加上一些现代派技巧。《生死疲劳》中的“土改”加上“六道轮回”,《蛙》中的“计划生育”加上“书信”,皆是如此。尽管这些小说写得精彩纷呈,但从中却看不到某种“现实感”。而蒋一谈的贡献其实恰恰在于重建小说的“现实感”,他通过几个简单的故事,“我手写他心”,便试图描摹出当下中国人的“灵魂”。
杨庆祥:我想再谈谈《Chinastory》这个短篇,我以为这个小说具有寓言的结构,这么说似乎回应了杰姆逊的经典论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书写,无论采用多么主观的形式,都不可避免是民族国家的寓言。但《Chinastory》这个短篇至少是在一开始就暗藏了某种质疑,寓言不仅是寓言本身,同时也是寓言的解构和反面。在这个作品里面,中国故事的讲述是借助英语这一强势殖民语言来完成的,而在故事的结尾,当中国父亲和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供职于外语杂志社的中国儿子完全“误读”的时刻,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国故事书写的迷途不仅存在于中国与西方的纠缠,同时也深深植根于我们意识的内部?或者说,书写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调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更需要调整中国内部的结构(城乡结构、资本结构、教育结构、语言的结构)?蒋一谈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短篇,同时还有《七个你》、《芭比娃娃》等触及到了一个历史的敏感点:必须从我们的根部开始重述中国故事。
刘涛:杨庆祥对《Chinastory》的解读非常精彩。蒋一谈小说有一个母题就是写农村人通过读书或通过打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母题或许与蒋一谈自身的经历有关(他出生于外地,之后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而且也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譬如《枯树会说话》言打工者回乡所见之故事,《公羊》写城里工作的儿子与乡下母亲的故事,《鲁迅的胡子》也涉及到城市工作的儿子与乡村父母的故事,《金鱼的旅行》也写城市中工作的儿子与乡村父亲的故事。《Chinastory》亦属这一故事系列,只是《Chinastory》以父亲为主,写刚留在城市中工作的儿子的处境与留在乡村中父亲的处境。
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国大体上走农业养工业,农村养城市之路,工业与城市的发展大体上建立在对农村的剥夺之上,可是这种供养与流向是单向的,城市却没有反哺,因此农村日益凋敝。二○○○年前后,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才逐渐引起决策层注意。《Chinastory》写出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儿子与父亲极有隐喻性,乡村好比这个父亲,父亲的一切都供养给了、寄托给了儿子,父亲最终轰然倒下,可是谁来救救父亲?这就是蒋一谈总结出来的“Chinastory”。
蒋一谈的文学抱负很大,他将宏大叙述寓于一个普通的小故事中,他写这对父子意在理解“中国”: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杨庆祥和我都比较喜欢这篇小说,或许与我们的经历有关,我们都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读书,然后毕业工作,现在不得不面临买房的压力,所以容易引起共鸣。
徐刚:我也是来自农村的,城乡关系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看得出来大家对《Chinastory》的喜爱,这个小说体现了乡村(或小镇)与都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当下中国“快车道”的发展之路来看,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故事”。包括《公羊》、《金鱼的故事》等,都写到了小镇或乡村的父母老人们,这是生存之根,也隐喻着中国并不久远的过去。而小说的叙述也在于如何弥合和抚慰“过去”与“现在”的“裂痕”。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关情感的创伤和寻找心灵慰藉的故事。这里面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时代变迁的印记,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体现人物内心的变化,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底层文学”。
这么多年来,“底层写作”实际上是过于外在化的,文学叙事已然成为历史变迁,阶级变动的注脚。然而,如何深入到底层的内心世界,却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蒋一谈的小说,会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Chinastory》的结尾,几乎一页的篇幅,写满鹩哥惊恐的鸣叫“Chinastory”,而全篇始终在对话和白描,写得深沉和内敛,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孤寂。整个故事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被不动声色地写了出来。同样,作为“底层文学”的《芭比娃娃》也与当下的“底层文学”大异其趣。当然,蒋一谈更多写的是城市,写国家的基本单元——家庭的故事,这也是更为内在的故事。
杨庆祥:感谢刘涛和徐刚对蒋一谈小说进行的精彩发言。对于蒋一谈这样一位在一开始即显露出不可替代性的作家,这种读解显然只是开始。据我所知,蒋一谈新的短篇小说集《栖》正在创作中,这是一部以城市女性为主题的小说集。这既是对当下中国生活的一个积极回应,也是蒋一谈对既有写作的一个突破。我们有理由对蒋一谈抱有更多的期待!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涛、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
(特邀编辑 陈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