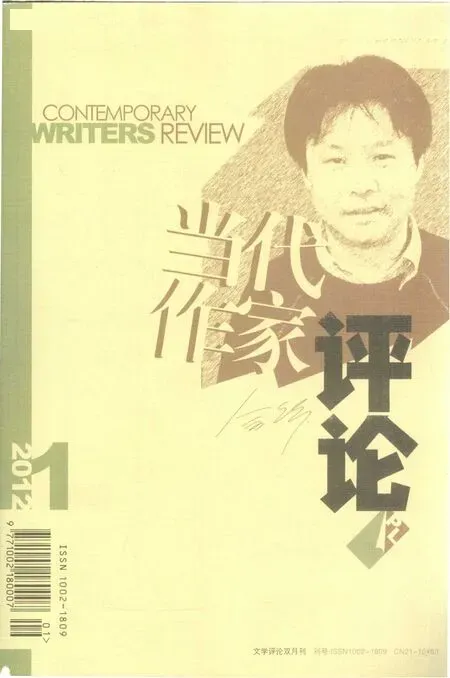一九四〇年代文学转型的另一种形态——以中国新诗发展为例
2012-12-17许霆
许 霆
胡玉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①胡玉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精细地分析了一九四〇年代初“随着革命中心向延安的转移,革命文学也被拉入到一个新的生长环境和运行轨道”,从而实现了文艺的话语立场、话语方式和作品形式的变革,这种转型和变革与“解放”、“革命”等历史话语,以及中共创造新世界、新历史的终极目标紧密相连。我完全认同胡文的分析,其实这也是学界早就形成的共识。我读胡文想到的是另一问题,即就文学转型来说,一九四〇年代初另有一种形态往往被人忽视,其实那一形态同样对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它同前种转型相比并非处于中心地位罢了。这里,我就以一九四〇年代初新诗转型为例来予以说明。
一
一九四〇年代初,抗战的大众诗歌和解放区的诗歌获得了新的发展,占据诗坛主导地位。其历史的必然性正如朱自清所说,“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②朱自清:《抗战与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45-34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这可以视为新诗的进步,诗人的进步。但是在看到这一现象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另一重要现象,这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聚集在四川的文艺界人士多次召开座谈会探讨新诗的发展问题,并开始对纯诗化和大众化两大诗潮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大家认为两者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都存在明显的缺点。与此同时或稍后,一批诗人发表意见对抗战以来的大众诗歌进行反思。这里列举数例。老舍在《抗战文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大概是因为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地,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原故,乃更关切于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专家和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深度。”①《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这段话值得注意。第一,老舍揭示了抗战初期应急的宣传式创作存在的合理性;第二,老舍指明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创作加深文艺的深度、放弃原有宣传的必然性;第三,老舍指明文艺存在两种倾向,一种继续追求短期效用,一种是加深文艺深度,而后者应是主流。这种概括代表了当时部分人的见解,也为后来抗战发展的事实证明。黄药眠指出:“一九二七年末,左翼的诗歌运动虽然在意义上把握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诗人们大都是首先从概念上去认识革命,因此,他们的诗多数成了革命的空喊。”至于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他们的世界是相当狭小的”,“单调狭隘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忧郁、伤感,陶醉在幻想的世界里”,“到了最后,不能不造成诗歌创作源泉的枯竭”。②黄药眠:《论诗》,桂林,桂林远方书店,1944。力扬在《我们底收获与耕耘》中认为:“这两支河流,也不像长江、黄河一样,南北分流,丝毫没有脉息相通的地方,而有许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交点。”在反思的基础上,切实改变抗战以来诗歌忽视艺术的局面,综合五四以来新诗优秀传统,形成全新的新诗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归,这就带来诗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一批诗人倡导冷静沉炼的创作风格,鼓吹融合纯诗化和大众化的“综合传统”理论。这相对于过去的诗歌发展来说是一种重要转型。
出现这种转型有着必然的客观社会原因和新诗发展规律。就客观社会原因说,就是抗战发展到相持阶段,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为人所认识,文学为抗战的短期效用追求渐渐冷下来,通俗化也自然降了温。在这种情形下酝酿着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的变革。这里再举两位评论家的概括。一是郭沫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的暴风雨似的刺激使作者们狂热,兴奋,在文艺创作上失却了静观的态度。特别是在诗与戏剧上,多少有公式化的倾向,廉价地强调光明,接近标语口号主义。等到战争时间延长,刺激就渐渐地稀微,于是作家们也慢慢重返静观,在创作上有较为周详的观察,较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因此风格与形式,抗战初期和现在有着显著的差异。”③郭沫若:《1941年文学趋向的展望》,《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另一是胡风的:“从武汉撤退开始,战争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候,‘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过程是艰苦的’,才渐渐由理论的语言变成了生活的实感。人民底情绪一方面由兴奋的状态转入沉炼的状态,一方面由万烛齐燃的状态转入了明暗不同的状态。人民底意志一方面由勇往直前的状态转入了深入分析的状态,兴奋生活开始变为持续的日常生活了。”“诗人底情绪渐渐由兴奋达到了沉炼。不是一碰就响,须得在生活对象里面潜流,酝酿,因而诗人底战斗欲求一方面和具体的对象结而为一,于是,把热情潜伏到具体对象里面,把思想融进了生活实感里面的抒情诗发达起来了,一方面不得不借助逻辑思维的力量,在生活底发展里面探索前进。”④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诗全编》,第72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想要强调的是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抗战文学包括新诗创作和观念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就是加强文艺深度的冷静、沉炼。由此变化而引起的,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深化,出现了在纯诗化和大众化基础上融合的“综合传统”论,并在“综合传统”论推动下的新诗转型发展。
就新诗发展规律说,新诗发展到一九四〇年代初已经有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纯诗运动的传统,其诗学追求可以概括为:在艺术对生活的审美上主张疏离或超越现实,在抒唱对象上转向内省,在表达上重视玄思和意象化,在表达上追求朦胧美风格,在诗语上追求精致的陌生化。这种追求把新诗艺术推向新的高度,并汇入世界诗歌发展大潮,但其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与一九三〇年代风云激荡的时代、交织着血与火的生活、平易通俗的战时大众文学所定下的基调相去甚远。另一是大众诗歌运动的传统,其诗学追求可以概括为:在诗与生活关系上主张面向生活,把握现实斗争;在诗的表达方面要求明白晓畅,直接鼓动人们投入现实斗争;在诗语形式方面主张面向大众的通俗,采用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民族形式。联系特定的社会情势看,大众诗歌的出现具有合理性。当然,其中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理论上“通俗到不成艺术都可以”的主张,更是潜存着新诗发展的危机。因此,稍后的唐湜认为当时中国存在“一个使人焦虑的问题”,即“一方面要设法继承中国传统(活着的生活、活着的人与风格的传统),继承传统的中国气派与精神,一方面又要设法接受最进步的世界新传统”。①唐湜:《辛笛的〈手掌集〉》,《新意度集》,第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这里正面呼唤着把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传统予以综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两股诗潮的长处,摈弃两股诗潮的缺陷,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这就带来了诗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新变。
二
冷静沉炼的创作风格和综合传统的诗学观念,引来了诗坛的新变,诗坛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的诗。朱自清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新诗杂话》中,说有两类诗,一是象征派的诗,一是社会主义倾向的诗,明确指出:“就事实上看,表现劳苦生活的诗与非表现劳苦生活的诗历来就并存着,将来也不见得会让一类诗独霸。那么,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包,放弃正统意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②朱自清:《新诗杂话·新诗的进步》,《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21页。他以这种观念,在《新诗杂话》中评论了新诗诞生后重点是抗战后新诗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体现了综合包容性的大家风度。
更多的诗人则探索把大众诗歌和纯粹诗歌的传统进行综合,具体表现为走现实主义道路的诗人,注意艺术地反映和把握现实,操纵现代主义手法的诗人,则注意突出现实,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代表这种综合趋向的就是其时诗坛两个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一是以胡风和艾青为代表的七月诗派,另一是以袁可嘉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两个诗派的外在倾向有明显差别,但是它们在抗战后面对新诗大众化诗歌主潮的深层次矛盾,有着相似的选择,都在那一年代保持着综合的追求和自身的独立,形成一个互补结构,为中国新诗和诗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两个诗歌流派的共同趋向就是新诗现代化。朱自清认为新诗在一九四〇年代存在着一个“新诗现代化运动”,这一运动基本体现在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追求之中。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中把七月诗派喻为“崇高的山”,“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把九叶诗派比作“深沉的河”,是“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两个诗派是两个高高的浪峰,由这两个高峰组成了一个“诗的新生代”,体现了新诗在一九四○年代另一种转型的实绩,体现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实绩。这种坚持“综合传统”的诗学与诗派出现,体现着新诗自身发展规律,同时也体现着诗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自觉地同时承担起社会历史责任和建设新诗艺术责任,并努力把两者结合起来,开辟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两个现实责任的“结合”和两种诗学传统的“综合”,形成了两个诗派的独特面貌,凸显着“综合传统”诗学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标志着新诗的一次转型,而且直接影响到建国以后新诗的发展。由于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存在,使一九四○年代新诗的另一种转型形态成为文学史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现象。
就诗学倾向说,七月诗派既反对离开现实的故作高雅,也反对急功近利的创作动机。胡风在《七月》半月刊创刊号《代致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中,一方面表示反对新月诗派的“形式的制约”和现代诗派“以形式来挽救内容的空虚”,说“这些,在战前是存在的,但战后大半消失了。因为是无法表现今天的情绪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示反对新诗创作的概念化倾向,说“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要求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底心,否则只是概念式或观念式的东西,只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而已”。①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胡风诗全编》,第613页。曾卓为《胡风诗论》作序指明,“针对这两种倾向的美学上的斗争,一直贯穿在他所有论诗的文章中”,认为胡风的诗论“既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强调诗应该表达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同时也强调‘诗首先应该是诗’(这是他引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对于什么是诗和如何达到诗,进行了美学上的分析和探讨”。②曾卓:《读〈胡风论诗〉札记》,《胡风诗全编》,第752页。在扬弃的基础上把新诗大众化和纯诗化综合起来,从而担负起时代社会使命和诗歌建设任务,是胡风诗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艾青认为:“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③艾青:《诗论》,《诗论》,第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强调了外界感觉、思想情绪和艺术表现的结合,其全部诗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七月诗人理论中有着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如人与诗、社会责任和诗人责任、主观与客观、力与美、形式与内容、情绪与形象、政治与艺术等,都运用综合的方式使之形成张力,从而完成诗学建构。七月诗人的创作把追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把现代派的“现代诗形”和艾青等人探索的“散文美的自由体”综合起来,并在战争环境中向着风格阳刚、崇高、壮美倾斜,从而建立了具有民族气派的自由体的成熟形式。其诗体特征一是突出抒情主人公,认为抒情主人公即诗人自己;二是诗的主体精神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将“具体形象”和“作者的心”融合起来;三是表达方式是现实主义真情实感与象征主义审美意象的结合,呈现半裸的抒情;四是采用散文美的自由诗体,努力使诗行定位“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
九叶诗人的诗论,同样是对于纯诗化和大众化的扬弃。袁可嘉认为以前的新诗有两个平行的毛病,即“说教”和“感伤”,其传统一个是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现实主义,一个是以法国象征派为首的欧陆现代主义。九叶诗人倾心现代主义,但试图根据现代诗人的处境和面临的课题进行修正,即以英美新批评为武器,接受艾略特、奥登等代表的当代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使诗歌批评、诗作主题和表现方法都“显出高度的综合的性质”。具体主张是新诗现代化,现实根据是现代人所具有的综合意识,核心是现实、象征和玄学的综合传统,表现方法是新诗戏剧化。对于这一诗派,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评价说:“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①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诗论》,第19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袁可嘉认为这一诗派“为新诗艺术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是比较蕴藉含蓄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②袁可嘉:《九叶集·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这都肯定了这一诗派实现两种传统综合的特征。后来的辛笛回忆说:“《中国新诗》更有意识地探索新诗现代化的审美理想,企图找寻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即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和谐地统一的可能途径……以上思路也构成了近年来所通称的‘九叶’诗人共同风格的诗学基础。”③辛笛:《怀念“九叶”诗友杭约赫》,《文汇读书报》1998年5月2日。九叶诗人自称是“民族的背剑者”(唐湜)和“中国人民的代言人”(辛笛),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面貌。唐湜撰写的《我们呼唤》是他们共同的诗歌宣言:“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我们都是人民生活里的一员,我们渴望能虔诚地拥抱真实的生活,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祈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④唐湜:《我们呼唤——代序》,《中国新诗》第1辑,1948年6月。“综合”使九叶诗派的创作与以前的现代派相比,有了以下重要变化:从寻找精神家园到突出人生现实,从情绪化到智性化,从意境化到戏剧化。九叶诗派在突进心灵的现实与突进生活现实的主题中,在理性和感性相融会的智性诗化与戏剧化表现中,形成了一种凝重、深厚、深邃、冷峻的创作风格。
三
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综合传统”,可以袁可嘉等为新诗发展寻求“一个新的出发点”来概括,这就是“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⑤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论新诗现代化》,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其中“现实”,就是“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的现实性”;“象征”,就是强调借助“意象”这一中介,使意象与抒情的结合更多地趋向意象与知性的融合;“玄学”,在九叶诗派诗中是敏感多思的知性,在七月诗派诗中是主观战斗的理性精神。“综合传统”直接针对新诗发生以来的两个重要传统,也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尽是反映现实,一个尽是躲进艺术,这显然都不符合诗歌表现“现代”复杂意识的要求(陈敬容),因为现代诗歌要求“最大量的意识活动的获致”,要以综合的性格去反映现代人综合而复杂的思维。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诗歌的共同趋向正是新诗现代化,其贡献就是使新诗更好地同世界诗歌发展主潮合拍,同西方诗艺传统接通,同中国现代人生紧密结合。这也就是新诗现代化的意义所在,也是一九四○年代由于综合传统论提出和实践所引起的新诗另一种转型的意义所在。
这样,中国新诗发展到一九四○年代就出现了两种转型的形态,即革命形态和综合形态,两种形态出现都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诗歌传统有关,都具有新诗发展内部规律的根据,也都体现了新诗面向未来蜕变的要求,因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两种形态的不同来说,革命形态是在解放区的空间中面向理想中国的想象性书写产物,而综合形态则是在沦陷区或大后方空间中面向新诗现代化构想的产物;革命形态直接反映现实,以融化自我的大众立场实现创作主体与历史实践的交融,参与新的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而综合形态艺术反映现实,强调以强烈的主观精神去拥抱现实生活,通过主观精神或主体经验的投注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革命形态强调通俗化和大众化,以此来形成民族气派和民族形式,达到诗歌启蒙思想和组织斗争的教育效果,而综合形态则追求新诗现代化,以此来形成具有包容性和戏剧性的现代诗体,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一九四○年代出现的两种转型形态,其实都在一九四○年代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对建国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影响。但是,两种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命运,由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体现的文艺思想,后来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所以一九四○年代后完成转型的革命形态就成为主流诗潮被充分肯定,而转型于一九四○年代的综合形态却始终被人忽视。因此,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阐明综合形态对于中国新诗的影响,把多年被遮蔽的事实揭示出来。
七月诗派是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以及《七月诗丛》等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艰苦岁月,经历了从上海到武汉到重庆、桂林等地,又到上海的颠沛跋涉。这一诗派拥有大量的新诗作品,拥有一支较为稳定的诗人群,如胡风、阿垅、彭燕郊、邹荻帆、冀汸、孙钿、绿原、牛汉、艾青、田间、天蓝、鲁藜、化铁、方然、贺敬之、杜谷等。鲁迅是这一诗派的精神领袖,胡风是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七月诗派呼应时代要求,“在最危急、一般的社会认识最混乱的时候,他们始终是确实认明了他们的任务与职责”。①欧阳凡海:《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七月》第7期,1938年6月。九叶诗派是一九四○年代中后期在上海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诗人从分散歌唱到集结形成流派,前后近十年时间。其名称既确指九位诗人,包括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祁、唐湜、袁可嘉和穆旦等,同时又暗含着那时一批年轻诗人,如马逢华、莫洛、李瑛等,在《诗创造》上发表诗作的有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包括卞之琳和冯至。这一批诗人利用刊物大量发表新诗创作、诗歌理论和翻译介绍外国诗歌,掀起了颇有声势的新诗现代化运动。此外还出版了两套诗歌丛书。一九四七年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创造诗丛”十二种,被誉为“轰动全国诗坛的一件盛事”。由此可见,两个流派在当时诗坛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诗歌大众化同政治化、民族化的潮流中,七月诗人和九叶诗人都试图坚守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试图综合各种矛盾、冲突的现实关系,开辟新诗发展的广阔境界。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却不合时宜,致使其在诗歌革命形态确立过程中受到抵制,结局可悲。就九叶诗派来说,在外界压力下产生分歧。《诗创造》的编辑方针是兼收并蓄,坚守知识分子立场,不向大众化、通俗化一边倒,引来责骂和批判,于是很快声明编辑方针有所变化。接着同人分化,新诞生的《中国新诗》站在现实与艺术之间两面有所兼顾。这个诗派处境尴尬,在一些批评家找来唯美的帽子以利招降或清剿下,只好走向自然湮灭。七月诗人如胡风等个性“鲠直”,甚至还比较固执,遭遇更加悲惨,在一九四○年代不断地受到批判。应该说,七月诗人和九叶诗人的探索不是完美的,但他们试图“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煎”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惜的是,那一年代没有给他们发展创造条件,从而阻碍了中国新诗多元探索的广阔道路。
但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趋向新诗现代化的综合形态诗歌,在建国以后仍然影响着新诗的发展。建国后很长时间是形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形态成为主流诗潮,综合形态的诗歌无法自由生长。但是七月诗人和九叶诗人仍有创作,胡风等的创作引来了更大的批判,终于被带上政治帽子而受到镇压。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一批诗人寻求新的突围,其诗论和创作同七月血脉相连,但很快受到压制。九叶诗人多数在建国后仍有大量创作,其创作后来由香港出版公司编成《八叶集》(一九八四)出版。尤其是一九七○年代末,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诗坛拨乱反正开启了多元探索时期。基本趋向是解构由延安定型,建国后发展到“文革”走向极端的革命形态,即诗歌政治社会模式。这种解构具有转折的意味,它把诗学和创作从服务政治格局中解放出来,努力接续新诗的优秀传统。而实践这种解构的是“归来者”诗人群体和朦胧诗人群体。“归来者”的主要成员是七月和九叶诗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白色花》和《九叶集》,宣告了两支劲旅的再生。此外还有一九五○年代成长起来而后遭受厄运的诗人。就其诗学说主要是倡导说真话,真实地反映现实和人生,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冲破僵化的思想禁区,倡导题材和形式的多元化;打破虚假欢乐和政治说教对新诗的统治,以挑战的姿态把悲怆的旋律和深度的人性引入新诗。它通过恢复和重建新诗优秀的历史传统为“文化大革命”后新诗创作找到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朦胧诗运动是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中的现代主义诗潮,一批年轻诗人是新的探索者,但其审美探索同九叶诗人存在着某种曲折而微妙的内在联系。郑敏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中说过:“几个年轻诗人在翻阅上半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集时,发现了灰尘覆面、劫后余生的四十年代的诗作,为之震惊,他们说:这些诗正是我们想写的,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开垦。”她认为:“如果将八十年代朦胧诗及其追随者的诗作与上世纪已经产生新诗各派大师的力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朦胧诗实是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库存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和收获。”许多朦胧诗人在自述中也坦然地认同这一点。通过以上叙述的两个诗人群体和诗歌创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其精神来说,接续了新诗诞生后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传统(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言说和方式),尤其是对一九四○年代较为成熟的诗学,即七月诗派的深化现实主义诗学和九叶诗派新的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归。这一时期的诗人通过拨“文革”语境和言说方式之乱,返新诗优秀传统之正,迎来中国新诗新的发展纪元。一九四○年代新诗转型的另一种形态,就这样成为一种优秀传统正在影响着新的历史时期新诗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只有当我们把以上线索梳理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新诗发展的演进历史面貌,才能正确评价新诗发展史上的诸多诗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