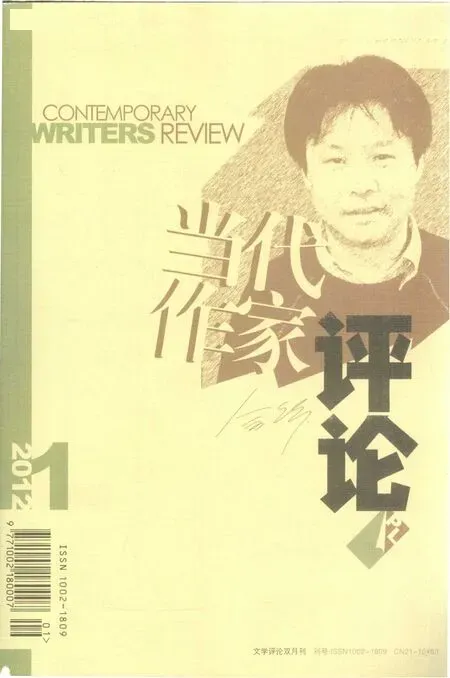文学与传统
2012-12-17格非
格 非
作家豪无疑问要处理当下的问题。对于当下的问题,作家作为社会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触须,当然会作出某种反应。今天我们谈传统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一直在断断续续思考这个问题。我自己经常想不通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传统?就是说什么时候传统会变得重要?从思想史来看,孔子当年的思想和言论,造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开端,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礼崩乐坏”。
确实,每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往回看,往后看。看看以前的历史进程,比如上溯到三代。这种往回看的传统,我觉得一直到明清,都是完好地持续下来的。比如孔子之后有司马迁,五百年之后必有圣人出现。司马迁之世,孔子去世差不多已经五百年了,需要有另一个人来重新观察、描述当时的时代和现实,正本清源。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里写得很清楚:“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到了唐代,“古文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排佛”,就是说,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一定的危机;宋代商业发展后也出现了新的危机,比如对于“汉儒”、汉学需要一个新的阐释,心学、理学开始兴起;一直到明朝灭亡,又开始出现这样的论调,就是说三百年后有圣人复起。就是黄宗羲、顾炎武一流的人,也喜欢往后看。
文化在痛苦中又重新回首过去,比如后来有很多人批评“宋儒”,认为他们对汉代儒学的解释错了。我发现,凡是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过去,这个局面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
从过去的文明史、社会发展里找到某种教训,寻找问题的症结,不断往回看,这是一个脉络。但是这样的情形,到了近代,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所承担的功能,它的影响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前一段在看日本人写的书——他们近代如何脱亚入欧,怎么离开中国的传统,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思想起点。在日本文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本居宣长,我最近在看他刚刚在中国出版的一本书,叫《日本物哀》。本居宣长很早就有意识地强调日本的传统,来区别于从汉学里、从中国接收的传统。他分析的主要对象就是《源氏物语》。他认为日本的文学传统是女性开创的,就是紫式部开创的。这个文学传统完全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有别于日本人过去的汉学传统。但“物哀”这个概念被本居宣长放大了。
再比如福泽谕吉,他写了一个《文明论概略》。他之所以要脱离中国的传统,并非简单地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孟子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不能适应近现代的变化,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挑战。如果日本不能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影响之下脱出身来,那前景会很悲观,会像印度一样沦为殖民地。当然福泽这个说法本身是很复杂的,也是有问题的。《文明论概略》也很复杂,但它直接影响了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我举出两个人的例子来讲,就是想说,不管怎样,日本在近代完成了传统的一个转换。我觉得整个东亚地区,这种转换完成得比较像样的恐怕只有日本。你很少听到日本人强调什么传统,因为他们的传统就在现实中延伸。过去日本人很重视“国学”这个概念,要知道,这个概念里边,也多少有一点与中国分道扬镳的意思。今天在日本,无人谈论国学,因为,所谓的现代社会转型,在日本已经完成了。
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或者也可以说,正在完成中。那么,在今天,每有风吹草动,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习惯往后看,甚至一直看到夏商周,习惯于去传统中寻找力量。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往后看,往回看,与明清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们毕竟有些不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情盘根错节,形成了很多的“小传统”。比如说从晚清到五四的现代启蒙运动,是不是一个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一个传统?再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算不算另一个传统?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新东西?要知道,这些新东西并不能很方便地放到那个大传统之中去。如果说,中国的思想界目前有点混乱,其实这也很正常。国家太大,历史太悠久,积累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资源太多。也就是说,即便是往回看,我们看到的东西已经很不一样,就好比一个广场,你没法跳过眼前的东西直接往远处看,因为堆积物的存在挡住了你的视线,你无法绕过去。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假装绕开这些东西,直接和古代的远方相连接,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当然,和古人不同的是,就算我们今天在面临“礼崩乐坏”的境遇,也不一定非得往回看,从传统中寻找力量。因为我们今天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往四周看。过去的中国一家独大,中国之外,并无世界。自己跟自己比的时候,未来并不存在,我们往往只有往后看。今天,我们却可以直接“往前看”了——跑在我们前面的是谁呢?我们能不能学学别人的样子呢?对于很多希望直接照搬人家制度的人来说,也可以说传统一点都不重要。
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文学与传统”这个题目时,必须了解到两个基本面:首先,传统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其嬗变的复杂存在;其次,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传统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当然,这两个问题都很复杂,我这里不再展开。
那么,在文学上,我个人如何看待传统这个东西?我倾向于认为,你只要浸润在一种文化之中,传统是无论你怎么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谓的与传统对话,恰恰不是到古代文化中去寻章摘句,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上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只有当你的写作迫使传统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与传统的对话关系才会真正建立。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与传统的对话,其实根本无从谈起。古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