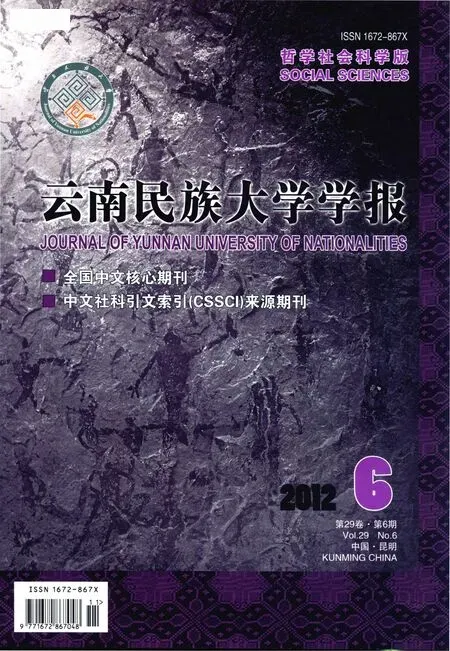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概念、分析要素与价值立场
2012-12-08王旭辉
王旭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规模和影响都持续上升。同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形态、参与主体和利益指向也日渐多元化,并成为影响我国利益分配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成因和治理对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关心的一个重要现实及理论议题。
客观来讲,国内外学者已就我国群体性事件展开了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但截至目前,学界在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概念界定、分析要素阐释以及价值立场定位上却存在明显分歧,限制了相关研究议题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将从“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1]两个角度来系统回顾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并重点通过对已有群体性事件研究中核心概念、分析要素以及价值立场的梳理和反思,来为后续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
目前,“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虽然已被普遍接受,但研究者在其概念内涵及范畴界定方面却存在明显分歧。实际上,有关“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的争论是制约这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
“群体性事件”及其类似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使用。“群体性事件”最初并非一个规范的学术或法律概念,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治安管理或行政管理术语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并常常与“突发性事件”、“突发性抗争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治安事件”等概念混用。进入21世纪之后,“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才普遍被官方、学术界、大众媒体所使用[2]。
概括而言,目前国内研究者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是“治安事件”说——“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3],这一概念界定强调其非法性和秩序破坏性。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因而通过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和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的群体上访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4],这一概念界定着重强调其非对抗性及非政治诉求性。第三种是“突发事件”说——“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的利益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与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或活动”[5],这一概念界定强调其短暂性和突发性。第四种则是“广义群体性事件”说——“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6],显然,这一概念界定强调其多元性及动态性。
与此相应,在应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展开分析时,不同研究主体对其概念内涵及范畴界定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外延模糊的“类型”而非概念,“群体性事件”可以被描述,但却无法被明确界定[7]。大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在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相关研究时,会普遍遭遇这一概念的“官学之别”、“中西之辨”问题。
一方面,虽然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已普遍接受“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但却在如何界定群体性事件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政府部门、公安政法院校研究人员多从便于定性和管控角度,主张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狭义界定,并在一定意义上认为“群体性事件”就是“群体性治安事件”或“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简称,以强调其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及偶发性。但与此相反,相当多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从广义层面、中性立场甚至是积极角度来对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以便于使其涵盖集体维权行为、集群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多种范畴,具有正负功能两个面向,并突出其在现有制度或体制背景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虽然可以将“群体性事件”翻译为Mass Incidents,Mass Event,Collective Event,Group Event,Mass Group Incident等英文词汇,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在强调“集群行为 (Collective Behavior)”、“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集体抗争” (Collective Protest)或“群体骚乱 (Group Riot)”等“家族相似性”概念的国外学术体系中找到其对应性概念。而且,即便国内学者不排斥借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研究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但大多数人却仍主张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而非“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等西方学术概念,来分析当前中国的群体性“维权、利益表达、抗议或抗争行动”。也就是说,虽然一部分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可以包含在国际学术界的“集群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研究范畴之内,但不可否认的是,“群体性事件”是具有强烈现实取向和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的现实及学理基础[8]。
上述“官学之别”、“中西之辨”问题不但集中说明了“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中的难题,而且还与研究者对核心分析要素的理解、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等议题密切相关。
二、“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分析要素
在笔者看来,“群体”、“事件”、“行动”和“制度”是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四个基本分析维度或关键分析要素,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四种分析单位。与此相应,要明晰“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分析指向、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以及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分析视角差异,就可从学理及现实指向两个层面,阐明“群体”、“事件”、“行动”及“制度”这四个分析要素,并理清它们之间关系。
首先,针对“群体”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由参与者所形成的“群体”的结构及性质。相应地,研究者主要从参与者的人群结构及社会经济特征层面,通过分析参与者的参与意愿、诉求、行动能力及组织机制,来探讨“分散的个体如何经过组织动员形成具备共同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群体”[9],进而阐明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性质及影响。在现实层面,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群体”实际上就多指向在利益表达、资源分配、权力占有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他们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剥夺感、不满情绪及法不责众心理,但却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实现机制,易于采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动策略。
其次,针对“事件”这一分析要素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由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动所诱发的“事件”谱系及其社会影响。从学理层面上讲,“事件”这一分析要素往往意味着在特定时空内对相关主体产生影响的关系、结构和过程,并涉及作为行动连续谱的事件过程及作为行动后果的事件影响。而在现实层面,“事件”在中文语境下往往意味着不好的、负面的事情以及事态的持续恶化,同时也意味着有关各方对“事件”的意义建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抗性”行动。与此相应,我们之所以把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集体围攻、阻塞交通等“群体性行为”称之为事件,主要因为其打乱了常规过程和常规秩序。
再者,针对“行动”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相关主体的行动类型、行动手段、行动过程及行动策略,并理清“事件”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回应群体性事件研究为何直接定位于“事件分析”而非“行动分析”的深层原因。在学理上,勾连起“群体”与“事件”这两个要素的中介性分析要素正是“行动”。与此相应,分析“群体性事件”最为接近和可用的学术资源就是“集体行动”理论[10]。在这一理论视角下,研究者主要从“参与者行动意愿、行动能力以及制度性代替选择缺失三个方面来探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动方式和行动逻辑”[11]。而在现实层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和纠纷化解渠道,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事件应对策略,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往往采取“道义经济抗争”、“依法抗争”等行动方式及行动策略。
最后,针对“制度”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则重点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根源性。当分散的个体集结成群,通过某些共同行动来实现其利益诉求、并在客观上导致特定“事件”发生时,群体性事件中各方行动背后的制度框架就不可回避。相应地,这一类研究者主要从制度化利益表达、权益维护及纠纷解决机制缺失角度,探讨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并主张通过建立合法的、规范的利益表达及诉求实现机制,来消减群体性事件。在学理层面,研究者主要从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制度执行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一部分研究者从宏观制度体系层面,关注我国司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政治参与制度、权力监督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不完善、不作为问题,进而探讨作为“制度外”抗争行动的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根源。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则从利益表达、诉求实现的具体过程层面,关注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在与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规范问题。而就现实层面而言,由于我国基层社会尚缺乏充分的法治土壤、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以及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群体性事件多表现为“组织化程度低、制度化程度低、改变现状诉求程度较高的集体行动类型”[12],“参与者则往往不采取诉诸法律的方式来实现预期诉求,而政府也不依照法治原则来应对群体性事件”[13]。
一方面,对于上述分析要素的界定和理解,关乎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虽然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受非理性因素支配的、无组织的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14],但却有更多研究者将群体性事件视为“理性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15]。实际上,我国学者所界定的“群体性事件”涵盖多种类型、性质的群体行为,并表现为“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两种形态[16]及其混合物。与此相应,群体性事件研究者尤为关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范畴,以澄清其与维权行动、暴动、有组织犯罪等社会行动的边界,并分析“群体性事件”从集体行动到集群行为、从集群行为到集体行动或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表意行为、集体行动的性质转变问题。另一方面,它还与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切入点及分析视角相关。据笔者了解,西方学者一般倾向于以参与者的行为类型、组织化程度和行为后果为基础,直接对集会、游行、示威、罢工、骚乱等群体性行动进行分类研究[17]。与此不同,“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而且,这些抗争性行动的性质及指向也不同于通用意义上的“集体行动”——主要为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行为”,并往往指向政府当局及其代理机构。相应地,“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一来是因为其字面上的意思是“聚集的群体所引发的事件”,具有“突发和无组织”特性,较容易被官方所定性;再者则是因为“群体性事件”这一说法中隐含了集体行动、社会抗争等多层面的意义,易于“中性化处理”,也便于学者统筹研究。
三、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价值立场
群体性事件研究兴起之初,公安机关、武警部队院校及司法系统工作人员在研究者中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采用“治安管理和政府管控”分析视角,关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和现场处置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规模和影响的扩大,以及研究人员构成的多元化,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分析视角也更加多元,而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也转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演变过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抗争方式及行动逻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及长效防控机制。
实际上,在十多年的研究脉络中,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体及研究对象都发生了一定改变,而不同研究者的分析侧重点、分析视角及具体观点也有明显差异。这除了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短暂性、难介入性以及动态性有关之外,还与其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性质认定上的模糊性以及价值判断上的多主体性有关。理清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分析视角和理论焦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澄清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切入点和价值立场。
目前研究者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主要有“利益表达”、“底层抗争”和“社会稳定”这三种研究切入点,实际上也代表了三种价值立场。第一种切入点及价值立场下,研究者多从利益受损、利益分配失衡、制度化利益实现机制缺失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必然性”。第二种切入点及价值立场下,研究者多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地方政府权力缺乏监督以及民众参与意识觉醒角度,讨论底层民众的体制外抗争行动及抗争策略。第三种切入点及价值立场下,研究者多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立场出发,将群体性事件视为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犯罪学应该关注的前沿问题”,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各不相同的群体性事件简单解读为“社会敌意事件”,并重点从管控方式和治理机制角度展开分析。
基于第一种价值立场,研究者主要从事件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倾向于认为群体性事件只是在社会转型导致利益矛盾增加、民众维权意识日益觉醒而制度化“维权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利益受损的公民集结成群,通过非制度化参与实现利益诉求、调解利益冲突的“理性”行动[18]。在这一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虽然也有情感性因素及情绪性因素的介入,而且会有过激甚至是破坏行为的出现,但本质上却以“利益”为导向——部分群众利益在社会转型期受损,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19],是相关利益主体在无法借助公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不畅的情况下而采用的“私力救济行为”[20]。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指向具体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目标,并不具有对抗性的政治诉求。这一价值立场下,研究者一般会聚焦于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及制度外行为的“制度化”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及协调机制的政策对策,主张通过具体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来消减群体性事件[21]。
基于第二种价值立场,研究者主要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恶化尤其是多级政府关系及“官逼民反”角度,在承认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民事法律地位和公民政治参与权力基础上,分析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权合法性弱化等地方性治理问题之间关系,并主张通过加强地方政府责任意识、依法行政,来化解群体性事件。研究者认为,由于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失灵”,基层民众对地方政府及正式制度的信任被严重削弱,当其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采用“道义经济式抗争”[22]、“依法抗争”[23]、“依理抗争”、“以法抗争”[24]等行动策略,通过要求上级政府主持正义和“失范的非常规行动”[25]以及“草根动员机制”[26],来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但研究者也同时指出,虽然群体性事件是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触发机制,但目前看来并不具有对抗性的政治诉求,也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
基于第三种价值立场,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现实需要成为群体性事件理论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偶合群体、非法性以及受人煽动后的群众闹事”则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标签。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和“官民对立逻辑”下,由于容易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抱持非理性假设,地方政府极易将合理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机械对立起来。同时,以权代法的工作方式、过分依赖行政力量强制干预的应对策略,也易造成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政治化、刑事化、意识形态化。基于此,研究者认为政府是当代中国社会“对抗性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中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即便群体性事件的抗争对象并非政府部门,我们也应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内展开分析,并以一种“政治统摄”逻辑和“维稳”立场来定性群体性事件,重点关注群体性事件是否具有改变政治秩序的可能性。
四、小结与讨论
目前,虽然群体性事件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领域,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明显不足:首先,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静态和宏观分析,而轻视对群体性事件演变过程的动态分析、微观分析。其次,现有研究多从政府管控角度展开讨论,过于强调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秩序的危害,而较少反思群体性事件的深层诱因,并回避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政治议题。再者,已有研究过于凸显治安性、刑事性甚至是政治性事件,对群体性事件的细分及每类群体性事件的针对性研究相对缺乏[27]。最后,研究者大多主张通过完善制度、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公平与平等来消解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但在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下,实现上述目标的路径及切入点仍不明晰。
上述四方面不足又与下列三个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第一,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为什么要通过“闹到上级政府、闹大、闹乱、闹出动静”来争取自身诉求的实现[28],而政府部门又为什么遵循“官民对立、强力压制”的应对逻辑?第二,个人行为、个体纠纷如何演变成为群体行动,群体行动又如何演变成为暴力冲突甚至“群体骚乱”?第三,为什么研究者在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偶发性、无组织性、非法性和政治无涉性的同时,又强调它的必然性、自组织性、合法性和政治生态性?
实际上,上述三个问题反映了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一个极大张力——群体性事件具备合理诉求和泄愤并存、官民对立逻辑明显的基本特征,研究者面临如何从对与错、合法与非法、理性与非理性、有组织与无组织、积极与消极等角度,对群体性事件属性进行细致分析的挑战。当然,这既与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制度及文化环境有关,同时也与事件参与者的人群特征及行动策略有关。
“群体性事件”是类似于“盲流”、“农民工”之类的时代性概念,不但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范畴不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被“政治性”使用的风险。即便是基于现实考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也一定要在明确界定“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基础上,澄清研究所关涉的核心分析要素及价值立场,并对其分析局限性保持警惕。
[1]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一种新的科学增长论[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5.
[2]刘能.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形象地位变迁和分类框架再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2).
[3]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Z].2000.
[4]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Z],2004.
[5]陈月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6]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7]王晓君.差异性社会中群体事件的认识与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2(2).
[8]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J].社会学研究,2009:2.
[9]高恩新.过程、行动者与危机管理——当代中国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6.
[10]贾宝林.利益、心态与身份地位: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
[11]吴亮.政治学视野下的民族群体性事件及治理机制[J].民族研究,2010(4).
[1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J].学海,2006(2).
[13]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5).
[14]王礼鑫.群体性事件:碎裂与建构——来自集体行动理论的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09(9).
[15]刘超.群体性事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1.
[16]王赐江.基于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对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的考察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2.
[17]王国勤.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J].学术界,2007(5).
[18]黄治东.从利益视角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1).
[19]王晓君.差异性社会中群体事件的认识与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2(2).
[20]张百杰.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23-24.
[21]吴佩芬、王国明.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
[22]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J].东南学术,2007(3).
[23]Lianjiang,Li.,and Kevin 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J].Modern China,1996,22(1):28-61.
[24]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J].社会学研究,2004(2).
[25]张兆曙.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J].社会学研究,2008(3).
[26]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27]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2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R],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