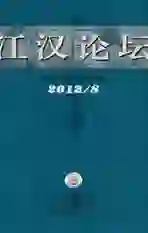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
2012-11-27吴道毅
吴道毅
摘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有着锄强扶弱、周穷济困与揭竿起义等较为丰富的内容或展开方式。作为千百年来民族集体无意识积淀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传统,它内在地渗透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中,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及改造。对革命历史小说来说,侠义文化的书写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不但适度消解了阶级话语,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历史局限,而且对革命英雄人物进行了文化还原,增强了其艺术生命力,促进了大批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的涌现,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形态或格局。
关键词:革命历史小说;侠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86-05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与主导叙事类型,以描写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小说向来被看作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看作阶级斗争政治理念的载体。这种看法虽存在一定的依据与合理性,但无疑也是片面的。事实上,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除了从政治上论证革命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与建构新型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外,也客观地凸显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反映了中国民众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百年梦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与此同时,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还积淀了中华文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如,儒家的忠义思想、气节观念,墨家的侠义精神等等,作为千百年来古老的民族精神,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一、侠义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展开方式
《红旗谱》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说起小说中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熟悉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为朋友两肋插刀。”朱老忠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乐善好施,深孚人望。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尤其是在被称为新英雄传奇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小城春秋》与《铁道游击队》等革命历史小说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朱老忠这样具有侠义品质的英雄好汉。在这些人物身上,侠义精神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谓侠客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一、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有超人的武艺。”行侠是否一定需要行侠者具有武艺有待商榷,这里姑且存而不论。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确实存在大量的现代武侠形象,他们身怀高强的武艺,一心匡扶正义,锄强扶弱。如同古代侠客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小城春秋》中,江湖好汉、武林帮会掌门人吴七一句“猴鳄!好好看戏,别饭碗里撒沙”,就为厦门学校剧场里的革命青年何剑平解了围,狠狠地镇住了寻衅闹事的地痞流氓宋金鳄。拳头虽未出,却是威风八面,让人肃然起敬。《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肖飞、丁尚武等人,个个身怀绝技,或刺杀威猛(史更新),或行走如飞(肖飞),或惯使大刀(丁尚武),当80多名同胞姐妹被日军关押与凌辱之时,三人深入虎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成功地将姐妹们救出险境。《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王强等,飞爬火车、威震敌胆、打得日本鬼子哭爹叫娘。《桥隆飙》中的老铁匠与肖元山,怒打恶人狄德、义救孤女李兰花……
第二,解囊相助,雪中送炭,救人燃眉之急。在古代英雄传奇《水浒传》中,宋江貌不出众,武艺不高,曾被“没遮拦”穆弘兄弟追杀到浔阳江边,走投无路,狼狈之极,幸得李俊相救才转危为安。然而宋江却在江湖好汉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乃至被梁山好汉一致推为首领,林冲、鲁智深与武松等一帮好汉一一归服。之所以如此,除了宋江有一定领导才能之外,主要是宋江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别人遇到困厄,他都倾力相助,广施钱财,因此被称为“及时雨”,闻名遐迩。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我们同样能发现许多宋江这样的乐善好施、专为他人着想的侠义人士。写得较为突出者,还数朱老忠。朱老忠的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更多的不是为人打抱不平,而是在邻居、朋友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倾囊相助,施以援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如用十多年闯关东得到的血汗钱为朱老明治眼;卖掉小牛犊,助江涛求学;运涛被捕,他主动代替严志和,千里迢迢去济南探监。《小城春秋》中的吴七,作为接骨医生,为穷人看病不收费。《林海雪原》中的中药医师韩荣华,医德高尚,“为救无价宝,情愿舍本草”——“无价宝”指的就是人的生命。《桥隆飙》中出身于名医世家的李侯君父子,“为穷人治病,分文不取”。有一次,李侯君在治好被人贩子骗来的三个小姑娘后,还特意派得力人员护送她们回原籍,使她们最终跳出了火坑……
第三,替天行道,啸聚山林,反抗官府。侠义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除了“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敢说敢为、勇于牺牲的人格精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于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当统治者的政府变为极端腐朽、与民为敌、社会公平彻底丧失的时候,民间的侠义之士就会组织起来,成立民间的武装,占山为王,揭竿而起,试图推翻腐朽的政府。历代农民起义便是这样发生的。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同样有绿林好汉、敢于与官府作对的侠客,他们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样,打击贪官污吏,攻城拔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桥隆飙》中以桥隆飙为首的绿林好汉。他们在桥隆飙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义军,在山东沿海一带打富济贫、除暴安良、锄奸反霸。他们“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以此来履行社会正义,铲除人间不平——当然,对他们来说,当异族的铁蹄无耻地践踏祖国的领土、奴役同胞的时候,他们同样予以坚决的反击。《苦菜花》中的柳八爷、《万山红遍》中的郝大成、《海啸》中的赵天京,也都是桥隆飙这样的义军领袖……
二、侠义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被书写的缘由
从主导话语上看,革命历史小说“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革命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或者按照当时的权威阐释:“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革命历史小说的落脚点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即通过革命历史事实的讲述,建构新型人民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建构民众新型的人生价值体系,它承载的是主流文化观念。既然如此,作为民间文化或亚文化的侠义文化为什么能够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被书写与表现呢?
第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我国的侠义故事和侠客型的人物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作为民间下层文化、亚文化或小传统,侠义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就提出了“任”侠观念,指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上》),把损己利人、急人所难、扶危救困作为平民社会的人生价值取向与道德行为准则加以提倡与践行。在汉代,出现了专与官府或地方豪强作对的朱家、郭解等民间游侠,他们广为下层民众服膺。大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均在史书中为他们作传,司马迁甚至在《史记》中盛赞了游侠们的侠义品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侠于是以其闪亮的人格精神获得了平民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平民百姓心目中仰慕与崇敬的英雄,对侠的期待也成为底层民众朴素而良好的社会愿望。唐、宋以后,民间结义风气盛行,讲义气成为一种广泛被遵守的江湖规则,见义勇为成为民众的好尚,侠义文化逐渐普及于下层社会与江湖社会,乃至成为平民百姓或底层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到了现代社会,侠义之风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并为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荣格指出:文学就是为集体无意识代言,作家的创作便“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荣格的话不无道理。就革命历史小说来说,从上述侠义英雄身上,不难看出侠与侠义文化的现实土壤,不难看出侠义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在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积淀,以及它们被文学书写的必然性。
第二,古代侠义文学的传承。如果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侠义观念深人到民众的无意识结构形成了侠义文化传统的话,那么,这种侠义文化传统渗透到文学中便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表里关系。从《史记》、《汉书》,到唐传奇《昆仑奴》、《柳毅传》、《红线》与《虬髯客传》,从明代的英雄传奇《水浒传》、历史演义《三国演义》到清代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组成了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侠义文学传统。柳毅传书、风尘三侠成为文学典故,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在普通民众中耳熟能详,乃至妇孺皆知。《三侠五义》的作者还专门解释了大侠展昭的侠义内核:“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第十三回)当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我国的侠义文学承前启后,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民国时期的旧武侠传奇、20世纪50年代以后港台的新武侠传奇、大陆的新英雄传奇可以说是我国侠义文学开出的三朵新花。就革命历史小说或新英雄传奇作家而言,他们不仅十分喜爱包括侠义文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而且从小就深受古代小说、英雄传奇与侠义文学的影响。如《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途说“古典小说和传奇故事”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作品。曲波的《林海雪原》更是直接改编、模仿或移植了不少《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至于古典小说中的侠义文化传统更是如春风化雨,浸润在革命历史小说之中。我们从《红旗谱》中朱老忠代替严志和到济南探监前对严志和的叮嘱中,不难看出《水浒传》中武松离家前告诫乃兄武大的痕迹,也不难看出古典文学的侠义精神在革命英雄人物身上闪现的夺目光彩。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1949年新的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同时意味着新文化建设的开始。作为新的价值观念,新文化是需要在根本上与旧的文化传统决裂的。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活动和政策以及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神话,发生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国性变革。”然而对于古代的侠义文化传统,贯穿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文化却采取了接纳的态度。这要归结于侠义文化与新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一致性。就新文化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从政治上解放普通工农民众或下层人民。革命的任务之一便是发动下层民众,吸引他们加入到革命阵营,壮大革命的队伍。就侠义文化来说,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的存在甚至为革命宣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无论工农大众的行侠仗义还是揭竿起义,都与革命行为相一致,因为打击坏人、反抗旧政府与追求正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工农大众还是革命的主力军,是主要的依靠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正是这样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小城春秋》中看到革命青年对江湖好汉吴七的团结,从《苦菜花》中看到八路军于团长对“土匪”柳八爷部的收编,从《桥隆飙》中看到革命军人马定军深入“飙字军”对桥隆飙的争取。但是,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对于侠义文化等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根据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加以整合;现代侠义英雄身上的江湖习气或哥们义气、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等缺陷,无不受到新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清算。《铁道游击队》中的侠义好汉李九一心杀鬼子,“只相信自己的勇敢和枪法,不相信群众的力量”,结果死于鬼子密集的乱枪之中。牺牲后被游击队长刘洪严厉批评为“犯了个人英雄主义”。《小城春秋》中最初鲁莽、急躁与蛮干的吴七,最终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革命英雄,从“打抱不平”的江湖好汉成长为“一个阶级战士”。
三、侠义文化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学意义
就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而言,它们是在当代严格与严密的文学规范约束中产生的。如同生产工业铸件的模子,当代文学规范为包括革命历史小说在内的文学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与范式。比如,贯穿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创造革命英雄形象、塑造英雄时越完善越高大越好等等。当代文学规范旨在将文学纳入到新文化整体建设之中,促进了一大批革命经典作品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即成为文学公式主义、概念化与英雄人物高大全、虚假化的主要根源。革命历史小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然而,侠义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被书写,或者侠义好汉在革命历史小说尤其是新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当代文学规范对文学创作的规限,拓展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话语空间,还原了英雄人物的文化本色,成就了特殊年代的文学文本。
第一,阶级话语的适度消解。革命历史小说表现革命斗争,而革命斗争发生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阶级话语的生产成为它的首要任务。阶级话语主要表现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思辨。革命年代,阶级斗争即政治,然而政治毕竟不能涵盖一切社会生活。人类的文化生活就远远越出了政治生活的领域。历史长河中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就很可能是两大斗争阶级所共同接受的东西,并决定着不同阶级、阶层人士的文化心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阶级意识的局限,“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使文学文本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与人类的文化心理。不妨先从侗族作家滕树嵩的短篇小说《侗家人》谈起。这部在1962年《边疆文艺》上发表的作品,虽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却穿插了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一个片断:1944年,棒老二首领、侗族妇女龙三娘半道上手刃了杀夫仇人、为恶多端的县长胡忘义,县长妻子受惊吓而死。之后,龙三娘抱起县长夫妻留下的女婴,解怀喂奶,将女婴作为义女加以收养——18年后,义女龙三妹被养母培养成一位豪爽而出色的猎人,母女情深似海。小说写龙三娘与胡忘义的阶级深仇,龙三娘报仇血债血还,贯穿了主流文化的阶级话语。然而,这一阶级话语最后却被民间话语所冲淡,取而代之的是龙三娘的侠义精神。或者侠义精神最终超越了阶级意识。也就是说,龙三娘并没有选择对阶级敌人斩草除根,而是坚持仇人的女儿是无辜的,并出于侠义情怀或江湖规则对其进行抱养。作品发表后曾得到好评,但一度被当成“阶级调和论”遭到严厉批判。实际上,龙三娘的举动既是侗族精神的写照,也是底层平民文化的反映,体现了侠义文化传统在民间的传承,反映了民族、民间文化对阶级理念的稀释。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也往往穿越了阶级的屏障,成为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精神相通的桥梁。比如,《战斗的青春》中的革命英雄窦洛殿,深入敌营后常常模糊阶级界限,与敌特、汉奸“真心实意”地“称兄道弟”。《烈火金钢》中的农妇田大姑,将曾经侵略中国、受伤的日本军人武男义雄收为义子,并细心养护与舍命保护,感恩的武男义雄后来也为了保护田大姑而与日本人作殊死搏斗——田大姑的行为显示了中华民族心胸的博大、宽容与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化解民族与阶级矛盾的更高境界,超越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念。作品中的伪军小队长刁世贵,平时作恶不少,但在许多同胞姊妹被日本人辱凌之时,却伸手施救,持枪与日军搏斗。作为敌对营垒的人物,刁世贵没有被写成简单的阶级符号,没有被妖魔化,传统文化的正面因子也流淌在这个“坏人”的血管之中。的确,作为“民间文化形态”,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第二,革命英雄的文化还原。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英雄是新型意识形态的载体,是群众学习的楷模。《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英勇不屈,牺牲在黎明前的黑夜。《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智勇双全,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作为新文化的符码,这些英雄到现在为止已经影响了几代人,发挥了突出的卡里斯玛效应。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英雄,他们往往是作为一种阶级“工具”而存在的,“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由于过于理想化,他们被浓缩为革命价值理念的集合体,而身上本来拥有的文化积淀乃至情感、生命体验都被抽掉了。他们越是高大,就离生活的距离越远,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成功,却未必是文学形象的成功。有人于是说:“《红岩》中的英雄群像……每个人的生命中除了政治生命就几乎别无其他内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质疑。然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却更多地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同,乃至与《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一起,被认为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寥寥可数的、较为成功的文学形象。梁斌曾说:“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也因为如此,我把原来朱老忠的火爆脾气改掉了。”尽管作家坚持遵循文学规范设想,将朱老忠刻画成理想、完美的英雄,以致改掉了朱老忠作为普通农民的火爆脾气;尽管在作品所描绘的四大主要事件一大闹柳树林、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中,朱老忠阴差阳错地均被“架空”了或与它们不太沾边,但朱老忠“出水才看两腿泥”,尤其是“为朋友两胁插刀”的性格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斌在创造朱老忠这一形象时,虽然力求吻合意识形态要求。注意到突出人物的阶级本性——即注意到与冯兰池父子的阶级对立,但同时却不经意地对朱老忠进行了文化的还原,即写出了朱老忠作为中国农民的文化本分,写出了侠义等古代文化传统在朱老忠身上的深厚积淀,因此赋予了朱老忠更多的“艺术生命力”。至于桥隆飙、柳八爷、吴七等现代革命英雄,更是较为普遍地被还原为民间侠义好汉,身上保留旧时代深厚的草莽英雄习气,显示出他们作为工人、农民固有的文化内涵及其缺陷,如此他们虽然没有卡里斯玛英雄那样完美、高大,但却更贴近文化的本质,富于人性的力量。
第三,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的涌现。侠义文化毫无疑问是一种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亚文化,它流行于民间下层社会,体现了底层民众的文化诉求。这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年代尤其如此。主流文化建设推动了主流文学的繁荣。革命历史小说也好,新英雄传奇小说也好,它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承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阶级叙事,乃至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红色经典。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亚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侠义文化较为普遍地渗透到了革命历史小说或新英雄传奇小说当中,并生成为一种包含着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义结构”,在作品中与主流话语或阶级话语形成了某种对话与潜对话关系,并使作品构成了一种潜隐的“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⑩,也使古代侠义文化传统与侠义文学传统在革命文学时期重现一片生机。这也无疑丰富了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形态,突破了十七年文学过于生硬与僵化的叙事格局。这些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除了前文提及的之外,还可开出长长的书单:《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山呼海啸》、《山菊花》、《迎春花》、《新儿女英雄续传》、《还我河山》、《叶秋红》、《大刀记》、《将军河》……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