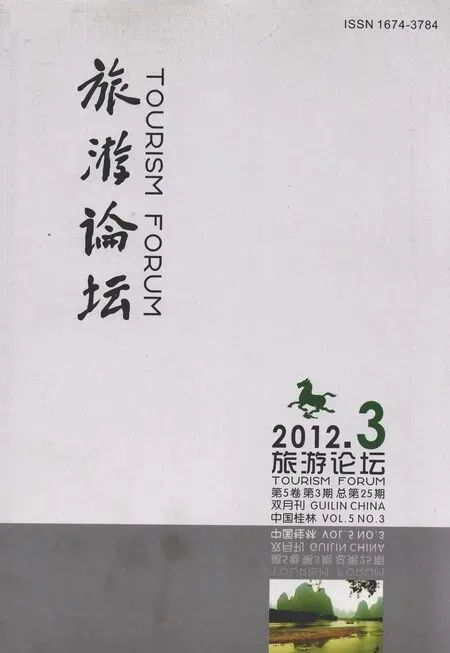太空旅游纠纷的司法解决初探*
2012-11-27欧阳爱辉
欧阳爱辉
(湖南工学院 工商管理系,湖南 衡阳 421008)
太空旅游,通常多指以航天器为主要运输工具,以外层空间为旅行目的地①,以向游客收取费用来获取经济收益的旅游方式之总称[1]。自从2001年4月底美国富豪丹尼斯·蒂托乘坐俄罗斯“联盟TM―32”号宇宙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成功实现太空八日游后,迄今已有多名对宇宙空间充满强烈向往的富商以支付高昂费用的方式(一次约2 000万美元)前往太空享受他们的豪华传奇冒险之旅。尽管囿于航天科技水准、飞行成本和高风险等因素桎梏,当前太空旅游仍仅能算做个别亿万富翁的奢侈游戏,但放眼未来,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太空旅游的商机显然无可限量。在西方国家,现已涌现了太空冒险公司、联合公司、维珍银河公司、空间岛集团等一大批颇具知名度的太空旅游服务机构,我国香港地区也已成立了中国首家宇宙空间旅游企业——香港太空旅游有限公司,它们在品牌推广、项目规划、筹办未来太空旅游产业方面都取得了不小成效[2]。
不过,太空旅游的勃兴,在具体运作中也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违约、服务质量或安全纠纷②。并且因太空旅游是一类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旅游方式,其操作之复杂、风险系数之大、成本之高以及对游客本身素质要求之严苛更远非传统旅游可比拟。如此一来,太空旅游在带给人们瑰丽奇异的宇宙景观的同时又必然会令相关纠纷出现机率大增。正如法学大师伯尔曼所言,“(法律)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3],针对太空旅游纠纷,很显然诉诸法院凭借司法解决乃切实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且最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当前各国涉足航天领域的法律制度本身就相当缺失,那么具体该如何着手有关司法解决便大成问题。有鉴于此,为能未雨绸缪对日后太空旅游纠纷之解决起到相关指导作用,顺利推动未来太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笔者特从太空游客法律地位、司法管辖权、证据制度、具体审理4个主要环节就太空旅游纠纷的司法解决展开初步探讨。
一、太空游客的法律地位
太空游客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太空旅游纠纷的司法解决中必须率先解决的前提问题。因为倘若太空游客的法律地位无法彻底明确,那就势必将给随后的法律具体适用造成诸多不便,进而令司法解决成了一句空话。笔者认为,所谓太空游客,归根到底仍属一类购买旅游服务用于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的消费者,只不过其具体旅游空间从传统大气层内地理环境置换成了广袤太空领域。因此在本质上,太空游客与寻常购买、接受旅游服务的消费者并无区别,法律地位也理当完全相同。
但是,倘若我们仅简单地将太空游客视为普通旅游服务消费者,则又很可能忽略了太空旅游的特殊性。毕竟太空旅游在具体飞行运作、风险系数、耗费成本、乘客自身素质要求等方面同传统旅游大相径庭,那我们若想草草借助传统相关法律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旅行社管理条例》等等来解决其间发生的纠纷就未必能如愿以偿。可目前专门涉及太空旅游的法规除了美国2004年颁行的《商业空间发射修正案》以外,真正相关法规各国均尚付阙如。并且,即便是大开太空旅游法先河的美国《商业空间发射修正案》,也只粗略规定了商业公司和个人在风险上之承担而已[4]。所以,在将太空游客界定为旅游服务消费者同时,我们自然还需就其法律地位做更广义理解。
众所周知,由于太空对所有国家均自由开放但又不归属任何国家主权管辖,故当前用于调整、规范人类在太空活动的法规主要便是各国签订的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这主要包括1967年订立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1968年制定的《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物体之协定》(以下简称《援救协定》)、1972年签署的《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以下简称《责任公约》)、1975年缔结的《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以下简称《登记公约》)和1979年达成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以下简称《月球协定》)。但这些国际条约受制定时代束缚都没有明确提及太空游客,而只是用“航天员”(astronauts)或“宇宙飞船人员”(personnel of a spacecraft)等称谓来指代条约中出现的人员。若从狭义语境上进行阐释,很明显太空游客作为宇宙空间游览观光猎奇者是断无法同肩负探索外层空间神圣使命的“航天员”或“宇宙飞船人员”相提并论。不过恰如德沃金所言,“法律解释具有与生俱来的整体性要求……解释者必须接受解释性的约束(即对何为最佳解释的假定)”[5],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亦强调国际条约的解释应遵循真实、一致、合理、有效之原则[6],加上当前太空游客在享受宇宙空间奇妙景象获取精神愉悦同时也承担了部分航天员的具体工作③。因此为防止太空游客在宇宙空间的活动趋向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之境地,切实捍卫各方正当权益,在目前专门性太空旅游法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妨将他们视为一类“准航天员”或“准宇宙飞船人员”来对待。
故此在法律地位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太空游客理当具备双重身份:其一为旅游服务消费者,其二同时又是“准航天员”或“准宇宙飞船人员”。如此这般倘若发生了相关旅游纠纷,我们便可双管齐下将传统旅游法规和人类太空活动国际条约一并运用查漏补缺,从而顺利解决彼此间的纷争。
二、太空旅游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司法管辖权作为各国法院以及一国内部各级法院之间、同级法院之间受理案件的分工与权限,对于纠纷最终成功实现司法解决具备重要意义。毕竟若我们事先不能就相关司法管辖权问题予以清晰界定,纠纷发生后便无法准确判断它究竟该由哪一国何地、何类别、何审级法院进行审理,进而严重制约到审判活动顺利开展。那么对于太空旅游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我们又该如何加以确定呢?在传统旅游纠纷中,遑论其系旅游合同违约、旅游服务质量抑或安全纷争,一般均可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或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背现行法律硬性规定前提下双方协议选择法院实施司法管辖。但太空旅游发生在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若由被告住所地法院进行管辖,可被告住所地又未必都是航天器发射、飞行状态监控管理地,此时法院受客观条件限制就很难彻底查明案情顺利定纷止争;若由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法院进行管辖,而合同履行或侵权行为具体发生地在太空旅游中既可能是航天器亦可能为宇宙空间甚至外星球,这时究竟孰为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法院亦很难界定;意思自治原则下形成的协议管辖虽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自愿,但鉴于航天飞行的高技术复杂化特征,他们自行选择的法院是否能真正满足审判需要呢?况且,倘若当事人事先无法达成协议又该当如何呢?
面对上述种种困惑,很明显,借助传统司法管辖权判断模式已经很难实现太空旅游纠纷解决的基本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98年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共同签署的《关于国际空间站合作的政府间协议》(以下简称《空间站协议》)则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路。该协议认为每个成员国对国际空间站里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权,若一方国民行为影响到另一方国民生命或安全,或发生在另一方组件上或对该组件造成损害,双方国家可协商解决。假设行为人国籍国在合理时间内同意另一方行使管辖权或没有提供保证对行为人提起诉讼,另一方即可对其行使刑事管辖权[7]。这种成员国属人管辖原则虽主要涉及刑事管辖权,但不难推导出,既然国际空间站发生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都奉行属人管辖,那么无丝毫社会危害的民事纠纷同样也可遵循属人原则。该判断方式应当说有一定合理性,毕竟《空间站协议》各成员国都参与了国际空间站设计制造或发射工作,由他们本国法院对本国公民实行管辖各方面相关情况都较了解。即便是不同成员国公民之间发生了纠纷,因成员国数目不多,利用协商或其他方式仍能够较快地确定管辖权。不过,当太空旅游业日渐兴起时,该方式也不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就目前而言国际空间站可谓太空旅游主要目的地,倘若日后进入其中旅游观光者并非《空间站协议》成员国公民④,例如非成员国中国公民王某与美国太空冒险公司订立合同前往国际空间站旅游,空间站引擎启动进行姿态变轨时因震动王某不慎被站内设备撞伤,假设此刻王某提起诉讼进行索赔,则究竟该由何国法院进行管辖呢?
笔者认为,在太空旅游日渐勃兴的信息时代,传统旅游纠纷司法管辖权判断模式和现行《空间站协议》属人原则都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启用宇航实际控制国管辖原则展开判断。具体而言,它又包括发射国管辖和航天器实际管理国管辖两方面。前者指一般情况下哪一国家将航天飞行器及人员发射入太空,那该国发射地法院就享有对航天飞行器和人员在太空中发生的各类纠纷之管辖权而无需考虑这些航天飞行器和人员究竟是否属本国国籍;后者则指若航天器(如空间站等)射入太空较长时间早已脱离了发射国控制,此刻太空游客在其中(如乘坐宇宙飞船进入早就投入使用多年的空间站观光)遇到的旅游纠纷应交由航天器实际管理国的相关航天控制中心所在地法院进行管辖。因为我们知道,对太空飞行来说,无论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或日后即将投入使用的多次重复轨道飞行航天器,其发射国或航天器实际管理国等控制国对航天器性能、成员状态以及具体发射升空、火箭助推器脱落、飞出大气层、二次点火、绕轨道飞行、返回地面等一系列过程往往起着实质性指挥、跟踪测量、监控和协调作用,它们与太空旅游合同具体履行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那么,由宇航实际控制国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在调查取证、查明案情、迅速判决等方面显然就均能收到更好效果,并且这种司法管辖权判断模式在现行部分国际公约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之肯定。如号称“外空宪章”的《外空条约》第10条就指出“凡登记把实体射入外层空间的缔约国对留置于外层空间或天体的该实体及其所载人员,应仍保持管辖及控制权”,《登记公约》第2条亦认为“任何此种外空物体有两个以上的发射国时,各该国应共同决定由其中的那一国依照本条第1款登记该外空物体,同时注意到关于各国从事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八条的规定,并且不妨碍各发射国间就外空物体及外空物体上任何人员的管辖和控制问题所缔结的或日后缔结的适当协定”。所以,我们使用宇航实际控制国管辖原则,只要游客系何国发射进入太空或航天器目前由何国实际管理,则认定该国发射地或相关航天控制中心所在地法院享有司法管辖权。这样做既简便易行,又和现行国际条约有效保持了一致性。
当然,确立了宇航实际控制国管辖原则并不意味着就对其他管辖方式的彻底杜绝。假设太空旅游纠纷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且选择的法院也具备必要审理能力,我们仍须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抉择。另外,考虑到太空旅游纠纷带有强烈高技术色彩造成的影响也较大,为确保审判的正确性在级别管辖上一般还须由发射地、相关航天控制中心所在地中级或高级法院进行审理,条件成熟时最好能够于发射地、相关航天控制中心所在地成立专门法院实施专属管辖。
三、太空旅游纠纷的证据制度
证据作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无疑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法院查明事实辨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捍卫当事人正当权益具备着至关重要之现实价值。就太空旅游纠纷而言,其证据收集理应像传统民事诉讼那样涵盖书证(如太空旅游书面合同)、物证(如毁损物品)、视听资料(如涉及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进行交流的音频、视频)、证人证言(如发射失败目击者的证词)、当事人陈述(太空游客与相关旅游服务机构的叙述等)、鉴定结论(如权威机构对飞行是否成功所做的判断)和勘验笔录(如在发射场或着陆回收区进行的实地查验记录)七大类。但是,考虑到宇宙航行之特殊色彩,在太空旅游纠纷的证据制度上除须使用传统民事证据规则外还应建构起一些特殊化规定。
第一,太空旅游纠纷在举证方面应强调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为主。尽管太空旅游纠纷从最广义上说仍属一类民事纠纷,但传统民事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做法很可能不利于对太空游客正当权益之保护。因为大气层外旅行带有极强的高科技性质,一般游客未必能具备足够举证能力顺利收集到支持自身主张的有效证据。并且较之实力雄厚的太空旅游服务机构或宇航实际控制国政府⑤,普通私个体力量微乎其微。故笔者认为,在此类旅游纠纷举证上我们必须主要奉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也就是说,若游客认为太空旅游服务机构或宇航实际控制国政府具体行为损害了自身合法权益,就可向宇航实际控制国相关法院提起诉讼。至于对方具体行为是否真正侵害到游客合法权益的证据必须由太空旅游服务机构或宇航实际控制国政府提出,假设他们无法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没有责任,法院便可支持太空游客主张判其胜诉。当然,倘若发动此类诉讼的是太空旅游服务机构或宇航实际控制国政府,如太空冒险公司认为旅客在旅行途中损坏了民营航天器要求予以赔偿,考虑到届时提起诉讼者举证能力远较游客充足,则无需贯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第二,太空旅游纠纷在证据证明力方面应更强调专家证言之作用。和传统旅游纠纷不同,大气层外的宇宙空间目前尚属高风险未知领域,要去这一未知世界探险,除了对航天器性能、具体飞行、地面监控有着极高要求外,游客自身生理、心理、文化素质亦至关重要。另外,一些影响安全的突发性偶然因素也经常出现,如太阳黑子活动频繁干扰通讯、微流星与航天器发生碰撞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当游客在太空旅游遭遇到了违约、服务质量或安全纠纷时,其具体责任承担之判断并非易事。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环境,专家证言显然极其重要。倘若国际空间组织、发射国地面控制中心、权威科学协会或航天领域专家能够就相关问题作出一个较全面公允之结论,那该证据理当具备较大证明力。
最后,太空旅游纠纷在证据搜集方面应准允私人调查机构介入。所谓私人调查机构,即私人侦探所、私人商务调查中心等非国家官方的赢利性情报、证据收集组织。尽管对太空旅游纠纷举证应强调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游客自身不得主动收集有利于己之证据。可普通游客单凭个人力量进行此类高科技取证又未免力不从心。这么一来,私人调查机构作为调查取证专业人士的优势便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平克顿、罗斯国际等一些享有盛誉的全球性私人侦探公司在高技术调查取证方面颇具成效,稍加调整、适应并在保密制度约束下(因为大多数航天器发射、飞行均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必能顺利满足太空游客需求,搜集到他们需要的有力证据。因此,准允私人调查机构进入此类旅游纠纷取证也是相关证据制度建构非常重要的一环。
四、太空旅游纠纷的具体审理
案件具体审理乃司法解决纠纷的最终步骤,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活动,才能彻底查明事实,理清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消弭分歧。对太空旅游纠纷来说,因其属民事纷争,在整体上理当遵照普通民事审判模式。但在具体审理活动内,鉴于宇宙航行、太空旅游之独特性,我们仍需进行部分特殊化设计。
第一,太空旅游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应强调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主。众所周知,审判公开乃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它能够防止司法专横、增强裁判公正性、提高判决公信力并改进司法工作[8]。但太空旅游与传统大气层内地理环境旅游不同,这种旅游要借助航天器在宇宙空间活动,而航天飞行在今后若干年内都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甚至垄断之行为,它往往要运用到本国各方面最尖端的科技成果,这些东西无不和国防安全等国家整体利益休戚相关。即便是个别私营公司独立研发之航天器如美国维珍银河公司制造的“太空船”系列载人飞船和俄罗斯企业推行的“太空旅馆”计划[9],它们也牵涉到大量国家严格监控的最新技术和公司自身商业秘密。因此,假设我们盲目照搬传统审判公开原则进行开庭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极可能导致诸多威胁国家整体利益的高新技术或公司重要商业机密大量曝光。故而,为防止带来过多负面效应,太空旅游纠纷的审理过程一般情况下便应主要采用不公开开庭的秘密审理方式。
第二,太空旅游纠纷案件的主审法官应由精通空间法的司法人员担任。尽管太空旅游纠纷案件归根到底仍系民事案件,但鉴于宇宙空间探险的技术含金量要求极高,而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又比较原则笼统化难以简单进行适用,“当某一个行为引起争议时,是不是违反国际空间法的界限并不一目了然。有些行为或许没有引发任何争端,但可能是公然违法的。有些行为可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仅凭现有的几个空间条约,可能无法直接认定它违法。”[10]倘若此刻任用普通法官来审理案件,即便他们传统法律知识非常渊博、过去司法实践经验异常丰富,就仍未必能轻松明辨是非。因而,我们必须要启用精通空间法的相关司法人员来担任太空旅游纠纷案件的主审法官,即使万一出现了现行法规过于笼统无法简单适用之情况他们亦可凭借特殊知识背景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作出有效判决。
第三,太空旅游纠纷案件的审理期限可比传统民事诉讼案件酌情延长。民事案件审理期限长短是一个牵涉到如何尽快明确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提高司法效率的问题。但对太空旅游纠纷案件而言,其审理期限理应比传统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普通旅游诉讼酌情延长。毕竟太空旅游纠纷发生在环境异常诡异复杂的宇宙空间,它牵连的高科技因素比较多且当前可适用的法律又相对较少,那么法官要根据当事人双方陈述、所举证据和互相辩论、质证情况依法迅速作出判决实非易事。譬如游客A要求太空旅游服务机构和空间站实际管理国政府对自己在空间站受到的人身伤害进行赔偿,但太空旅游服务机构和空间站实际管理国政府则辩称A所受伤害系微流星与空间站碰撞的不可抗力造成,游客A及其律师却认为此类碰撞空间站航天员在事先轨道计算时已经完全预料到。这么一来法官要参照庭审调查和法庭辩论结果对具体责任承担着手判断就并非可一蹴而就实现的。因此,顾及到诸多复杂因素,将太空旅游纠纷案件的审理期限视情况延长便更加合乎此类纠纷司法解决实际。
总之,恰如全球首位太空游客丹尼斯·蒂托所言,“太空不是宇航员的太空,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11]伴随时代不断朝前发展,太空旅游的全面普及化正距离人类社会愈来愈近。但太空旅游的普及,也就意味着相关旅游纠纷亦将很快随之浮现。身处这样一种新科技浪潮中,我们只有事先对此类纠纷的司法解决尽早规划,方能切实保障当事人正当权益, 顺利推动太空旅游业之健康有序发展。
注释:
① 不过这里的外层空间鉴于当前航天技术水准限制宜作广义理解。某些亚轨道飞行如美国维珍银河公司正积极筹备推广的“太空船一号”和“太空船二号”系列航天旅行飞行器尽管大部分飞行时间均在高度为100km以下的大气层空间内,但其火箭动力装置与传统飞机的喷气式发动机截然不同,故理应也视为外层空间飞行。
② 当然,考虑到目前航天技术尚远未臻成熟完备,出现改变行程、降低服务质量等纠纷的可能性相对较少,而因飞行安全问题遭致太空游客人身、财产损害的安全纠纷则可能相对较多。
③ 譬如首位太空游客丹尼斯·蒂托除观光冒险外,在“联盟TM―32”号宇宙飞船上还承担了相关无线电通信、导航与供电工作。具体可参见《富翁热衷太空探险旅游 带旺新型航天器开发热潮》,载《广州日报》2010年6月6日A13版。
④ 实质上,这种非《空间站协议》成员国公民进入国际空间站旅游探险已初现端倪。例如2002年全球第二位太空游客游览国际空间站的亿万富翁马克·沙特尔沃思就是非成员国南非公民,不过好在他同时还拥有成员国英国的国籍且未出现任何意外。
⑤ 因为《外空条约》第6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际责任”,《责任公约》第2条和第3条也强调发射国必须对其发射的外空物体应承担责任,故宇航实际控制国政府特别是发射国政府同样可能成为太空旅游纠纷被告。
[1] 薄守省.太空旅游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2009(3):26-28.
[2] 蔡高强.中国发展太空旅游的对策与立法建议[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2-35.
[3]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4] 文青.美国应建立完善的太空旅游法[J].国际太空,2005(11):17-20.
[5]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M].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周洪钧.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 阎忻.外层空间旅游法律问题探析[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
[8] 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06-507.
[9] 百度百科.太空旅游[EB/OL].(2011-07-12)[2011-7-23]http://baike.baidu.com/view/173919.htm#sub173919.
[10] 周丽瑛.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的法律问题[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11] Mangazine.艾瑞克·安德森:让太空成为所有人的太空[EB/OL].(2005-09-30)[2011-6-21]http://news.sina.com.cn/c/2005-09-30/115379092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