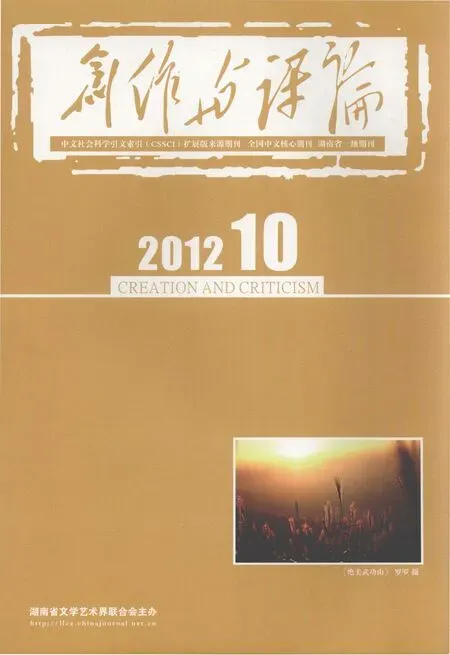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读王祥夫的短篇小说《颤栗》
2012-11-24陈进武
■ 陈进武
作家是要成为“在天上飞”的“鸟类”,还是做“在草间跳来跳去”的“昆虫类”呢?当代作家王祥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当然,他自己并不愿做——“茫茫大地在他的下方展开,闪烁的星斗在他的上方铺陈”的“飞翔式”的作家,而更“喜欢草间的风霜雨露”,因为“草草叶叶间能让人看到更多更质感的东西,和更多更细致更丰富的东西。”实际上,这样一些比喻式的陈述是想表达这样一种理念,即文学创作应该“贴着生活写”。①而他发表在《创作与评论》的短篇小说《颤栗》②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选择之下创作的。
其实,如果把大概两千字的结尾部分先去掉(只是先搁置起来),那么,整个小说就并不像题名《颤栗》那样会给人某种“颤栗”的感觉,反倒处处充溢着温情和善意,我们可能会说《颤栗》是一部关乎善的小说。至此,我们不禁会问:小说中的这种“善”体现在哪里呢?小说开篇,王祥夫这样写到:“怎么说呢,说到乱,再没有比火车上更乱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乱”法?王祥夫对此作了细致的描绘:“各种各样陌生的脸、各种各样陌生的声音、各种各样陌生的姿态,再加上各种各样陌生的气味,都会一下子朝你扑过来,会搅在一起把你裹挟住。”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人都怀有戒备心,人人都是谨言慎行,无疑,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的确会让人感到真正的“无所适从”,而这样的开始并没有透出丝毫的“善”。不过,在种种“乱”之后,王祥夫精妙地转了笔锋,温情和善意的情境便出现了——一个“结实、干净、红黑的皮肤”的中年妇女、一个才一岁零五个月的小男孩“澳门”、一个精瘦的老婆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这样主要的四个人及其言行便构成了“善”之场景的中心。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细节力量的推动之下而展开的,第一个细节是“于无助之中得助”,中年妇女抱着还没断奶的孩子,上了火车,但苦于找不到可以暂歇的座位,正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老婆婆善意的“招手”让她感到了安稳、温暖和感激。第二个细节是“从彼此陌生到认亲认戚”,这种“认亲认戚”是从老婆婆开始的,她向中年妇女介绍自己和小男孩是祖孙关系,并适时让孩子叫中年妇女为“姑姑”,这样甜蜜而温柔的交流,让中年妇女“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孩子”,自然不会带着一丝疑虑,保有一份所谓的戒备了。第三个细节是“给予家人的关心与呵护”,中年妇女把孩子“用了一块绣花兜布”牢牢地兜在了怀中,当她去上厕所时,老婆婆热情地说:“把咱孩子给我”,但中年妇女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了,不过,老婆婆并不“放心”,而是跟了去,守在厕所门外,一句“咱媳妇真不容易”,又一句“咱媳妇在里边呢”,这样一来,场景确也温馨——“人们都觉得她们是一家子,婆婆和媳妇”。此后,老婆婆的关怀进一步升级:抢着去打热水、主动要求给孩子喂牛奶、给中年妇女买来当做午餐的盒饭……遇到这样的好人,中年妇女感动不已,还表示“我要是有您这样的婆婆就好了。”第四个细节是“闲话家长里短”,老婆婆向中年妇女掏着“心窝窝”说话,叙说自己的苦楚:她做过下乡知青,参加过知青创业队,当过乡长和副县长,不过,为了“响应号召”而错过了生孩子的最好时期,只得领养孩子,可惜的是这些孩子长大后都“脑子不行”……这些话句句都紧紧地贴着中年妇女的心,她“忽然就觉得跟眼前这个老婆婆就更亲了。”这样一来,中年妇女把自己家的情况一股脑儿都掏给了这位看似善良、和蔼、可亲的老婆婆。当然,这里呈现的细节是否涵盖了小说所有的细部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在这样一些细节描绘之中,我们看到了王祥夫把握和建构细节的能力,有评论家曾经这样说到:“作家应该对生活中的细节具有异于常人的敏感,并有很强的对细节的记忆、加工、组织、营造和驾驭的能力……富有创意的、生气勃勃的、真实的因而也就是具有力量的细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说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就是一种尤为讲究细节的艺术,而王祥夫正是这样一位具备相当的能力来驾驭细节的作家,可以说,他小说的艺术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之上就是取决于这样一种极为出色的突出细节的能力。不过,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细节有力地呈现出了关乎“善”的一幕幕。
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王祥夫的《颤栗》仅仅是一部关乎善的小说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回到我们的标题“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以及其后加上的一个大大的“?”。在这里,我们又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会“不惮”?又“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看这句话的出自哪里,其实,这是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的,原话是“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③实际上,《颤栗》这部小说倒在一定程度上正契合了鲁迅这句话的某些意蕴,只是,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来看待,即“我们不得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当下的中国人的恶意”。在这里,我们需要把之前暂且搁置的小说结尾部分加以细读,这两千左右篇幅的文字一扫小说前面铺就的善意和温情,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恶、关乎恶的现实情境之中。小说中,下火车之后的老婆婆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她理直气壮地抢夺中年妇女怀中的孩子,且看看她对中年妇女说的话:“好了,就到这里吧,把咱孩子给我,让你累了一路”。(老婆婆对她说)——“把咱孩子给我,辛苦你抱了一路。”(老婆婆又说了一句)——“把孩子给我。”(老婆婆声色俱厉)——“把孩子还给我!”(老婆婆大声说,扑上去解兜布)——“还我的孙子!”(老婆婆扯住中年妇女)。当然,老婆婆并非孤身作战,那几个自称是老婆婆儿子的男人也开始喊道:“快把孩子还给咱娘,还给咱娘!还给咱娘!”最不可思议的是,连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也加入这场抢夺孩子的“战争”,他多次大声叫起来:“把我弟弟还给我奶奶,你这个大坏人!”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势单力薄的中年妇女倒成为了真正的“恶”的代表,而老婆婆等人却是“善”的象征了。在旁人看来,这只是婆媳两个不和所起的“争执战”,谁又会想到这是一个公然抢夺孩子的极恶事件呢?说到这种“恶”,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的动力的表现形式”,④当然,这里的“恶”自然不具备与“进步”相关的意蕴,这里的“恶享有着某种特权。它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坏蛋身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力量,而这是任何一位美德的使者望尘莫及的。”⑤毫无疑问,小说至此把读者带入了另一番天地之中了,比起那些关乎善的细节,这些恶的描绘似乎更让人心惊动魄,这些恶的代表人物似乎更“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说,这种“注意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作者自己以及小说中的所有在场人物),也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老年的妇女、中青年的男子、年幼的孩子——从不同的年龄阶段代表和诠释了“恶”。因此,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也不能够只是沉浸于善的享受之中,还需要或者不得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了。
到这里,我们“颤栗”了。无疑,王祥夫的《颤栗》这篇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类似于某种新闻式的报道)而又高于现实生活,小说从一个稀松平常的场景入手,却把这一场景写得水起风生,处处暗藏着伏笔,那个陌生的老婆婆及其所谓的一家人对孤身带孩子的中年妇女比亲人还要亲百倍,比真实还要真千倍,他们的所作所为蒙骗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最终是这个所谓的好心老婆婆凶性毕露而公然抢夺孩子,这时中年妇女才醒悟了,但所有人都以为她们是婆媳关系的缘故,而没有人管这事。幸亏得到丈夫周福生的声援,中年妇女才挣脱围困,才使得一颗被揪得紧紧的心松了下来。不过,在这样一个反差极大的情境中,我们却不得不感到颤栗了。王祥夫是一位老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经有丰硕的成绩。他的笔触多集中在表现底层,关注“社会底层卑微人生的个体日常生存”,⑥关注的是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被遗忘者”,这些书写可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来自于他的记忆,“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地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经实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⑦尽管《颤栗》并不是这类纯粹的源自“记忆”的“底层关注”小说,但是体现出了王祥夫倾心于“底层”的色彩,更体现了他创作的“问题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言:“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因为,有些人都没有谈问题的勇气。怀疑、问题、质问,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⑧《颤栗》所涉及的是当前较为普遍而又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问题,反映了某种社会之厄,可以说,从当前的小说创作情况来说,作家们难以拒绝现实社会或生活的诱惑,但是优秀的小说作品往往具有叩问永恒意义的能力,这就要求作家能够同情现实,又超越现实,既存在于现世的时间之内,又可以超脱于时限之外了。当然,王祥夫正是把这些社会问题巧妙地转换成为了以人为中心的主题,也就是说,王祥夫透视种种社会和文化变迁情境之中呈现的问题,从细微之处来把握时代的某一侧面,并以此深入到人性的深层真实。就《颤栗》而言,所触及的是当下社会之厄,深入到的是人性之恶,这也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颤栗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良善的老婆婆们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更体现了当前“人性的衰减”(洛伦茨语)趋向,如学者张光芒所说的是“人性根基丧失与人心文化畸变的互渗”,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们身上暴戾之气的弥漫;二是内心的虚弱与恐惧。当然,这种“暴戾”不仅仅是人性底线的缺失,不再有同情感和敬畏感及追求真善美之心,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种恶的存在,而这种“虚弱”和“恐惧”则在《颤栗》中那位中年妇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这种恶,她充满着恐惧之感(当然,这里也有遭遇没有预知事件下的茫然感)。其实王祥夫的许多作品大都倾注了这种人性的关注,但《颤栗》以冷峻写实的笔调和现实批评精神,以及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把人性之恶进行了深远的透视,这种现实干预和人性拷问产生了一种更为撼人心魄的震撼力量。
最后,不是说王祥夫的这篇《颤栗》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一部短篇小说能够有这样的现实力度,表现出如此的人性深度,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当然,我们所说的“可贵”还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如沈从文于1941年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讲演时说到的,短篇小说的处境“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而这种处境在当代中国文坛同样如此,王祥夫始终坚守中短篇小说创作阵地,这是非常可贵的。二是像鲁迅曾说的,“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⑩可以说,短篇小说的真正魅力是难以阐释的,这或许是短篇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所在,而王祥夫能够在这片领域常出精品,也丰富了短篇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注 释
①李云雷:《底层关怀、艺术传统与新“民族形式”——王祥夫先生访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
②王祥夫:《颤栗》,《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5期,第22-30页(文中作品的出处不再详列)。
③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④[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⑤[奥地利]弗朗茨·M.乌克提茨著,万怡、王莺译:《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⑥傅书华:《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3期。
⑦[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曹晚红、魏雪萍译:《自卑与超越》,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⑧王祥夫:《小说与农村》,《山西文学》1996年第10期。
⑨张光芒:《警惕互害型文化蔓延》,《人民论坛》2012年第7期。
⑩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