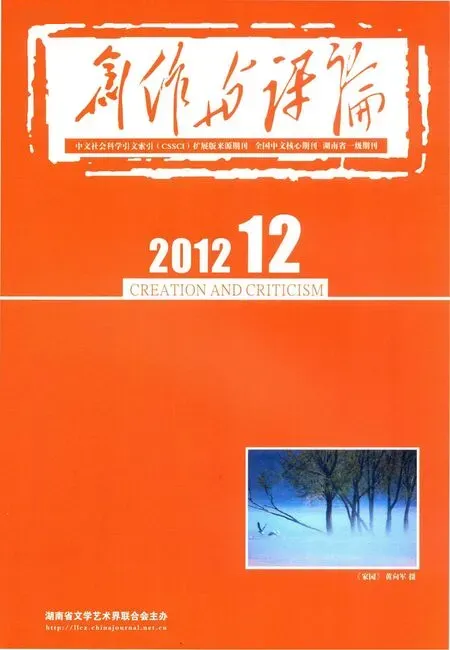新媒介时代的诗歌创造
2012-11-24冉华
■冉华
诗歌是人类精魂中伟大的情感传达形式。它对整个宇宙、人类生活做深入本质的思考,既强调忧愤深广而又追求着意旨悠远,也是将蕴含、寄托人类文明精微之要义和根本性思考融合在一起的文体形式。自进入电脑、手机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时代,以论坛、博客、微博客(M icroBlog)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媒介催生了新的媒介观念,建立在虚拟的网际空间里,从混为一谈的整体到部落化的群聚再到个体的私语,其实质也是人类精神的表达与诉求的一种演变史。虽然两者都是载体,可诗歌是一般的传统认知里严肃的文体形式,而诸如微博等新式样媒体却是属于散漫的一类。这二者之间,作为媒介载体的形式而言,是同质的。在当代生活中,微博这一类表现形式风靡全球,引领时尚。相对而言,诗歌这一形式却要低迷得多,似乎也成了放松和严肃在民众内心争价与角力的外在反应。如果从此处刨根究底,不难想见,在形式的一侧表现出来的东西应该也是时代精神与思想暗流的外在表现。但两者的同源性却在于:微博等媒介所代表的新时代向细微之处日趋靠近的时候,诗歌对精微之要义的追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始终坚信,一切优秀的艺术创造总与精心与细致相伴,而可喜的是——我们的时代由内而外均有向“精细”靠近的动向。
一“微时代”的内在特征
自从论坛、博客、微博等新生代媒体寄生在电脑、手机等通讯工具上以后,个体的表达权利得到了较大可能的实现,个人的意志得到较大可能抒发,人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个人的特征在这个新生的时代里得到更多的显现,时代就越发的是“微时代”了。
1.生命本能的存在感,微言大义的责任感
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处“微时代”精神的正向特征,即是生命本能、发乎自我的生命欲求以及个体理想层面的建设,而关乎细微的表现在每一个个体的微观层面——也即是日常生活状态的。发声和发言权利的要求,极大的鼓励着每一个社会个体不被作为他者的声音所掩盖。出于中华文明的礼乐熏陶下的中国人更加强调一种向内转的欲求和向内里收缩的克制,儒家文化为载体的人文实质所映衬出来的自我修养类型的内在责任的要求。这也是一种“微言大义”文化内涵的外在体现,以小博大的心理动机,以及对社会公权的情感宣泄,都体现在细微的时代思考力之上。而这种向内转强大的原动力以及所要求的责任感,与当代生活中那种个体之间信任感的缺乏形成了强大的对冲。
2.被动的乌合之众与若无所思的意见领袖
越困窘越需要表现的内心需求,我们似乎能感受得到。但是在新媒介时代,这种表现越发被夸张和放大。在新媒介时代的用户们更多的行动是点击“转载”、“分享”等按钮,而在“评论”的部分大多内容多是千篇一律的,诸如“好”、“顶”、“支持一下”等。这一类被动的思考也和主体的表现欲形成激烈的内在的碰撞。盲从与失望会引导着我们走向难以预言的深渊,那是一种随遇而安,以及伴随真理追求时无感的退让。
而在这个世俗化的革命年代,社会趣味与大众精英混杂在一起,精神革命与人文讨论潜藏起来。在微时代的大众认知里边,那些意见领袖多是时尚消费文化的青壮年人,或者是那些大众媒体各个行业的领袖人物。诸如“凤姐”、“春哥”等人都可以成为舆论和意见的引导者。舆论聚集中心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趣味里边被消遣的那一部分,也即是说,他们是带有消费性质的;而另一部分的社会精英是借着自身所寄托的机构,他们消费的是公众舆论机构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当代意见领袖由于时代精神的狭隘,自身的知识和技巧层面也缺乏足够的自信。由于影响力来源于一定的专业领域,他们的表达当然就具有自身所属学科领域的局限性。再者,就算不过多苛责他们自身的专业能力以及表达的影响力,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自身诉求也缺乏完全的自信。作为意见领袖,他们的思考是专业属性的,他们学习能力不强,但也不能不做出表达。他们人文追求不是惠及全人类的,做的也不是纯粹理性的考量,经常由于思考能力的不足,养成了这些若无所思的意见领袖。
二、诗歌作为一种创造
1.当代生活与当代的诗歌创造
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诗歌是精微的,是载道的。它做的是全人类文明的尖端思考,强调的是人类的先锋体验。而那个被称为“诗人”的群体,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强调独立思考和自在自为的表现。他们是英雄模式的思考,自在自为的独立,大度开朗的潇洒和风度;他们在喧嚣闹腾的世界里,他们依仗着自己淳朴的真心和强大的内心实力,无论外界怎样他们尽力做到内心的虚无和平静。在当代的社会生活里,他们凭着一己之力的勇敢,果断的抽打社会趣味的耳光。诗性精神自从人类产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着,它透露着人类向上、向前超越的原动力。在时代的进程中,诗歌可能无限风光;在有的时代的遮蔽中它也无法出头,不能抛头露面,做时代的弄潮儿。可是诗性精神,从来都没有消隐过,只要人类存在,对人类文明的探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谓之诗性长存。
可是诗歌要求的是极为精微的,追求的是那种细微的,无比细腻的内心思考和文明的理会。它强调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辞短短但意旨幽远,细微和精心是它终极的追求。载道的文明或者并不是人类文明极力所夸赞的,可是在当代的生存状态里,每个人都强调内心的存在,却无奈舆论主体自身的修养缺乏强大的内在力。但在当代,经历了诗歌风靡一时的八十年代的之后,现在的确已经沉寂下来,确确实实在某一角落里栖居起来了。但无疑,诗性精神总是不会潜藏着的,当它作为隐形存在的时候,诗歌也给出了隐含的启示。它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使命,亘古不变的探索精神命题的承载者,可是在中华文明当下的诗歌国度里,诗歌成为小众的,虽然从业者众多,但能够自信满满的人却少之又少。
2.危险时代:虚空的精神意志
跟我们的时代精神记述的一样,这的确是一个相对危险的时代,我们强调的是朴实、坦荡。诚挚内心的精神意志,尽可能不违背内心和原则,心与心血的追求和强调。那么我们真正能做到表里如一吗?当你内心虚弱的时候,精神缺氧的时候,是否也真能做到如实的表达出我们精神的困难和迷思呢?这可能对于大多数的表达者来说,是为难的;与其说是这些书写者的能力为难,毋宁说是他们的确强调写作之名义比对写作本身的强调更多。他们或多或少在意写作之上的附加成分,大有灵魂出窍的架势,可这就是这个时代印刻在每个从业者的身上的烙印。虚空意味着淘尽自己的灵魂,洗尽自己的铅华,让自己处在一种自在自为的生活状态里。跟我们惯常的文化心理有关,谦虚、谨慎是我们日常生活强调的伦理观念,也即是说明了再怎样强硬的文化心理也是难以强行突破惯常的伦理观念的。
所谓危险的时代,即是虚空的精神阻碍人们内在灵魂的追逐与参悟。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强调中庸的观念和意识,不太强调世俗的人们做极限的思考。而我们所言的诗歌,正是对极限、精深、别具一格的人文诉求加以突破和冲撞,它并不是对两极对立的二元模式的执着和刻意,而是强调做一种属于个人的自我表述权利的张扬,或者对大自然、生存感的维护和拥戴。可是追逐者得付出百般的努力,全心全力的追求,可人心容易劳累,在向上、向前的追求中,精神追求者难免精疲力竭、难免无力为继,那对于所有的强力追求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毫无选择的坠落和沦陷。而他们的战利品,可能也会收效甚微。这无疑会加重时代的危机感,诗歌创造也就难免会被隐匿起来。整个时代的灵魂是破碎的,他们对工具的依赖感很强,但是对作为载体的工具又缺乏基本的信任。偶然的孤独会让所有的参与者感到困难,强烈的挫败感会让他们迷失在去往寻找人类最终极文明的追逐和思考的路上。
三、“微时代”与诗歌最近的距离
虽然我们处在一个精神贫瘠的年代,但并不碍事,因为那些脆弱的年代依然足以让诗歌的状况好起来。微时代里的人们披荆斩棘,谨小慎微,一点点的求以生存,这是自知式微的表现形态。但是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欲求而言,越微小却反倒有可能激发出更大的能量。精微的心灵是属于诗歌的,作为媒介载体则是以精微、小巧为主,这恰好构成了精微的心灵和细微的形式的组合。微时代继续前行着,微媒介所携带讯息显性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诗歌却潜藏起来,在背后着力。两者相互的行走着,或者在等待某一刻的相交、瞬时的迸发,我们期待这样伟大的时代的重合点,必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进步重大的时刻。诗性精神的传承,牢牢的粘贴在现代传媒的载体之上,这颇具现代意义和现代性的文明的开拓价值。作为期待者,我们怎样去完成这样一次史诗性质的、现代底识的突破呢?
诗歌原来不是载体的,它是作为文体本身;而在当代的文化语境里,诗歌的触发点和敏感点在于怎么突破作为传播媒介的讯息本身。
1.从俗还是朝圣的?
对于大多数的个体来说,我们的确需要良好的自我认知,并不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够承载大型的思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平凡者,并非每个人都是精英,虽然在社会生活给予的压力之下,我们都是共同的受害一方。当我们营营苟苟经营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是平凡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承载着尖端、极限的思考,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的避免生活上的摩擦和碰撞,在一些无所谓的问题上去争执,避免那些无所谓的能量消耗。戒掉个体在微小生活中的浮躁,时代的精神也就能随之而抛去铅华。朴实的社会风气是好的,因为社会生活的进程已经趋于细微化,只要社会心态趋于平实,这种平民生活化的状态将极大可能促进诗的创造。避开那些不负责任的虚伪精神负载,当然也不是直接地回避崇高。我们只要保持其内质不变,作内心与人格的升华和强化就可以了。在急速前进和社会转型期里保持平静的内心,那才真是时代风潮的体现。
当我们的时代用无数小说标题去网罗一大堆现实生活的时候,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对诗意的无限浪费。因为我们只要用微小的诗歌命题就能说明数以千计的生活琐事。但这也无不暴露出我们能力的缺陷,我们确实缺乏持续的诗歌创造能力。至于原因,莫不是我们的内心缺乏恒久的耐心,缺乏对生活的热爱,那种持续的、连绵不绝的能动力。究其根源,也是指向了我们对精神和灵魂的本源的思考能力。对生命本源的思考缺乏耐心和持续力,就会让诗歌的命题难以为继,也许我们并不太刻意强调那种损坏生命的爆破式推进,但是与微时代的特征相应,我们在耐心的基础上还得加强细腻的锤炼。当我们初识大体的时候,我们得有耐心的走到问题的精深之处去,那就是思想的火花了。对生命的珍视和爱戴,对精神追求理路上极大的挑剔,这就是诗歌的本来埋藏。当我们从人文精粹的部分游走了,远离了思维的真核部分,艺术存在感觉也不在了,人类的诗意就无法栖居了。
2.作者比读者多,集合还是散沙?
在新媒介时代,我们才逐渐真正的体会到了以前时常说的“作者比读者多”的尴尬。以前把这句话用在诗歌上,颇有点嘲讽、羞辱的味道;可如今对于大多数的新媒介的使用者来说,这种嘲讽无疑不彻彻底底的反弹在他们身上。其实对于人类追求的精神文明来说,作为表达者和受众都相差无大,差距只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自身对人、事、物的体会。就将刚才提及的那句揶揄之语夸大一点,大多数人都成为了作者,只有少量人是读者,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人类的群聚社会里,部落化、族群化是鲜明的,但也不可能绝对的单一化,孤立起来,因为后者不符合正常人类的健康心理培养。“媒体的新姿态:你‘关注’的人应超过‘关注’你的人”。①强调作者的少数,意味着大多数人对自己失语和表达得到的尊重程度并不满意;强调读者的多数,其实质突出的是个体内心的愤愤不平。两者均不是一个良性的作者和读者的组合,我们大约可以猜想它们恶性发展可能会有的抵达:一群乌合之众和一盘散沙。
3.碎片化的信息源与破碎的灵魂
这确实是一个依靠话语和表达效能就决定文化心理承载的社会形态,但我们的谈吐平台是建立在虚拟的网际平台之上的,我们的信息源是零散的,我们的思考是被动的,我们思考的内容是碎片化的信息。灵魂的空虚和无底的探求,导致我们也很快适应了这种快去快来的生活模式,也养成了回避崇高的生活状态以及对真理探求源动力挖掘的动力,也就导致了我们追求动力蓄力的不足。
由于甘于长久以来的表达压抑,对现实和现状的长期乏力的审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立刻获得了表达之权。可是我们难免会习惯性的对社会趣味言听计从,对时代诉求的承载难免乏力。伴随着工商业社会对农本时代精神的替换,我们对身上的那些封建年代的积习容易感到莫名的忧伤。这就是我们时常所言的那种空虚悲伤感的由来,我们眼高手低的入世,却很快堕入了快去快从的消费时代的流程里。除过空虚之外,我们一无所剩。
如西方“新批评”一派倡导的观点所说,焦虑成诗,也如我们的古人说的忧愤出诗人。可是当我们过度的消遣自己的灵魂和精神的时候,我们难免堕落成性,无以为诗。建立在微时代的语境之上的个体和族群之间,必须得尽可能快的加强对自我诉求的定格和完善。因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必然是那些系统的、思想的、理想的诗歌格调兼以自身修养的品味和完满的期待心态。
四、大众之业与小众之诗
时代的问题是,似乎我们的微言大义的欲望被提起来了,可是我们仍难以改变我们人微言轻的命运。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大众来说,他们的精力更多的消耗在对自我的盲目冲撞的过程中了;当面对真理指导的时候,总是显得无所事事和随遇而安。电子时代的技术革命对大众的洗脑,是让其在快速转换中,让人无尽的虚空,产生一种不在当代的感觉。“对于微博来说,其最为核心的功能就是信息的发布与获取,这两种应用分别对应的是微博信息的发布者 (微博主)和索取者。”②我们习惯性的出于一种缺席和不在场的样子,这就是穿越剧和科幻剧很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的思考场域要么超前,要么落后,我们就很难立足在当今这个时代做静静的思考。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
似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东西已经征服了我们,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却望尘莫及,诗歌也就缺乏存在的基础了。在微时代里,我们渐渐可以接受这种情感上的不对等了,这就是时代带给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心态才会变得从容与平和。媒体介质的价值在于,虽然是通过实用的器物构建了虚拟沟通平台,其实质是通过形而下的器物向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上的构建。也就是说,通过了这中间一层的转换和比较,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表达效果和内容不再针对起来。
我们所期望诗歌时代的来临,无非是建立在这种对科技载体、讯息媒体和人的内心结合起来的基础之上。可微博等接点类型的媒介尽可能的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学会分享与倾听,这似乎已经是诗歌创造最大的源动力了。“此外,微博的碎片化信息恰恰成为我们获取灵感的绝佳来源,也可以说是新闻爆料站。”③这儿也可以说成是诗歌创造最好的驿站了,因为强烈的表达欲也的确会促进单个个体的创造能力和创造动力。我们期待媒介工具与人的内心以及时代的机遇精微的牟然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积极憧憬的心态。时常可以看见的是,人与人有冲突的时候,面对面的反应可能要激烈得多;当我们共同的诉诸于媒介平台之后,我们就显得礼貌多了。假如让虚拟的媒介承载一些我们负面的情绪,只要创作主体在自我的思考中投入多一点,把诗歌文体不经意的解放出来;哪怕是小众的诗,似乎大众的业绩也是可以追求的。
注 释
①③韩晓芳:《微博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编辑之友》2010年第2期。
②喻国明:《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