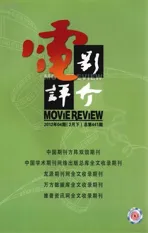香港电影中移民形象的“他者”审视
2012-11-22张莹
在以移民为题材的香港电影中,张婉婷执导的“移民三部曲”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对移民形象的“他者”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移民三部曲”到九十年代的《人在纽约》《红番区》《甜蜜蜜》,“他者”始终是移民题材电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形象,作为人类学中的一个术语,“他者”是对移民群体的异邦性的高度概括,而对“他者”的审视则是一种对关乎人自身的生存价值与文化内涵的表达,这种表达在电影中主要从身份表达、存在价值、人文内涵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他者”的身份表达与城市空间
“电影中的城市,并不是现实中城市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因为究其本质,电影所建构的空间是一种由二度平面形成的空间幻觉,是一种想象的产物。”[1]在香港移民题材的电影中,这种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空间幻觉与移民形象不可分割,繁华的异地城市往往作为电影中最为耀眼和醒目的背景,突显出“他者”客居异地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折射出其中形形色色的价值选择和个人追求。由此可见,影像在呈现出城市空间与“他者”形象的多方面联系的同时,实质上是在完成一种诉诸于国族认同的身份表达,这种表达在相关电影中从边缘化的城市奇观,街道的想象以及城市空镜头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边缘化的城市奇观,展现的是国际大都市最底层,最阴暗的一面,纵欲,犯罪,结党斗殴,一系列暴力与色情的展现使得城市的边缘地带在银幕上呈现出奇观化效果。边缘化的城市奇观不仅呈现出移民复杂艰难的生活环境,更是一种移民作为“他者”的尴尬无奈的身份表达。
《红番区》中的纽约红番区就是这样一块鱼龙混杂的地区,充斥着各种不安分因子和地下非法交易,无业游民白天堂而皇之地抢劫国外移民在当地开的超市,晚上混迹在街头和各种娱乐场所。成龙所饰演的陈汉强在第一天来到红番区,就目睹了暴走族深夜街头飙车扰民的情景,之后又被卷入黑手党之间的不法钻石交易,陈汉强和来自香港的移民们甚至差点在这次不法交易中沦为牺牲品。由此可见,《红番区》中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他者”作为弱势群体,只有抱着“少管闲事”的态度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他们与来自中国香港的警察汉强形成鲜明对比,成龙一如既往地诠释着正直善良,除暴安良的英雄警察形象,然而在成龙式英雄拯救的光环下,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的移民仍旧无法改变作为二等公民的“他者”身份。与《红番区》主张世界各地公民平等的主旨不同,影片《非法移民》中唐人街帮派之间的互斗并没有在一种张扬主人公英雄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消解,影片结尾时对唐人街酒吧中枪击事件的表现,惨烈逼真,镜头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他者”身份不可逃脱的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街道作为城市空间中具体的建构元素是电影画面中参与表达的空间元素。哈顿曾经对街道做出这样的阐释:“人与物之间的中介——街道是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在街道上,主体与客体、观看橱窗者和娼妓、精神空虚者和匆匆过路人、梦想与需求、自我克制与自我标榜在不断接替。”[2]如果说,街道对人与物的承载还仅仅是表象的话,那么,街道的想象所揭示的则是表象背后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他者”与街道的联系主要有两种:疏离与国土想象。
关于疏离,最典型的画面是在《秋天的童话》中,当钟楚红安静地坐在公交车上时,一边的美国大街繁华的街景像浮光掠影般呈现在车窗玻璃上,车窗内的人与车窗外的街道相互映衬,呈现出的是一种永远无法融入的疏离感和异地感。最能体现国土想象的典型个案则是《甜蜜蜜》中黎小军骑自行车的景象,离开香港移民到美国的黎小军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美国汽车林立的街道,显得格格不入,黎小军曾说:“在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就好像在天津一样。”在充满怀旧气息的《甜蜜蜜》中,黎小军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一次次的完成了“他者”的国土想象。
二、“他者”的存在价值与个体性
个体性是“他者”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是隐匿在“他者”生存困境背后的精神价值的体现,也是“他者”审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者”个体性可大致分为丧失主体性的“无依者”,自尊自强的“奋斗者”,安于现状的“生活者”三种。
丧失主体性的“无依者”是指主体价值缺失的“他者”,移居海外的移民在异邦始终无法找到“自我”或者逐渐丧失“自我”。《非法移民》中的张君秋是一个始终无法找到“自我”的典型,他在大陆没有户口,在香港没有身份证,在美国没有绿卡,因此,张君秋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存在证明的人。终于可以通过结婚来取得美国的绿卡,可是在最后关头,他却在一次帮派互斗中失去了爱人,同时也失去了办绿卡的机会。朋友告诉他还可以去移民局买死人未报销的绿卡,不过这样一来“张君秋”就是另外一个人了,直接道出“他者”丧失主体性的悲剧性命运。《人在纽约》中的赵红则是逐渐丧失“自我”的典型人物,她第一天嫁到美国就被丈夫汤玛斯要求说英语,随之而来的是话语权也在一点点地消失,而生活上对男性的完全依附也使她作为女性个体价值开始丧失。尽管赵红不像张君秋一样为生活发愁,但是却一样逃不过丧失自我的悲剧性命运。
自尊自强的“奋斗者”是带有梦幻色彩的“他者”,他们通常积极乐观,极具开拓精神。《秋天的童话》中的船头尺是自尊“奋斗者”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对李琪说:“我是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还有自尊。”船头尺不依附任何人,也不妄自菲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完成梦想,在海边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虽然电影刻意淡化了船头尺创业的奋斗过程,但是他所一直坚守的有尊严地活着的信念和决心却是令人印象深刻。《人在纽约》中的李凤娇则是一位自强的“奋斗者”,颇有经济头脑的她孤身一人靠着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服输的信念在纽约唐人街打拼,终于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安于现状的“生活者”是安安稳稳生活在异乡的“他者”,他们沿着自己的生命轨迹亦步亦趋,平静地接受生活的一切给予和掠夺。电影中这样的“生活者”很多:《红番区》中渐渐适应移民区生存规则的伊玲,《甜蜜蜜》中安分守己,踏实工作的黎小军,《八两金》中平凡的出租车司机。这一群看似平凡的“生活者”,实质上是将中国人身上特有的隐忍的民族气质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群人。
三、“他者”的人文内涵与历史烙印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移民题材电影中的“他者’”审视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殊历史文化的烙印。异邦与本邦的文化冲突,移民潮的反思,个体情感困境的揭示体现出的是对生活在夹缝中的个体存在的普遍矛盾性的反省和思考。站在历史的高度,电影中所体现出的人文内涵是对“他者”群体的深层观照。
异邦与本邦的文化冲突势必会产生一场跨国的文化对话,这种跨国的文化对话通常是发生在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他者”身上。最具代表性的是《人在纽约》中的黄雄屏,她是一位在美国发展多年的戏剧演员,看似早已融入纽约生活的她,内心却始终彷徨于中国文化和异国文化之间,国土文化像根一样始终挥之不去,而外来文化却像空气一样天天充斥在自己的生活中,但始终无法真正融入。黄雄屏在对赵红提起中国自古对同性恋就报以宽容的态度时说:“你不信,《汉书》上就有,我在国内是念历史的。”而当美国人面试官问她,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来演麦克白夫人,她说起了中国汉朝的吕后。吕后与麦克白夫人,中国历史与外国戏剧,黄雄屏始终无法抹去内心深处的中国文化烙印,于是在一次次的衡量与比较中,本邦文化与异邦文化产生一次次的碰撞。
可见,文化冲突中的“他者”作为一个矛盾混合体,本身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碰撞和对话,而实际上这种对话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两全效果,除非一方甘愿做出妥协。
香港移民题材电影中对“他者”情感困境的关照体现出的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也正是“他者”审视最终回归到“人”的文化价值之所在。“他者”是一群生活在夹缝中的群体,不论是否拥有地位、财富或是学识,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性是不可能消解的。地域上的分离和情感上的疏离往往使“他者”在面对生活时不得不陷入困境,他们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或者无奈地向现实妥协,与真情擦肩而过,尤其在一些具有较高文化品格的电影中,对“他者”情感困境的关照通过镜头呈现出一丝脉脉的温情和时间沉淀的厚重。《八两金》中的男男女女遇到的是“围城”似的困境,移民海外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内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出来的男人遇到了进去的女人,即使彼此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也只能擦肩而过,至少此刻,他们只能彼此错过。《人在纽约》中看似坚强的李凤娇,身处异地的寂寞和苦闷曾经让她徘徊于女人和男人之间,而当爱情真正到来时,一直渴望获得真情的她却被爱情拒之门外。于是,我们看到了张曼玉的掺杂着茫然与酸楚的脸庞,在驱散寂寞和寻觅爱情之间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甜蜜蜜》中,迷茫失落的漂泊感也曾使来自大陆的黎小军和李翘对情感产生强烈的渴望,于是他们情不自禁地相爱,但是陷入了道德困境的他们,最终在现实面前选择了分开。直到邓丽君逝世,她的歌声在异国街头响起,黎小军和李翘才再次相遇,此刻,九年的沧桑和辛酸历历在目,而镜头中的两人却相顾无言,唯有笑。寂寞与空虚使得“他者”对情感极度的渴望,然而“他者”身上同样背负的道德重担,中国人的“仁”,使他们学不会决绝,因此,“他者”在面对情感困境时往往陷得更深,付出的更多,徘徊,犹豫,妥协,放弃,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在对“他者”情感困境投以深切人文关怀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丝反观自身的悲悯情绪。
香港移民题材电影中的“他者”审视是一种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审视,从“他者”的身份表达,到个体的存在价值,再到人文内涵的揭示,这样一种审视通过影像表达出来,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深沉厚重且耐人寻味。
注释
[1][2]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⑴ 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⑵ 黄剑波《文化人类学散论》,民族出版社,2007。
⑶ 张燕《映画:香港制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