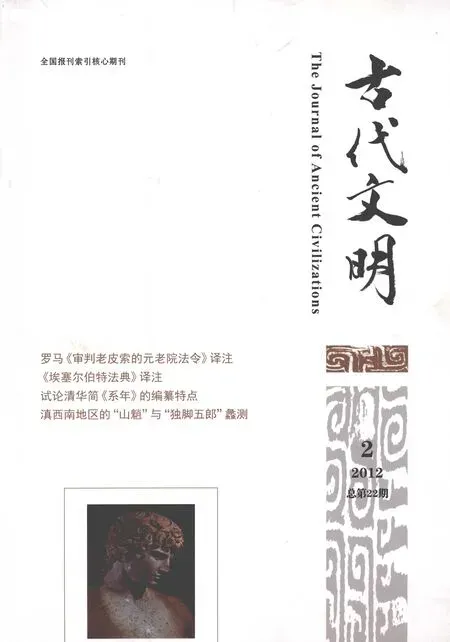爱尔兰宗主权之争——从《祝祷书》到《抗议书》
2012-10-22王云龙
王云龙
一、《祝祷书》是教皇个人的书写行为
上帝仆人的仆人阿德里安主教向主最恩宠的儿子——杰出的英格兰国王,致以崇高的敬意与使徒的祝福!
如同任何一位基督教王公一样,陛下令人敬佩地致力于彰显主的荣耀与拓展教会的边疆,向野蛮蒙昧的民族宣喻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在大地上根除罪恶的莠草,增添天堂永恒之福的护佑。为达此目的,你征询教廷的建议,寻求教廷的支持。教廷确信,你的目的是高洁的,你的行动是审慎的,主赐福于你,你的成功指日可待,因为它源于信仰的热忱与对主的热爱,将无往而不胜。
爱尔兰(Hibernia)及所有岛屿必须沐浴在主的公正阳光下,接受主的信仰与教义。这就是我们在那里播散信仰上帝的种子的原因。你,主最恩宠的儿子,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进入爱尔兰岛的决心,使那里的人民遵从法律,根除那里罪恶的莠草。你决意从那里每户的年贡中,拿出一便士,奉献给教廷。
我们赞赏你的虔敬与令人敬佩的决心,赞同你的行动,认为这是主乐于看到和接受的。拓展教会的边疆,扼住邪恶的洪流,革除罪恶的风习,播撒美德的种子,光大基督的荣耀,你进入爱尔兰,力行一切有益于光耀主的圣德与救赎的行动,务使那里的人民尊你为可敬的君主。同时,维护教会毋庸置疑的、圣洁的统一,从每户的年贡中,拿出一便士,奉献给教廷。
12世纪,罗马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之争日趋白热化,以上帝的名义,教皇处心积虑地抬高自己的权力,压低世俗君主的权力,推行教权高于君权的政策。《祝祷书》内容是教皇对于世俗君主拟制封建关系(quasi-feudalism)的文本,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不是世俗君主行为,而是教皇把爱尔兰人民分封给了虔敬的基督徒亨利二世;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是受托于教皇,并且向教皇缴纳岁贡,履行封臣对封君的义务。这当然是阿德里安四世一厢情愿。阿德里安四世从1154年—1159年担任教皇,只有四个年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为了维护教权,先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西西里国王 “恶棍”威廉发生冲突。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当然不是尊崇教皇、履行封臣的义务。
从载体来看,《祝祷书》不是写在教皇敕令专用的公牛皮上,而是写在教会通用的羊皮卷上。首刊《祝祷书》的威尔士教士吉拉尔杜斯八卷本《著作全集》,是在教会羊皮卷文献主管指导下、由圣库传教士团编制而成的。正是由此,《祝祷书》始被冠以教皇敕令。
《祝祷书》受到英格兰的欢迎,激起爱尔兰的抗议。
二、《抗议书》全面反驳《祝祷书》
1317年,自封为“阿尔斯特国王”(King of Ulster)的唐纳德 •奥尼尔(Donald O`neill)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致信并附以《祝祷书》誊写本,史称这封信为《抗议书》()。阿尔斯特(Ulster)是爱尔兰古代省份的盖尔语名称,英格兰入侵后成为爱尔兰的代名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是阿维尼翁教廷的第二代教皇,首鼠两端,处事圆滑,没有直接答复唐纳德•奥尼尔的《抗议书》,而是就《抗议书》分别致信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和教廷驻英大使。1308年—1377年,罗马教皇驻留法国阿维尼翁,托庇于法兰西国王,表明教权在与王权的角逐中落败。罗马教皇高于世俗君主的普世权威一落千丈,风光不再。因此,爱尔兰的奥尼尔无所顾忌地上书现任教皇,直斥前任教皇,逐条批驳《祝祷书》。
针对《祝祷书》宣称英格兰入侵爱尔兰是“使那里的人民遵从法律,根除那里罪恶的莠草”,《抗议书》指出,正是英格兰入侵者把爱尔兰人当作异教徒,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杀一个爱尔兰视同杀一只狗或其他的畜生。《抗议书》否定了英格兰征服爱尔兰的法理方面的合法性。
针对《祝祷书》宣称英格兰入侵爱尔兰是“进入爱尔兰,力行一切有益于光耀主的圣德与救赎的行动,务使那里的人民尊你为可敬的君主”,据此,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抛开在爱尔兰定居的英格兰代理人,意图直接统治爱尔兰,《抗议书》指出,无论我们,还是我们的先辈,既没有效忠爱德华二世,也没有效忠爱德华二世的先辈。《抗议书》否定了英格兰征服爱尔兰的公理方面的合法性。
三、两个文本的历史语境辨析
历史文本研究实际上是历史语境的辨析,《祝祷书》与《抗议书》形成了历时性对立关系,对立的焦点是爱尔兰的宗主权(suzerainty),不是民族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宗主权是封建制度的权力形式,《祝祷书》以赋权的形式,强调教皇对于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普世宗主权。《抗议书》以申论的形式,重申爱尔兰本土的世俗宗主权。《祝祷书》不能成为后来的大英帝国占据爱尔兰的神圣合法性的根据,《抗议书》也不能为新芬党等现代爱尔兰民族独立政党及其领导的运动提供历史性依据。
两个文本是封建法范畴内的对立,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无关。《祝祷书》的历史语境是依据《君士坦丁奉献》(),11世纪教皇权势达到鼎盛,俨然是西欧封建主义世界的天下共主。首次依据《君士坦丁奉献》,以教皇敕令的形式提及的地方是,1051年教皇立奥九世(Leo IX)在《宣教谕》()中言及的意大利托斯卡纳群岛最北端的戈尔戈纳岛(Gorgona)。无独有偶,一个世纪后,阿德里安四世写下《祝祷书》,将爱尔兰主权给予亨利二世是教皇自以为是西欧“天下共主”的观念使然。《抗议书》在尊重教皇普世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唐纳德•奥尼尔是爱尔兰一脉相承的王统的真正继承者,强调爱尔兰基督教传承的合法性与纯正性,全面批驳阿德里安四世《祝祷书》,宣布英格兰进入爱尔兰是违背基督教神圣正义的。这是依据历史的宗主权的申论,是典型的封建法的表述。两个文本都是基于宗主权的言说,《祝祷书》是普世宗主权的言说,《抗议书》是地域宗主权的言说。两者关涉的既不是国家主权,也不是人民主权,只是普世封建主与地方封建主的笔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风云际会之时,新芬党创党集团中,以吉内尔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在继承爱尔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系统地构建了爱尔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谱系,把爱尔兰民族的发生上溯至古代凯尔特文化,从根本上划清了与英格兰的界限,把凯尔特—爱尔兰文化与经历罗马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诺曼征服一路走下来的英格兰平行并置。进而由文化言说,上升为合法性言说。在这种历史与合法性叙事中,《祝祷书》与《抗议书》由历史文本变成历史事件。爱尔兰民族文化是爱尔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源泉,解构《祝祷书》、伸张《抗议书》是爱尔兰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前提,也是新芬党爱尔兰民族国家合法性言说史学的基础。但是,从文本的史实性语境来看,《祝祷书》与《抗议书》均不足以承担爱尔兰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构建的重任。文本解读亦即历史释读,这是历史科学的史学与其他一切类型史学的根本区别。因而,基于历史科学的立场,既不可一厢情愿地把《抗议书》看作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历史宣言书,也不可望文生义地把《祝祷书》看作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授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