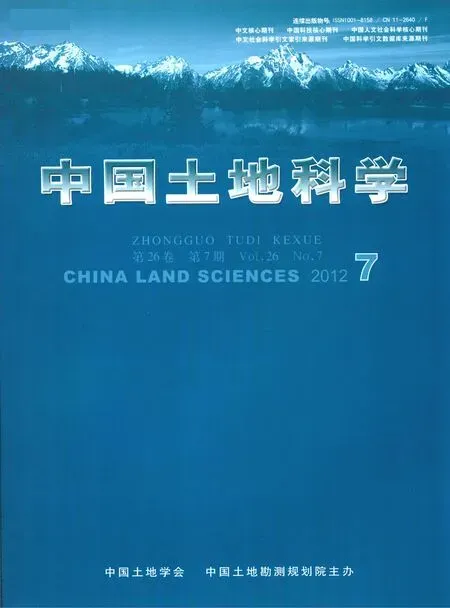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划定方法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
2012-09-23陈飞香苏少青胡月明缑武龙程家昌吴顺辉
沈 明,陈飞香,苏少青,胡月明,缑武龙,程家昌,吴顺辉
(1.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广东广州510075;2.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广州510642;3.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4.广东省土地开发储备局,广东广州510635;5.广东友元国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642)
1 引言
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有全民共识的国家战略决策[1]。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国土资源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中明确规定各地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中,要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整备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点区域及重大工程,以及土地整治规划所确定的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及重大工程、基本农田整理重点县等列入建设重点区域。这些重点区域分布在省内各个县(市),数量众多。为做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更好地指导全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要从以上众多的重点区域里选出省级建设重点区域。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的确定,既是省级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省有效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重要保障。日前,《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已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并实施,全国省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进展顺利[3],如何确定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显得更加重要。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基本农田的划定主要从土地评价、GIS技术、宏观政策层面等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李赓等从基本农田的特点出发,建立了划定基本农田的指标体系[4];孔祥斌等依据农用地利用等别成果,借助聚类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进行基本农田划定和保护研究[5];石英等利用属性层次模型,通过耕地综合质量排序和耕地入选两个决策过程划定基本农田[6]。基本农田划定是土地质量和土地生产潜力等的综合评价[7-8],需要考虑各个方面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价因子,这些因子要涉及土地分布、区位、土地利用协调性等多项指标[9]。相关研究还有对大都市边缘区基本农田功能特点的界定及其划定方法研究[10]、利用GIS技术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划定基本农田地块[11]、结合农用地整理规划探讨基本农田划定[12]等。国内学者对基本农田划定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级区域[11,13-15],这些研究成果为县级基本农田的确定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依据,但是,现有文献对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域,以及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如何划定鲜有研究。因此,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划定方法,确定全省重点建设区,以期为编制省级土地整治规划及推动全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应包括:(1)集中连片、规模较大的基本农田集中区;(2)土地整治潜力较大、整治效益明显的区域;(3)各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同时为便于开展工作,省级重点建设区一般不打破县级行政界限。在此基础上,笔者采用特尔斐法选择确定评价指标,应用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在进行评价指标量化后计算综合评价得分,最后根据综合评价得分确定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
(1)评价指标确定方法——特尔斐法。选取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划定的指标不仅要反映耕地资源禀赋,还应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特殊性进行考虑。因此,反映客观并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的特尔斐法,成为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
(2)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因素成对比较法主要通过因素间成对比较,对比较结果赋值、排序,是系统工程常用的—种权重确定方法。为准确反映各因素的重要性差异,常采用多种赋值方法,如按相对重要性程度在l内进行分割的比例赋值。无论采用何种赋值方法,应用都需注意:①广东国土资源年鉴编委会。广东国土资源年鉴(2011)[Z].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1.所有因素均要进行两两比较;②重要性关系要符合成对比较法的前提(A>B,B>C,则A>C)。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域与资料来源
3.1.1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属于东南丘陵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东北部和西部都有较高山脉,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为低丘、台地或平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大陆海岸线长3368.1 km,居全国第一位,沿海滩涂资源十分丰富。
广东省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重,管护压力大。据土地调查统计,2009年末广东省基本农田面积为285.00万hm2①,而根据广东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下达广东省到2020年全省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255.60万hm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规则期间落实保护任务的难度将增大,同时,耕地质量下降,中低产田面积大。全省地力监测结果表明,土壤肥力和灌溉设施较好的高产稳产农田不足40%,中低产田占60%以上。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的发展,工业和生活“三废”排放量不断增加,基本农田质量提高的压力加大。
3.1.2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自于课题组于2011—2012年参与的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专题研究编制工作中的相关数据,包括2010年全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数据、广东省相关规划数据、全省近年经济社会数据等。
3.2 特尔斐法确定评价指标
在咨询前期,专家们拟定连片指数、耕地等别、粮食生产能力、水利设施配套、政策支持情况、耕地整治潜力、农业生产禀赋共7大因素作为评价指标。经分析,耕地等别的确定是以早期的农用地分等成果为依据,数据现势性弱;单个地块的粮食生产能力很难一一体现,改为可以反映地方对粮食生产重视程度的粮食生产政策;水利设施配套和农业生产禀赋难以量化;政策支持情况的概念过于宽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前期推动与后期维护需要地方具有强有力的财政能力;连片指数的计算涉及数据众多,主要面向后期的大比例尺的重点工程建设,对前期的省级层面的整治规划及建设重点区域划定而言,工作量过大而价值不明显;考虑生态环境对建设重点区域的影响。经反复咨询,增减相关评价指标,最后确定耕地整治潜力等6项作为评价因子,并具体界定连片程度等因子内涵,以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反映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劣等。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3 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表1中6个影响因子按照因素对比法进行两两对比,由专家给出每两种因子的重要性对比值,然后利用式1求取各个对比值的平均值。

然后,计算出各比较值总分,并最终得到各个影响因子的权重值。具体公式为:

因素成对比较法最终确定的因子权重如表2所示。

表1 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域划定的评价指标Tab.1 The indexes for the zoning of key areas of high-standard primary farm land development at provincial level

表2 因素成对比较法所确定的因子权重表Tab.2 Factor weights determined by paired-factors comparison method
3.4 影响因子的量化
3.4.1 耕地整治潜力 耕地整治潜力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大小与土地利用现状密切相关,取决于某一地区当前生产力水平和耕地整理标准[16]。本研究以耕地整治的可实现利用潜力与新增耕地面积作为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依据。其中,可实现利用潜力等于耕地实际产能与可实现产能的差值;新增耕地面积用新增耕地系数表示。利用样点数据确定广东省各县新增耕地系数,结合计算得到的各县可实现利用潜力,将全省耕地整治潜力分为三级,其中,新增耕地系数大于2.0%或可实现利用潜力大于7000 kg/hm2的划为一级潜力区、新增耕地系数小于1.5%且可实现利用潜力小于4500 kg/hm2的划为三级潜力区、其他各县(市、区)划为二级潜力区。全省116个县(市、区)中,耕地整治潜力一级30个,二级55个,三级31个。量化原则为潜力一级的县(市、区)赋值100分、潜力二级赋值80分、潜力三级赋值60分。
3.4.2 水土资源匹配程度 通过水土资源匹配系数进行反映。水土资源匹配系数是指表征特定区域农业生产可供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在时空上适宜匹配的量比关系,采用单位面积耕地可拥有的水资源量来表示[17]。区域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分布的一致性与量化水平越高,其匹配程度就越高,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就越优越[18]。本文采用广东省2000—2010年各年度水资源年报数据、2010年耕地数据,运用式4计算得到全省各市水土资源匹配系数,采用均值标准差法将全省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划分5个等级,等级划分标准与量化见表3。

式4中,Ri为市域水土资源匹配系数;Wi为市域水资源量(亿m3);Li为市域耕地面积(万hm2);a为市域农业用水比重。

表3 广东省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分级表Tab.3 Classification for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3.4.3 耕地连片程度 以广东省2010年1∶1万乡级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基础,在不打破县域行政界线的前提下,分别以相邻图斑与空间距离100m以内为条件对基本农田图斑进行融合。鉴于广东省在2000—2010年期间完成验收的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符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要求,根据整治规划要求和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该类项目不列入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因此将融合所形成的图层减去上述2010年前完成项目的基本农田整理地块,得到未来将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图斑,其图斑面积即未来需建设的总面积。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对这些图斑进行面积分析,确定以连片面积大于40 hm2的地块作为连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耕地连片程度即这些连片地块面积与基本农田总面积的比值。
耕地连片程度因子得分=未来建设连片基本农田面积/未来建设基本农田总面积×100
3.4.4 粮食生产政策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目标是建成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地方政府是否有压力和动力去推动粮食的高产稳产,与粮食生产政策密切相关。为确保这项政策的贯彻落实,逐步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中国采取了面向产粮大县,包括财政奖励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促进广东省粮食生产高产稳产,广东省采用评选省级产粮大县的方式促进相关县(市、区)的粮食生产工作与政策落实,故本研究以是否被评为省级产粮大县作为粮食政策因子得分的衡量。广东省政府授予全省40个县为“省产粮大县”称号,并将产粮大县建设列入省政府工作重点,对这些产粮大县2009—2013年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做出了具体要求,并每年安排2000万元优先建设优质产粮大县。这些政策将极大地促进地方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的热情。本因子量化以省级产粮大县(市、区)赋值为100分、其他县(市、区)赋值为50分。
3.4.5 人均可支配财力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农民意愿与社会效应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根据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地方财政实力越强,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的前期推动与后期维护上投入越多,农民参与意愿则越强,社会效果也越好。本研究综合考虑广东省近年经济发展与基本农田建设资金投入情况,以2010年人均可支配财力作为量化基准。各县(市、区)人均可支配财力因子得分以全省2010年人均可支配财力最大县为100分,其他县(市、区)与该县(市、区)进行比较得到全省所有县级单位评价得分。
3.4.6 生态建设 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要考虑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重点生态保护区应尽量避免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作。鉴于研究基于省级工作尺度,为便于与省级重点生态保护区成果相衔接,本因子的量化简单易用,即将列入全省生态重点保护区域的县(市、区)量化为75分、其他县(市、区)量化为100分。
3.5 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的确定
各因子量化后,按加权计算,得到广东省涉及基本农田的116个县(市、区)的综合得分。最终选择得分大于60分的县(市、区)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共计40个(表4;图1,封三)。
4 结论与讨论
(1)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的划定是一项既强调技术,又需要考虑相关政策的复杂工作。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影响因子、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权重,有利于综合专家经验与客观实际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划定应充分考虑建设潜力、能力、财力与生态环境4大因素,耕地整治潜力、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耕地连片程度、粮食生产政策、人均可支配财力、生态建设6个因子。其中,最重要的因子是耕地连片程度,其次是财政支持和耕地整治潜力,最后是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粮食生产政策和生态建设。

表4 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重点建设区一览表Tab.4 Key areas for high-standard primary farm land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3)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划定时既要考虑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也要考虑实际工作开展时所需要的前期及后期经费支持等社会经济因素。
(References):
[1] 张满红.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工作20年回顾与展望[J].广东农业科学,2010,(1):251-254.
[2] 吴海洋.高要求与硬任务迸发新动力——谈如何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和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J].中国土地,2011,(10):16-18.
[3] 郧文聚.加快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应重视规划引导[J].中国国土资源网,2012-2-28.
[4] 李赓,吴次芳,曹顺爱.划定基本农田指标体系的研究[J].农机化研究,2006,(8):46-48.
[5] 孔祥斌,靳京,刘怡,等.基于农用地利用等别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J].农业工程学报,2008,(10):46-51.
[6] 石英,程锋,朱德举.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自动化成图中图斑分割决策模型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5):39-42.
[7] 戴旭.关于农业土地评价的质量鉴定问题[J].自然资源研究,1987,4:1-5.
[8] 范柯伦,沃尔夫,杨守春,等.农业生产模型——气候、土壤和作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
[9] 郑新奇,杨树佳,象伟宁,等.基于农用地分等的基本农田保护空间规划方法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7,23(1):66-71.
[10]董涛,孔祥斌,谭敏,等.大都市边缘区基本农田功能特点及划定方法[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2):32-37.
[11]胡辉,谢梅生,蔡斌,等.GIS技术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基本农田划定中的应用——以江西省安义县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12):28-32.
[12]杨志荣,吴次芳,叶艳妹.龙海市县域农用地整理规划[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3):58-62.
[13]潘洪义,蒋贵国,何伟.基于农用地产能核算成果基本农田划定研究——以安县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2,(8):160-165.
[14]杨树佳,郑新奇,王爱萍,等.耕地保护与基本农田布局方法研究——以济南市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07,(2):4-7.
[15]涂建军,卢德彬.基于GIS与耕地质量组合评价模型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J].农业工程学报,2012,(8):234-238.
[16]张正峰,陈百明.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4,18(5):37-43.
[17]刘彦随,甘红,张富刚.中国东北地区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格局[J].地理学报,2006,61(8):847-854.
[18]姜秋香,付强,王子龙,等.三江平原水土资源空间匹配格局[J].自然资源学报,2011,26(2):270-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