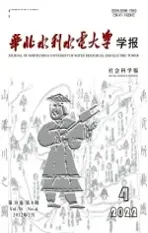简论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2012-08-15杨涛
杨涛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简论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杨涛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曾国藩始终将为国家培养出色的人才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之一,重视人才是贯穿曾国藩一生的重要思想;在选才标准方面,采取“广收博取”的原则,要使人才都有用武之地,人尽其用;在“广收博取”的前提下,还应该坚持“慎用”的原则,要按照选材的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具有典型的儒学思想特征,同时又与其开放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结合,共同促成了曾氏幕府的一时盛极。
曾国藩;人才思想;儒学特色
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筹备湘军,剿灭太平军,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因此号称“中兴第一名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其一人之功,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其幕府聚集了大批的人才谋士,他们出谋划策、各尽其能,最终帮助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不仅如此,曾氏幕府中的许多人后来凭借自身的能力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功,成为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数之众、领域之广,不仅在当时社会无人能出其右,就是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这样的人才盛况也十分罕见。因此,笔者拟就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做一番简要论述,以期了解曾国藩的人才培养及任用标准,进而探究曾氏幕府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众多杰出人才的原因。
一、重视人才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十分重视人才,始终将人才的得失视为国家盛衰、政事兴废的根本。当他在京城任职的时候便上疏咸丰帝,提出人才的重要性,说:“当今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1]《奏稿一》(P6)之后,在接办湖南团练后,曾国藩根据当时的情形,认为“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2](P30),一开始就将团练的重点放在将官的培养和任用层面,并以此来教导曾国荃,说:“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1]《家书一》(P359)在与太平军作战的军旅途中,曾国藩也是处处留心搜罗人才,据说当时其幕府中的“幕僚总数超过四百”[3](P15),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李善兰、华蘅芳、吴汝纶、王闿运等。甚至直到曾国藩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奏请朝廷派出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据此可以看出,对人才的重视始终贯穿曾国藩的一生,人才始终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居于决定性的位置。所以,当咸丰十年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有人提议迁都时,曾国藩坚决反对,他说:“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1]《书信三》P1839认为国家的盛衰,其根本在于人,只有君勤臣贤,才能使国家免于被侵略。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和客观的。
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及其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就为社会有识之士所推崇。李鸿章在其所作《曾文正公神道碑》中,对此评价道:“持己之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4](P92)评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也对曾国藩在人才举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扬:“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二、人才选用标准
曾国藩的学生薛福成在谈到曾国藩选用人才的秘诀时总结道:“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5]卷四而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1]《日记二》(P740)其中,“广收”和“慎用”说的是取人标准,即薛福成所谓的“致力延揽,广包兼容”;而“勤教”和“严绳”则是讲育人方法,即薛福成所谓的“御之有本”。关于后者我们将在后文详加论述,在此先看前两者——“广收”和“慎用”。
曾国藩的幕僚,来源十分广泛,有至亲好友,如刘蓉、郭嵩焘;有亲朋子弟,如李鸿章;有门生故吏,如陈士杰、梅启照;有慕名来投的,如李元度、薛福成;有他人推荐的,如吴汝纶、赵烈文;还有曾国藩自己物色的,如朱孙诒;除此之外还有降服人员以及朝廷分发的候补人员等。从籍贯来看,更是包括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
曾氏幕府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人员构成,与曾国藩的用人标准分不开。或许受其学术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的影响,曾国藩在用人方面也始终存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主张对于有才之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历史如何,都会给予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1]《书信二》(P1520)关于这一点,薛福成的总结更加详尽:“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巍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馀力。”[5]卷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四处网罗人才,为其所用。这种开放的心态,是曾氏幕府盛极一时的前提保证。
曾国藩的选用人才虽然不存在地域、出身等外在限制,但这并不表明曾国藩对人才没有取舍标准、一概收容,而是在“广收”的前提下做到“慎用”。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取舍的滥收人才,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他曾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1]《书信一》(P382)如果一味地广收博取,而不分良莠好坏,只会造成真正的人才因不甘与不贤者为伍而离开。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的分辨人才呢?也就是说,辨别人才真伪的考察标准是什么呢?在此,曾国藩沿用了儒家的“德才观”进行说明。他说:“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1]《诗文》(P390)从中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的眼中,德与才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称之为人才,即贤者。但是现实中的情形往往是很少有人德才兼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取舍呢?曾国藩对此的回答是:“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1]《诗文》(P390)
三、人才培养方法
首先,有了人才选取的标准后,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按此标准进行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的教化思想,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在位者以身作则,克己修身,这样必然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气氛,整个社会风俗也就归于醇厚,于是自然会人才辈出。“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1]《日记一》(P681)这里所谓的“为人上者”,从整个国家来看是指当朝皇帝,从地方来看,则是指地方的督抚、县官以至士绅。他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1]《奏稿一》(P6)又说:“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1]《诗文》(P451)
其次,曾国藩认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还与整个士风环境有关。他说:“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并进一步阐述道:“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襢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1]《诗文》(P443-444)
再次,具体来看,施教者还应该“勤教、严绳”。曾国藩满怀报效朝廷的热情,凭借其深厚的理学功底,不仅致力于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且将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重要责任。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1]《日记一》(P421)。而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1]《诗文》(P441),如果不严加管教,即使再有天分也不会成才。他说:
“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1]《诗文》(P156)所以,曾国藩对于人才始终坚持严格的培养标准。在他看来,人才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1]《书信二》(P1574-1575)据此,曾国藩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基本手段,即“赏罚”二柄。他说:“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善,刑一人而天下恶。”[1]《诗文》(P743)因此,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应坚持赏罚的原则,“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1]《书信一》兴苗,即鼓励其优秀品德;凋物,即翦除其缺点和毛病。通过这一赏一罚,即可起到鼓励和惩戒的作用,对于人才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以上论述了曾国藩基本的人才思想。首先,重视人才是贯穿曾国藩一生的重要思想,曾国藩将为国家多培养出色的人才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之一;其次,对于人才应该采取“广收博取”的原则,要使人才都有用武之地,人尽其用,而不能随意将其拒之于门外;第三,在“广收博取”的前提下,还应该坚持“慎用”的原则,所以还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要按照选材的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最终的目的,则是“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倡成一时风气”,并“藉以图报国”[1]《书信二》(P1546)。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学士大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征。由于脱胎于西周的宗法制,儒家思想带有十分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个特质贯穿于整个儒学发展史,从某种程度可以说这是儒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同时,这种思想体系预设了一个德才兼备的“圣王”作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认为社会的治理只要通过圣王自上而下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便可以自然完成,这便是儒家的教化思想。以此来比照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无论是其上行下效的人才培养方法还是“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的人才选用标准,都带有典型的儒家文化特色。可以说,曾国藩人才思想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其儒学色彩浓厚。
但是,在那个中西交汇、酝酿剧烈变革的特殊时代,曾国藩的开放心态却赋予了传统儒家人才思想新的活力,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曾国藩的开放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曾国藩虽然是典型的儒学士大夫,但却不排斥西方的现代文明,他热心洋务,并任命专人来负责介绍传播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如容闳、李善兰、华蘅芳等人,甚至在其去世前一年还上奏促成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其次,曾国藩的开放心态体现在他“广收博取”的用人标准;此外,曾国藩的开放心态还体现在他不仅按照传统的政治体制“因岗选人”,而且还根据不同人才的特点进行“因人设岗”,充分发挥不同人才的特长。正是这种开放的思想结合儒家的人才思想,使得曾国藩幕府盛极一时,正如容闳所论:“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6](P74)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4]曾国藩.曾国藩哀荣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薛福成.庸庵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A Discourse on Zeng Guo-fan’s Theory of Talent
YANG Tao
(College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alent is very important in Zeng Guo-fan’s theory.He took it as a great mission to discover and educate talents.In Zeng Guo-fan’s theory,talent has a very broad meaning,everyone could be a talent.Then,he advocated educating the talent according to his specialty.Zeng Guo-fan’s Theory of Talent is classically Confucian.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Zeng Guo-fan’s open mind brought out lots of talents around him.
ZENG Guo-fan;Theory of talent;Confucian
D921
A
1008—4444(2012)01—0066—03
2011-10-20
杨涛(1971—),男,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