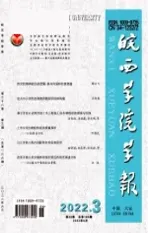公共文化与城市传播能力的拓展
2012-08-15焦德武
焦德武
(1.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230051;2.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1)
公共文化的含义见仁见智,广为接受的是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目的,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为导向,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04年以来,公共文化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深入推进。就目前来看,公共文化建设的话语指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层面,重在“服务”与“文化惠民”;二是公民层面,重在文化权益的诉求。两者都有被动、组织政策的意蕴包含其中,而主动的、关涉城市形象的视角则极少见。
一、公共文化:城市的精神地标
文化具有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中的所有人正是认同了某一文化价值观才聚集到一起[1]。从这个角度,公共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存在于公共领域、面向大众的文化。
这种重视空间的公共文化含义因历史和中国当下语境发生了嬗变。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是公共政治文化的早期形式。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17、18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大众文化的扩散,以艺术沙龙和公共咖啡馆为载体的公共领域生产着包括文化在内的价值观。就中国来说,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其主要是基于国家力量的文化公益,是和文化产业相对应的概念。它体现的是政府文化治理思想[2],具有意识形态前置的内在运作逻辑性[3]。
这种略显窄化的公共文化内涵不仅在话语形式上拒绝了社会参与,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公共文化建设也是沉重的负担,“无论现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还是中国在未来的理想时代富裕到何种程度,政府公共性支出永远都无法完全满足社会的公共性需要”[4]((P140)。所以,从话语形式上应该改变现有公共文化的内涵,回归“公共”具有的原有含义。一方面,政府可以将社会力量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中来,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扩大的公共文化内涵可以调动社会的参与热情,化被动发展为主动作为。
作为面向公众的文化空间,公共文化不仅是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不仅是文化下乡、电影放映、村村通等,还包括城市皮肤的雕塑、广场、科技馆、动植物园、艺术画廊、音乐厅、影剧院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表征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内涵。
衡量城市发展的体系是变动的。城市诞生时,主要目的是人类可以共享生活的边际效益,逐渐地城市成为政治、经济、军事能力的实体。进入21世纪后,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脱离有形的物质竞争,让渡为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文化软实力的衡量向度对城市的文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创意文化产业带来注意力与利润,也表现为公共文化所表征的城市精神内涵。特别是公共文化因其具有的公共性、普适性、公益性,远离了资本的血腥与争斗,更为社会所接受。
二、作为城市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
把公共文化作为观察城市的重要尺度,体现了对城市为人类幸福服务的再认识,这也是城市发展的终极文化目标。辩证地看,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公共文化的发展,公共文化的提升又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动力。
城市传播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手段和目的,让人难以忽视城市的传播艺术。传播学者卡尔·拉森(Carl E.Larson)等人认为,传播能力是在给定的际遇里,社会化地、恰当地表现传播行为与知识的能力[5]。当然,这里传播能力的论述集中在人的层面。但是,城市作为有生命力的存在也具有传播“策略”、“技巧”、“互动”、“情境”和“关系”等“能力”要素,重要的是城市和人类的传播能力相同,两个基本面是行为和知识。而城市的知识,主要就体现在因历史原因、管理理念、经济实力、文化传统等形成的文化表现上。公共文化又是城市知识的基本元素,决定着城市传播能力的行为。
(一)公共文化传播城市内在精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品格与精神,正是这些不同的存在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城市内在的品格和精神,很多时候被赋予一两件具体的物化形式,通过这些具有历时和现时意义的空间,传递整个城市的文化风貌。提及西班牙毕尔巴鄂,就会想起古根海姆博物馆;说到悉尼,就能联想到歌剧院;言至俄罗斯,就会忆起莫斯科红场;如去捷克,就不能不去布拉格广场游览一番。
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公共文化常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展现城市的生活、人情、风貌,体现该城市之所以为该城市的原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由这个城市创造的,体现着这个城市的制度、信仰、价值观。甚至小至一只垃圾桶的形态与摆放,都能体现出城市管理的理念、城市公民的素质、城市发展的取向。
(二)公共文化传递城市文化活力。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她不仅是公民生存的载体,也有自己的律动与活力。城市活力不仅仅体现在凯文·林奇所说的“旺盛生命力”,还体现在能传递一种文化,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生命力。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兰蒂认为,对于21世纪的国际城市来说,最需要的是一种有创造力的文化,也即保持灵活性的文化,保持城市的文化活力[6]。对于每个城市来说,公共文化是体现城市文化活力的重要方面。
不可否认,文化创意产业同样赋予城市文化以生命力,具有创造性。而公共文化一般认为是由政府组织实施、提供基本文化需求的体制化文化。实际上,公共文化不仅有自己的灵活性,还能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活力与资源。例如,同样是城市科技馆,一般都是针对青少年的科普知识和科学现象,而有的城市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动脑筋,还在聚集人气,带动周边文化产业上下工夫,甚至把植物标本、自然现象、模拟动物、影视、餐饮、文化产品销售等搬进科技馆。这种科技馆俨然成了旅游集散地,成为聚集人气、传递一个城市文化活力的窗口。
3.公共文化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城市发展的方式是多样的,文化是重要的路径之一。通过文化的设施、文化业态、文化产品、文化场所、文化消费的聚合与规划,优化城市发展方式,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各国城市发展均进入瓶颈期,传统的工业立市因经济衰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技术进步等已显落后,积极向文化转向也得到共识。而公共文化因其背靠政府的优势,在规划、整合、资金、人才方面潜力无限。
三、公共文化增强城市传播能力的思考
作为人类的重要的生产方式,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今天在强调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创新的同时,公共文化的发展似乎受到了冷落。实际上,公共文化的生产同文化产业一样,也有其产品。公共文化的产品,除了负载意识形态、价值观、心理、情感等外,也负载着为文化产业奠定基础,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活力的使命。
城市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文化发展城市已经成为国际认同的趋势。通过对富有创意的文化产业的强调,盘活整个城市的文化资源。而进一步利用公共文化增加城市传播能力,则是城市发展的两架文化马车,缺一不可。从目前来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公共文化,这不仅不利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道德观念、幸福生活法则的传递,还容易造成资本逻辑的扩展,侵蚀文化的社会功能。因此,从城市发展文化的角度来说,同等强调文化发展的两翼意义深远。
第一,体现创意,提升公共文化活力。目前,不少城市在政府逐年加大投入的情况下,建起了一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亮丽的图书馆、新建的博物馆、窗明几净的文化馆、干净整洁的街心公园等,但是仔细看来,大多建设雷同,没有多少创意。建设者要么被动地满足“国标”要求,匆忙上马;要么简单选址,远离生活区,缺少规划。这样建成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只能是政绩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后续潜力可挖。
公共文化的建设,在满足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应体现自己的创意。每座城市因历史渊源、区域位置、城市文化的不同,各有特色,公共文化应结合城市特点予以建设。试想,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国家图书馆”,都有风格相似的科技馆,还有什么可引人之处?
第二,挖掘历史,体现城市文化内涵。每个城市都无法割断历史的脉络,对于公共文化的建设同样要体现城市的历史深度。很多城市,都是靠历史文化来体现城市的魅力。比如,提到成都,我们就会想起武侯祠、杜甫草堂、百花潭公园;来到合肥,就不能不去看看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对于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特别要突出历史性,体现城市的文化意蕴。这要求注重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传播,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以及善于利用历史文化。城市公共文化的建设要和城市历史文化相结合,体现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第三,注重规划,打造立体城市文化。城市公共文化的建设若是单一的、散落式的,则难以体现群聚效应。公共文化的发展也跟文化产业相同,具有集群效应,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即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便利性。特别是当前基本的公共文化设施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则会趋向多模式、多类型、多形态。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公共文化不仅要在财政投入方式、资金使用效率、资源整合力度方面进行规划,还需要对公共文化建设方式、建设地点、建设风格进行规划。
第四,全面发展,建设公共文化软设施。公共文化的建设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文化设施,另一个是无形的道德风貌、精神状态、人文素养,这一类可以说是公共文化的软设施。公共文化经过近10年的发展,基本的文化设施已具规模。下一步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应注意城市公共文化软设施的建设。如通过城市精神的传递,无形中提升市民素养;通过积极的文化活动,提升市民的文化修养;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平和的心理、积极奋进的精神状态。
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命题,她在满足公众的文化权益的同时,也在表达着城市内涵。城市公共文化的发展只有和城市发展相结合,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荣跃明.公共文化的概念、形态和特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3):38-46.
[2]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J].江淮论坛,2011,(4):143-149.
[3]王列生.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4]阿耶·L·希尔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政府的责任与局限[M].王国华,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王怡红.西方“传播能力”研究初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57-66.
[6]董慧,常东亮.城市文化活力研究:理论资源的探寻与发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