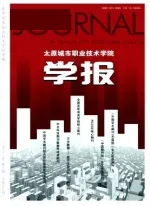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特点
2012-08-15宋文华
宋文华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长治 046000)
鲁迅小说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他在小说创作中把中国传统的讽刺艺术和外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讽刺艺术熔于一炉,他的小说不仅揭露了社会,而且揭示了人性,在平凡的生活中洞见了生命的苦难。鲁迅的小说语言的讽刺艺术之所以影响极大,是因为他的小说语言的讽刺艺术有以下不同于他人的特点。
一、隐晦曲折的描写
在当时残酷的黑暗统治下,反动派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人们非但没有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而且受到身心极度的压迫。在这种恐怖政策下,作家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味使用锋芒毕露的语言,这就是自寻死路。正如鲁迅所说:“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这就决定了鲁迅在创作时必须采取较为隐晦曲折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品的武器功能。鲁迅认为讽刺的目的是对反动、落后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但是鲁迅也要求讽刺小说不但应该穷形尽相,而且特别要做到含蓄、深沉不露,也就是要把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蕴涵在艺术形象的真实描写之中。所以在鲁迅创作时,作者更多的是使用了一种隐晦曲折的描写方式来讽刺那些社会中的黑暗的现象和不革命的群体,这种描写方式最好的体现就是反讽式的叙事方法。鲁迅是使用反讽的高手,写人叙事,插入一两个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不仅使文章充满幽默和活泼,而且使他的讽刺锋芒更为尖利。他自己也说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次遇到辩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由于作者强烈的批判思想,使他的反讽往往显出反话正说的特点,且用词精当、一步到位,体现出了隐晦曲折的特点。比如《风波》中介绍七斤时说他“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一词往往是与功名相关,而七斤的“飞黄腾达”却是三代不种田,讽刺了七斤实际上的贫穷落后;“时事”往往指的是具有较大范围影响的有意义的大事,而七斤的“很知道些时事”却是“雷公劈死了蜈蚣精”、“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农村的迷信谣言,在文中,“时事”实际上讽刺了七斤是一个麻木落后、愚昧的农民典型,也从另一个角度讽刺了当地村民的愚昧落后。对赵七爷的介绍也有相仿的描写,说赵七爷“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但下文的叙述却暴露出了赵七爷既无学问,更不出色,用反讽修辞讽刺他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封建遗老。《阿Q正传》中更多地使用了反语,阿Q与别人打架打败了偏说是“优胜”,还美其名曰是“儿子打老子”,还说阿Q“武勇”,是“完人”,既深刻揭露了人物行为和思想的缺陷,又反映了小说中人物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反而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可悲。在“革命”的时候,未庄人陆续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以示革命性谓之“英断”,实则是讽刺了村民的愚昧和革命的形式主义。作者没有直接地揭露,而是借助反讽,用一些“意在言外”的词语来表现人物和自己的情感。倘若七斤不“飞黄腾达”,赵七爷不“出色”,则村民就不会愚昧落后;倘若阿Q不“武勇”,村民不“英断”,则未庄将不再是未庄。
二、真实基础之上的夸张
夸张,是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当然,夸张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础,而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什么是讽刺》中反复强调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所以鲁迅的描写对象往往取材于真实社会,但是在具体的描写中并不是不加艺术加工的反映,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所夸张,这样才能更好地讽刺社会的黑暗和当时国民的麻木冷漠。《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作者在文中还借助一些修辞手法来表现夸张,比如比喻,作者没有只做简单的比喻,而是在比喻中经常要做注解,以示人物的荒唐可笑。“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这是作者对《示众》中看客的一个比喻,没有简单地把人物比作皮球,而是对皮球有一个注解,“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表明了人物动作之快、兴趣之大。在《阿Q正传》中,作者同样用了一种夸张的细节描写来表现赵太爷一家的贪婪的形态,当赵太爷听说阿Q有便宜货时,赵府“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且特准点油灯”,可偏偏阿Q说东西卖完了,因而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赵太太“慌忙说”,秀才也开始讲“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而且秀才娘子还“忙一瞥阿Q的脸”,一系列的动作细节描写,表现出来赵府虽然有无上的尊荣,可是还要从穷苦百姓阿Q的身上捞取便宜货,可见他们的贪婪了。
三、幽默诙谐的言语
鲁迅的小说语言幽默诙谐,具体表现在作者作品中的一些描写上。比如说在《起死》中庄子有一段自述,这段话阐发了庄子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八、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但是,这段话并不是要真实表现庄子的理论,而是鲁迅对于“第三种人”的讽刺,所以庄子的观点一经鲁迅形象贴切、略带夸张地“转述”,作者想要表达的迂腐和荒唐也就能够一览无遗,读之令人喷饭,然而大笑之余又能余味绵延。这正是对当时那些自命不凡、主张超然物外的“第三种人”的极好的揶揄讽刺。在作品中,幽默和讽刺总是能被鲁迅焊接得天衣无缝:“只有当观赏者笑过之后,从对戏剧动作的嘲弄进入对戏剧形象的评价,也就是从下意识的形式到积淀着的‘理性’时,从他的心底、嘴角和眉梢渗出了会意的微笑,出现了艺术家所期待的那种包含复合情感,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幽默意境。这才是幽默本身所造成的独特的审美效果。”所以,作品中的讽刺总是能够显示作者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他反击的智慧。
鲁迅小说语言的幽默还体现在文中作者通过一些称谓词的改变,来表现人物语言前后语气的变化以揭示人物的本质。赵太爷和他的这一群体对阿Q本是不屑一顾的,甚至不许他姓赵,可是当革命来时,却又是另一副嘴脸。从“阿Q”、“浑小子”到“老Q”、“Q哥”,表现了人物前后态度的转变。在最初时,赵太爷对阿Q是以一种质问的语气来说话,而且不给他回答的机会,而当革命来时,却又是另一种试探、疑问的语气,让读者看到赵太爷的态度想问又不敢、疑疑惑惑、小心翼翼,其实赵太爷他们是想投机革命,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在这里要表现的是这些老爷们对革命的畏惧,也讽刺揭示了这些人对革命的恐惧、投机的心理和变色龙的嘴脸。语言的古今杂糅可以造成文风的活泼跳跃、幽然风生。如《治水》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只听得上下在讲话‘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里’……”“大学”、“幼稚园”和汉化外语都是在大禹治水时的古人生活中所不可能出现的,而作者之所以这样用,显然是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中崇洋媚外者的顺手一击。
不仅对敌人的反动要无情地揭露,就是对人民的愚昧落后,鲁迅的讽刺也是犀利的,鲁迅虽然主张对人民的落后要进行善意的讽刺,所谓“含泪的笑”,但他对存在于人民身上的种种弱点并不姑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他还是主张“揭出苦痛”的。
[1]王培坤,郭玉霜.绍兴师爷刀笔吏——谈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 [J].语文学刊,2006,(7).
[2]刘渝霞.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形成与特点[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3]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4]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