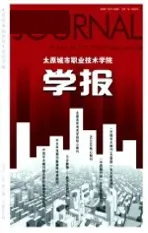鲁迅精神世界解读
2012-08-15杨莉
杨 莉
(吕梁高专汾阳师范分校,山西 汾阳 032200)
一、鲁迅的精神世界
1.真的猛士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鲁迅以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身份自觉承担起了改造国民性格的重任。他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为国人争取最基本的“人的价值”,他认为,“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他奋斗的目标是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是人的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希求改变国民的“瞒与骗”,改变国民卑怯的性格。他希求通过自己不怠的呐喊,让国民能正视现实、剖析现实,发现封建礼教对自身的束缚和压制,进而能奋起反抗束缚和压迫,在反叛传统的同时确立独立的自我。但是,鲁迅对抗的敌人太强大了,连他自己都说那是“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所对抗的敌人是隐形的,是“无物之阵”,他的努力常常如一箭射入大海,无声无息。更让人绝望的是,他致力于拯救的对象往往无动于衷,不仅没有倾听的诚意,有时还会作为相反的力量反扑回来,所以在他的梦中,一位老妇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露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无词的言语。他无法看到一丝光明和生机,感觉身边有黑暗和虚无,他是在荒凉处荷戟独行的过客。尽管如此,他依然要掮住黑暗的闸门,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沉重的历史责任。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向一切黑暗开战。鲁迅最令人敬仰的精神品质就在于此。
2.梦中的小小少年
在鲁迅的作品中,除了看到一种执著坚毅的姿态外,我们还能感受到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亲切和可爱。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境界令鲁迅心醉和神往,那是一个充满着自由与欢乐、人与人之间友善互助的精神家园。在那个世界里,不再有《阿Q正传》中的奴役和无知,不再有《过客》中的孤寂和冷峻;不再有《狂人日记》中的对峙和敌意,不再有《肥皂》中的虚伪和龌龊……虽然他的作品中有关这种美好的精神家园的描述并不多,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鲁迅的欣喜和陶醉:百草园里的童真和趣味,故乡月夜下的冒险经历,乃至阿长告假回家时给他买来的《山海经》,已成为他记忆中“最心爱的宝书”。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任《社戏》中,伙伴们驾着小船,在两岸碧绿的豆麦田里穿行,和着豆麦和水草发出的清香,伴着潺潺水声,在水气和夜色中,有说有笑向赵庄奔去,其实不为看戏,只为相伴出行的欢乐。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分明看到一个轻快的、自由的、幸福的鲁迅,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亲切自然且普普通通。
然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鲁迅的形象并不是这样的,人们更熟悉的是一个“骨头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勇猛的、决不妥协的“斗士”,甚至于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神”,完全摆脱了作为普通人的任何情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主宰着话语权的政治化解读。
二、政治化解读——伟大的、冰冷的“神”
1.“神”的崛起
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接受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人们熟悉的鲁迅的作品也往往是教材中所选的篇目。但是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受政治影响的教育来说,对鲁迅的解读明确地彰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政治的烙印。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一直把鲁迅先生评价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实这一观点是一直沿用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观点。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了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教育界一直恪守着这一金科玉律,不断地强化鲁迅的战斗性,再加上教学参考书的唯一规定性的导向,以及应试教育下的标准化考试,鲁迅的“战斗精神”被尊崇到了极致。教师在课堂上用固定的思维模式,贴标签式的概念化分析,将鲁迅一步一步推到了无比崇高的地位。鲁迅被解读为一个决不屈服的战斗者,“神”性彰显,人性化分析萎缩,他丰富的情感世界被一点一点地忽视并逐步抽离。
2.接受者的背离
在学校教育中,教学参考书的话语霸权使得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成了失语者,鲁迅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意义彰显,他的形象被刻意地单一化解读,以至于使接受者内心产生了一种印象,鲁迅太坚定了,太伟大了,在普通人的身边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纯粹的人,只有天神才可能像他一样。太过遥远的距离产生了心理上的间离,鲁迅的面孔越来越冰冷、遥远,不真实,甚至有一些高高在上而令人生厌。在这种极端化的解读下,教育收获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从教育中走出的人们与鲁迅的真实心灵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膜。
二、人性化回归——真诚、质朴的人道主义情怀
1.普通人的情感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鹫,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与其说百草园是一个充满了颜色和声音的生命世界,不如说鲁迅的心里就装着这样一个童心世界,那是一个令他留恋忘返的精神家园。在青青的野草丛里,氤氲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动人的故事里闪耀着热爱、追求、趣味、快乐。我们在这篇作品中仿佛看到了一群孩子充满了色彩和趣味的童年:他们走过杂草丛生的园子,侧耳细听有无油蛉在低唱,有无蜈蚣精突然出没;就连最为熟悉的蟋蟀的叫声,也有如弹琴一般悦耳;就连夏日此起彼伏的蝉鸣,夜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捕鸟、钓虾等事,都变得更加意趣盎然起来。这些色彩斑斓而浪漫温馨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了鲁迅童年的记忆里,也播撒在了读者的心田,我们似乎摸到了鲁迅的心跳,看到了鲁迅的微笑,他离我们这么近,举手可以触摸。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鲁迅先生大概有无数次回想起百草园的快乐,在他忧患和苦痛的时候,儿时的这段快乐也许已成为了他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前进的巨大勇气。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一个小孩子被允许做一件事之后的迫不及待、欢欣喜悦,便在一连串的动作中一气呵成。再加上月色水声、欢声笑语,幸福和快乐便跃然纸上。这一切带给了我们多少欣喜,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鲁迅。
当我们对鲁迅的解读脱离开教材编者和教学参考刻意的引导,不在意新旧时代的对比,不再关注旧时代的种种罪恶和新时代的无比优越时,反而进入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真正品出了作品的韵味,也走入了鲁迅的心田。
2.打破话语霸权,尊重接受者个性化解读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读者是文学活动中最主要的环节。接受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曾说过:“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在作品的解读中,更应关注的是读者,是读者究竟从作品中发现了什么。
接受美学的另一理论家H·R·姚斯曾这样表述:“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文本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
作品的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可能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作品的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显示赞同与拒绝的审美活动。当我们把鲁迅的作品看成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载体,以说教的方式把亲切可感的鲁迅形象排除在外,试图硬生生地以刚强的鲁迅精神去塑造下一代的灵魂时,恰恰遭到了阅读者的拒绝。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曾指出:“文艺欣赏是谁都有的份的。”不能以国家意志、政治意图绑架一个个有自我个性的读者,牵强地抛给他们一个结论性的、不允许更改的形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对话语独尊、中心性、秩序性的消解,学校教育对鲁迅作品的接受也应该这样,要重视解读的个性化,将接受者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还鲁迅精神以本来的存在。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要打破话语霸权,以接受者为中心,由群体转向个体,尊重个体话语,创建多元阐释模式,在世俗化的社会生活当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原则,让每一个人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鲁迅,这样鲁迅先生的精神才会真正地散发不朽的魅力。
[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3.
[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25.
[3]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5.
[4]张廷琛.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