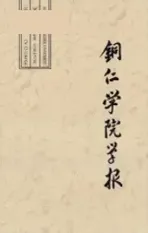关于全面、辩证、科学地看脂批问题——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二
2012-08-15张兴德
张兴德
(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宣传部,辽宁 大连 116017 )
回应俞平伯先生晚年关于红学研究乱象的自省是目前红学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俞平伯先生在晚年自省时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1]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2]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的红学界至今没有对俞平伯先生晚年这个沉痛的负责任的反省作出积极正面、科学严肃的总结和探讨。笔者窃以为,这是目前红学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众所周知,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胡适新红学大厦的重要基石。这以后,有些人为了营造这个大厦,以脂批为出发点,以脂批作论据,作了大量的考据和推理文章,并由此出现了以研究所谓“脂批本”为主旨的“版本学”,以研究曹雪芹家世为主旨的“曹学”,以研究脂砚斋为主旨的“脂学”,以腰斩《红楼梦》为主要特征的“探轶学”、“秦学”,以及以探讨《红楼梦》背面的所谓隐去的“真故事”为主旨的新索隐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有些人不以为然,且从不同的角度发出强烈质疑,认为脂砚斋是后人的假托,脂批是假,脂批不可靠,红学的大厦不能建立在脂批的基础上。而反对和不同意“脂批是假”的专家学者,也并没有在主要论据和材料上,令人信服地驳倒“脂批是假”说。他们坚持脂砚斋真有其人,“脂批”是真,但对脂砚斋究竟是什么人,他的真名实姓是什么,是男是女,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是曹雪芹的长辈还是平辈,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朋友,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仍然是众说纷纭。有人不得不把它列为红学研究的“死结”之一。于是,怎样评价和对待脂砚斋和脂批,就成了红学史上留下的重大分歧之一,也是红学研究中诸多分歧得不到统一认识、长期纠缠不清、乱象纷呈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情况,也有人哀叹,因为材料所限,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扯不清了。也有一些人对不同的质疑之声一概置之不理,不顾这个客观存在的实际,仍然把脂砚斋和脂批看作不可动摇的根基。他们把脂批看作是不容怀疑的“圣经”和“最高指示”,继续埋头研究,“雷人”的新论迭出,以至于使红学研究失去了应该有的学术品格,出现了一种泛娱乐化、泛趣味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的倾向[3]。这些研究远离了《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本身,使一部国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学名著,成为一部不知所云的“奇书”、“怪书”,不仅增加了红学的乱象,也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和外国朋友对《红楼梦》这部中华民族赖以骄傲的文学国宝的正确解读和赏析。
无须讳言,红学界目前存在的这种情况,仍如俞平伯先生当年所论,我们应该也须要对俞平伯先生的反省作出正面积极的回应。俞平伯先生的反省内涵颇多,须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研究探讨。本文仅就全面、辩证看脂批问题,谈点浅陋意见,作为作者研究、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一,以供欲研究俞平伯先生反省的专家学者参考。
一、研究脂批,应该研究全部的脂批,并且要作综合分析,而不是片面强调某一部分
许多人对“脂砚斋”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从“脂批”中得出的,其有代表性的结论主要有:
(1)脂砚斋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的批不是小说正文以外的赘物,而是被作者本人看作为小说的一个附加部分;他是得到作者本人承认而且写入正文的批者。
(2)脂砚斋是隐然以部分作者自居,而往往与署名作者并列的。
(3)脂砚斋不仅仅是因为他参与过《石头记》的写作和修改而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是《石头记》最早的论评者,而且他最知作者的底里。
(4)脂评作者本身,还兼有一定程度的作者的身份;不仅如此,更兼有小说情节和人物素材的身份,也即是过来人的身份。
简言之,脂砚斋同曹雪芹关系极为密切,很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和曹雪芹本人;他了解《红楼梦》的创作情况并建议和指导过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写作、修改;曹雪芹也很尊重和听从脂砚斋的意见和指导;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结论就论者所引的脂批看,并无大错,是可以这样解读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可能被这些人忽略了。就是这些结论只是从脂批的一部分内容得出的。而据有人统计,全部“脂批”近五千条,这些结论只是这五千来条脂批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也就百分之二三的样子,加上被一些红学家称为对研究《红楼梦》有价值、有意义的批语也不过十分之一左右。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研究脂批,应该研究全部的脂批,并且要作综合分析,而不是片面强调某一部分。
我们如果全面地、仔细地研究这全部五千来条“脂批”,就会发现,还有另外许多批语得出的“结论”和这上述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结论”之间十分明显地在“打架”。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批语质量也不敢恭维。从批语本身看,曲解书中原意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有之;杜撰者有之;废话者有之;甚至还有歪批和轻狂的批语。由此看来,脂砚斋其人并不懂小说,不了解曹雪芹,也不懂《红楼梦》的艺术构思和主题思想,甚至他的人品格调也不高。
当然,如果脂砚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出现上述情况可以理解。但是,被一些学者和专家确认为是脂砚斋本人批语的甲戌本《脂砚斋重平石头记》中的脂批,也十分明显地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了。
让我们从甲戌本《脂砚斋重平石头记》中摘录一些可以确定为“脂砚斋”本人的一些批语略加分析。
(一)关于“好了歌”
“好了歌”和“好了歌解”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曹雪芹借鉴和仿照明初重臣刘基在《司马季论卜》中的句式和某些思想创作的一首哲理诗歌[4]。全篇结构严谨,混然一体,表达了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的哲理思考,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统帅全书的。它和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的“判词”不同,不是作者专为书中某一人某一事而写的,因此不能把它拆解为特指书中某一人某一事。而我们这位脂砚斋先生却认为,其中某句话是指某某人,而另一句话又是指另外某某人。如,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批指“宁荣未有之先”;将“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批指为“宁荣既败之后”;将“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句的上句批为“潇湘馆紫云轩等处”,下句批为“雨村等一干新荣爆发之家”;等等[5]。简直是乱批一气,把一首完美的诗歌,弄得七零八落。从这几条批语看,脂砚斋根本不懂诗歌,不知这首诗歌的出处和深刻含意,不懂曹雪芹创作此诗的良苦用心。对此,就连一向推崇脂砚斋的周汝昌先生都认为是不妥的。
(二)关于宝玉
宝玉是《红楼梦》的主人公,脂砚斋在一些批语中标榜自己了解宝玉。其实,从另一些脂批中看恰恰相反。在第十三回,秦可卿的死讯传到荣国府时,宝玉“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在这句话的旁边,有脂批:“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5]
《红楼梦》写可卿死讯传到荣国府时,阖家“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但具体反应又各不相同。如,凤姐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那长一辈的想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这些描写是各有深意的。单就作者写宝玉吐血而言,就留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不同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可能是宝玉在可卿房间里睡过午觉,梦中与可卿有太虚幻境之会;也可能是因睡梦中听说,事出突然,毫无心理准备,表现出宝玉心理脆弱;还可能是因秦氏是秦钟之姐,且年轻貌美,因秦钟之故和可卿关系极为密切;等等。但是,再多的想象空间,也不会是脂砚斋批语中说的认为可卿是“定可继家务事者”的原因。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宝玉是个从不问家务事的人,这在书中有多处或明或隐的描写。在第六十二回更有一处极为典型的描述。在与黛玉议论探春理家时,黛玉先提起了家务说:“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他这种不管事的超然态度,曾被探春等人批评过。一个连自家事都不虑的人,他怎么竟关心起宁府家务事了?怎么可能为宁府失去未来的内管家而吐血?再说,当时在宁府理家的是尤氏,她只不过三十多岁,什么时候能轮到秦氏管家?这岂不是没影儿的话。贾府上下老幼人等都没有想到这层意思,怎么只有宝玉单单“早已看定”这等事?可见,脂砚斋根本不了解书中宝玉的思想性格,也不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他对宝玉“吐血”的这个解读,连一个最普通的读者都不如,简直是一种低能。这样的“批语”怎么可能是“经过作者本人承认而且写入正文的”批语?曹雪芹怎么可能认可脂砚斋的意见,和他一起修改《红楼梦》?
证明脂砚斋不理解书中的宝玉的批语还有很多。如,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判词时,在书中“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句处,有甲戌眉批:“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出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别书中所无。”[5]
脂砚斋说《红楼梦》“通部中笔笔贬”、“语语谤”,而且是“人人嘲”宝玉,只有警幻一人不嘲,是“意外之意”。这样的批语,也只能证明脂砚斋对《红楼梦》全无了解,至少是没有认真读过《红楼梦》。无论是作者的第三人称的描述、介绍,还是书中人物对宝玉的态度都并非如脂砚斋所批。脂砚斋全不明白作者之意,而是把宝钗、湘云、袭人平日劝宝玉,贾政、王夫人管宝玉都看成是对宝玉的贬、嘲、谤。事实是,书中不仅黛玉、宝钗等人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称赞过宝玉,就是经常打骂宝玉的贾政也在许多场合称赞过宝玉[6]。在大观园题对额时,就有多处写贾政对宝玉明贬实褒的语句。如,在“蓬来仙境”,宝玉有些疲劳,表现出“精神耗散”时,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时了。也罢,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饶。这是要紧一处,更要好生作来!’”
这“竟有不能之时”是典型的正话反说,是寓褒于贬,分明是赞宝玉以前之“能”。同时又将“这紧要一处”的题联交他“明日”对来——赞赏、信任、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在第二十三回决定让众人搬进大观园时,这样描写贾政看宝玉:
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
最明显、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是在第七十七回和第七十八回。在第七十七回,就在晴雯死的那天清晨,宝玉正同袭人议论梦中情景时,有这样一段:
及至天亮时,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立等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即时叫起宝玉,快洗脸,换了衣裳快来,因今儿有人请老爷寻秋赏桂花,老爷因喜欢他前儿作得诗好,故此要带他们去”……宝玉此时也无法,只忙忙的前来……贾政向环兰二人道:“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勉强你们作诗,宝玉须听便助他们两个。”王夫人等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真是意外之喜。
……宝玉等人回来……王夫人忙问:“今日可有丢了丑?”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份。”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作何诗词等语毕,只将宝玉一份令人拿着,同宝玉兰环前来见贾母。贾母看了,喜欢不尽……
这是一幅家庭和谐的图画!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宝玉。贾政喜欢、欣赏宝玉的诗才,并以此向他的同僚们显摆推荐。而宝玉尽管有晴雯之死的忧伤,却并没有影响他跟随贾政到各达官显宦处卖弄诗才!并得到了贾政的同僚们的赏识。在紧接着的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嫿词”中又有进一步精彩描绘。当贾兰、贾环二人作完诗后,宝玉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对林四娘这样的“英雄事迹”应该写成“长篇歌行方合体”。书中写道:
贾政听了,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写。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谁许你大言不惭了!”
儿子吟诗,老子竟主动甘愿为其执笔抄录誊写!我们看宝玉写《姽嫿词》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幅慈父爱子的图画!其间虽时而夹有贾政对宝玉的责骂和“申斥”,那不过是“骂是爱”、“正话反说”、“寓褒于贬”的不自觉行为而已!
上述这些不统统是“赞”么?看来我们这位脂砚斋先生不是粗心便是低能。
(三)关于曹家
脂砚斋自称了解曹家的家史,从有些脂批看却未必。如,其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旁批道:“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5]
脂砚斋的这条批语意在借此说曹家后继无人。其实,这说明脂砚斋不仅不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和《红楼梦》一书的主旨,也不了解曹家。小说的确是写一个封建大家族的衰落,人口虽多,但是后继无人。但这不是曹家的家史。曹寅子孙并不多。曹家的破败,始于曹寅之死,曹寅死时,已留下大量亏空。康熙一死,曹家失去靠山,败局已定。因此,曹家的“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绝不是因为“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小说写贾府衰落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真实的广度、深度要比曹家的实际更具典型意义。再说,对“一把辛酸泪”的解释也是全错了。“一把辛酸泪”是指曹雪芹在“举家食粥”的困境中,坚持写作十年辛苦不寻常,而又担心无人读懂《红楼梦》——“不解其中味”,而非为贾家(或曹家)无后问题。
(四)关于《红楼梦》的艺术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珍品。思想博大精深,艺术上含蓄蕴藉。在甲戌本的脂批中虽有些关于解读《红楼梦》艺术的批语,但多是空泛议论,不着边际。还有些批语,明显看出脂砚斋对书中的艺术描写旨趣全然无知。如,第八回,宝玉黛玉在薛姨妈处喝酒,正高兴的时候,奶母李嬷嬷即来拦阻,弄得大家扫兴。黛玉对奶母李嬷嬷很烦厌,偷偷地对宝玉说:“……别管哪个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李嬷嬷不知高低,埋怨黛玉不该助宝玉喝酒,反让她劝劝宝玉,黛玉很尖刻地讽刺挖苦和斥责李嬷嬷说:“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你这算了什么。”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妈一面又说:“别怕,别怕,我的儿!……”脂砚斋在“腮上一拧”旁批语是“我也欲拧”四字。[5]
其实,宝钗拧黛玉这一动作,含意颇深,一是表达了宝钗对黛玉的亲密;二是赞赏黛玉的话说得有劲儿,也代表了她想说而不便说的意思;三是有意借此化解当时李嬷嬷的尴尬处境,也给李嬷嬷一个台阶下。这一笑一拧的肢体语言和一句话,是“一箭多雕”。在在场的几个人中,也只有宝钗才能做出来、说出来,也只有宝钗才可以这样做、这样说。从旁观看,这是只有两个亲密的闺中少女才能有的独特动作和语言,是作者描写宝钗的精彩一笔。宝钗这一拧的细节,和后面第二十七回扑蝶误听小红的私语作出的快速反应遥相呼应,是作者借此描写宝钗的成熟老道、睿智敏捷,而非是写黛玉。而脂砚斋“我也欲拧”的批语误以为是仅仅用宝钗的话赞黛玉的(当然,宝钗的话也确实是赞黛玉的),足见脂砚斋没有完全读懂书中宝钗的用意,更没有懂作者的艺术匠心。再说,你脂砚斋何许人也,去拧一个少女?这里不仅看出脂砚斋对红楼艺术的全然无知,也足见脂砚斋之轻狂浅薄。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同是第八回,宝玉回去睡下之后,袭人把“通灵宝玉”摘下用自己的手绢包好放在褥子底下,以免第二天早起带着凉。这个细节本来是表现袭人之细心周到,并为后来无缘无故丢玉作铺垫和照应,是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作为批书人批书,是不可不注意到并以此引起读者注意细品的一个地方。可脂砚斋却在此处批为:“试问石兄此一握,比青埂峰下松风明月如何?”[5]这不仅完全歪曲了这个细节的本意和作用,也足见脂砚斋之无聊和庸俗。
脂批中不仅连这样含蓄性较强的细节和艺术构思没有看出来,就是对有些极一般细节的描写,在脂砚斋的笔下也让人笑掉大牙。如,第四回门子对贾雨村说英莲的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旁边有脂批道:“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痣人可知矣。”[5]
英莲眉心有痣,这跟钗、黛各自的“热”、“怯”特点毫无类比关系。书中写宝钗热毒是为了写冷香丸,写黛玉怯弱,是为了写黛玉有病吃药,这都是描写宝黛二人思想性格和以后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铺垫部分。写英莲有痣,只是说门子以此为据,准确无误地认出了英莲的来历,仅此而已。我们看不出这个“痣”在以后的故事中对英莲的思想性格描写还有什么作用。脂砚斋却根据有痣知道了英莲是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一点都不靠谱的胡说么?这也足见脂砚斋不懂《红楼梦》,不了解曹雪芹起码的描写手法。
再如,在第一回空空道人“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旁,脂砚斋批道:“本名;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5]
这批批得毫无道理。空空道人要将《石头记》问世传奇,自当慎重一些,再检阅一遍本是通常做法,并无不当。书中这样带上一笔的细节,显作者用笔之严密,但并无文外之意;再说,空空道人本是神仙,怎么竟成了“世之一腐儒”?脂批说空空道人这样做是腐儒,倒凸显出他自己是个缺乏起码的写作常识、没有文化底蕴、不懂艺术的地道的“腐儒”。
再如,贾雨村靠贾府之力复职后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呆霸王薛蟠为抢英莲打人致死案,贾雨村原本想“公正”判案,后来听了门子的关于“护官苻”的说法后,书中写道:“雨村听了亦叹道:‘……若能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总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在这段话的上面,甲戌眉批:“使雨村一评,方补足上半回之题目。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5]
这段话本来是说贾雨村为了保官,忘恩负义,准备胡乱办案。但在门子面前又不能不装一下,隐瞒一下自己的意图。他对冯渊、英莲这段婚姻的评论,对英莲的假惺惺的同情,只不过是在门子面前演戏,是说给门子听的,用以安抚和麻痹门子,为以后胡乱判案打掩护的缓兵之计和铺垫而已。这表现出贾雨村的处世之奸滑、狡诈。而脂砚斋的这条批语不仅语无伦次,辞不达意,也全然不知作者这样写的用意,并没有读懂贾雨村的话,而是抛开了书中的具体描述的内容,搞抽象地谈什么“繁中虚”、“省中省”、“省中实”,把读者引人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云。
这类批语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列举。
总之,仔细品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批,可以看出脂批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脂批在“打架”。如何看待这种“打架”现象?首先,如前所述,我们所述引的批语均是地地道道“脂砚斋”同一个人的批语,这些脂批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用“脂批是一个群体,矛盾在所难免”去解释的。其次,这也不能用所谓“精华”和“糟粕”去辩解。脂批里面确有糟粕。但是,这和明显的“打架”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再次,也不能用“批的时间不一样,有先有后,难免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去辩解。这种明显的“打架”和认识上的某些改变,有明显的不同。脂批这种“打架”情况的存在,只能证明一个说谎者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混乱,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脂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自我标榜的同曹雪芹关系很铁,“最知作者的底里”,“更兼有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素材的身份”的一些批语,不过是自吹和谎言。相反,许多批语明确无误地暴露了他并不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旨趣,更不了解书中的人物。他对书中许多内容的解读,连一个普通的读者水平都不如。很难想象曹雪芹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人一同写作《红楼梦》?
二、脂批即使是真,也不能把脂砚斋的批语作为研究《红楼梦》的根据和起点,红学研究应从脂批中走出来
有人可能不认同鄙人的上述论断。我们可以退而言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承认脂砚斋确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同曹雪芹很熟悉的人,全部脂批也都是真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红楼梦》的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那么多的红学分支呢?
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以的。首先,脂批即使是真,也并不等于其批语句句都是正确和精辟的,就可以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经典”。无可讳言,就连把它奉为经典、认为脂批“是研究红楼梦的第一必读书”的专家学者,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误批、谬批也不少”。[7]谎言不可信,“误批、谬批”也同样不可信。这里还有这样一个逻辑问题:这些专家认为的误批、谬批的地方固然是“误批、谬批”了,那么,那些没有被这些人认为是“误批、谬批”的批注,是不是就一定不是“误批、谬批”呢?再有,脂砚斋至今也是一个来路不明、面目不清、语言混乱的人,这样的人说话,我们怎么能深信不疑?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信度究竟有多少?这些,是迄今为止哪一个信奉脂批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明确说清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红学的大厦根基建立在不可动摇的“脂批”的基础上,把脂批奉为绝对正确的经典是不是有些过于轻率了呢?
其次,再退一步而言,脂砚斋和曹雪芹关系确如一些人说的那样密切,是不是就可以对脂批深信不疑了呢?愚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它是用艺术形象感染人、教育人的。作为一部文艺作品的《红楼梦》,它一经离开了作者曹雪芹流传于世,就成为一部独立的、属于曹雪芹又不属于曹雪芹的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人们就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学体验去解读它、欣赏它。对它的理解、评价可能同作者的原来旨趣相同,也可能相异。这是一种在古今中外的一切经典文艺作品中常有的文化现象,《红楼梦》也不例外。曹雪芹自己也充分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才有“谁解其中味”的感叹和担心。对《红楼梦》的解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红楼梦》,就如鲁迅概括的那样,不同的人从《红楼梦》中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清朝的张新之也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强求。对《红楼梦》的解读出现的这种复杂现象恐怕是曹雪芹自己也不会料到的。从《红楼梦》流传史上看,绝大多数的人始终是把它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去品评欣赏的。在解读《红楼梦》面前,就是曹雪芹本人的批注也不能完全拴住读者想象的翅膀,何况是脂砚斋?脂砚斋作为一个《红楼梦》最早的读者和批书者之一,他的批语也不过是他个人的读书随笔而已,既不能把他同曹雪芹等同起来,他更不可能完全代表曹雪芹。批语违背曹雪芹的原意或不了解曹雪芹的原意都是可能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脂砚斋,更不能神化脂砚斋。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讨论,即,如何看待脂批中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一些故事情节以及所谓曹家“真事”、“是事”的批语问题。愚以为,对脂砚斋提供的这些“信息”,即使是可靠的,也不必十分当真,更不必费我们的无穷精力去考证、坐实。首先,这些信息本身似实而虚,虚无缥缈。红学史的研究实践证明,无从坐实。其次,《红楼梦》的本质属性是小说,即使反映的是曹家的事儿,它一进了小说,性质就变了,就是独立于曹家家事的文艺作品,二者已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按迹循踪”去坐实,让脂砚斋牵着我们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8]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引导到解读、赏析《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上,而不能将无穷精力放在研究其素材和模特上。
总之,愚以为,对脂批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注意脂批的参考价值,又不能过于迷信,神化脂批,不能把脂批毫无保留地作为我们解读《红楼梦》唯一的、权威的根据,更不能站在“脂批”的基础上讨论《红楼梦》的问题。一切以脂批为据的创新学派,都是违背艺术欣赏原则的。
红学研究应从脂批中走出来,回复其文艺作品的应有品格。让红学研究从泛娱乐化、泛趣味化、神秘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的倾向中走出来!
[1] 俞平伯.乐知儿语说红楼:宗师的掌心[M]//俞平伯文选(第4 卷).长沙:岳麓书社,1999.
[2] 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3] 张兴德.腰斩红楼梦有罪,程伟元高鹗有功[J].辽东学院学报,2011,(3):109.
[4] 张兴德.好了歌解与司马季论卜[J].红楼梦学刊,2012,(2).
[5]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主人评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 张兴德.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162.
[7] 梅节.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4).
[8] 鲁迅.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