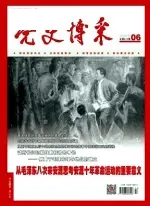论群体事件处置中的政府公信力
2012-08-15何永红
何永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 河北廊坊 065000)
论群体事件处置中的政府公信力
何永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 河北廊坊 065000)
政府公信力与群众工作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构成预防和治理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子。政府公信力事关稳定大局,做好群众工作,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让底层民众重拾信心,恢复社会信任感,这是政府合法执政、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基础。从治本与治标两个层面治理群体性事件,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公信力;群众工作;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社会公共事件消耗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事件发生后的当地政府缺乏可供应急使用的信用资源,面对民众,显露出无能、无威望、不服众的窘态,出现管治危机。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以及2011年沿海城镇发生的新塘、增城与潮州骚乱等群体性突发事件,都从不同程度反映了在公正、诚信、服务、法治、民主等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欠缺。为了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提升政府公信力;而要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度,更主要的是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
一、政府公信力、群众工作与群体性事件的相互关联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行为的公正、民主和法治程度,社会公众对政府履行职责权力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以及政府获取社会认同的能力程度。党的群众工作,指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为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政府公信力、群众工作与群体性事件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组织、宣传、教育和服务群众?信任在群众工作各个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公信力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如刘孝云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问题, 他认为政治不信任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1]。社科院于建嵘教授认为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是社会泄愤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他认为政府的管治能力低下,本质上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漠视[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表明老百姓对地方政府不满,对基层公务员群体不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单光鼐研究员认为要突破上述困境,最直接的措施,是建立政府的公信力。罗竖一在《联合早报》认为辽宁省海城市城建局、河北省栾城县国土资源局等之类的于客观上失信于民的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而2011年5月深圳宣布撤回禁止上访讨薪规定,向农民工道歉的消息又一次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也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信任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干群相互宽容和妥协的心理气质,有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姚亮和彭红波也对提高政府公信力与群体性事件之消除进行了研究[3]。
其次,有效的群众工作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如近几年来,公安边防部队的“三访四见”、爱民固边战略和“大走访”开门评警等活动,是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有益尝试和新亮点,是应对群众工作新变化和解决群众工作困境的重要举措。该活动和举措真正找到了群众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立足点;找准了群众工作的切入点,抓住了执法机关与群众关系的实质。这些群众工作实践活动确保了我国边防辖区的安全与稳定。截至2009年7月31日,公安边防部队共在边境辖区创建爱民固边模范村1549个。模范村建设始终保持活力,大多实现了零发案、零纠纷,成为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的示范点[4]。
最后,群众工作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它们共同作用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效的群体工作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政府公信力提升同时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中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因此,要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就必须加强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是提高政府与群众间的信任社会资本和实现社会稳定。提升政府公信力、获取群众信任就要走近群众,走进群众,了解群众需求,尊重群众、贴近群众和依靠群众。正确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保障。因此,不断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提升政府公信力,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政府公信力、群众工作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公信力和有效的群众工作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各个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预防阶段,政府公信力和群众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如下:有助于建立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落实信息责任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大部分是由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无奈采取的自发的集会,以大众的力量向政府施压以期唤起政府的注意,从而改变现状,解决社会问题。如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云南勐连事件等规模较大的事件都与民众与政府之间不信任有关。政府是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领导主体,其信任关系的好坏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状况。基于政府权威和信用的政府信任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能够避免因制度政策缺失、利益纠纷而造成危机,有效地进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部分基层组织的长期不作为,没有说服群众、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公信力等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是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举措之一。
[1]刘孝云.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问题分析[J].探索,2009(5):78
[2]于建嵘.反思社会泄愤事件.南风窗,2008-7-18
[3]姚亮,彭红波.提高政府公信力与群体性事件之消除[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9):35
[4]公安边防部队爱民固边战略取得新进展——创建模范村1549个(N).人民公安报,2009-8-4(1)
何永红,(1969—),女,天津人,汉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处置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升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而信息的不公开和不透明易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因此,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在群体性事件处置阶段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政治不信任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部分基层领导不作为、干群关系恶化等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缘由之一。群体性事件的合情、合理、合法处置需要政府主导和民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民众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影响力,实现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合作,共同化解各方矛盾和利益冲突,达到团结、稳定和秩序的处置效果。
在善后阶段,政府公信力对于稳定干部和百姓的心理,化解各方利益冲突,有效避免事件的反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民众与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干警为代表的政府依法调查取证,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区别情况,分类处置,查处违法犯罪成员,依法追偿所造成的损失;有助于政府在对整体的处置工作进行最后总结时,将调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并采取相应措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确保群体性事件的不再复发;有助于对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制意识是化解矛盾的重要一环。三是民众与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做好伤亡的善后工作,降低社会救治的成本。如瓮安群体性事件后,政府为重新建立了各方的信任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举办一系列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文体活动,来稳定干部和百姓的心理;对老百姓进行一些法制教育,让他们懂法、守法;对干警进行教育,规范干警的行为,限制好干警社交群。
从以上分析可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群众工作乏力具有直接的关系。政府行为失当,信息公开机制缺位,无法展开有效的群众工作,从而导致群体自救行为和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