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市寺庄镇公共空间的变迁
2012-07-30莫微
莫 微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1 乡村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具有社会空间和建成空间的双重性质,本文中的公共空间是指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开展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等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1]。
2 公共空间的分类
本文将寺庄镇地区的公共空间划分为行政型公共空间、制度型公共空间以及生活型公共空间。行政型公共空间包括文革时期修建的舞台广场、村委会以及其他行政性集会的地点;制度型公共空间包括关帝庙、仙翁庙、白衣阁等神佛崇拜的场所,以及宗祠和大户人家的宅邸;而生活型公共空间包括房前屋后的平地、理发店、小卖部、村口的大槐树、水源处等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点。
3 寺庄镇概述
山西高平市寺庄镇位于晋西南角。全镇东、西、北三面环山,中南部为河谷地带,地形平缓。超过半数的村落的建筑沿着大的丹河支流分布,河谷平川的村落较大且集中,山区的村落较小而分散。
高平县春秋初期为戎翟所居。战国时为长平,属韩。至北魏,改置建州,长平为郡,领高平、泫氏二县。唐肃宗废高平郡,恢复泽州。从此以后,高平县一直属泽州。经历五代,宋、金、元、明、清不废。1961年后,分县后,恢复高平县建制至今。早在春秋时期,寺庄镇就有史书记载。《竹书纪年》:“晋烈公元年(公元前419年),赵献之城泫氏”,泫氏城故址在寺庄镇王报村。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的古战场也在寺庄镇内。
4 寺庄镇公共空间变迁
笔者于2010年7月~8月对山西寺庄镇36个村子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访谈和史籍资料得到寺庄镇的村落中心及公共空间的变迁。以时间为脉络将寺庄镇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第二阶段是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今。
4.1 第一阶段:解放前
晋东南地处太行山区,在儒家传统礼教影响下,遵典礼而重明禋,故祠祀遍及城邑乡里。此地炎帝崇拜之风非常盛行。清康熙二十年,赤祥村炎帝庙“增修炎帝庙记”碑文云:炎帝之祀,“最盛莫如吾邑,计长平百里,所建不止百祠祀之”[2]。除炎帝庙外,以农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神灵为崇拜对象的玉皇庙、成汤庙;以子息繁衍相关的神灵为崇拜对象的观音阁、观音庙;以科举功名相关的神灵为崇拜对象的文昌阁、文庙、夫子庙等;以佛教道教神灵和传说中的其他神异人物为崇拜对象的老君庙、仙翁庙、二郎庙、关帝庙等,在当地都非常常见。另外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对该地均有影响,且互相融合。安家村西珏山为当地最高的山之一,西珏山顶的三清观为寺庄镇最大的寺庙,三清观里三清、玉皇大帝和观音共存(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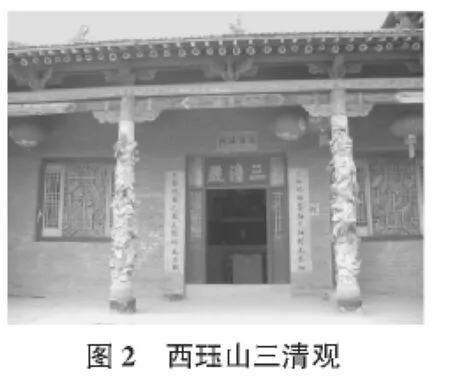
在古代社会,村庙是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文化娱乐中心。民俗活动往往依托村庙进行。如各庙的庙会及迎神赛社活动。大庙一般都有庙会,时间定在该神生日期间,会期短则一日,长则半月二十天,有的庙会一年两三次。庙会期间,烧香布施求子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3]。
宗教建筑也对村落格局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阁是村子的出入口,控制着村落的发展(见图3,图4)。直到今天,村子里的老人仍然有“出阁”一说。即村子在向外扩建的过程中,不可超过阁所限定的界限,不然就会遭到神灵的谴责。这个空间上的边界,并于观念上的“阁”,共同构成了村落的边界。


宗祠在血缘基础上起着建立村民联系,并且完成建立伦理基础的作用,如靖居村的东堂和南堂。而大户人家作为村民的精英,对制度的形成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地大户人家院落代表当推釜山村的棋盘六院。棋盘六院在釜山村主干路南,修建于清乾隆元年,宅院原主人名叫王六泉,是清代釜山有名的富商。因王六泉先生膝下有六子,故而营建六院供六子居住。
4.2 第二阶段: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力量几乎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所有领域。此时的乡村社会整合于国家权威之下,行政化公共空间在乡村占据了主导地位 。虽然这个时期相当短暂,但在寺庄镇的每个村落都留下了痕迹,河泊村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舞台广场是当时村民活动的中心,也是最受人瞩目的公共空间(见图5,图6)。另外随着政治运动如乡村土改、人民公社化等的开展,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与亲缘文化受到了强大的冲击[1]。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传统的制度化空间受到严重影响。


4.3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1)制度化空间的衰落与转变。
自现代社会之始,制度化空间的影响就在逐步地减弱。原本受人祭拜的神庙逐渐变得冷清,部分衰败下去无人修葺管理(见图7);部分经历了重修却难以再延续以前的香火;还有相当多的庙宇完成了功能的转变,与新的公共建筑结合设置,从而形成了新的村庄中心。
李家河的关帝庙就经历了多次功能的变迁(见图8)。建国初期,这座古庙一度被作为供销社使用,1970年后,供销社逐渐变成了商店。釜山的玉皇庙、望云村的佛堂殿在解放前期改成了小学。北王庄村的汤王庙在文革时期曾经作为大队的办公点。靖居村的庙宇结合村委会,卫生所以及警务联络室等发挥着公共中心的作用。


村委会、供销社、小学、卫生所、舞台以及商店等公共建筑逐渐替代了宗教建筑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人们的意识也开始发生转变,从崇拜鬼神,向神灵寄托命运到重视世俗生活。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建房政策的改变而修建起来的整齐成排的青砖房改变了村落空间格局。而进入新时期后,行政化空间也随着体制的转换而逐渐冷清消解。
2)生活型空间的延续。
在制度化空间和行政化空间相继衰落后,由村民的生活习惯主导的生活型空间在延续千百年来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
村民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作息;生产性活动仍然是当地的日常性活动,在农村生活里占据了极大的成分;生产性生活公共空间延续着,如石磨处、水源处;村民所处的仍然是熟人社会;村民分享着充满人情味的自发性活动空间。
3)乡村传统边界的消失和乡土社会的新变化。
制度化空间的没落使得原来作为村落边界限制的庙和阁不再起到限制作用,在村落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村落千百年来的边界消失了。即使经历了社会制度变革,市场化经济的冲击和城市化的大潮影响下的寺庄镇本质上还仍然是重口头语言,均质化的乡土社会,但近年来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千百年来以阁为界限的村落空间不断向外扩展。山坡上的村往山下走。平原上的村子突破阁的限制不断扩展。王报村位于开阔的平地上,老建筑在村西侧,越靠近主路和寺庄镇,房子越新。在村落最东边,则全是独门独户红砖红瓦的整齐的新农村样板房。
其次,村落地出现了空心化和老龄化的现象。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离开本村出去务工,留守和在家种田的大部分为老年人和儿童。又随着村落向外扩张,村内的老房子因为交通不便逐渐被废置,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
再次,村民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寺庄镇有长平、伯方、望云、百盛、高良5个国有和二轻煤矿。高良村位于过境道路北侧,规模较大,村边即是煤矿和选煤厂,村子经济情况较好,村民的生活方式较北部村落如河泊村也有所不同,村民的生活更加接近城镇居民的生活。室外生活的消失导致了生活型空间的没落。
5 结语
制度化公共空间自古以来极大地影响着寺庄镇的发展。解放后同一性的政治型公共空间曾经短暂地主导着村民的生活。随着村落不断发展和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制度性空间渐渐衰退。新的公共建筑和村落中心开始出现,不过以前的宗教建筑并没有被全部拆毁,更多的是与新的公共空间相结合,形成新的村庄中心。
改革开放后新村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共同改变了村落的生活,城市化的脚步加快,室外生活消失导致村民们之间变得陌生和生活型空间的没落。
[1] 戴林琳,徐洪涛.京郊历史文化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成动因、体系构成及发展变迁[J].北京规划建设,2010(3):74-78.
[2] 贺晚旦,杨红保.炎帝故里在高平[N].山西日报,2007-08-11(A04).
[3] 冯俊杰.山西神庙与戏台调研小结[J].中华戏曲,2002(1):26-70.
[4]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2005(6):6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