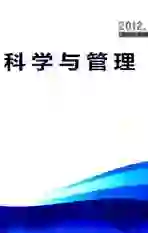600年来中国带鱼种群历史专题导言
2012-04-29李玉尚
李玉尚
编者按:2012年始,本刊推出《环境与社会》栏目,旨在鼓励研究者探索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从历史角度看,资源与环境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极为复杂。本期刊出的“600年来中国带鱼种群历史专题”揭示了600年间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变迁过程,也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发展海洋渔业”提供了一个历史解释。
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和带鱼曾经是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但现在大、小黄鱼濒临绝迹,墨鱼形不成渔汛。带鱼的资源量虽然业已严重下降,但作为仍然幸存的第一大渔汛,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本专题四篇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都与历史有关:为什么带鱼在1930年代之后才挤身于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之列?在没有成为四大经济鱼类之前,它在闽浙和其他一些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中为什么绝非无关紧要?1930年代及其之后,它的渔获量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变动?捕捞因素之外,自然环境以及种群之间在其区域分布和资源数量中又扮演什么角色?
从渔获量上来说,1980年代以前带鱼在南海北部的经济鱼类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王涛关于清代以来南海北部带鱼渔场变化的论文,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清代所进行的一场生物之间的“渔场战争”的生动故事。他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发现粤西和北部湾的带鱼种群渔场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化,用历史经验证明了两个地方种群之间的独立性。南海北部还有粤东种群,它和粤西种群以珠江口为分界线,但清代以来其渔场并无太大变化,王涛的解释是,这一种群和东海越冬鱼群混栖一段时间后,已有很强的东海带鱼的特征。
黄渤海的带鱼虽然属同一种群,但其产卵场和索饵区,如海州湾、乳山湾、烟台沿海、莱州湾、秦皇岛外海、盖州-复县海区和庄河沿海等,相互隔离,各有领地,互不打扰。由于纬度的关系,海州湾、乳山湾和烟台沿海产卵场汛期为春汛,其他海区则为夏汛。受制于麻制网具,传统时代黄渤海渔民渔捕的时间多集中在阴历三至五月,资源数量丰厚的带鱼就阴差阳错成为清代和民国年间诸城、莱阳和牟平的第一大渔业;夏季才到达河北、辽宁沿海的带鱼却一直过着一种少被渔民打扰的日子,无意中让鲚鱼成了“替罪羊”。虽然平静的日子在1930年代之后被打破,但让带鱼们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是1950年代夏汛、秋汛乃至冬汛捕捞力量的加强和机动船数量的迅速增加。
让带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迅速跻身东海“四大经济鱼类”行列的戏剧性一幕是嵊山渔场的发现。传统时代的渔民,如若遇到海上荒歉的年份,还能靠着一亩三分地勉强熬过;但若海上作业时遇到风潮浪灾或海盗,则关乎身家性命。民国时期嵊山属江苏崇明县,属于远洋之区,这里却是海盗们的乐土,渔民自不敢轻易靠前。张謇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之后,因为渔政船的保护,闽浙渔民遂蜂拥群至,带鱼渔场就这样被意外发现了,由此奠定了带鱼在东海中当家花旦的地位。
韩志浩给我们讲的嵊山渔场的精彩故事只是东海北部带鱼的一段插曲。梳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和渔业调查报告,他发现在这两个时期,捕捞带鱼的群体都是以福建沿海和浙南沿海的渔民为主;而在离舟山渔场距离最近的宁波地区,一直以来都以捕捞大、小黄鱼为大宗。这确实出人意料。原来,明清以来福建沿海和浙南沿海地区粮食一直不敷食用,带鱼的汛期恰为冬汛,大量捕捞正可解决冬季缺粮的难题,和渤海和黄海北部的带鱼群相比,东海带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在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巡抚张延登的《请申海禁》疏中,他对福建沿海渔民到浙南和舟山地区捕捞带鱼之事可谓耿耿于怀。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朝廷告福建渔民的状呢?陈亮的论文告诉我们,原来明初以来朝廷出于备倭考虑,厉行海禁,对闽省渔民出海渔捕的海域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比如福建渔民不许至浙省捕鱼;但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海防体系的衰败,兵防船只巡海范围大为内缩,航海水平竟然退化到远不如老渔民的境地,闽省渔民蜂拥跨省钓带,遂引起张延登的关注。受平定台湾的影响,清承明制,对沿海渔民出洋捕鱼仍多有限制,但雍正之后驰禁日松,至嘉庆年间,赴浙钓带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许可,自此之后,浙省渔场中又出现福建渔民那熟悉的身影了。陈亮的论文还告诉我们,明清时期福建带鱼的资源数量极为丰富,明清时期国家海禁政策的执行,恐怕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
从本专题所讲的600年间中国海带鱼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种群自身、地理环境、国家政策、渔民生计、渔场发现、船网变革、渔业保护等因素对其资源数量和渔获量的影响。这些故事当然没有终结,可能还有精彩的续集,比如气候突变、入海河流水量、水团、风力对其种群资源数量变动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