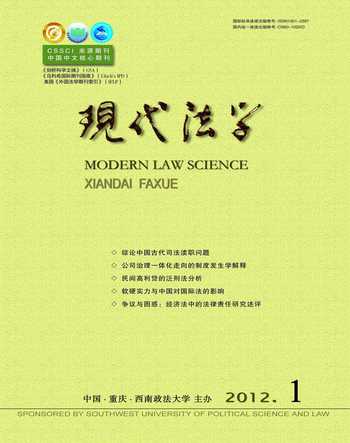论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
2012-04-29周叶中,梁成意
周叶中,梁成意
摘 要: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表明,学术追求与政治担当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在于: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洞悉历史逻辑,揭示宪政规律;立足客观实在,形成宪法共识;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而中国宪法学家政治担当(推进民主政治)的基本维度在于:中国国情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基础,宪法思维是促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智慧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
关键词:古典政治哲人;宪法学家;学术追求;政治担当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02
一、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政治哲人
费希特认为:“人总是有求知的意向,特别是有一种认识他所急需做的事情的意向。但发展天资与满足意向需要人的全部时间与全部力量,这就催生了一个职业阶层即学者。学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人的使命主要是由职业化的学者来完成。”[1]
在古代,科学知识水乳交融般地纠缠在一起,呈现出整体状态,而所有关于整体的知识统称为“哲学”。探索这种知识的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统称为“哲人”。但随着智识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类,就连人文科学也出现众多分支学科。事物的整体仍然属于哲学关注的对象[2],
而各个部分则属于其他学科关注的对象。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宪法学关注部分事物,是部分知识。但在法律科学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因此宪法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特别是在立宪主义理念与宪法至上的观念下,所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宪法问题。因此,在法学体系中,宪法学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哲学韵味也更加强烈。作为整体,宪法学本身就是哲学;作为部分,宪法学必须从(总体)哲学中获得理解。[注:
“人们只有借助部分才可理解整体,但何为部分,唯在对整体具有一种‘前理解时,方能知晓。”(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钡贝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敝S懒鳎译北本:法律出版社,2002:52保]在这一意义上,对宪法学的理解以及对宪法学家的定位,都必须首先寻求对总体哲学的理解,而古典哲学则是最为纯正的总体哲学。
由于只有哲学,没有分门别类的科学,因而古代世界只有哲人,没有分门别类的学者。因此,古代世界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学家”,但有关法律的思考却从一开始就存在。从事这种思考的人,后来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哲人”。古罗马的瓦罗把这类人的作品称为“神秘神学”或“政治神学”。这两类人在圣奥古斯丁眼里其实是一回事。18世纪的法理学家维科认为,这类人就是政治哲学家。[3]
由此可见,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原初都寄生于政治哲学中;包括宪法学家在内,所有学者的原初形象都是政治哲学家。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政治是人的联合。在人的联合中,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国家共同体因自足性与互助性成为最高的、最权威的团体。由于人的动物性,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共同体(如城邦)或任何将来可能出现的共同体(如“欧洲共同体”)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传统”、“习俗”、“宗教”等规则之上。这些非理性的规则,作为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保证了共同体的特殊性与封闭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与封闭性,使绝大多数人成为“自然洞穴”中的“囚徒”[4],
从而产生个人生活最需要、最迫切的秩序。
然而,人的理性促使人反思、审视自己的生活。政治生活虽然迫不得已,但毕竟不是理想状态。因此,政治生活的尊严源于某种立足于政治并超越政治的东西。柏拉图把这种“超越”理解为人在自然洞穴中的“上升”过程。“上升”的终点是哲学,目的在于为政治社会描绘一幅善的、正当的、理性的理想蓝图。哲人的(今天意义上的学者)使命首先在于探讨并告诉人们超越于政治的理想生活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说,这种使命就是“学术追求”,即不考虑现实中的任何因素,在理论上探讨理想生活的“原型”。[注:
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如此。如牛顿“第一定律”假设的无摩擦力的“理想状态”。]这是所有人都不反对的“使命”,甚至有当今学者视其为唯一使命。
一般说来,由学术描绘的理想蓝图是一回事,而根据理想蓝图改造政治社会却是另一回事。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学者有没有促进政治生活达至理想生活的使命。如前所述,学者的使命在于服务人的社会生活,因此理当肩负这一责任(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一点)。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哲学”对政治的关照,是彻底否定政治社会进而采取颠覆性“战术”,还是“正视”政治社会的迫切性、首要性及其当下的正当性,进而采取改良性“战术”?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意识到后者是必然的选择,并开创了“隐讳教导” [注:
“‘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捉摸文本才能领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惫诺浔J刂饕逭治哲学的复兴[G]绷邪•施特劳斯弊匀蝗ɡ与历史,彭刚,译北本:
北京三联书店,2006:80保(与苏格拉底的“俗白教导”相对)的古典传统。
在“自然洞穴”的隐喻中,政治哲学家(古典时代的法学家属于此列,如亚里士多德)的使命首先是“上升”(走出洞穴)战略,即超越政治,追求真理,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其次是“下降”(回到洞穴)战术,即回归政治,改良政治,指引人的生活,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政治担当。必须明确的是,本文所说的学者、哲人是指一个“阶层”或“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共同体”应该有双重使命,而不是说每一个体都必须具有双重使命。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作为一名宪法学家,学术追求无疑是必备的、首要的,政治担当则是延伸的,也是可以选择的。但一旦做了“延伸”与“选择”,就应该懂得如何关照政治,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会破坏、颠覆政治社会。
综上所述,古典政治哲人的特质可做如下概括:第一,胸怀理想,追求真理,力求为政治社会描绘一幅理想蓝图。第二,立足现实,服务社会,建设性地促进政治生活向着理想蓝图迈进。前者是他们的学术追求,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担当。这双重使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构筑了他们的完美形象。
作为古代学者的总称,古典政治哲人尚有学术追求与政治担当的双重使命,那么现代学者更不能例外。就身份而言,作为学者的宪法学家当然具有学术追求的使命。而且,由于宪法学家以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为研究对象,并以民主、法治、人权、宪政为基本追求,探寻治国理政的原则、方法与实施方案,因而无疑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担当。因此,基于学者的身份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学术追求与政治担当毫无疑问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
二、学术追求:拓展研究领域,把握宪政规律,形成宪法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一般说来,学者应该从三个方面研究自己关涉的领域:哲学方面、历史哲学方面以及单纯的历史方面[1]40。哲学要求人们通过纯粹思辨获得永恒不变的真理,历史哲学要求人们通过曾经、已经、即将的存在(这三者属于广义的“历史”范畴)获得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二者在终极意义上是同一的(即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都属于哲学范畴,只不过达至哲学的手段不同而已。通过纯粹思辨的方法获得真理是唯心主义的方法,通过曾经、已经、即将的存在(表现为历史中的经验)获得真理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本文秉承唯物主义的方法,认为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是基于历史的方法,揭示宪政规律,寻找宪法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一)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
科学家应该从现象中归纳出原理,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5]。
这一论断说明了归纳与演绎是科学活动的两个基本环节。科学理论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归纳,科学理论的应用主要依赖于演绎。科学理论的证明是一个满足归纳“格”的问题。归纳是基于经验所做的概括,因此归纳既是发现、又是证明命题的活动[5]65。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在精神科学这个领域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6]。
然而,归纳法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其有效性的质疑。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归纳原理的质疑,即归纳作为一种推理方式,不能用来证明归纳原理,即不能用归纳来证明归纳[5]71。用休谟的话说就是,从我们经历过的(重复)事例推出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其他事例(结论),这种推理(方式)我们证明过吗[7]?
二是对推理结论的怀疑。由于归纳推理依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而这些经验材料有些反映本质,有些不反映本质,有些属性为全体所共有,有些属性只存在于部分对象中。从这些个别的、有限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不一定是事物的共性,不一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因此,归纳推理往往不严密,属于或然推论[5]79。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归纳法,优选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基础。因为由归纳得出的理论能够概括归纳对象(经验)的本质,至少能为已有的经验所检验。换言之,从终极意义上讲,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论,我们就不得不选择接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并称之为“合理的”。“合理的”是从我们知道的这个词最明显的意义上讲的:接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就是迄今为止最佳的理论,而且目前还未发现有什么更好的理论[7]25。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做的是明确归纳法的两个“软肋”,并在运用过程中尽量予以克服。第一个“软肋”(对归纳原理的怀疑)是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而第二个“软肋”(经验的有限性)告诉我们,经验材料越多,归纳出的结论越相对可靠[7]63。因此,尽管不能穷尽所有经验材料,但一定要尽量多地发现、整理经验材料。只有这样,才能使结论更科学、更合理,从而提高结论的逼真性。这也是所有科学的目的。[注:
波普尔认为:“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因而科学的目的是“追求逼真性”,“提高逼真性”。(卡尔•波普尔笨凸壑识[M]笔嫖肮狻⒆咳绶桑等,译鄙虾#荷虾R胛某霭嫔纾2005:53,65,80保 ]
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准则。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自然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符合宪法学的定义,即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然而,现代宪法学是以近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宪法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因而摆脱不了归纳法作为或然性推论的“软肋”,即西方现代社会以外的宪法现象能接受现代宪法学的检验吗?宪法的全球化(特别是非西方文化圈宪法的兴起)、欧盟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等新的现象都充分说明,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性、地域性,充分暴露了现代宪法学的理论困境。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宪法学所能做的首先是求教于历史经验[8],丰富宪法经验材料,扩大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提高宪法学的“逼真性”。
历史是人和事的记录,把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即为历史[9]。
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经验史(在此基础上才是思想史,如下文阐述宪法学中的观念史问题)。而当今宪法学认为,宪法史就是宪法的法律史,因而“非法律性的”宪法史由此失去其价值,宪法的非法律现象(如宪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也未能进入宪法学视野[10]。
也就是说,当今宪法学是以宪法的法律现象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对宪法的“非法律性”现象则缺乏关照,甚至否定非法律性宪法现象存在的合理价值。笔者认为,当代宪法学必须扩大宪法的历史视域,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将目前能够把握的各种宪法现象纳入宪法学视域,以对现有的宪法理论与研究范式做出修正。在科学方法上,无论库恩的范式理论,还是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认为,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应该去修正理论,而不是削足适履、为理论辩护而否定新的经验。
(二)洞悉历史逻辑,把握宪政规律
人类政治从古代过渡到近现代的核心标志,就是宪政的产生。正是近现代宪法的产生,人类政治才由“权力支配法律”的时代进入“法律支配权力”的时代;正是近现代宪政的产生,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法律状态”;正是近现代宪政的产生,人类曾引以为豪的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才演进为代议共和式民主[11]。
因此,宪政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治国理政方式的变化。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治国理政方式的变迁,在本质上就是要洞悉历史逻辑,厘清宪政思想的历史演变,把握宪政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宪政建设的成败得失。
历史首先是经验事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不是事件本身)则形成相互关联的逻辑链条。当人们只观察事件而不洞悉背后的思想时,历史就表现为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经验事件。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不仅是经验史,更是思想史。作为思想史,历史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发展,因而历史过程便是一个逻辑过程。可以说,历史的转化就是将逻辑的转化置于一个时间标尺上。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在这里,逻辑的先后关系并没有被时间的先后关系所取代,相反却被它丰富和加强了。所以,历史中的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我们对一个历史过程的认识不仅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据此能够看出它的必然性[12]。
这一史学观告诫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经验,更要明晰隐藏在经验背后的思想与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洞悉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据此,中国宪法学尤须考虑宪政发展的历史逻辑,明确具体宪政制度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纵观宪政史,到目前为止,西方宪法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观念(古典社会)到政治宣言(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政治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通过制宪的方式确认革命时期的政治宣言)再到今天的宪法法(通过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真正成为立法的依据、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以及司法机关的最高裁判规则)的发展过程。很显然,这一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人类认识的逻辑,因而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宪法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政治观念阶段,思想家们讨论了宪法的政治哲学,主要问题是宪法、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法律、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宪法法的产生奠定思想基础。在政治宣言阶段,政治家们主要是描绘社会的理想蓝图,提出社会变革的价值追求,为成文宪法的产生奠定坚实基础。在政治法阶段,宪法文本得以产生,但其政治功能远大于法律功能,宪法作为名义上的根本法未能实际主导整个社会治理的规则体系,相关部门法如民法等反而成为现实社会治理的主要规则。在宪法法阶段,宪法的法律属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根本法地位在法律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一切法律都可能成为宪法的审查对象,而政治形态则表现为宪法政治即“宪政”。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宪法与政治革命如影随形。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宪法一直是革命的纲领。只是到现行《宪法》颁布之后,宪法作为革命理念与成果的色彩才得以淡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政还处于政治法发展阶段。然而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不能洞悉宪政规律与中国宪制所处的历史阶段,因而我们总是习惯于以西方当下的宪法法审视作为政治法的中国宪法。如有学者基于宪法法,认为宪法的功能体现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而由于中国宪法没有被司法适用,因此出现了“宪法无用论”;由于不能理解处于政治法阶段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因而不能理解由《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引发的宪法与民法之间的争论。因此,如果能正确理解宪政发展的一般阶段、各阶段宪法实践的一般特点,以及中国宪法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中国宪法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指责,也不会有过于苛刻的要求。相反,实事求是的态度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完善方案,以推动宪法从政治法向宪法法的转变。
其次,一国宪法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一国宪法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横向比较研究,还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历史考察。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宪法以西方分散型文化传统为基础。而中国宪法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之所以一波三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初以西方现代宪法为蓝本(比较典型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宪法),因而在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后,才逐渐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型文化)。现行宪法体制(民主集中制)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逻辑的耦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传统对宪法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对具体制度的理解,不能仅与它国宪法做横向比较,还要对之进行纵向考察。例如,如果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演变,以及后来国共两党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仅以现代西方政党理论与制度作为研究工具,那么就不能合理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而且,这种对政党制度的研究还可能导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果。因此,既做横向比较研究,又做纵向历史探究,是中国宪法学理解、解释中国宪政的重要途径。
(三)立足客观实在,形成宪法共识
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的对象往往是文化事件。[注:
转引自:马克斯•韦伯鄙缁峥蒲Х椒论(汉译本序)[M]焙水法,莫茜,译北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5盷进入科学研究范畴的文化事件总是由事实与价值两个要素组成。因此在逻辑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式。事实判断就是要对事实做客观描述,以厘清事件本身的各种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价值判断则可以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13]
因而具有极大的主观性。然而,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论断后,人们即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构建整个社会科学,而事实判断的科学功能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结果把理论当作历史的客观事实。这种方法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危害极大:“由于选择出来的概念标准所产生的类型系列,因而好像是具有规律必然性的类型的历史次序。于是,概念的逻辑秩序这一方面,和概念在空间、时间和因果连接中的经验秩序这另一方面,显得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致为了在实在中证明结构的真正有效而对实在施加强力的尝试,几乎不可避免了。”[13]51-52现代西方宪法观正是如此。
现代西方宪法立基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记载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回答了“宪法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是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价值判断。当人们毋庸置疑地把这种特定地域的文化价值作为普适价值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韦伯所说的“为了在实在中证明结构的真正有效而对实在施加强力”,亦即为了证明理论的有效性,总是无视、贬低、否定新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去反思理论。这正是现代宪法学的现状。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逐渐得到相应社会的认同。这样,与西方宪法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由于价值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使各宪法之间无法形成主观上的有效性,更无法形成基本共识。然而,由于科学总有一种普适化倾向(这种倾向是正当的),因而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形成共识。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这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宪法学理论。
由于宪法学研究者之间的共识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而客观性有赖于遵循价值无涉的研究原则,[1322客观描述研究对象,因此,探求宪法学的客观性,必须首先对宪法进行事实判断。社会学家涂尔干对这一研究方法曾做过精彩阐述[14]。
宪法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努力描述宪法固有的本性,即客观实在性,以此告诉人们宪法是什么,从而阐释其客观性、实在性与历史必然性。这一描述、阐释如能统摄所有宪法类型,则说明其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逼真的。如有例外,则说明这一描述缺乏科学性。因此,客观、有效地回答“宪法是什么”,实际上即寻找到了宪法的同一性,为宪法学搭建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
在这种共识基础上,即可把特定宪法放在特定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之中(即特定的共同体中),追问“宪法应该是什么”,以回答宪法的正当性基础与精神价值。然而,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宪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相同。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以客观性、必然性、同一性、普适性为基础的宪法共识,来源于对宪法进行的事实判断,而差异性则源于对宪法进行的价值抉择。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宪法是什么”做一个统而概之的回答,因而是个客观共识问题。但对“宪法应该是什么”只能基于特定语境做具体回答,因而是个地方性价值问题。然而,基于宪法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又必须在事实判断基础上探求宪法的价值抉择,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构建宪法共识。因此,我们并不否认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必要,只是必须明确价值判断的科学功能(解决宪法的正当性问题)、适用范围以及与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
(四)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解释、解决社会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的使命,也是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所在。自1970年代后,社会科学的应用性和现实性不断增强,出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知识产生方式,取代了以往“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当下社会科学在追求增加人类社会知识这一目标中,更加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15]。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中心,以解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己任,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这既是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也是中国宪法学生命力之所在。笔者以为,正当性、基本功能、根本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规定性。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在于正确地解释这三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问题。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正当性的根本方法。一切权力,甚至包括一切生活,都要求为自身辩护。[注:
哈贝马斯焙戏ɑ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鄙虾#荷虾H嗣癯霭嫔纾2000:127 ]一部宪法也是如此,也必须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以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等问题。世界各国宪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回答自身的正当性:一是将宪法的正当性建立在超验的基础之上,如西方宪法将“天赋人权”作为其正当性基础,伊斯兰世界将宗教信仰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基础。这种将“天命”、“宗教信仰”、“绝对精神”等主观意识作为宪法正当性基础的,可统称为“唯心主义”宪法观。与唯心主义宪法观相对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宪法观,它将宪法的正当性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宪法的正当性。然而,物质生活条件总是表现为客观的、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通过历史叙述物质生活条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证成宪法的正当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宪法的重要特点,如《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宪法》、《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
我国宪法序言记录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重大社会变革,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叙述历史,制宪者确立了建国宗旨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及制宪目的和宪法指导思想。宪法把这些“经验”、“宗旨”、“目标”、“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这种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宪者试图通过历史性的叙述表明,中国需要宪法,但需要的不是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宪法,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因此,“序言”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正当性。由于建立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并通过历史来展现这种客观实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中国宪法正当性的根本方法。
第二,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功能。[注:
参见周叶中苯袢罩泄论坛,2007年第8期有关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双重功能为: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两者的地位并不平行,前者以后者为目的。因为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则是多数人的统治,宪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正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现。
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就是试图抑制国家权力的恶,发扬国家权力的善,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宪法在强调规范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要对国家权力及其运行进行有效配置,保证国家机关既能够充分行使权力,又能在法制轨道上行使权力。同时,国家权力还应受到有效监督,包括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以及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基本精神。当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权力主体在分工合作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强化对各权力主体的监督,如何建设民有、民享、民治的法治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课题。
公民权是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而人权是一国公民尊严和地位的体现,人权保障是一国民主与法治状况的反映。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因而如果失去对人权的价值追求,缺乏保障人权的机制,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宪法。从公民主体性而言,正是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使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在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同时,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在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宪法自身的活力,使宪法真正得到公民的信仰。而且,我国在公民权保障方面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在人民逐步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实现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逐步扩大公民政治自由权的范围,不断提高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因此,确认与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功能。如何促进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重要课题。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经验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然而,我国宪法中的主权在民原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与西方阶级虚无论的主权在民原则有着本质区别。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范了我国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与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权力配置方式有着本质区别。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有许多起不同作用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工会制度、军事制度、司法制度等。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决定了这些政治制度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并构成一定的政治制度体系。在这个政治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凝聚、协调政治制度体系的作用,支配着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是根本(或基本)政治制度。”[1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凝聚、协调、支配地位,使其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宪法学家首先应该解读宪法的政治基础,阐释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而不是抨击甚至否定根本政治制度。这是由宪法学的职业性质决定的。[注:
戴雪在1883年的牛津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为“英国法可以在大学中传授吗?”)中强调了职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分野,认为法学的任务“就是将法律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加以阐明,并分析界定法律概念,将浩如烟海的法律规则化约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原则,并协助、激励和指导法律文献的改革和创新……”。因此,宪法学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他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护卫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因此,宪法学者对宪法的解释必须首先承认宪法(整体意义上的类型,表现为特定的宪法体制)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解、解释、应用宪法。选择何种类型的宪法是政治家(是最为典型的职业界)应该做出的政治决断,而不是宪法学家的职业领域。(马丁•洛克林惫法与政治理论[M]敝8辏译北本:商务印书馆,2000:33,23保]其次,在阐释人大制度正当性的基础上,坚持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坚持民主集中的权力配置原则,坚持一院制的结构模式,坚持党的领导。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如健全各级人大的组织制度,完善人大议事制度,提高代表综合素质与参政议政能力等。最后,以促进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己任,解释、构建、完善、说明相关法律制度。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推进依法行政;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促进宪法的法律实现。而能否实现人大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促进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判断“解释”、“构建”、“完善”、“说明”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
三、政治担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正如前文所言,笔者将费希特的“单纯的历史”理解为(曾经的、已经的、即将的)存在,特指人的社会生活,属于政治范畴,而如何将普遍真理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则是学者的“政治担当”。因此,学者们运用第一、二层面的知识(哲学与历史哲学)关注人的社会活动,就是其政治担当。具体说来,中国宪法学家的政治担当就是以宪法为媒介,运用宪法知识改进中国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宪法学视野中,民主政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形态。虽然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异常复杂,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民主政治作为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而且将其视为不懈奋斗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即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基本形成。基于此,笔者将中国宪法学家的政治担当概括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中国国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以中国社会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即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注: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原理:“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5)]因此,宪法学家要服务于民主政治就必须理解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当前,国人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评价不高,有学者甚至希望通过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一夜之间建立民主政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理解民主政治所立基的中国国情及其特殊性。中国国情极其复杂,方方面面的问题颇多。本文在此简略介绍决定中国国情的三个基质因素及其对当下政治的深刻影响。
1.传统文化:国情的历史之维
人是文化的动物,由特定文化传统所决定。因此,描述任何社会的当下境况,都须追问这个社会的文化。[注:
“文化仿佛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面,外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者‘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约恩•吕森崩史思考的新途径[M]濒爰赘#来炯,译鄙虾#荷虾H嗣癯霭嫔纾2005
:39盷文化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传统下的“生活样法”。[注:
转引自:许章润彼捣 活法 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本)[M]北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9盷首先,文化乃是特定民族智性、心性、德性与生存智慧的凝结、积累、总结、传承与丰富[17]。
因此,文化是一种集体智慧。宪法、法律等社会现象只是部分表达这种集体智慧。其次,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智慧,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最后,文化作为长期实践的集体智慧,具有历史的“惯性”。[注:
惯性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惯性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与速度无关。在此,我们把文化形成的历史比喻成物体的质量,以说明文化传统的特性。]这种惯性使文化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趋势,从而具有延续性。并且,文化的历史越悠久,则其惯性表现得越强烈,越不易改变,即使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相当大的成本。因此,文化也会成为“历史的包袱”。[注:
这里借用了昂格尔的“历史包袱”一词。(R•M•昂格尔毕执社会中的法律[M]蔽庥裾拢周汉华,译北本:译林出版社,2001:1盷尽管如此,但为了维持最基本的价值与秩序,不可能暴风骤雨式地卸下这一包袱,而必须背上它慢慢前行,在适当的时候,不知不觉、一点一滴地卸下包袱中的旧东西,并填充新东西。在上述意义上,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当下境况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任何社会变革,都是在尊重传统、尊重秩序基础上进行的适当调整,它根本不可能割断文化的延续性。
与西方文化传统(笔者将其界定为分散性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集中统一型文化。其特点主要表现在:(1)中国传统文化无论观念上,还是经验上,都强调一个统一的中心,并基于此中心,演绎出不同层级的次级文化,形成了“万物归一”的思维模式。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统一型文化。在与西方分散型文化相对的意义上,也可称为集中型文化。(2)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元文化,始终强调世界的一元性,以及基于一元性所构建的和谐社会。这种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宪制的集体主义品格,且与“民主集中制”高度契合:在内涵方面,“宪法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18]
宪法典从整体出发来界定根本法,强调“整体”;在形式结构方面,《宪法》的“总纲”凸现出国家的整体布局,其次才是作为部分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和“国家机构”;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虽然也存在国家职权的划分与分工,但所有权力都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划分(注意我们是“职权划分”);在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方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制度安排上突出“集中”。以上这些方面,都足以体现我国宪法的整体主义思维模式。
从中国近现代史看,民族资产阶级宪法以西方文化为背景,但其在中国的失败,促进了“新三民主义”与“宪政三阶段”的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即将背离西方的政治逻辑。自此以后,无论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都抛弃了西方的经典宪法模式,探讨中国自己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早就已经萌芽。
2.新三民主义:国情的现代之维
纵观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其三个核心要素:
一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人们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西方社会建构的共同体,于180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19]。
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等孪生思潮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强大的地方(如欧美等国家),民主政治的实践就较好,那些处于战乱、分裂的国家,基本无民主政治可言。据此可见,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民主政治的实践。当今不少人都惊叹,甚至垂涎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美国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之理念,而不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二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经济力量。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古典思想看来,正义需要沉思的生活,依赖以实践为基础的技术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始终是最危险的幻想[20]。
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乃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20]2。在此理念下,西方世界经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大量商品,从而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并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从当今世界的情况看,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说来其民主政治大多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往往无民主政治可言。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常常存在正相关关系。从上述意义可见,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经济力量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民权”。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从而将人从自然、集体中解脱出来,并为自由奠定坚实基础。而在自由状态中展现自我精神价值,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则是民权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民族”、“民生”、“民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因素,只是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而已。就中西方而言,由于西方现代化较早,三者在历史上基本是“历时性”地依次经过;而中国的现代化较晚,三者在历史上基本是“共时性”的,这正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复杂性所在。
在中国,孙中山先生最早看到三因素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并将中国问题概括为三民主义,后来国共两党都提出要继承“三民主义”。然而,基于对“民权”、“民生”、“民族”三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国共两党对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于国民党不能认识“民权”、“民生”对于“民族”的意义,因而孤立地理解民族主义,认为只要军事革命完成,宪法、宪政就可实现。关于这一点,钱端升先生认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急的任务在于维持国内治安,增进行政效率,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了,则民治民权尽在其中,宪政自然是顺水之舟,不求自来,因此,当政者不要急于字面宪法的完成,而应努力于政治经济的改进[17]178;如果定要立宪,则也要明白,它只是借用宪法的名义,“简要,切合国情,不涉理想,也不夸大”,而成为国家组织大纲[17]179。这种认识本质上是通过强化国家权力、增进国家经济实力等方式,强化国家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形成现代民族国家。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应有之意。但问题在于,国民党未能理解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关注“民生”、“民权”对于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意义,更未能将国家建设取得的成果循序渐进地转化为公民个人的福祉(包括民生、民权),因而将公民个人的福祉机械地置于国家建设之后。因此,在国家统一后的一段时期内,只有形式的国家而没有实质的个人,国家不为个人所有而为一个政党所有,一党专制与党政不分的“训政”随之成为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
然而,共产党自革命之日起,就充分理解“民权”、“民生”、“民族”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民生”是“民族”的根本动力,“民族”是“民生”的必要条件;“民权”是“民族”的根本价值,“民族”是“民权”的根本保障;“民生”是“民权”的物质条件,“民权”是“民生”的价值升华。可见,三者中任何一项的实现都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其它两项的实现,单纯地实现其一都是不可能的;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表现为国家与个人(在法的视野中表现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即国家的存在以个人的存在为目的,不以个人为目的的国家既无价值也不可能“现实”地存在,但个人的存在离不开国家的存在,离开国家的个人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而不是之后),必须与之相适应地进行以个人为中心的民生与民权建设。因此,逻辑上以民族独立为核心的军政、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训政、以民生与民权建设为核心的宪政三个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空间上的相互渗透关系。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共产党几乎没有考虑“三阶段”理论。尽管“民族”、“民生”、“民权”相互依存,因而理应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存在差异,这个平衡点势必也会存在差异,并致使其中之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特别突出,从而成为问题的根本矛盾。
应该说,“三民主义”揭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并将其中国化(这在某种意义上大概是孙中山先生能够成为“国父”的重要原因)。尽管三者之关系在当下中国的表现不同于过去,但这三要素及其新关系仍然存在。因此,在民权高涨,民主政治大力推进的今天,仍要历史地、辩证地审视三者之间的关系,谨防在将民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唯一考量因素而不顾其他两个因素的情况下,激情地呼吁民主。否则,其最终结果可能是“悲情”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权建设一直伴随着民生建设而展开,民生建设始终是民权建设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的新论断。
3.自由民主:国情的西方之维
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是近现代中国问题(民族、民生、民权),都是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入侵背景下提出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王朝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中法战争失败说明洋务运动的“坚船利炮”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随后催生了维新变法的改良派,自此西方民主政治思潮进入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的视野。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开端,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开始。以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英国为榜样,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要求建立一个主权在民、权力分立的民主共和国。“无论是虚君共和也好,还是民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形式,但实质一致,即要求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走向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民主分权制。因此,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手段虽有不同,但在目标上却是相似的,都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与践行者。”[21]
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民主作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政治形态。中国现行宪法不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还规定了“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承认肯定,最后到积极促进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意义上,自由民主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维度,并随着民族、民生问题的解决而进一步提升其重要性。
然而,尽管当下的政界、思想界乃至普通民众都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并形成基本共识,但通过什么制度、以什么速度来实现,却存在严重分歧。比如有学者倾向于通过借鉴西方的分权政治制度予以实现,政治家则倾向于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予以实现。笔者认为,西方分权政治制度总体体现了西方分散型文化传统,是西方人心智与生活方式的反映,从总体上对其予以借鉴,不能解决中国人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下“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安排,既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也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当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矛盾(即到底民主是主导方面,还是集中是主导方面)是历史性的。另外,有学者总想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政治家则倾向于循序渐进地推进。笔者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民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发展程度取决于民族建设(强大、统一、有序的国家)与民生建设(核心是经济问题),若没有这两个基础,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毫无疑问,国情的这三个基本因素从整体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性。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仅仅将“中国特色”作为政治口号。其实,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封闭性、差异性是共同体(国家是其形态之一)的本质,因而是绝对的,而开放性、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智慧。
(二)宪法思维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
尽管有不少学科的学者服务于社会的方式是将其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但宪法学家则必须以宪法为媒介,将其理论间接地运用于社会生活,而不能抛开宪法规范径直地运用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不仅要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理论思维,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宪法思维。本文将宪法思维界定为运用宪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1.宪法思维是法治思维
从价值角度而言,宪法思维以保障人权为核心,同时融合民主与法治的精髓。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法国《人权宣言》认为,凡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正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催生了宪法,宪法中的各项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保障人权服务。因此,是否有效保障人权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优良的重要指标。甚至可以说,不保障人权、不体现人性尊严的宪法不足以称之为宪法。同样,宪法思维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标,是“以人为本”的思维。它从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用人的思想思考世界,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转换为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保障人权实现宪法自身的价值。同时,民主和法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两项基本价值。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其精髓在于人民是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体现了人民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是人民作为宪法主体地位的彰显。法治即“法的统治”,它要求“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2]
。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受到普遍制定的法律规制。然而,民主与法治又是两个容易被人扭曲的概念,譬如民主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法治则易成为当权者凭借法律恣意侵犯人权的工具。而宪法思维则将民主与法治的精髓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保障人权服务:宪法思维是民主的思维,它通过制度安排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宪法思维也是法治的思维,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权力的执掌者尊重宪法的极大权威,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宪法、崇敬宪法的良好氛围。可以说,宪法思维既使民主处于法治范围内,又使法治具有深厚的民主基础,并使两者在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宪法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宪法思维是历史思维
宪法思维兼顾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宪法是一个民族传统的积淀。作为主观性范畴的宪法思维,在思维者头脑中形成的过程,就是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作为具有客观性质的宪法思维,在形成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外在于思维者的文化背景影响,从而带有传统的烙印。因此,解读宪法,运用宪法思维执政,不可忽略历史的延续性、传统的深刻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唯回溯历史、回顾传统、回归文化,方能全面、透彻地把握宪法。同时,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其主要的指向对象是现实社会关系,而宪法思维毕竟是现时代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主观认知,因而现实环境对宪法思维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宪法思维的立足点,在于其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它关照现实生活以及社会运行实际,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着力点。此外,宪法不仅是传统的产物,不仅以现实世界作为其主要作用场域,而且宪法还关注未来。当代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之一,在于透过主张拉长的时间规范对后代子孙进行规范控制[23]。
因此,宪法思维以构筑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为主要目标,以一种长远的未来眼光,注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宪法思维的传统性、现实性与未来性并不是孤立的。它关注不同世代的宪法对话,以宪法为媒介将不同世代的人类利益集合在一起,并进行合理分配。
3.宪法思维是综合思维
宪法思维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思维。其一,宪法思维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它主张市场开放、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并为市场运行提供根本性的法律保障。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宪法思维是以民主政治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以人民主权为逻辑起点,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同时,宪法肯定国家的民主性质,规定国家的民主制度,明确人民的民主权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宪法思维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人民的意志,并通过合乎民主的方式执政。其三,宪法思维是以宽容文化为导向的思维。宪法不仅是有形的制度,也是无形的文化。宪法是自由民主文化的产物,因而先天地具有浪漫主义文化气质。它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为多元文化的表达和繁荣提供制度空间。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尊重多元文化,努力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文化氛围。其四,宪法思维是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是制宪过程中人民共识的产物,是社会各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渠道。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合理疏导社会矛盾,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
(三)政治智慧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
政治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总称,因此政治智慧是实践智慧(与理论思维相对),受制于人的心智与经验。由于人的心智与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政治智慧没有统一的理论与固定的形态。尽管如此,但纵观理论家的思考与政治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将政治智慧界定为主体通过理论(或信念)改良政治生活的活动,因此是主体处理理论与政治之关系的实践活动。据此,可把政治智慧分解为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主体;二是政治;三是理论。由于政治要求主体正视现实,理论要求主体追求绝对真理,而人的生活要求政治与理论审慎妥协,这就要求学者在两个极端(正视现实与追求真理)之间寻求妥协的技术:表达技艺。因此,在内容上,可以把政治智慧界定为学者在正视现实基础上通过高超的表达技艺,实现理论与政治之间审慎妥协的活动。
1.正视现实是政治智慧的源泉
宪法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不仅要有成熟的理论,更须“正视”现实。“正视”要求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区分主观价值与客观存在。对于社会问题,须首先追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来的,并客观评价它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正视”既不等于为现实辩护,也不等于不批判,而是将其作为批判、构建、完善、变革的前提。因此,这样的批判是“睁开眼睛批判”,而不是“闭上眼睛批判”。
“正视”首先是一种为学的方法。它要求我们在批判之前设身处地地理解批判的对象,客观评价它的历史基础、当下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以及在未来历史变迁中,这些基础与条件是否存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确立战略(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终极目标),更能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巧妙灵活地确立、运用 “战术”(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具体方法)。因此,作为一种方法,“正视”不是保守守旧、固步自封、原地踏步。相反,它是为了更有的放矢、更富建设性、更具可行性的“批判”。其次,“正视”还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一种精神境界。许多政治道路的确立与选择、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并不依凭于个人的喜好,绝大多数是某一精英阶层甚至是历史(本质上是所有人的无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凝聚着前人的经验与智慧。从主体上看,“正视”当下政治,就是理解前人的智慧,设身处地地“思前人之所思”,“想前人之所想”,而不是“两耳塞豆”,“思自己之所思”,“想自己之所想”。因此,“正视”在方法上要求理解并超越前人,而不是抛弃,甚至彻底否定前人。这是一种“谦逊”的美德。对于个人,这种美德关乎道德修养与生活品质;对于民族,这种美德关乎社会进步与法治文明(俗话说,“文明源于道德”)。美国宪法的良好实施并不是因为宪法文本多么完美(任何法律、制度都有缺陷),而在于“谦逊”与“妥协”的民族精神(如“遵循先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谦逊精神的体现)。这样,每个人都会审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基于此,笔者认为,美德不是法律之外的抽象说教,而是存在于法律之中的活的灵魂,并在为学、为人、为事中得以表现。因此,方法即态度,方法即精神,一体两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法学关注当下的倾向越来越强。然而,由于有些学者仅仅只看到当下,因而要么抛开法律而屈服于现实,表现出为现实辩护;要么直接运用现行法律,批判现实与法律严重脱节;更有甚者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体无完肤地批判现实与制度。在笔者看来,忽视“当下”的历史性是一些学者不能客观“正视”当下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回顾“过去”,就能知道当下的“源流”;洞悉“现在”,就能准确把握眼前的根本矛盾;把握历史的逻辑,就能寻找到未来的方向。基于此,“看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看到历史,要有历史意识,懂得历史渊源,这是基础。有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调查,法律基础才更成熟,才会懂得某些案件该怎么处理,某些冲突该怎么防止,防止它成为法律事件。有的成为法律事件很好,有的成为法律事件不好,很麻烦,要制止。”[24]
为了“正视”现实,宪法学家应该“培育一种基于宪法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培养基于宪法序言的政治意识。中国宪法序言跟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就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政法制度的基础,是一种艺术。”[24]在我们看来,《宪法》序言与《宪法》第一条是中国宪法的灵魂,也是其他制度的基础,是理解中国宪法的钥匙。序言阐述了中国宪法的历史正当性:通过历史的梳理,制宪者实际上在告诉人们,中国需要宪法,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而需要基于中国历史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宪法第一条则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本质——人民民主专政。所有其他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是在这一决断基础上做出的。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中国宪法学家将宪法与法律相等同,因而将其注意力都集中于制度规范,从而忽视了宪法中的政治考量。
2.审慎妥协是政治智慧的灵魂
政治智慧是处理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高超艺术的总称。然而,关于人与人类事物的理论,人们最早关注的要么是最佳秩序、正义的秩序,要么是自然状态。但这两种理论关注的都是最理想、最简单的情况(这就像牛顿第一定律描述的“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一样),它们绝大多数是并不存在的“假设”,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但现实政治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因而没有纯粹的正义,并且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根本有别于自然状态。因此,政治智慧总是与例外、修正、平衡、折衷或混合打交道。这是因为,当“形而上学的权利在进入日常生活时,就像光线在穿过厚厚的介质一样,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它们笔直的线路被扭曲了”,既然“社会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原初的人权”就无法坚持“在原先方向上的那种简洁性了”,“[这些权利]在形而上学上有多么真切,它们在道德和政治上就有多么虚假。”因此,政治智慧需要“最精妙复杂的技巧”[25]。
由于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单性与有限性,而人的政治生活具有复杂性与无限性,因而当我们观察现实时,视角可能单一,理解在多数情况下则可能片面,故任何对现实的改造都必须审慎。因此,政治智慧需要“审慎”,而不需要“激情”(它是理论的美德)。用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柏克的话说:“审慎,是一切事物的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审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标准。”[注:
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虽然审慎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但应该对之形成如下共识:首先,审慎反对走极端,要求遵循“中道”,即寻找“过度和不及的居间者”[26]
。具体说来,不要直接用理论代替现实,将理论不折不扣地实现,因此审慎要求理论“打折扣”。其次,审慎反对一蹴而就,要求循序渐进。社会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理论的实现也必须循序渐进。最后,审慎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更需要肯定现实的态度,这一点前文已经做了讨论。
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在这一意义上,“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妥协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一方或多方,为推动事物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采取非对抗性方式以解决矛盾而遵循的思维方式、处事准则和制度规范。在古典时代,社会相对单一,妥协主要指政治与哲学的妥协。笔者以为,这是人类社会最源初、最基本的妥协。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在社会多元化与权利(力)分立化的情况下,妥协主要指主体之间的妥协。因此,宪法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也应该妥协,以达成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交流、沟通与对话,从而实现理论对社会的有效关怀。
3.表达技艺是政治智慧的手段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真理就其本性而言具有“癫狂性(madness)”。也可以说,就其本性而言,真理与政治社会往往并不相容:为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真理必然会漠视一切道德习俗、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政治社会来说很可能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然而,政治生活是人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绝对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因而人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因此,“正视现实”(即政治)与“超越政治”(即真理)使人面临两难的境地[注:
“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意见和生活方式)沆瀣一气,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与他们相隔离,并力图获得完满性,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它所希望的东西,难于登天。因为必然会有两种命运降临在他头上,要么丧命,要么丧失完美性。”(阿尔法拉比卑乩图的哲学[M]背讨久簦译鄙虾#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3保]。
尽管真理对政治可能具有颠覆性影响,但政治生活又是人无法回避的。因此,学者既要表达真理以改造社会,又要考虑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这就要求其表达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古典哲人将这一技艺概括为“隐微修辞”,亦即要求表达要言语适度,切忌原封不动地将癫狂的思想予以直白表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学者的真理往往是少数人的知性活动,而大多数人生活在不合理的“意见”(与真理相对)之中。由于意见对维系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合理的“意见”具有了合理性。因此,理论对“意见”应给予必要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地用知性真诚改造,甚至取代社会“意见”,否则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古希腊人以“毒害青少年”为名,判处苏格拉底死罪,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具体而言,关涉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宪法学,必须关照中国宪法,对历史传统、当下问题、社会生活、宪法体制等给予深切理解,切不可脱离现实,不顾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一味地用西方宪法改造中国,用理想代替现实。其次,相对于“意见”而言,知性真诚毕竟是理想。为了实现知性真诚对社会的改造,真理必须被表达(书面或口头)出来,以促进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真理与当下“意见”可能会存在冲突,而“意见”对于维系当下社会秩序又是必须的。因此,为解决这对矛盾,古典政治哲学在表达过程中力求“言语适度”。古人将其称为“隐微修辞”,“政治上有忌讳而不直言的‘真正的教导”,这与任何人都能一读(听)就懂的“俗白教导”相对立。笔者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坚持“言语适度”的表达技艺,还有一个原因即自己的真理不一定正确,即便正确也可能具有相对性。“言语适度”是一种不十分确信的表现,是基于对个人有限性的认识。因此,古典哲人始终对理论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现实始终给予几分尊重。这既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也是宪法最为重要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与理念,而仅凭法律技术,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结语
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对当下的忧患意识。尽管中国宪法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仍然相对乏力,其社会贡献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并不相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提出了本文的命题。虽然文中的许多观点有待推敲,但希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共鸣。ML
お
参考文献:
[1]费希特甭垩д叩氖姑•人的使命[M]绷褐狙В沈真,译北本:商务印书馆,2008:37-40
[2]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钡贝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敝S懒鳎译北本:法律出版社,2002:6
[3]林国华惫诺涞摹傲⒎ㄊ”——政治哲学主题研究[M]北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2
[4]李鹏程,等闭治哲学经典:西方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2008:26-34
[5]刘大椿笨蒲Щ疃论•互补方法论[M]蹦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33
[7]卡尔•波普尔笨凸壑识[M]笔嫖肮猓卓如飞,等,译鄙虾#荷虾R胛某霭嫔纾2005:4
[8]哈罗德•J•伯尔曼狈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序言)[M]焙匚婪剑张志铭,等,译北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
[9]南怀瑾崩史的经验(前言)[M]北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
[10]卡尔•施米特甭鄱嫌敫拍睢—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C]//朱雁冰,译鄙虾#荷虾H嗣癯霭嫔纾2006:236
[11]周叶中毕苷: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J]苯西社会科学,2004,(5)
[12]R•G•柯林伍德崩史的观念[M]焙握孜洌张文杰,译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33-134
[13]马克斯•韦伯鄙缁峥蒲Х椒论[M]焙水法,莫茜,译北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36
[14]爱弥尔•涂尔干泵系滤桂与卢梭[M]崩盥衬,赵立玮,付德根,译鄙虾#荷虾H嗣癯霭嫔纾2006:11
[15]陈振明鄙缁峥蒲У纳命力在于解决社会问题[J]碧剿饔胝鸣,2000:(5)
[16]刘茂林敝泄宪法导论[M]北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5
[17]许章润彼捣 活法 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初版序(增订本[M]北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77:129
[19]三好将夫笨绻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M]蓖絷停陈燕谷蔽幕与公共性北本:北京三联书店,2005:489
[20]魏因伯格笨蒲А⑿叛鲇胝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M]北本:三联书店,2008:12
[21]李泽厚敝泄思想史编(中)[M]焙戏剩喊不瘴囊粘霭嫔纾1999:653-655
[22]亚里士多德闭治学[M]蔽馐倥欤译北本:商务印书馆,1965:199
[23]张文贞敝卸系南芊ǘ曰埃合芊ń馐驮谙芊ū淝脉络的定位[J]碧ù蠓ㄑ论丛,2003:6
[24]冯象痹谛苤形熊,在鸟中为鸟[EB/OL]県ttp://www.calaw.cn/Pages_Front/Article/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5168
[25]列奥•施特劳斯弊匀蝗ɡ与历史[M]迸砀眨译北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314
[2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译北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6
Tasks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Experts
ZHOU Ye瞶hong, LIANG Cheng瞴i
ぃ╓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Wuhan 430072)
Abstract:The classical image of constitutional experts illuminates that both academic pursuit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re their missions. The academic pursuit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experts may center on seeking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expanding the domain of researches. Also they should try to gain an insight of historical logic, unveil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lly they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aking up political pursuits, they should be aware that political democracy is rooted in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pattern serves as the pillar in facilitating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wisdom is the key point in realizing political democracy.
Key Words:classical philosopher of politics; experts of constitution; academic pursuits; political purs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