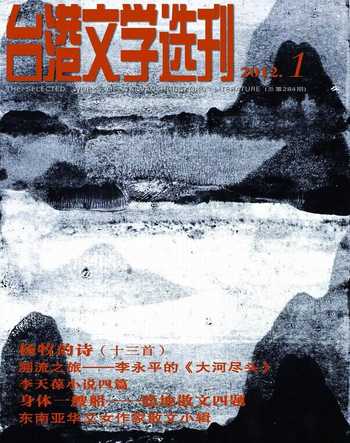招魂——朱鸰,归来
2012-04-29
那时我真的不知道,甚至抵达终点时也没察觉——我只是个十五岁的懵懂少年啊——这趟航程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在大河尽头我又会找到什么东西,发现什么人生秘密。我只是感觉好爽,心中很痛快,因为我完成了一趟同侪们没有机会经历,心里准会羡慕得要死的冒险旅程……
昔我往矣……今我来思。
倏忽,咱俩睽违已三年,丫头,别来无恙?
你还记得台北天空乍然飘起的那场绮丽的雨雪吗?古早、古早曾泛漫燕赵大地,漭漭沧沧,那天晌午,好似变魔术一般,当我们在台北市一间小学门口结缘时,蓦地,悄没声地,纷纷洒落在热烘烘闹市街头的那一场雨雪?
你眯起眼睛,指着那坐落在回归线上东海中的台北城,笑道:瞧,雨雪霏霏四牡 。
于是就在那天夜里,我们大小两个展开了一趟奇幻迷离的台北旅程。
你,丫头,一个名叫“朱鸰”的那时才八岁的小女生,背个大红书囊,秋日穿得一身土黄卡其长袖上衣和黑布小裙,朔风中,耸着一头蓬草样焦黄发丝,睁着两只乌亮眼瞳子,趿着一双破球鞋,拖拖沓沓,亦步亦趋只顾追随我,穿梭在那满城飞雪里,迎向北台湾淡水河口观音山头的落日,从古亭小学出发,踩着人行道上的方格子红砖,走下长长一条罗斯福路,踢跶,踢跶踢,来到了寿而康川菜馆,歇歇脚打个尖,叫店家现杀现烹一尾生猛的肥大鲤鱼(我的恩师,湖南大汉颜元叔教授,生平最爱品尝的寿而康豆瓣鲤鱼喔),丫头,你边吃鱼边噙着泪,怔怔地听我讲述一则发生在南洋的悲惨童年往事,听完故事吃完饭又背起书包,伸出你那只油腻的手爪子,扒梳了梳你脖子上那刀削般齐耳的一把短发丝,踢跶踢走出店门,继续与我行走。雨雪霏霏,婆罗洲赤道地平线上一轮火红的日头下,台北市满城一蕊一蕾四下绽放的七彩霓虹灯中,你迎着荒冷的朔风,边走边听故事,似懂似不懂,时而质疑我的南洋童年,时而皱起眉头绷住脸孔,闷声不响,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就这样咱两个一路从城南走到了城西,淡水河畔,那一窟灯火妖红鬼影幢幢人头飘忽、缱绻缠绵哼哼唧唧、哀声四起的宝斗里盘丝洞……踢跶踢哩跶啦,你趿着两只破球鞋一口气行走个把钟头,脚都起水泡啦。拜托,我们在华西街夜市逛一逛吧。于是我就找一家海产店,邀你在临街台子旁坐下来,喝生啤酒,一边观看隔壁蛇店老板杀蛇宰鳖,活斩龟头,血淋淋操刀弄棍指指点点,吓唬那一伙搂着台湾女子的小腰肢、腆着大肚膛、呆呆团聚在蛇店门口伸长脖子窥望的阿凸仔米国人,一边扯起嗓门,比手画脚口沬横飞亢奋地向你诉说,沙共游击队在婆罗洲雨林出生入死的事迹。两大杯啤酒下肚,故事也讲完了,我一把揪住你的发根,拖着你,丫头,走出华西街国际观光夜市,登上河堤,观音山头一瓢月光下,白雪雪满江九月芒翻飞呼啸声中,背着你,一步一蹭蹬,只管沿着乌臭的新店溪跋涉,溯流而上,探索山中一窟活水源头,寻访那群栖息在黑水潭底,而传闻中绝灭已久的台湾纯种原生鱼——庵仔鱼……
庵仔鱼,你听!泼剌剌一声迸响,晨曦中只见千百只银白的鱼,扑突扑突鼓胀着红滟滟的肚腩,成双成对互相追逐着,交缠着,轮番窜出黑水潭,迎向天边一枚残月,醉态般迸迸溅溅癫癫狂狂自顾自捉对儿戏耍起来啦。
丫头终于记起来了?这可不是一趟奇幻至极的旅程、千古难逢的际遇么?一个秋日傍晚,台北市骤然飘起那场古老的北方雨雪,咱两个,一大一小一男一女来自天南地北,邂逅于这座东海的孤城,于是结起伴来,踢跶迌,朝向海峡波涛半瓢月,竟然就在那城开不夜的台北街头相偕游逛到天明。丫头甩着发,趿着鞋,拱起肩膀背着你那只沉甸甸的大红书囊,顶着荒冷的风,只管紧紧跟随我,一路央我讲述我在婆罗洲的童年——我怎会不知道,丫头,你心里真正想听的是热带丛林版的天方夜谭,阿拉丁、辛巴达水手之类新奇有趣、充满魔幻冒险情节的故事呢?可是不知怎的,故事刚开始虽还有点好玩,但每次一讲到我的伤心处,那则童年往事就会被我扭曲成变调的梦呓般的《忏情录》,凄楚、阴森、残忍,连我自己听了都禁不住毛骨悚然,浑不似丫头你期盼的有趣童年。但你始终按捺住性子,并没向我提出抗议,只默默垂下头来踯躅在我身后,任由我向你吐露一件件埋藏心底多年的罪过和秘密。听到后来,丫头心肠软了,扑簌簌流下泪来啦,竟扮演起母姐的角色——而你只是个八岁大的小学女生——温言抚慰我、开导我,月光下苍白着一张小脸子,耐心地让我诉说完我成长过程中那一桩桩,喔,难以启齿,却又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悔恨和懊恼。
台北夜游,至今已三年了,而今你也消失了三年。朱鸰,别来无恙否?念甚——真的很想念,终日牵肠挂肚,否则我今天只身寄寓在花东纵谷这一座十亿台币打造的美丽新校园,半夜惊醒,也就不会霍地起身,呆呆坐在书桌前,面对居南村窗外月下的嵯峨大山,心中忽然酸楚,眼圈红啦,于是抓起一支原子笔,以笔代香,再摊开一叠稿纸权充纸钱,朝向中央山脉北端台北城那一簇无比灿烂荒冷的红尘灯火,月下开始呼喊丫头,招丫头你的魂……
魂兮——
丫头终于听到了?记得了?那夜在台北霓虹街头给你讲完十二则婆罗洲童年故事,天也亮喽。我长长伸个懒腰,揉揉我那两颗血丝斑斓的眼珠,叉着腰,望着一轮红日头从东海波涛中翻涌而出,直想扯起喉咙,仰天狂啸一番,因为那压在我胸口的千斤石担,今晚被你这小小姑娘一手卸落了。我那紧绷好多好多年的心,倏然一松,我竟狠起心肠来以最冷酷的方式报答你;我最忠实最体恤、最聪慧善解人意的听者——我又给鬼迷住心窍了啦,就像当年我们七兄弟姐妹突然集体抓狂,争先恐后咬牙切齿,纷纷拿起石头,活活砸死我们家那只忠诚的老狗……丫头哇,三年前那晚我对你做出了一件极冷血、极不可饶恕的事:咱俩一大一小互相扶持,历经一夜跋涉终于走到了河溪上游,这趟溯源之旅完成了,你亲手把我这个浪子给带回家了,我便把你留在终点站,将你放逐到那一窟阴冷幽深千年不见天日的黑水潭,头也不回,自个儿扬长而去啦。放逐你,这个素昧平生、与我有缘在台北街头相聚一夜的小学女生,朱鸰。我心里原本盘算,这么一来,我就可以永远摆脱心中那只兽,可以一了百了把那幅贴在我们李家大门口几十年的妖妇符咒,给揭掉喽。可是,万万没料到,丫头你这一走我整个人反又失落了啦,我的心顿失依托。三年后,从台北市飘荡到东台湾的乡野,从东吴大学逃遁到东华大学——我一度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失语症,终日恹恹,懒怠开口,只因为我已经习惯对你讲话,絮絮叨叨呢呢喃喃,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向你这个陌生却又觉得十分熟稔、仿佛前世结缘过的小姑娘,毫无顾忌地陈诉心事……三年前那晚,陪伴我走了一趟溯源之旅,丫头,你终于把我带回到了家门口,可近乡情怯哪。我,这个老游子,还需要你伴我走这最后一程,带我跨过家门口那道门槛。所以今夜中宵梦醒,坐在花东纵谷一盏台灯下,对着窗外那守望在奇莱山巅、笑吟吟、三年前曾经俯瞰我们一大一小两个人跋涉在观音山下黑水河中的月娘,我终于鼓起勇气,厚着脸皮召唤你:魂兮归来,朱鸰。
十月的新店溪,潭水冷冽,你莫在潭底流连太久。我深知你的性情,即便被囚禁在一座暗无天日的水牢,纵使形体早已化为一条魂魄,可你这个好动的丫头儿呀,依旧会圆睁着你那两只清澄的充满好奇的眼瞳,张开双臂扭动腰肢,长发漫漫(三年了,水底下没人帮你剪头发,你那刀削般、西瓜皮式的齐耳短发如今已留长了吧),好不逍遥快意,自管游弋在那黑水潭中,喜滋滋地探索潭底的世界,东张西望,试图寻找它守护多年、终能不让人类知晓的重大秘密。告诉我,你可曾找着了她们——我们上回一路溯溪一路察访的台湾原生鱼?那每年六月春夏之交,西北雨季,新店溪水暴涨时节,成群结队鼓着她们腹部那一毬一毬红扑扑圆滚滚的卵巢,浩浩荡荡逆流而上,直来到水源头,集体产卵的母庵仔鱼——她们果真如学界所断言的早已灭绝了吗?或者,她们之中是否有极少数的一群,鬼使神差,侥幸逃过了当年海东渔郎们使用氰酸钾,鬼鬼祟祟半夜摸黑进行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式的集体捕杀?如今,这会儿,她们是否正偷偷栖息在黑水潭底那巨大的老树根窟窿中,悄悄生殖、繁衍,耐心地等待有朝一日——终于盼到了河清之日溪畔又见杨柳依依——破潭而出,百尾千尾万尾成双成对骤然汹涌出水面,发狂似的噼噼啵啵,再度飞腾交欢在观音山头一轮皓月下,逗弄那群笑哧哧吐着血痰、鬼卒般团团蹲伏在黑水潭边窥伺的渔郎——就像当年,一九六七年,我刚来台湾读大学时,有天晚上跟随学长夜游,在新店溪上亲眼看到的那一幕月下群鬼乱舞、水中群鱼狂欢、壮盛得令人禁不住流下热泪的场景?
朱鸰,你必得信守承诺……
嘻,扯淡!我有对你做过任何承诺吗?
我不管,你一定要从潭底世界游罢归来,向我报告你在那儿的见闻。
你切莫忘记那天清晨日出时,彻夜的行程终了,我叉着腰,站在溪上那片哗喇喇迎风狂啸的芒草中,眼睁睁,看着丫头你,摇甩起你脑袋瓜上那一蓬子浪游一夜沾满风尘的枯黄发丝,背起红书囊,拂拂身上那件土黄卡其上衣,系紧腰下那条黑布小裙,桀骜地,昂扬起一张水白脸子,迎向晨曦边唱儿歌——妹妹背着洋娃娃,走进花园去看花——边回头乜斜起你一只眼睛狡黠地瞅着我,满脸笑,打赤脚踩着溪床上那堆乱石,一步蹭蹬着一步,自管自走进水源头一窟黑水中寻访庵仔鱼姐妹们去了……
从新店溪回来,我迫不及待,拾起纸笔将这一夜在 迌路上随性给你讲的十二个故事,摘要抄录下来,尔后再做一番必要的润饰整理铺陈,辑成一本小书,给它取个颇为正点、符合学界品味的名字《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虽然也算了结一桩心愿,但不知怎的心中却始终觉得不踏实。朱鸰,那晚你在北台湾一条溪的尽头,黑水潭中,寻找到了你的家园和你的姐妹,可是我呢,你那个陌路相逢、有缘做伙一夜的旅伴——我,昔我往矣今我来思,自甘放逐二三十年的浪子兼游子,完成了这趟新店溪之旅,经历了一场宛如古希腊“卡萨尔西斯”式的清涤焠炼,果真能回到心灵的家园,回到我心目中永恒的歌手,齐豫,用她灵魂的颤音所咏唱的那个“梦田”么?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
一颗啊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
丫头你的耳朵最灵敏,你听到了没?就是这样的几句最朴实、最单调的歌词,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在齐豫吟唱下变成一篇荒老苍凉的咒语,阴魂不散,自新店溪归来后就一直萦回在我耳鼓中,嘤嘤嗡嗡挥之不去,好像那奥德赛海上女妖的召唤,一声凄厉一声,叫我莫再延宕,莫再逗留,赶快回到卡布雅斯河上游,天际,那一座草木不生、光秃秃兀自矗立在暗无天日原始丛林中一轮赤道艳阳下的石头山——峇都帝坂——丛林的守护者、猎人头战士达雅克人心目中与天地同生的圣山。他们说那是大河的尽头,生命的源头。
每个人心里一亩 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 一个梦
机缘凑巧,自十五岁那年的暑假,它,峇都帝坂,成了我心中私淑的(除你之外从没跟别人讲过的)一亩梦田。丫头,瞧你听着听着两只眼睛忽然机灵灵一转,你心里好想知道。这座石头山究竟在哪里,对不?在黑水潭底幽锢三年,你依旧那么好奇,一如当初我在古亭小学门口遇见你时,你乜着眼,睨住我这个来自南洋的浪子,头上脚下打量个透,两道目光森冷森冷,直欲看穿人家藏匿在心底的秘密似的。老实讲,那时,我还真被你一双眼睛盯得心里直发毛……好啦,我不卖关子,你打开一张世界大地图吧,看那赤道之上,东经一百一十五度与赤道之交,南中国海之南,爪哇海之北,偌大的一片热带水域不是横亘着一个岛吗?这岛,你莫看它状如古锥,胖嘟嘟,活像一只怀着一窝胎儿蹲伏在地上的母狗,满脸慈蔼福福泰泰,它却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大陆岛,南海硕果仅存的雨林,自古的瘴疠之地,不知埋葬过多少欧洲传教士、阿拉伯商贾、荷兰官吏和眷属、日本皇军和营妓、美国嬉痞浪人和华侨猪仔矿工的骸骨。这岛有多大?长一千三百公里,宽一千公里,百分之八十的面积覆盖着密不通风、热雾弥漫的雨林,氤氤氲氲,终年蒸腾在赤道那一轮火红的太阳下——丫头,这已经够壮观了吧?可慢着,岛上还有六大河系——拉让江、巴兰河、加央河、玛哈干河、巴里托河、卡布雅斯河——发源自岛中央的加拉毕高地,好似一只庞大的八爪鱼,四下辐射伸张,顺着山势奔流而下进入内陆丛林,倏地,蜕变为千百条黄蛇,在雨林中钻进钻出,穿梭过那星罗棋布一洼又一洼连绵不绝的沼泽,来到海岸冲积平原,汇成六条大川,变成六只黄色巨蟒,砰砰溅溅一路翻腾嘶吼着分头闯入爪哇海、西里伯斯海、苏禄海、南中国海。这六大河系之首,便是号称印度尼西亚第一大河的卡布雅斯,长一千一百四十三公里,流经面积广大的西加里曼丹省,华侨管它叫卡江,达雅克人干脆称它“大河”。就在大河的尽头,天际,赤道那颗大日头下,苍莽雨林中,拔地而起,阴森森赤条条耸立着开天辟地时布龙神遗落的一块巨石——峇都帝坂。
十五岁那年夏天,在一桩诡谲的因缘安排下,我有机会在这座雄踞南海中央的大陆岛上,从事一趟卡江之旅。说它诡谲,只因为当初神差鬼使,我误打误撞上了那艘船。丫头,咱俩在台北街头浪游那晚,我给你讲过一个童年故事,说我父亲年轻时喜欢飘流,南洋大热天,他终年穿着他那套漂白夏季西装,头戴一顶米黄草帽,手提一口黑漆皮箱,进出岛上的英国与荷兰地界,风尘仆仆,不知在干什么勾当,后来竟做起走私黄金的营生,着实发了点财。我顶记得,我三岁那年的春节,大年除夕我父亲带着满脸胡碴子半夜从外地赶回来,一踏进家门就把我从床上叫醒,笑嘻嘻站在床头,解开大衣钮扣,让我瞧一眼他腰间锃亮锃亮缠绕着的三四十根金条……但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有一次摸黑穿过英荷边界,他终于失手,被荷兰警察逮着,押到荷属西婆罗洲首府坤甸,打入大牢。后来透过一个荷兰女子克莉丝汀娜·房龙,买通典狱长,才得以脱身,鬼赶样一身清洁溜溜逃回英属北婆罗洲,从此雌伏,蹲在家里不再飘流。长大后我听他的事业伙伴黄汝碧叔叔说,那时出得狱来,我父亲走投无路,便厚着面皮向那荷兰女子商借三千盾当作路费,否则准会客死坤甸城。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我父亲和房龙小姐的,只隐约感觉到有点暧昧,似乎有点不可告人,让我那苦守在家的母亲受了委屈……但这件事我不想弄明白。反正,那个时代英荷边境龙蛇杂处,各路人马各色人种蝇集,觊觎西婆罗地区的金矿,于是苏丹王国的小京城——坤甸,一夕之间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丛林中的销金窟,啥事都可能发生。你知道吗,我们的客家乡亲,梅县人罗芳伯曾在那儿建立一个共和国,号称“兰芳大统制”,自封“大唐客长”,统领卡江下游几十座金矿和数万华工,真个声威赫赫,荷兰人莫可奈何。直到罗芳伯死后,荷兰兵才乘隙突袭,将兰芳共和国消灭。这固然是史实,但跟我要讲的故事无关,终归闲话一句,表过不提。反正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上名校古晋中学高中部。为了犒赏我,父亲让我去坤甸,在克丝婷姑姑家的房龙农庄住个把月。虽然一开始——也许为了我母亲的缘故吧——我对那荷兰女子殊无好感,甚至有点恶感,但乐得乘此机会,离家一阵子独自在外度个暑假,况且,我从未去过西婆罗洲,尽管它与我居住的北婆罗洲沙捞越邦只隔一条山脉,而我父亲,那个垂垂老矣、饱受痛风折磨的浪子,当年便是在这个地界进进出出,干他那荒诞的营生。于是无可无不可,在他老人家亲手打点下,我,十五岁,初次离家的少年,穿上父亲慎而重之从箱底取出的那袭窖藏多年、压得十分服帖平整、依旧漂白如故的夏季西装,手里拎着他那口黑漆皮箱,内衣袋中揣着他托我交付那洋婆子的三万盾现钞(以及一包密封的不知名物事),于七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早晨,从沙捞越邦首府古晋出发喽,搭乘大海船,顶着滚烫的大日头,穿过赤道线,越过南中国海与爪哇海之间那片沸腾的水域,朝向南极星,航向卡布雅斯河口那座城——坤甸。可丫头哇我做梦也不曾料到,后来证明,这趟坤甸之旅只是前奏,一段短短的序曲而已。它的功用在于开启另一趟更荒诞、迷幻、更匪夷所思,以至于令我刻骨铭心终生思念克丝婷这洋婆子的航程……
喔,神秘的卡江之旅。
就是呀!丫头聪明,一听就明白。
于是那年暑假你在克丝婷姑姑带领下,从坤甸出发,沿着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一路溯流而上,航向大河尽头达雅克人的圣山——峇都帝坂。
我早就说过,别人的心只有一个窍,而朱鸰你这小丫头儿的心却生了七八个窍,机灵得紧。自从新店溪别后,三年来叫我怎能不日日思念你、牵挂你,可如今你独个儿悠游在那个不见天日的黑水潭底,自得其乐流连忘返。
咦,你有没有发现?你那年暑假的卡江之旅,跟我们上次的新店溪之旅有个共同点哦。
同样是溯流而上……
抵达水源头……
寻找……
一件失落的东西!
人生真奇妙。我一生最奇特、最重要的两次旅程,就在一双巧手(丫头,是你的手喔)拨弄下莫名其妙、天衣无缝地给连接了起来。朱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缘法呢 ?
嘻嘻,上帝的安排自有美意,
你莫嘻皮笑脸,我是跟你讲真的。不过,当初展开卡江之旅,我倒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就像你,朱鸰,一个小学女生偶然与我结识街头,迷迷糊糊伴随我,漫游夜台北,两个人一大一小沿着一条腥臭的黑水河,边走边讲故事,寻寻觅觅直到旅程快接近终点,心中才灵光乍现,恍然大悟:原来,咱们这一夜跋涉,溯溪而上,竟是在寻找传闻中早已灭绝多年的台湾原生鱼——庵仔鱼。
这就是探险旅程好玩的地方呀,哥哥!你想,你若一开始就知道你去寻找一件什么东西,那不就像到市场买菜,或像上学读书一样无趣吗?那不就不是迌了吗?你记得我在古亭小学门口,水泥地上,用粉笔写给你看的两个方块字“ 迌”?这是最美丽、最奇妙的冒险呀。只是你十五岁那年的卡江之旅,比后来我们的新店溪之旅更神秘阴森,路途更长,时间更久,花了你一个暑假。这样的旅程中肯定隐藏着一件更奇特、更有意思的东西。当初你穿着父亲的旧西装,提着父亲的黑漆皮箱——嘻!你那个模样一定很古锥——独自搭船到坤甸,出门时难道真的一点预感都没有吗?
没。那时我心里只想离家出门在外度一个暑假,玩玩,散心。
那就好玩了!这个行程听起来有点意思哦,我真想也走它一趟。
当初到了坤甸,糊里糊涂,就在克莉丝汀娜·房龙小姐带领下,我跟随一群陌生的白人男女,乘坐达雅克人的长舟,沿着卡布雅斯河一路逆流而上,穿透层层雨林,航行一千一百公里进入婆罗洲心脏。大伙哼嗨唉哟,推着船,闯过一滩又一滩怪石密布水花飞溅的漩涡急流,直抵大河尽头的石头山,峇都帝坂。那时我真的不知道,甚至抵达终点时也没察觉——我只是个十五岁的懵懂少年啊——这趟航程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在大河尽头我又会找到什么东西,发现什么人生秘密。我只是感觉好爽,心中很痛快,因为我完成了一趟同侪们没有机会经历、心里准会羡慕得要死的冒险旅程……就像你,朱鸰丫头,这会儿竖起两只耳朵,睁着一双水灵灵充满好奇和疑问的眼睛,凝神屏气,准备聆听我讲述卡江之旅,可你心里压根也不晓得,这桩经验,这则乍听起来紧张刺激、曲折离奇、洋溢着异国情调和热带风情的探险故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而找到它之后对你一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朱鸰,就让我们再结缘一次,再度结伴出门 迌闯荡去!喂,出发喽。现在就让我们沿着那条黄色巨蟒般的大河,共同展开这趟贯穿南海原始森林的少年暑假之旅,让咱两个肩并肩一起经历、一起见闻、一起感受、一起探索和发现这个穿渡秘境,直抵天尽头、大河尽头的航程,然后拜托你再度把我给带回家——真正的家,我刚才向你诉说的我内心中那亩梦田。
一颗啊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春又来
那是我心里一亩一亩田
丫头,你听!在这台湾东端的花东纵谷,夜深人静,虫声唧唧,占地二百五十公顷的偌大校园灯火零星,整排宿舍暗沉沉,只我一人不眠,独自儿呆呆坐在书桌旁一盏灯下,让齐豫那邈古苍凉的歌声,招魂般反反复复,不住回荡在我耳际,心中只顾追索多年前那一个月的旅程——逐日逐个小时地追索,分分秒秒地重温——往事纷至沓来,于是捡起纸笔,发愿似的不住书写,一字一思念,召唤你。魂兮归来,切莫在新店溪上一窟窿黑水中逗留太久喔!你看窗外一瓢清光,整夜映照我,可不知什么时候就幻化成一钩暗淡的下弦月,披上一幅青纱,悄没声,隐没到阿美族的圣山黑色奇莱的背后去了。往东,海岸山脉草木葱茏,蓦地迸出簇簇金光,一轮红日从太平洋中升起来啦,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丫头拜托你再度伴随我走一趟迌之旅,丛林中烈日下,让咱俩追随那条黄色巨蟒一路溯流而上……一如三年前,你这个八岁大的与我偶然相遇街头的小小女生,带领我进入台北那片灯似锦、海市蜃楼般的世界。你,朱鸰,就像一只领路鸟——就像我十五岁那年卡江之旅一路上不时遇到的那一个个守护河船的小天使:小苍鹭、婆罗洲鱼狗、矶鹬、黑冠翡翠鸟。这些栖居婆罗洲内陆丛林的水鸟,小不点儿,总是颤颤巍巍孤蹲在河畔一根伸向河心的树枝上,静静守望往来的商旅。眼一亮,她看见我们的船陷入险境,便嗖地从树上直扑下来,飞到船头前方,不声不响,引领我们穿过滚滚洪流,渡过处处险滩,直来到约莫五百码之外,她的疆域边缘,才悄然折返,栖停回自己那根树枝上,将引路的任务移交给守候在下一段水域的领航员,那另一只娇小玲珑、孤零零、骨碌骨碌圆睁着眼瞳子蹲在水边树枝上的翠鸟或小鱼鹰……朱鸰,对我而言,你不也是一只领路鸟么?你看你的名字——
鸰——
多么奇妙,字里不就蕴含着一只——
领路鸟?
对了,就这三个美丽的方块字组合成一个更美丽奇妙的方块字,鸰。红领路鸟:朱鸰。
咦?这我倒没想过哦。但我不要做小鸟,我愿意化成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一条哀怨凄美的幽魂,湿淋淋从水中倏地冒出来,飘飘袅袅一路追随你这个老想回家的浪子,闷声不响日日夜夜纠缠你、陪伴你,直到大河尽头那座光秃秃鬼气森森的石头山,才悄然折返,独个儿回到新店溪上游黑水潭底,我自己的家,跟我那群庵仔鱼姐妹们重聚厮守。嘻嘻,走!咱两个这就上路吧,一起出发前往卡布雅斯河口那座城——坤甸。
(选自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0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