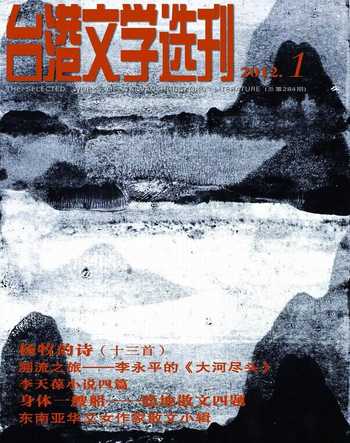身体一艘船——隐地散文四题
2012-04-29隐地
隐地(台湾)
一日神
一日喜,一日怒……一日甜,一日苦……创造神、破坏神、保护神……人,谁能摆脱这些神?它们在天地之间形成一面天罗地网。
看起来是三分天下,世界之大,岂止此三神?三神各有兵马,这些兵马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宇宙诸神,它们掌控着万物的命运;人想创造自己的生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诸神听了,只在我们背后窃笑。
话说有一个最不为人注意的一日之神,它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只和我们相处一日,就离我们而去,所以,从来也不为我们发现,人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
一日神身轻如燕,它天明来,夜半去,悄悄相处一日,就和我们说拜拜,何日再相逢,它不知道,每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它在哪里,但知道它在,也知道它已经走了。
一日神和一日神何时交换卫兵?我们完全无法察觉,只是一日之隔,喜讯已成噩耗,为何相差天地之远?
昨日明明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只是睡了一觉,清晨醒来,世界仿佛全变了样。
不对,就是不对,一大清早照镜子,出现一个看了好让人讨厌的糟老头,昨天还老得满帅气的,怎么一下子就丑了?此刻瞧着,就是不舒服。他拿起梳子梳啊梳的,怎么梳也梳不服帖,头发就是不听话,更寻不到一丝光泽;继续梳,仍然梳不出一个样子来,有的,只是溢满脑际的懊恼。
俱往矣,生命就这么萎缩了吗?六十年,整整一甲子,应当是无限长的生命,看来好日子都过去了,春花、秋月,全成了过去式,而夏日的灿烂,怎么我从未感受过,却已经成了杳不可及的梦?
他战战兢兢地度着他的一日。一日之计在于晨,他最担心一早起来恶兆临头,果然,整日的不顺心,从自己的头发引起。快乐总是如白驹过隙,而郁闷却经常如漫漫长夜无边无际,啃蚀得他连胃都翻腾着痛,一旦胃不适,食欲全无,一天也就自然报销了。
噢,今天的一日神,看来并非是凶戾的煞星,一定是一位恹恹之神,把我弄得一天都无精打采。赶快用柔和之心来挡它,千万不要和它发生摩擦;讲理要和讲理的人讲,神鬼更如此,一旦来了不讲理的神,你就快闪,闪过这一天,天下太平,闪不过,会死人的,人死了,你就和鬼一样,也成了鬼。
“我就是闪躲不过嘛!”所以啰,这世上早已鬼多于人。你就得更加小心地过日子,幸好保护神永在,一日煞星也只能纠缠你一天,明天会有一个吉祥的微笑之神向你迎面走来。
人间多么好,只要黑夜之后的黎明你醒得过来,树在、花在,云飘在蓝蓝的天空,一轮旭日正冉冉上升。这人世间多美好,鸟正为你歌唱之际,你还可为自己煮杯咖啡,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乐声更让你感觉幸福已团团围成一个圆圈,在荡漾开来……
二十岁的时候,他像一架上升的飞机,世界在他面前都是会飞的、上扬的,连他小小的阳具,也都经常往上抬着头;四十岁的时候,他读《如何在四十岁前成功》,书上竟然这样写着:“四十岁不健康,健康不起来,四十岁不成功,成功不起来,四十岁没有钱,有钱不起来……”到了六十岁,原先无神论的他,变成一个多神论者,且处处感觉与神同在。甚至,他认为,每一日,都有一个“一日神”陪伴着……创造神创造了他,人人都该感谢自己的创造神;我的创造神是谁?有一天,突然他这么问自己,他要用温柔的感恩之眼,向他的神膜拜。“你不用向我膜拜,重要的是,请不要激怒你的‘破坏神就好了!”一种遥远的声音仿佛来自天际,他看不到“保护神”的脸,却清楚听到一种来自它的关怀的声音。原来“创造神”创造了他,最怕自己的作品不能长长久久地存活于世。“破坏神”无所不在,但只要不去惹它,破坏神也有它自己忙不完的工作。“对,”保护神微笑着说,“你不惹是生非,我的日子也可过得轻松自在。”
自从感悟到有诸神存在,如今他凡事小心翼翼,可“一日神”中捣蛋鬼特多,常来寻他开心,让他经常有虚幻之感。
他有两串钥匙,一串用来开办公室的各种门锁,一串用来开家里的门锁。除了钥匙,还有眼镜和钱包,也是他经常在寻找的。爱捉弄他的“一日神”,经常喜欢和他玩躲迷藏,总以他身边的这几样东西逗着他玩——静物是没有脚的,却怎么老是跑来跑去,“明明记得放在桌上”,桌上就是寻不到他要找的;“一日神啊一日神,我是有些年纪了,开始记不住这样那样东西放在确切的位置,请不要整天和我过不去,一定是你偷偷移动,让我总是不停地寻找。”
有一天社区开住户大会,三十二户人家互相怪来怪去,彼此说话都毫不客气,左邻右舍都有院子,院子里家家都种着花树,树长高了,难免枝叶会伸展到隔壁人家,于是起了纠纷。根据一种说法,你的树枝进到我家院子,我就有权把它剪除,结果是你剪我家的树,我当然同样可剪从你家延伸过来的树枝,如此剪来剪去,邻居自然成了冤家。
这是什么神嘛,让邻居和邻居都不得安宁!如果是“一日神”还好,脸红耳赤吵一架,第二日彼此若肯反省,双方说声对不起,一笑泯恩仇。可惜这不是“一日神”能解决的,“一日神”之上还有一位“月神”,“月神”的上司是“年神”。啊,有人为了一棵树,变成一辈子的世仇,“年神”也不得不退在一旁,只好让“破坏神”亲自出征,从此隔邻两家成了世仇,吵到后来,刀啊枪啊全部出笼,结果出了人命,好好的人不做,全去做了鬼!
“我不惹破坏神,让我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他在心底祈求“一日神”。是的,就算只有一天,也是好的,有了一日的平平顺顺,明天就算有煞星登门,我也会低头忍着,吃苦、受气,本来都是人生免不了的运命啊!
“真的吗?”躲在门角的“气神”显然不信,它是一个让人从早气到晚的神。只要它和你缠上,包你气鼓鼓地板着一张脸,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全身上下就是有气,不想还好,越想越气,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着自己什么,想起往事,更是件件让人生气。气自己那么容易生气,为何别人的脸上能经常挂着笑容,可我就做不到,晚上睡在床上翻过来转过去就是睡不着?当然也为睡不着生气,彻夜翻腾到天明。容易生气的人,还在为一整天气鼓鼓的自己生着气。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日神”啊,今天我的气生得够多了,我不喜欢生气的自己,明天给我一个心平气和的日子吧!至于明日的明日的明日,“一日神”,我是子民,在天地间,我已看尽人生百态,尝尽人生酸甜苦辣滋味,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请让我心平气和地过一些平常日子,请不要再以惊涛骇浪考验我,“一日神”,我只求能平凡地呼吸于凡人之间。
喜怒哀乐伤身,我只要平心静气过日子,“一日神”,请多派些老派且温和之神保护我,那些古灵精怪、顽皮透顶的“一日神”,让它们和青少年去周游,少年人精力旺盛,也喜欢刺激,就让他们一块去搅和吧!
(选自2009年9月14日台湾 《中国时报》)
身体一艘船
身体,是一艘没有航道的船。从生命诞生的一刻起,他就和天上的云水中的鱼一样飘着游着。从早到晚,从春天到冬天,我们的身体游走于大地,就像船一样在海洋里行进着,有时后退,有时打转,有时也停泊到一个码头,或进入港口休憩。
我让自己的身体斜靠着,成为一艘会思想的船。随着烟尘往事,想着人在大地上的存活。人,从诞生到死亡,航行于茫茫海洋,新日子转眼成旧日子,新的一年叹息之间来了又走了。我们活在短暂的时空里。只因为活着,生存着,就像船不停地来来回回开动着。有了身体这艘船,我们可进可退,可驶往人潮,也可退出江湖。
我喜欢我的身体,因为他像一艘船。每天醒来,他把我驶到楼下,取出信箱里的报纸,顺手将羊奶也带上楼,就着灯光将报纸摊在早餐桌上—— 一个世界立即展现在我眼前。报纸把世俗人心的温度传染给我,有时感觉温暖,有时整颗心开始淌血。有人告诉我,这是世纪末,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人类新一波的浩劫正在等待我们。
我,一艘航行了六十年的老船,想着我的生命、生命中的偶然必然茫然。四周不断有新的生命涌来,纸船、小帆船、独木舟……新人类是多么勇敢,他们什么也不准备,一样和我们并肩前行。我看着前面的大轮船,多么庞大的身躯,在汪洋中载浮载沉。当年初航的勇猛,显然风一般地消逝了,他踽踽独行,还能在这逆风冷雨的海上支撑多久呢?我知道答案。人生的收尾还会有什么好戏?他最后会沉没,我也会沉没,随后赶来的独木舟、小帆船和纸船一一都会沉没。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历史会记载我们的航程,虽然历史也将沉没,沉没才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命运。
囡囡宝宝,你是一艘什么船?汪洋大海一片,为什么我们竟然撞上了?噢,两艘撞在一起的船,是喜剧还是悲剧?或是悲剧之后的喜剧,喜剧之后的悲剧?人类还能演出悲悲喜喜、喜喜悲悲之外的什么剧呢?
噢,什么荒谬的悲喜剧全都出笼了。在这个号称后现代的末世代,人咬狗已不是新闻,人变狗或许才是新闻。用身体的船继续向前航行吧。活着,就可欣赏光怪陆离的世界,看尽光怪陆离的现象。这是人性大解放的年代。地府天宫想象不出的情节,魔术师全为我们变了出来。声光视听,更是国际水准。谁的魔术变得巧,谁就是这个世界的王。
我望着阳台上一双又一双的鞋,这些像船一样的鞋,它们载我行过大街小巷,让我成为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在春夏秋冬里老了,我们的城也因为春夏秋冬而年轻。许多遗忘的老历史被翻陈了出来,另一些新绿,却盖上了黄土。这会儿的羞辱,曾经也是人们欢呼过的荣耀。一棵树的茂盛、憔悴,原来就是一座城的故事。
我的身体是我的船。二十年前,我就扬帆远航,越过太平洋。我也曾徜徉地中海,更游历了巴黎的母亲——塞纳河。不要对这世界抱怨,这世界一直是美丽的。我们要为自己活着骄傲,要为活在当代感到荣幸。特别是,我们活在中国,险象奇象且有点异类的中国,一个古老又绝对新鲜的国家——透过五千年历史文化,我们看到自己国家龌龊的和龙飞凤翔的一面。人要愈活才愈知道,世间的真相其实不容易看到。人是矫情的,城市是矫情的,连我这艘船也是矫情的,不是吗?我们从来不曾赤裸着站出来。有谁看过原木船?不管是什么材料的船,都要上漆。上漆是对船身的保护,穿衣也是。我们用衣服保暖,也用衣服和朋友保持距离,保持我们的尊贵。
而你,囡囡宝宝,我们是赤裸的,我们用赤裸的身体相互取暖,两艘纠缠在一起的船。我们飘浮在海洋,我们是两块原木,可以互相拆解,也可以拼装合成一艘船。
一艘船,一艘愚人船,这世上数以亿计的愚人。可笑的是人人都自以为不凡,自以为是美少年、美人儿。其实,我们一点儿也不美、不年轻。所有年轻的、气盛的、自恋自傲的,让生命继续往前走三十年。三十年的光阴,在亿万年的时空里,只是眼眸一眨,而你已经老了。对着镜子谁都可以瞧瞧自己,皱纹一横一画地长出来。眼袋有没有,每个人心里都有数。身体这条船,如此不堪一击。脆弱是你的名字,摇晃在茫茫人海。人啊人,可怜的是人人只望见别人的老,别人的丑,从来不曾想到自己也是愚人船上群愚之中的个愚。
你说你是一艘船吗?你航进了漆黑的世界,你是在黑夜的海上。光亮,在世界的另一端,日与夜连贯着。我身体的船,用睡眠衔接太阳与月亮的换班游戏。世界的彼端,开着一片美丽鲜花,大地欣欣向荣。成长着的年轻人,眼前除了希望,还有梦,你不做梦吗?你这艘老船,你忘了自己曾经年轻。地球是圆的,时间也是圆的。你的船旧了、破了、沉了,新的船一艘又一艘正在进行他们的初航。何况,这世间多的是不老的老人,不是吗?你听谁说过圣诞老公公老了?老人不是永远围在我们四周吗?这世界从来没有缺少过老人,也就永远会有自称像船一样航行着的老身体,以及老牛老马老公鸡,以及老钟老鞋老冰箱,还有老婆和老情人。让老的和老的涂上微笑的漆,也漆上希望和梦。让一艘艘慢慢行驶着的老船,全身上下都闪出光亮。
我想飞,我的身体挂满了零件,我飞得起来吗?我必须提醒自己只是一艘船。如果青春靠紧我的身体,我想,自己会是一艘飞船,可以飞得起来的。可惜,贪心让我挂满零件,我的身体成为一座欲望之城。
让城,坍塌吧,恢复我为一艘船。我喜欢自己的身体像一艘船,甚或只是一叶轻舟。我要趁自己还能动的时候,游历这个世界。
囡囡宝宝,请携手与我同行。
(选自1997年1月13日台湾 《中国时报》)
角落·画面
六十年前,一九四九年,我十二岁,父亲受不了母亲整天嘀咕,准备带我们返回上海。想不到逃难的人潮一波波从基隆码头上岸,原来国共内战如火如荼,国军节节败退,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失守,父亲终于有了借口,不是他不肯带母亲回上海——从小生在苏州,长在昆山却喜欢上海的母亲,梦想从此破碎,她再也回不去上海。一直要等到三十八年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台湾开放探亲,民众重新可以返乡,母亲才回到上海、昆山和苏州……前后两次去回,她选择终老台湾,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父亲就没那么幸运,他于一九七○年九月过世时只有六十九岁,两岸还在互相为敌的年代,因战争而隔离的游子,谁也别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祖父母一一过世的时候,父亲不能回去奔丧;父亲过世,同样,浙江永嘉(温州)的乡亲,我想连讯息都无法得到,就算知道了,也只能仰天长啸。
当年身为农夫农妇的祖父母卖了田地供父亲读大学,怎想到他远去上海,再跨海渡台,一个长大了的儿子,战火隔绝两岸,父亲和祖父母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连带着祖父母当然更见不到他们的孙子;我从生下来从未看过他们,所以祖父祖母对于我只是一个名词。
我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角落。我的祖父母生活在属于他们的角落。台北和温州,各有老的一代和小的一代。明明有血缘关系,却因战争让原本一个家庭成为陌生人。这种诡异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不只占着一个角落,角落里还有更多的画面,已经六十年了,仍久久挥之不去。
永难忘记的一个画面是隔壁孙伯伯吊死的场景。他一个人渡海来台,住在公家配给的宿舍里,和照顾他生活的年轻女佣发生了关系,把女佣的肚子搞大了。孙伯母就在那节骨眼上,从大陆逃到香港,办了许多手续又从香港千里迢迢来到台北,找到先生的家里还来不及兴奋,竟然发现先生藏着怀孕的小女人,一夜争吵的结果,第二天清晨孙伯母醒来看到自己的先生悬梁而死,身子早已冷。孙伯母从此守寡,她变成一个脸上再也没有笑容的人。有时我会在福州街蔡万兴饭店看见她弯着腰的身影,九十多岁的她显得格外孤零,她总是一个人吃饭,然后独自离去。
时移境迁,今天,没有人会觉得婚外情有什么大惊小怪,可在六十年前,那是严重得天都会塌下来的事情,孙伯伯就是受不了那压力而自杀身亡的。而孙伯母罪不在她,但因先生死了,她深感自责,她恨自己吵闹不休,把所有的罪过揽在自身,自此,不快乐成为她的注册商标。
孙伯伯死时三十五岁;孙伯母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她一生未再婚。她的幸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埋葬在一场战火里了;要不是战乱,她和先生不会分隔两地,更不会突然多出这么一个怀孕的小女人。
还有一个画面也常在我心头涌现。那时农复会成立不久,引进不少留美的归国学人。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妇,都在农复会服务,他们租了对门林伯伯家的一个房间。那时可能因为克难年代的关系,一般住家还不十分讲究卫生,看在这对年轻夫妇眼里,他们显然有太多的不放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天天把消毒挂在嘴上,厨房厕所里的每一样用品都要消毒,每次吃饭之前,不但碗要消毒,筷子也要消毒。这么爱清洁的一对夫妻,后来从宁波西街搬到南昌路一幢新盖的二层楼建筑,夫妇俩请林家四千金和我到他们家吃饭,仍然不停地在厨房里消毒各种餐具。原来环保观念早就深植在他们心中,后来他们回台服务三年期满,又返回美国,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
在王永庆于一九五四年成立台塑公司之前,塑胶已经是一件让人产生好奇的新材料,父亲嘴上就经常挂着P.C.、P.C.的。原来,爸爸虽在北一女中教英文,后来转到南昌路、公园路(现烟酒公卖局对面)口的樟脑局服务,但他其实一直想做贸易,所以经常有海外的各种样品和商品目录邮寄到他的信箱(爸爸在那么早的年代,就在台北博爱路邮政总局开了信箱,直到一九七○年过世,他仍租着邮政信箱),塑胶品是那个年代当红产品,那也是尼龙、达克龙、帝特龙、特多龙、毛丽龙、爱丝龙和什么龙流行的年代,连男人穿的衬衫也常常都是半透明的尼龙做成的;因为半透明,人们还喜欢在上衣口袋里放一张百元大钞,以示自己是有一些钱的人。
那是多么贫穷的克难年代,口袋里让人看到放着钱,当然是表示一种炫耀,甚至于家里用的家具,或书籍杂志上都要上一层胶,一切要看起来光光亮亮的。后来台湾流行的磁砖文化,也是因为磁砖有一种光亮度,东贴西贴,许许多多建筑物墙面都贴着磁砖,配上一面红门,家家户户如此,一直要等到外国观光客嘲讽“到了台湾像是一脚踩进厕所里”,磁砖文化才逐渐退潮,连带着书籍和杂志开始改用雾光,用到几近浪费的铜版纸,才为大家知晓那是一种缺少质感的纸张。
塑胶统治台湾超过五十年,一直到今天,塑胶碗、塑胶杯无所不在,塑胶袋更是如影随形,想丢也丢不掉,而我们还必需承认,塑胶用品明知它会溶解毒素,但人们似乎已经离不开它了。
六十年,隔了六十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台湾,从克难年代走来,经过繁华、富裕,开始崇尚简约,会妙用对比色,也懂得同色搭配的质感,从建筑物到个人穿衣,如今旋转一圈,虽然我们又进入穷困年代,但大家的眼力和敏锐的感受度,都和当年克难时代的人们不一样了。我们已见识过各种场面,从热战、冷战、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到民进党陈水扁的贪渎,都让人们大开眼界;而李登辉横跨日本、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台联党,像这样的人物我们都领教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人?六十年的台湾代表着丰富、魔幻、多元、惊奇以及不可思议,是活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相遇的神奇,这是一个比天上彩虹更多颜色的岛屿,从最贫困到最富裕,从最富人情味到最无情无义,从最纯朴到最奢华,从最有办法到软弱无能,从创造神奇到无奈叹息,世上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都会在台湾发生……在这个岛上生活六十年,让我感觉仿佛已经活了好几生。在我心底的角落,不管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住了六七十年、八九十年,仍然是新住民,真像是吃到了新鲜的大白菜),我们都应感到幸运,感恩千载难逢的奇遇,我们竟然在这个岛屿上碰在一起,互相取暖,却也爱恨纠缠,或许还在吵着。但无法否认,我们就是生活在一条船上,不肯解开死结,也就只好在海上东西南北无方向地继续漂荡了。
(选自2009年3月4日美国 《世界日报》)
百年人生·起承转合
——外加一首诗,为重阳节而写
首先,要向已经超过一百岁的人瑞和接近一百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告罪,看到这个题目多少会有些不舒服,就像为九十七、九十八或九十九岁的老人家祝寿;你说“祝你长命百岁”,听在老寿星的耳里还真不是味道,他心里会想,难道我只剩下一两年好活?
所有靠近一百岁或已活过一百岁的老人都是福星,都是前世修来的,也是你今生爱惜身体的福报。活到老,还要活得好。我的侄女柯宁宁,住在美国圣马雷诺,她的邻居是一位高龄百岁的人瑞。一提到人瑞,你可能认为一定是鸡皮鹤发,老得令人生畏,不,不,柯宁宁的这位邻居,是位女性,是位摩登的女性,或许你觉得不可思议,她每天都会在她家里附近社区开车转一转,到了晚上,家里三不五时都有舞会,四面八方不知哪儿转来的一大堆老先生老太太,没有百岁,也都高龄九十以上,他们喝酒、聊天、跳舞、唱歌、读诗,啊,真是快乐的人生。
其实,如果世间没有战争,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不斗争,不闹事,生活规律,不暴饮暴食,做一个百岁人瑞不是梦,人人可以活到一百岁。一百岁正是一个世纪,我们常说圆满圆满,一百岁的人生,才是人生大圆满。人生就像一场万米赛跑场,能跑完一圈——跑到人生终点,才是人生幸福的完成。
老天本来给人的阳寿就是一百岁。可惜大多数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该睡不睡,而且纵欲过度,折损了宝贵的生命。
百年人生像一首歌,如果不急不缓地将人生之歌唱完,可分起承转合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刚好都是二十五年。
第一个二十五年,自呱呱落地到二十五岁,是人生一切的开端,人生也是从这个阶段“起”始——从嗷嗷待哺,到牙牙学语,然后读小学、中学、大学……没有机会入学的,仍可在家里、庙里或社会上,学做人的道理。等到二十五成为成熟之人,就开始承担人子的义务,负起一个成人应尽的责任。
二十五至五十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创业、成家、养育子女、孝敬父母,人生在这一个阶段,责任最重,得“承”受一切的重责大任,就像一栋建筑物的一根栋梁,壮年人生,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家庭里的一根大柱子,要挺起全力,尝尽人世间风雨阴晴。
人生第三个阶段,是“转”的人生,也就是从五十一至七十五岁,这二十五年,是人生的另一个高潮。人活一辈子,不能像老牛一样,永远挑负重担,进入五十岁后,人生旅途,已至中站,好像看戏看到一半,需要中场休息——换场之后,人生迈入另一境界,要以“转”换人生的态度迎接新的下半场人生戏码。
“转”,如何转?五十岁以后的人生,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生新的兴趣。卸下人生的责任,或游山玩水,或与大自然为伍,减少赚钱的念头,多读书,多听音乐,多与艺术生活结合。重新发现人生活着的趣味和意义,以前因忙碌的生活而忽略的许多人生乐趣,此时均应一一找回来。人生像舞蹈,跳到流汗忘忧,才知人生律动的节拍里,原来隐藏着这么轻快的舞步,自己却从未发现,啊,“转”的人生,终于让人感受到不虚此生。
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完全为自己而活。这是生命的收获期,就像秋日,总是凉风习习,而稻田里金色的稻穗,让终于也为自己活着的人,觉得活着真好。生命的福报,越发让人感恩。
然后,像夕阳西下,仍是晚霞满天。此时,我们的生命进入第四个阶段——“合”,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合一,与朋友、子孙合一,即便终生未娶未嫁的人,也需与自己一颗心合一,在“合”的氛围里,七十五至一百岁的最后最宝贵的二十五岁生命,应改扮“付出”的角色,把身边储藏的财富捐出来,根据自己的实力,尽量帮助值得帮助的年轻人,或孤苦伶仃极为不幸的孤独老人,让苦命人偶尔也得到些微欢乐。
人生最后阶段,一定要变“独乐乐”为“众乐乐”,从“取的人生”变成“给的人生”,只要肯给,老人会发现,陪在四周的全是笑眯眯之人。人一旦不计较,快乐就在我们身旁。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活到百岁,更会发现人间真是无限美好。这样微笑着离开的人世,留在我们脑海的将是无憾与感恩!感谢自己曾经在人世游历一场,原来,活着就是一场丰富的人生之旅。
老人之歌
生病,是身体对我们的抗议
要谦卑倾听,来自生命的警讯
我不传简讯
我只接受警讯
存活在大地之上
警讯来自四面八方
不要和新人类
比酷比狂比风流
要时时记得抬头观天象
倾斜的世界暖化的地球
随时会将贪婪之人
狂扫进地层下
海也会翻过来
将人这种动物全部歼灭
莫说龙卷风或土石流
还有无所不在的微生物
正觊觎着我们的身体
譬如一场小小的感冒
就是身体传来的警讯
病毒正全方位向我们进攻
明天醒来看似轻微的喉咙痛
说不定就是你我的致命一击
哦老了别忙传简讯
耄耋之后要时时刻刻
警觉来自飞机车辆空气和浴室滑石的生命警讯
(选自2010年10月15日台湾 《人间福报》 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