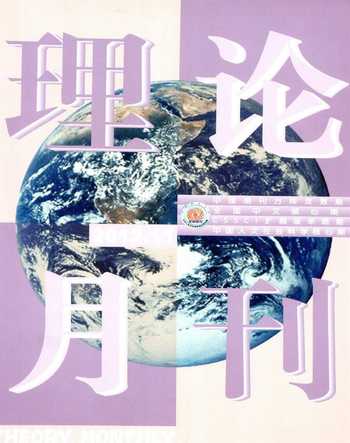普特南论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及改造方案
2012-04-29李章吕
李章吕
摘要:意义理论是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围绕着“语词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众多的意义理论。但是,普特南认为,这些传统意义理论有两个错误的假定,即把意义等同于心理实体(“内涵”),以及把意义等同于外延,这就使得它们无法把“意义”这个概念搞清楚。甚至它们所談论的那些所谓的“意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放弃意义就是心理实体的教条。把外延作为意义的一部分,然后来重新建构“意义”这个概念。
关键词:意义理论;心理实体;意义;内涵;外延
中图分类号:B712.5;N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049-04
意义理论是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作为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的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rm)也受到了这种哲学主流的影响,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语义学问题。不过,在他看来,以往的语义学理论从来都没有把“意义”这个概念搞清楚,甚至可以说,它们所談论的那些所谓的“意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虽然以往的语言哲学家们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正确揭示语词的意义,以至于语义学理论仍然处于“黑暗”之中。不过。普特南却并不赞同蒯因取消“意义”的激进态度。在他看来,我们的语义学仍需要“意义”这个概念。他认为,传统意义理论之所以不成功,并不是意义这一概念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们談论意义的方式不对,只要我们改变传统談论意义的方式方法,就可以构建起充满生命活力的新语义学理论。“我的建议就是,要定义‘意义这个概念,我们不能去找一个与意义等同的什么东西。而是要以一个正常的形式(或者毋宁说是一类正常的形式)对意义做出描述。”因此,他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语义学理论。
一、传统意义理论失败的根源:两个错误假设
普特南认为,传统意义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没有经过检验的假定基础之上的。(1)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meaning),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2)一个词项的意义(“内涵”)决定了它的外延(相同的内涵必定具有相同的外延)。第一个假设把意义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也就是说,一个词项的意义是与某人听到、看到或想到这个语词时头脑中的概念或观念是相等同的。因此,当某人理解某个语词的意义的时候,他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第二个假设认为,具有相同外延的两个语词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比如,“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具有相同的外延,但却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具有相同的内涵的两个语词却不可能具有不同的外延。对于这两个假定,普特南将论证,“任何概念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假设,更不要说意义这个概念了。因而,传统的意义概念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理论之上的概念。”传统意义理论的基本主张就是: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外延。
(一)两种“心理状态”的区分
普特南认为。“心理状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一个哲学家在談论心理状态的时候持方法论唯我主义假设,即心理状态是唯一的存在,任何真正的心理状态都不会预设该状态所属的主体(的身体)的存在,那么他所談论的“心理状态”就是“狭义的心理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像“嫉妒”和“嫉妒某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这样普通而又繁多的心理状态就不能算是心理状态了,因为,在普通的用法中,“X嫉妒Y”意味着Y是存在的,而“X嫉妒Y对Z的态度”则意味着Y和z都存在。按照方法论唯我主义的这种要求。那么每个人都只能嫉妒自己的幻觉或想象的东西了。而不能嫉妒某个实实在在的人或其它什么东西。与此相反,“广义的心理状态”就是普通用法上的那种心理状态,它承诺了对象的存在,这种心理状态也是普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普特南认为,传统哲学家们所談论的都是“狭义的心理状态”。根据对“狭义的心理状态”的解释,普特南对那两个假定进行了重新阐述。“设A和B是任意两个外延不同的词。根据假定(2),它们的意义(内涵)也一定不同。根据假定(1),知道A的意义和知道B的意义都是狭义的心理状态,但是,就像这两个词的意义(内涵)决定外延一样,这些心理状态也决定着A和B的外延。”通过普特南的这个重新阐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意义理论认为,心理状态(狭义的)决定着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义又决定着语词的外延(当然,心理状态也就决定着语词的外延了)。同时。还把语词的意义等同为语词的内涵(即个体说话者心中的概念或心理状态)。
(二)狭义心理状态并不决定外延
普特南认为,上述那两个假定合起来得出的结论,即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外延,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下面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即“两个人所处的心理状态(狭义的)完全相同,但一个人所说的A的外延却不同于另一个人所说的A的外延。”普特南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了论证。
1.个体的心理状态不能决定语词的外延。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证,普特南用的是“榆树和山毛榉”的例子。假如你和我一样,都不能辨认榆树和山毛榉;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所说的“榆树”的外延是榆树,“山毛榉”的外延是山毛榉(如果你说的“榆树”的外延是山毛榉,那么,你肯定就不会说“榆树”,而是说“山毛榉”了)。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在“榆树”的指称和“山毛榉”的指称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差别是如何造成的呢?(即我们都不能辨认榆树和山毛榉,但是却知道我们所说的“榆树”和“山毛榉”有不同的指称对象。为什么?)普特南认为,这肯定不是由我们关于“榆树”和“山毛榉”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榆树的概念与对于山毛榉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在说到“榆树”和“山毛榉”时,我们的心理状态可能完全一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存在一个和地球极其相似的孪生地球,在那里,除了“榆树”和“山毛榉”这两个语词的使用是对换的(即在孪生地球上,“榆树”的外延是山毛榉,而“山毛榉”的外延是榆树)之外,其它的一切和地球上的完全一样。甚至连普特南在孪生地球上也有一个和他完全一样的人(每一个分子都一样,连言语、思想、气质等都一样),因而,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当普特南1和普特南2同时说“榆树”一词的时候,普特南1所说的“榆树”一词的外延是榆树,而普特南2所说的“榆树”一词的外延是山毛榉。因此,在确定“榆树”这个词的外延时,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说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外延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这个例子只是表明,个体的心理状态不能确定语词的外延。但是。集体的心理状态是否能确定语词的外延呢?
2.集体的心理状态也不能确定语词的外延。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证,普特南用的是“孪生地球”的例子:设想1750年之前,近代化学尚未问世,除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和地球几乎完全相同的孪生地球。唯一不同的是,孪生地球上称作“水”的液体虽然和地球上的水看上去一模一样,用起来也一模一样,但其分子结构却并不是H20而是XYZ。当时,由于还没有近代化学,所以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孪生地球上,都无人知晓这一点。那么,地球上的人和孪生地球上的人对于那两种液体的心理状态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了。他们有相同的感觉、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内部语言和相同的心理状态(当然是对同一个事物或事件而言)等,因此对于一个在当时看来完全一样的事物,即地球上的水和孪生地球上的液体,很难说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对于这两种液体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理状态应当是相同的,比如地球人在说“水”的时候,他所想到的肯定是那个无色、无味、透明、可以解渴等的液体,同样,孪生地球人在说“水”的时候,他所想到的肯定也是那个无色、无味、透明、可以解渴等的液体。因而我们也可以说,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在当时对“水”这个词项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所说的“水”,一个的外延是H2O,另一个的外延却是XYZ。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集体的心理状态相同,但意义却不同。因而,集体的心理状态也不能确定语词的外延。
至此,普特南论证了心理状态(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不能决定语词的外延,因而也就论证了传统意义理论的“心理状态(狭义的)决定着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义又决定着语词的外延”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改造传统意义理论的方案:放弃其中的一个假定
在对传统意义理论的错误进行分析之后。普特南指出,要想改造传统意义理论,必须抛弃传统意义理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糟糕做法,把他人和社会都包括在语言中来。实现这一想法的方案有两个。
(一)放弃“意义决定外延”的假定
改造传统意义理论的第一条路线是,“保留意义与概念的等同性,但要放弃意义决定外延的说法。”即保留假定1,放弃假定2。这就否定了传统意义理论的那种“心理状态决定语词外延”的主张。
其实这一主张,一些语言学家也曾提到过。比如旨在对加利福利亚语义学进行改进的哲学家就建议,“一个内涵就是一个函数,它的自变量不仅包括可能世界,而且还包括一个说话者和一个非语言学的表达系统。”这样一来,传统的模型就得到了修正,并可以容纳某种索引性和某种语言的劳动分工了。采用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就正如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所主张的那样,“像‘水这样的词,它在地球上和孪生地球上具有相同的内涵(相同的函数),只不过外延不同而已。”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结论里面包含着“严格性”和“跨世界同一性”,也就是说,结论中所说的不同并不仅是本地外延上的不同,而且是世界外延上的不同。更通俗地说就是,不管在哪一个可能世界中,地球人所说的“水”这个词项的外延和孪生地球人所说的“水”这个词项的外延都是不同的。因为“严格性”和“跨世界同一性”确保了下面这一点,即对于地球人来说,只要是H2O分子,不管它在哪一个可能世界里,不管它离我们有多远,它都在地球人所说的“水”这个词项的外延之内。对于孪生地球人来说,当然也如此。
不过,普特南认为,这条路线虽然对传统意义理论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它只适用于一些语词。“这种思想路线。对于‘我这样的绝对的索引性词项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些词项(不具有索引性的自然种类语词——引者注)来说,却是不正确。”的确,对于“我”这样的索引性词项来说,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在使用的时候,其意义确实是相同的,即都是指“说话人自己”。但是,对于其它那些不具有索引性的词是否也如此呢?对此,普特南依然利用了前面提到过的“榆树”和“山毛榉”的例子,即在孪生地球上,“榆树”和“山毛榉”这两个词刚好倒过来了,孪生地球人所说的“榆树”一词的外延是山毛榉,而他们所说的“山毛榉”一词的外延却是“榆树”。那么,对于同一个词项“榆树”而言,正如前面所论证过的那样,地球人和他在孪生地球上的副本对它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能说“榆树”这个词的意义相同吗?普特南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我们会说,我的副本所说的“榆树”意指山毛榉。
对于这条路线,普特南在1981年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又构造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缸中之脑”论证来说明它的不可能性,即纯粹的心理状态不仅没有任何指称(即不能确定语词的外延),而且连其自身也是不可言说、不可设想的。这个著名的缸中之脑假设就是:设想有个邪恶的科学家将一个人的大脑切下,放在一口能使之存活的装有特殊营养液的缸中。大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这位科学家使用了一种定点消除记忆的方法,使他完全失去被缸化这段时间里的所有记忆。而且,由于这台计算机十分先进,它能使他的大脑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他所获得的“感觉经验”(即计算机传输给他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与他以前所获得的感觉经验完全相同,因此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缸中之脑。再设想科学家本人也是缸中之脑,所有人类都是缸中之脑,宇宙中仅有的只是一台超级自动机,它管理着一个装着大脑的营养缸。正因为有了这台自动机,我们便有了一种集体幻觉,能“看到”、“听到”、“感觉到”他人、物体、天空等等,彼此之间能自由地交流,而实际上这一切并未真正发生。
所以,缸中之脑中的人们虽然能够想和说我们所能想和说的任何话语,但对指称来说,他们说的、想的,有意义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他们说的、想的,毫无意义。比如他们会说“我们是缸中之脑”,“我面前有一棵树”等,但这里无论是“缸”、“脑”,还是“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没有指称内容的,因为当缸中之脑这样说时。并没有想到实在的缸或树,他们所说的、所想的。无非是那样一些电子脉冲而已,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思想中的“缸”或“树”表征现实的缸或树(和现实的缸或树联系起来)。所以,内在的语词或意向(或心理状态)并不必然指称它的对象。
事实上,缸中之脑连想或说“我们是缸中之脑”都不可能。因为,如果你真是缸中之脑,也就是说,如果你被缸化,或整个世界都被缸化,却无法自知(因为缸化的过程已经被邪恶的科学家消除了),那么你所知道的一切无非都是邪恶的科学家或自动机所输入的信息,这些信息与你通过感官所获得的信息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超出这一切信息知道你自己不是缸中之脑呢?很显然,在假设的一切都是真的情况下,如果你是缸中之脑,那么你是无法(通过合适的手段)得知你是缸中之脑的。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形成“我是缸中之脑”的观念。至此,普特南就清楚地论证了他的结论,并彻底割断了心理状态(狭义的)和语词意义之间的联系。所以,在普特南看来,这条路线并不可行。
(二)放弃“心理状态决定语词的意义”的假定
在否定了第一条路线之后,普特南提出了改造传统意义理论的第二条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更可取。“一种更为可取的路线,似乎是将‘意义等同于一个实体的有序对(或者可能是一个有序的n元组),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外延。”也就是说,普特南主张放弃传统意义理论的第一个假定,同时把外延作为意义的一部分。
如果采用这条路线。那么在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那里,即便他们的心理状态完全相同,但“水”这个词项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了,因为地球人所说的“水”的外延是H2O,而孪生地球人所说的“水”的外延却是XYZ。同样。对于“榆树”这个词项而言,在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那里,外延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条路线同样达到了否定传统意义理论的“心理状态决定语词外延”的主张,并且,还不涉及到个人的心理状态(狭义的)。
于是。对于语词的意义这个问题的论述焦点便由内涵的讨论转向了外延(指称)的讨论。因此,传统的意义问题也就分裂成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揭示外延是如何确定的,第二个问题是描述个体的能力。对于第一个问题所要表达的意思,大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就有些疑惑了,即为什么要描述个人的能力呢?这对于确定语词的意义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第二个问题正是普特南进行转变的一个核心话题,因为传统意义理论是问“意义是什么”,但是,普特南却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談论意义的方式,我们应该问“(1)什么是知道一个词的意义;(2)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我们所談论的两个词具有同样的意义。”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自然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了。这就是普特南为传统意义理论走出困境所找寻到的“出路”,并且他的这条路线对于原来那种談论“意义”的方式来说,完全是一种颠覆性的转变,对于传统意义理论来说,也是一种彻底的改造。对这些问题的具体阐述。也就是普特南所构建的迥异于传统的新语义学理论了。由于普特南将人们探究意义的思路由内在心理状态转向了外在环境和社会,凸显了指称在确定语词意义过程中的地位,因而,其语义学理论又称作“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malism)。
三、小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传统意义理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由两个错误的假设。事实上,我们的心理状态(狭义的)并不决定语词的外延,具有相同内涵的两个语词可以具有不同的外延。因而,传统意义理论把意义等同于心理实体(“内涵”),以及把意义等同于外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首先,“词项的外延并不是由个体说话者头脑中的概念(狭义的心理状态——引者注)决定的,这既是因为外延(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决定的,也是因为外延(部分地说)是被索引性地决定的。词项的外延有赖于充当范例的特定事物的实际上的本质,而这种实际上的本质,一般来说,不是完全被说话者所知晓的。”其次,“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忽略了对外延起决定作用的两种贡献——来自社会的和来自真实世界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于是,普特南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把外延作为意义的一部分,把他人和世界都包含在意义理论中来。事实也证明,他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响。正如下面的这个评论所说的那样,“普特南1975年提出的那句话‘心理状态并不能决定语词的外延的观点现在将得到如下这个科学假设(指孪生地球论证——引者注)的支持永远地改变了哲学的面貌。”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