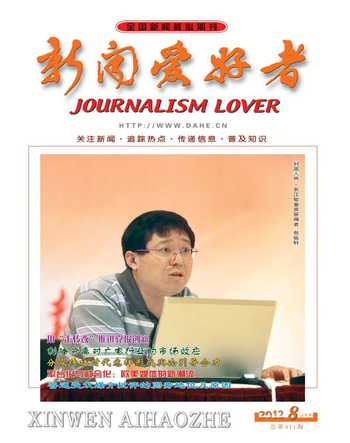“舆论政治”:《国风报》与晚清宪政文化的实践
2012-04-29
从戊戌变法以后,宪政就一直是国内外报刊热衷探讨的问题。改良派人士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不仅将西方的立宪制度条分缕析地介绍给国内读者,同时还将宪政文化作为一种国民常识进行普及和宣传。尽管革命派创办的《民报》对君主立宪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对于以宪法实施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异议。辛亥革命的结束无疑也结束了清政府立宪实践的可能,但改良派人士在宪政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并非毫无“遗产”可言,至少在一些报刊的议政方式上已经将“舆论政治”变成了宪政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这不仅在新闻史上意义深远,也给现代政治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国风报》于1910年2月创刊于上海,作为一份旬刊,它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在这份由何国桢编辑发行的刊物中,早已在舆论界有着赫赫名声的梁启超(使用笔名沧江)是其主笔。它也是《新民丛报》停刊之后,改良派人士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在《国风报》刊行出版之时,正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如火如荼之时,宣统帝固然还无力主政,一班耆旧老臣和封疆大吏也各有盘算。于是,围绕国会问题、铁路举债问题和民变处理等问题,《国风报》以每期8万余字的篇幅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言论,起到了转移一时舆论的作用,创刊后便行销十七省及南洋、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
“舆论政治”与宪政文化
在《国风报》的叙例中,论者便称“夫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1],在长舆的《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中进一步发挥,称“专制政体之下,固无舆论发生之余地也。立宪时代则不然,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2]。立宪政治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成果,它所确立的三权分立模式是在于一种权力的内在制衡,以及遵循一种普遍法来治理国家。清政府在最后十年其实已努力在政治体制上做出一些改变,为了维持稳定以及皇族的利益,预备立宪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辛亥革命客观上也使宣统五年的立宪没有出现,另外在立宪过程中简单地将从前的官僚机构改变成为新设的咨议局等做法也违背了程序正义,这也是其后各种历史叙述将其看成“骗局”的根源。
从1896年的《时务报》开始,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宣传的政治改良其实有过一些变化和曲折。在戊戌变法前后所宣传的改良主要是一种“自改良”,主要是对具体制度环节的改变。而在《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过程中,维新派人士在拥戴君主的同时,其实已经不断地介绍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成功经验,并经常以日本明治新政作为师法的对象。在革命派和维新派论战的开始阶段,双方的焦点主要在于改变政治的手段以及满族的统治是否合法的问题。但在清政府开始通过积极姿态应对危机时,革命派报刊对各种政治改革均抱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报刊言论上也多以揭露内幕为己任,对于相关制度的介绍和宣传远不及《国风报》等立宪报刊深入和透彻。
由于历史的后设性,《外交报》、《中国新报》以及《国风报》经常被看做努力维护满清统治的利益,而很少被认真看待它们在宪政文化实践中的贡献。只要衡量一下这些报刊的言说,它们对立宪政治的设计其实非常清楚。他们将国会问题当做最先决的前提,然后再由国会进行政党的构造和重建,在内阁组成之后,具体的政治治理将接受广泛舆论的监督,投票表决也将因此而具备真实的效果。
探讨国会的开设与否是当时政论报刊中的热点,以《国风报》为代表的报刊强调国会的积极意义,并期待其迅速召开。孙洪伊等人也因此上《国会代表请愿书》,条陈迅速召开国会的必要性。而以《新世纪》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则对国会的存在持全然否定的态度,认为政治是人民自决,不需要组织任何形式的政府。在《河南》、《云南》等留日学生杂志上,看到的更多是国会的负面效果,吕志伊的《国会问题之真相》里极言“以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利用国民者也”[3]。
对于留日学生杂志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国风报》自然也关注筹组国会的实际情况。一旦发现皇族内阁的雏形,该报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并几次三番地组织请愿活动,这似乎不能简单看做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敌视群众,敌视革命,对群众暴力革命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清政府的不满”[4]。这些预演对于清政府固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但对于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产生了不小的压力。至少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不可能不考虑舆论对于国会的期望。而与国会相联系的政党虽然没有对垂暮的晚清起到作用,但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已经明显能起到一些制约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宪政实践逐步产生效应的结果。虽然《国风报》没有迎来三权分立的立宪政治,但却收获了舆论左右政局的可能性。
舆论与国民启蒙
在《国风报》所提出的“舆论政治”中,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使之行之有效;二是引导社会思潮,对普通国民进行启蒙和政治教育。舆论的势力之大,已经是晚清报界人士的共识,而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也是国民受到不当言论引导走上偏激之途。当时各地发生的民变固然没有太多舆论的介入,但报界人士不断告诫政府,一旦民众受到舆论的鼓动产生对政府的不满,则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沧江(梁启超)将国会与国民课本放在一起,“筹备案中有编辑简易识字课本、编辑国民必读课本、创设简易塾等条,最为可笑,吾前曾言之。夫国家教育之本意,非驱一国之民悉从事于政治也,故普通教育重焉。所谓政治教育者不一端,而官私大学之教授,报纸之论列,政党之指导,其最要也”[5]。梁启超辨析了普通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区别,认为在国民教育中常出现泛政治化的错误做法,而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步骤。理想的国民教育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启蒙,而启蒙的结果是能够自如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而具备基本政治常识的要领无非是大学的教授、报纸的宣传以及政党制度的不断深入。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但没有进入大学学习或者不属于政党成员的人来说,报刊舆论无疑是强化其政治参与性的最便捷途径。
晚清的国民启蒙问题一直是研究近现代史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众多学者的辛勤研究,思想家个人的启蒙理路已经呈现无遗。但对于一般民众的启蒙问题,则往往只是着眼于基本素质提高的层面,对于白话文运动和下层启蒙运动的研究都可做如是观。但其实,在鼓动一时之风气的精英与等着亦步亦趋的下层民众之间,肯定还会存在一些中层人士,他们受过相当的文化教育,但对于世界大势或者政治观念并无深入了解,他们有固定的阅读时间,也有参与政治的必要资本。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地方咨议局的成员,也有可能成为宪政民主的直接实践者。他们接受的政治训练可能并不专业,而对政治事务的实践往往要乞助于先有的“案例”,而这些往往是报刊信息与政论碰撞的结晶。
探讨国民文化的复杂性不在于掌握当时究竟有多少缺乏基本文化素质的国民,而在于一些思想界精英虚构了国民的文化形象,也简单化了知识精英与欠修养国民的对立。保存国粹与批判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在一致的,都是虚拟了一种理想的国民文化境界,然后希望所有的国民都按照同样的路径去发展,而放弃了可能有的其他选择权。在国粹派或新文化人士视野下的国民,都是知识未定的青年,对他们的启蒙是方向和价值,而不是选择和同情。而借助舆论引导的国民,则会给予他不同的选择权,他可以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但一定会清楚自己的权益,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国民。
晚清的立宪政治没有成功,但宪政文化却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一些较为新鲜的维度,而《国风报》凭借舆论启蒙国民的思路也是彼时国民文化中的一个新思路。从《申报》开始,中国出现了不少商业报纸,它们构建的新闻文化不见得完全是呼应西方的市民社会,构筑起来的空间具备一定的公共性,但其讨论的策略决定了它对政治问题的隔靴搔痒。而《新青年》等构筑的文化空间则将文化建设当成了建国方略,目标悬之过高,常会成为各种主义和信念交战的场所,与普通国民的政治权益相关度较低。而清末民初的一批立宪派报纸,尤其像《国风报》,既能探讨重大的政治问题,也为略有常识的国民提供了解政治的各种参考,尤其是了解到自身的权益。这对于现代国民文化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也对“舆论政治”的真正形成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国风报》,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86页.
[2]《国风报》.第十三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24页.
[3]《云南》.第十六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56页.
[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页.
[5]《国风报》.第十七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41页.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博士)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