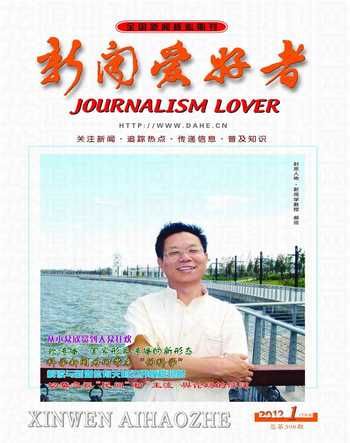庄子、张衡与曹植的“骷髅”系列作品
2012-04-29孟光全
孟光全
古人曾感叹:“死生亦大矣!”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认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关注生死,是人类、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
战国时,中国哲人庄子就思考过这一话题。《庄子·外篇·至乐》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内容十分奇幻:
庄子去楚国,路见一具骷髅(古为髑髅),就问:“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庄子问死者是贪生失理被杀的,是故国灭亡被杀,还是做了坏事愧对家人而自杀?是饿死冻死,还是自然老死?说完,庄子“援髑髅,枕而卧”。夜半时,骷髅出现在庄子梦中,梦中两人对话:骷髅大谈人死后的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死后就再也没有君臣,人人平等,没有一年四季的劳碌,永远与宇宙同在。庄子说愿到“司命”那里,让死者复活,重回亲人身边,骷髅皱着眉头断然拒绝,故事到此结束。
庄子的“髑髅故事”奠定了“髑髅说死亡之乐”这一故事的母题:通过“生之苦”与“死之乐”的对比,来铺陈活着的痛苦艰难,渲染死后之乐。对此我们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写出了道家的生死观,流露出浓厚的悲观厌世情绪。其实早在《诗经》时代,就有这种情绪。《诗经·兔爰》一共三章,每章结尾诗人都哀叹,“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说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前天下太平,自己一出生就遭遇各种痛苦,所以愿死去。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说,“反映很严重的厌世思想,实在是衰世之音”[1]。
另一方面,这故事又深刻揭露了战国中后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与庄子大体同时的孟子就说,战国群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其实,揭露活着的艰难痛苦,意在正视严峻的社会问题,引发对社会的讽刺批判,这才有疗救的希望,这样看,骷髅故事就有了批判现实的力量。清代胡文英说得好,“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总之,对这个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故事,我们要全面来看,不能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这则寓言兼有消极悲观的情调与批判讽刺的力量。
我们再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
庄子曾提出了十分独到、深刻的文艺思想,认为“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战国是乱世,就不能正经八百去谈论,于是就“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用大量虚构的寓言来说理,“寓言”一词也始见于《庄子》一书。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皆空语无事实……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由此可见!
首先,庄子“髑髅故事”想出天外,有奇幻诡谲的想象。作者虚构出简单而奇幻的情节,虚构人与骷髅的对话,而且骷髅会思辨、有情意、能说会道,还有表情神态。
其次,庄子亲自登场亮相,成为故事中一重要人物,这样就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最后,作品成功塑造了庄子、骷髅两个“人物”形象,人物刻画鲜活生动,使用了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神态以及对比刻画等手法。庄子一上场就连发五问,用辞赋的铺陈手法,问得周全,又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骷髅说他是个“辩士”;接着庄子“撽以马捶”、“援髑髅,枕而卧”,尽显其洒脱善辩的风采。作者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神态描写刻画骷髅形象。
庄子“髑髅故事”思想深邃独特,又富于文学性,思想、艺术上都奠定了“髑髅说死亡之乐”故事母题的坚实基石,成为古典文学影响深远的经典名作。
张衡的一生,正好处在东汉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换时期,政治开始腐败,社会开始动荡。汉赋史上,张衡是个十分重要的作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继续写大赋;另一方面,又写充实饱满、富于情韵的抒情小赋,如《归田赋》,从自然到家园,再到丰富充实愉悦的精神世界,层层深化,写想象中的田园之乐。
张衡的《髑髅赋》沿用了庄子髑髅故事母题。[2]
张衡漫游,“顾见髑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就问他是饿死还是客死他乡,生前是智者是愚者,是女是男?死者回答说是“游心方外”的庄周。于是张衡愿主动到神灵那里,让其复活。庄子拒绝,极力诉说死亡之乐:“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风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张衡只好让仆人“假之以缟巾,衾之以玄尘,为之伤涕,酹于路滨”。
我们来比较二作的不同:
首先,从人物关系看。庄子“髑髅故事”中,庄子傲岸洒脱,说话咄咄逼人,是个辩士,尽显其“眼极冷”这一面,和骷髅处于对立面;而张衡作品,人物关系变得和缓起来,张衡亲切善良,富于关怀心、同情心,起初“怅然而问”,结尾“为之伤涕”,掩埋枯骨,这样,作者“自画像”就变得亲切,让人亲近,人间气息大大增加。这深刻反映出东汉中后期,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学更贴近生活。
其次,从结构上看。庄子文章按庄子傲岸发问,骷髅铺叙死亡之乐,再到庄子愿让骷髅复活(其实,这里更多的是诱惑,来试探骷髅话的真假),最后骷髅拒绝复活。张衡作品变为:张衡得知死者是庄子后,立即主动说愿到神灵处,为其祈求复活,然后庄子铺陈死亡之乐,最后增加了含泪掩埋枯骨的情节,这样有助于刻画张衡亲切的形象,也让故事更完整。
再次,从句式上看,两者的差别更大。庄文有一些对偶句,但主要还是自然畅达的散文。而张衡作品,则更多铺陈,完全是辞赋写法:对称性句子多而密,既有“死为休息,生为役劳”两两相对的对偶,更有不少“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的排偶,将对偶与排比合二为一,这样的作品就更显整齐,富于装饰、对称之美,篇幅也就加长了。
另外,张衡加入了写景成分,如晚秋“微风起凉”、骷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渲染了晚秋尤其是骷髅的凄寒,让人生哀闵之心,富于感染力,这也似乎预示着山水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作品还化用典故,如巢许、离朱、尧舜与桀纣等。
曹植《髑髅说》[3],写的是曹植漫游水边,看见块然独居的骷髅,就问是殉国君而死,还是战死疆场?是病死还是自然老死?与庄、张笔下骷髅不同的是,这具骷髅更富于思辨性,大段说理,“夫死之为言归也。归也者,归于道也。道也者,身以无形为主,故能与化推移。阴阳不能更,四节不能亏,是故洞于纤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见其象,听之不闻其声。挹之不冲,满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荣。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逾”。阐述人一死,就能与“道”相伴,而道能自然而然变化,无处不在,能洞察并把握宇宙的各种变化,这样人、道都能永恒。后面的内容情节大体相同,此不赘言。
作者用“说”来命名,恐是基于骷髅大段说理吧!众所周知:魏晋名士注重清谈、思辨,于是有了学术史、文化史上著名的“玄学”,同时,注重思辨的佛教传入中国,玄佛合流,就大大增强了士人抽象理性思辨的能力。因此曹植笔下的骷髅也染上了浓厚的玄学家色彩。
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古,“说”这一文体十分近于辞赋,二者往往是异名同实。曹植的作品一样用了辞赋的传统写法,如注重铺陈渲染,句式多对偶排偶,借对话展开情节等。
纵观汉唐,辞赋一直是文坛主流文体之一,它一身兼诗、文两大文类,广泛吸纳了先秦几乎各种文体的滋养、技巧,而且辞赋所表达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辞赋在表现内容与叙写功能上特别富于包容性。
回到曹作论说玄理上,中古以赋思辨说理并非曹植偶一为之,如论玄学的《意赋》(庾子嵩)、《得意亡言赋》(谢观),论佛理的《浮沤赋》(杨炯)都是典范之作。曹虹认为这类作品,是“思想史与文学史交涉”[4]的产物。
总之,骷髅这一故事母题,从遥远的先秦走到汉魏,从诸子散文到辞赋,蕴涵了国人对生死的沉思,意蕴深邃;文学上有沿有革,文随时变,文学史演进的脉络没有中断,华夏文明就绵延不绝。
今人要做的,就是放远眼光,多方沉思,尽量同情性理解中华文化、文学,进而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文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M].隋树森,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54.
[2]钱钟书.管锥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4:1011~1013.
[3]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60.
[4]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纵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97.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