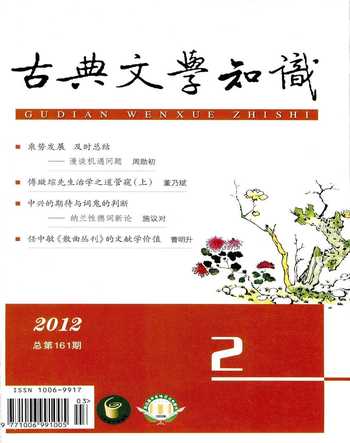陆机《文赋》在韩国
2012-04-29杨焄
杨焄
近人骆鸿凯曾说:“唐以前论文之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废也。”(《文选学》附编二《文选专家研究举例》)将《文赋》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足见陆机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本土,也波及到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国家。在韩国历代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就能发现所受《文赋》影响的种种痕迹。
一、 《文赋》与韩国历代文学创作
早在唐代末年,新罗文人崔致远(857—?)在其作品中就已经多次化用了《文赋》中的辞句。例如,在奉新罗真圣女主之命而撰写的《无染和尚碑铭》中说:“大师于有为浇世,演无为密宗;小臣以有限么才,纪无限景行。弱辕载重,短绠汲深。其或石有异言,龟无善顾。决叵使山辉川媚,反赢得林惭涧愧。”一方面表露对无染和尚的无限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对于由自己来承担撰写碑文之责表示信心不足。其中“山辉川媚”一语即约取自《文赋》中的“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陆机原意指佳句处于文章之中,虽无与其相称者,但仍犹如石中藏玉、水中含珠一样,可以使全篇熠熠生辉。崔致远则借用来赞誉无染和尚德行出众,足以映照世间。另如在《智证和尚碑铭》中,崔致远说到撰写该文:“事譬采花,文难消藁,遂同榛楛勿翦,有惭糠粃在前。”“榛楛勿翦”一语出自《文赋》中的“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陆机原赋中的这两句紧随着“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两句,意谓平庸之句因为映衬着佳句而不致被删除。崔致远借用来谦称自己文辞芜乱,犹如未加修剪的丛生杂木。崔致远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渡海入唐,随后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历官溧水尉、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都统巡官,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才重新返回新罗。或许正是在停留中国的十馀年时间内,接触到了陆机的这篇赋作,从而得以借鉴其辞句。崔致远在韩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屈一指,被尊为“东方文学之祖”。他对于《文赋》的关注,乃至对于其中辞句的借鉴,自然也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其后的韩国文人。
在崔致远之后,韩国历代文人在创作中化用《文赋》辞句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是直接借用陆机的成句或成辞。例如《文赋》正文一开始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韩国文人纷纷将之援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如韩忠(1486—1521)《封建赋》云:“伫中区以玄览兮,观吹万之物理。”沈彦光(1487—1540)《鼓赋》云:“伫中区而玄览,索至理于渺冥。”金义贞(1495—1547)《寰宇赋》云:“伫中区而玄览,收远视于八纮。”虽然各篇内容不一,每位作者却不约而同地在自己赋作的开头借用陆机的原文,随后才引出后面的铺陈描绘。《文赋》在论述各种文辞体式时以“诗缘情而绮靡”发端,自后“诗缘情”一辞也就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术语之一。在韩国文人的作品中也常常可见其踪迹。例如洪彦弼(1476—1549)《次华使赠湖阴韵二首》其一云:“诗缘情性正非奇,乱派馀波更尚词。”洪暹(1504—1585)《送别明仲归觐》云:“诗缘情到无佳句,身为官忙阻别筵。”都用到了“诗缘情”一辞,虽然作者在创作之时未必刻意想要借用《文赋》的成辞,但受到后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有些韩国文人在自己的诗文作品中,有时并不直接借用《文赋》的成句、成辞,而是会对原文略作改动,或加以节略,然后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有时只对部分语句予以改动,而仍然保持原文的意蕴。例如郑弘溟(1582—1650)《次归去来辞》云:“颐情志于载籍,庆赜玄而钩微。”“颐情志于载籍”一句模仿《文赋》中“颐情志于典坟”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有些文人则在改造、借鉴原文之余,对其本意还会有所引申或转变。例如《文赋》云:“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李德寿(1673—1744)《颂己赋》云:“骋艺林而振羽兮,凌学海而扬鬣。笼天地而挫万物兮,盖将齐光耀于日月。”《文赋》原文本是论述作者选材谋篇时的特点,李德寿则加以节取和合并,转而成为对自我才能的赞扬和肯定。某些韩国文人并不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文赋》中的个别辞句,有时还会对其中的大段描写加以括。例如陆机在描绘构思之际想象活动的情状时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接着又强调创作时需要借鉴前人著述,“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然后说明遣词造句时存在或难或易的不同情况,“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这一大段析理真切、形容绝妙、层次分明的文辞就被韩国文人崔演(1503—1549)改编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逐诗魔》云:“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窥蠹简以剽盗,咀六艺之芳润。……沈辞若游鱼衔钩,浮藻似翰鸟缨缴。”崔演用拟人的手法和戏谑的口吻,极言文士耽于诗文创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将《文赋》原文略作修改后,就使之浑然一体地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二、 《文赋》与韩国历代文学评论
韩国文人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也时常会受到《文赋》的影响。韩国学者许世旭在《韩中诗话渊源考》一书中曾提到高丽时期李奎报(1168—1241)的论诗主张和《文赋》之间的关联,随后又列举了朝鲜时代众多诗话类著作中的议论,来与《文赋》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充分说明《文赋》对于韩国历代文学批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这一类内在理路上的隐性影响之外,韩国文人在评论时有时还会直接借用《文赋》里的文辞。在某些场合中,作者会直接说明自己是引用了陆机的意见。例如郑弘溟(1582—1650)《与赵善述论文书》云:“抑又念词家才藻,固非一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者,势有所不免。故昔者坡翁评子由文曰:‘吾弟高处,追配古人,拙处犹愧俗辈。陆士衡亦云:‘或受嗤于拙目。以古准今,若此类何限。而争名者虽好议论,岂亦并与其所长而掩之乎?”作者批评文人相轻的世态,尤其反对掩人所长之举,并征引了中国的相关议论以为佐证。文中所引苏轼之语出自《与子由弟》:“吾弟大节过人,而小事或不经意,正如作诗高处可以追配古人,而失处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点检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随后所引陆机之语则出自《文赋》。苏轼的诗文在韩国历史上备受推崇,早在生前,其文集就已经传入韩国。在高丽朝中期,甚至还出现过文士“专学东坡”的局面。郑弘溟在征引苏轼言论证明自己观点时,连类而及陆机的《文赋》,足见此赋在韩国颇为文人所熟习。
更多的情况下,韩国文人并不加以说明而直接化用《文赋》的辞句。有些时候还沿用陆机原文的意思。例如任叔英(1576—1623)《感旧诗序》云:“缘情动兴,采二仪之菁华;体物成章,飞一篇之炤烂。追陆机之赋,眷恋于遗存;视吴质之书,殷懃于往昔。”“缘情”、“体物”取自《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又如丁范祖(1723—1801)《拙斋洪公遗集序》云:“故其诗缘情设辞,雅俗杂出。而平澹醇质,不失轨法之正,尽可讽也已。”“其诗缘情设辞”一句显然也受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启发。又如权愈《茶山集序》云:“故意不称物,词不逮意,虽浮艳之声,妖冶之色,间发于句字之间,而漂翻而无归。”“意不称物,词不逮意”两句无疑脱胎于《文赋》序中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有的作者在化用《文赋》原文时,对原意会有所引申或改变。例如尹舜举(1596—1668)《睡隐姜公行状》云:“公之文才,得之天赋。自幼少时,已有作者手,沈词怫郁,浮藻联翩。”化用了《文赋》中“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数句,原文本是形容作者措辞时而顺畅、时而艰涩的情形,这里则用以称赞姜氏文学才能出众。又如李万远(1736—1820)《讷堂遗稿序》云:“若讷堂金公,英才逸气,苕发颖竖。”《文赋》原文:“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本是用来比拟突出超群的文句,李万远却转而用来表彰金氏的超迈俗流。另如李晚秀(1752—1820)《书〈竹石枫岳记〉后》云:“然以子瞻之慧,识匡庐之胜,应接不暇,有不识真面之叹。今子七日而周万二千峰,自以为泠然善也。苟使山灵示以杜德机,则子之观,得无近于一瞬而再抚四海乎?”《文赋》原文:“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本是用来形容思维活动的迅疾和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李晚秀文中用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来做比较,言外对于《竹石枫岳记》作者的走马观花之举似不无微讽之意。
三、 《文赋》在韩国文化其他领域中的影响
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文赋》在韩国文化的其他领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丁若镛(1762—1836)在其《中庸讲义补》中曾说:“蔡曰:‘本是七情,今只言喜、怒、哀、乐四者,何也?乐兼爱,哀兼惧,怒兼恶,欲属土而无不在也。又约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今案:七情之目,始见于《礼运》。原是喜、怒、哀、惧,不是喜、怒、哀、乐。班固《白虎通》又以喜、怒、哀、乐、爱、恶,谓之六情。而古今言六情者更多。《诗序》云:‘六情正于中,百物荡于外。《汉书·翼奉传》云:‘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陆机《文赋》云:‘六情底滞,志往神留。何必七情为天定乎?六情、七情之外,亦有愧、悔、怨、恨、懻、忮、恪、慢诸情,岂必七情已乎?经云喜、怒、哀、乐者,略举一二,以概其余。蔡说拘矣。”按《礼记·礼运》云:“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明言有七种不同的情感表现,而《礼记·中庸》却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提及四种情感。后世儒家学者为了弥缝其间的矛盾,不免有各种牵强附会的解说,上文所引蔡氏之说即为其中之一。丁若镛认为古人言及“情”时并无固定不变的数目。《文赋》中的“六情底滞,志往神留”二语本来是描绘文思艰涩的情状的,但丁若镛并不关注其内涵具体所指,而是关注其字面,以此来证成己说,从而强调研读儒家经典不能胶柱鼓瑟。丁若镛在学术上倡导实学,反对儒学者的“空理空谈”,从以上所征引的这段议论即可见其学术视野并不局限在儒家经典之内,对于《文赋》之类诗文评著作也有所关注。
韩国历史上施行科举取士之制,在考试策问时也出现过采摭《文赋》内容进入试题的情况。例如朝鲜正祖李祘(1752—1800)在一道策问中曾提到:“顿挫清壮,《文赋》所称;警诫切劘,东莱有言。则古人之论箴体者,果孰得而孰失欤?”按《文赋》:“箴顿挫而清壮。”清人方廷珪释云:“顿挫,谓不直致其词,详尽事理。”近人徐复观也认为:“顿挫与直率相反。”则“顿挫”当含有措辞委婉之意。而宋代吕祖谦则认为“箴是规讽之文,须有警诫切劘之意”,强调直言其事,以达到规讽警戒的目的。两者彼此扞格,因而引发李祘的疑问,遂令应试者对其间得失予以评骘。
四、 由杜甫《醉歌行》在韩国的接受看《文赋》在韩国的影响
唐代杜甫《醉歌行》云:“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虽然清人何焯认为杜甫此说源于对《文选》李善注所引臧荣绪《晋书》的误读,但在此之前及之后,仍然有不少学者据杜诗来推断《文赋》的创作时间。
杜诗在韩国历史上流传颇广,影响深远。在韩国文人的诗文中也常常可见运用这一典故的。有些是为了悼念早逝的亡者。例如成伣(1439—1504)《祭世通文》云:“缀句权舆于李贺之七岁,作赋发挥于陆机之二十。”按《新唐书》本传谓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作者运用此典,并化用杜诗,旨在突出逝者才能之出众。又如权好文(1532—1587)《金秀才三戒薤曲十四韵》云:“昔闻颜夭争相惜,今见公亡我最哀。天上石麟曾孰送,人间玉树早能培。迢遥艺苑当年志,籍甚声名绝代才。文赋陆机堪自敌,平诗子建可追陪。”按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历数当时作者,逐一予以评论。作者在此处与杜诗之典连用,将对方比作陆机、曹植,惋叹其才能出众却不幸夭亡。另如全湜(1563—1642)有《挽赵棐仲翊》云:“聪明管辂右,文赋陆机前。”管辂精于卜筮,陈寿《三国志》评为“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里与杜诗之典连用,突出逝者的智谋、文采超越管辂、陆机。再如吴始寿(1632—1681)《韩进士宗范挽》云:“修短由来不可期,如君早夭最堪悲。陆机未就文章赋,潘岳先题寡妇辞。”潘岳有《寡妇赋》,收入《文选》卷十六,据李善注云:“寡妇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孤寡之意,故有赋焉。”作者既用杜诗之典感叹死者英年早逝,又用潘赋之典来比况自己赋诗哀悼。
也有借杜诗此典反衬,用以自伤年岁老大。例如崔昌大(1669—1720)《元夜分韵》云:“士衡《文赋》年,我年又加二。奈何愚蒙者,名实或殊异。回顾永伤惭,文理未森邃。如彼未琢玉,冀成清庙器。”感慨自己业已二十二岁,超过陆机创作《文赋》的年纪,但仍然一事无成。当然也有用杜诗此典来赞誉他人的,例如全湜(1563—1642)《示全上舍命龙》云:“科声苏辙后,文赋陆机前。翦拂吾门族,光荣我祖先。”《宋史》本传称苏辙“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第”,诗人将之与杜诗之典合用,意在赞誉对方年少即成就功名、文采斐然,足以光宗耀祖。另如赵(1586—1669)《稣斋先生集后叙》云:“游关东诗,仅逾士衡《文赋》之年,而其老苍奇健,奚谢晩年。”称赞卢守慎(号稣斋)年方二十出头,就已经文章老成,与其晚年作品相较毫无逊色。
以上所述虽然不能直接说明这些韩国文人熟稔陆机的《文赋》,但也可以作为例证,说明《文赋》在韩国文坛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中、韩两国比邻而居,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通过上文所举诸例,不难发现,上起新罗时期,下迄李朝晚期,陆机《文赋》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至其他诸多领域之中,对韩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现代以后,韩国学界对于《文赋》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展开。1985年,金世焕教授率先发表了《〈文赋〉研究——注释一》,可惜这项注译工作最终并未能完成。至2001年,车柱环教授发表了用现代韩语翻译的《文赋》全本,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2010年韩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李揆一又出版了专著《文赋译解》,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中、韩两国的研究成果,对全赋做了极为详尽的注释、翻译和评析。这些成果势必会引导韩国学界更为深入地研究《文赋》,而对于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也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