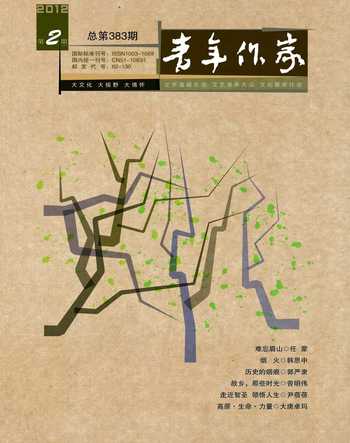田野中的汉灵
2012-04-29白郎
白郎
鲁迅曾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四川,作为汉代文化遗存最丰厚的地方之一,留下的那些当初与亡者有关的绚烂石刻,在今天已成为一笔祖先的赠礼。由此,相隔约两千年的两个时代在一个甬道上达成了美的融合。
汉阙,追寻谢阁兰的步履
“雄健而人性”,这是维克多·谢阁兰对汉代气脉的感言。1914年,这位出生于法国海滨小城布雷斯特的才子带领一支考古队考察了四川汉阙。那是晚春时节,处处青翠,黄花烂漫,万物氤氲着蓬勃的吉气,谢阁兰骑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穿行在异域的诗情中。他曾向妻子宣称自己“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现在,这位秘密的“神秘主义者”正从包裹着重重光影的真实中苏醒过来,将其撞醒的是神秘主义之物汉代石阙——中国留存于地表之上时代最早的建筑物。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四川汉阙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谢阁兰寻访了十几个汉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首次发现,考察成果后来被收入《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当如此多约两千年前的中国建筑被揭示出来时,欧洲学界不禁吃了一惊。
谢阁兰到达著名的高颐阙的时间是1914年6月25日前后。在一大片玉米地旁的萋萋荒草间,高古雍容的石阙带给他一种欢愉的震颤——有孔的高颐碑上端缠绕着“汉代体范最美之螭龙”,两头长着羽翼的神兽腰部高高耸起,蹿入他精神高地的幻象之巅。谢阁兰之前,一个叫“阿隆”的法国人曾实地来看过高颐阙。之后,1939年深秋,梁思成和刘敦桢对高颐阙进行了实地考察,绘制了线描图,并借助高架木梯爬上阙顶进行细部测量。从他们拍的现场照片可看出,阙顶上长出的灌木已有一米多高。
高颐阙位于距雅安东郊八公里的姚桥乡汉碑村九组,当地人把这里叫“石马社”。2011年4月17日午后,我来到这里时,春光正顺着黛青色的金凤山湿漉漉地飘过来。早先的玉米地早已围成了专门用做保护汉阙的仿古院子,一进门就能看到两头长着双翼的汉代神兽张着巨口守在汉阙外,似狮非狮,似虎非虎,气韵万千,身上到处是斑白的苔藓。守阙人是四十五岁的赵文平,他已在这里守了十年,接的是父亲的班;其父守了十多年。
高颐阙的东、西两阙相距十三点六米。东阙现仅存主阙的阙身,由五块红砂石垒成,顶盖系后来配做。西阙的主阙、耳阙基本保存完整(除了耳阙的脊饰有所残损),是全国现存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的一尊,为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其主阙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四部分构成,共有十三层石材,通高五百九十厘米;耳阙共有六层石材,通高二百九十四厘米;阙体密布着柱、斗、拱,四隅斜伸出俨若顽童的角神,四面雕饰着各种线刻图、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像,题材有出行图、献礼图、鼓琴图、季札挂剑图、西王母图、鸟兽率舞图等等;阙盖造型为重檐庑殿顶,下方雕有枋头二十四双,最顶端脊饰正中栖着一只衔有绶带的雄鹰,头朝北——汉阙专家徐文彬认为应该头朝南才对,是后人维修时把方向搞错了。1940年,为保护西阙,西康省修建了一个保护亭。“文革”后期,这个亭子被大风刮倒。
高颐,字贯方,曾任益州太守,颇有政名,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此人看来是个著名的孝子,距其墓阙不远处原有一个高孝廉祠,高颐碑就是后人从那里搬迁过来的。
一群在附近做工的汉碑村乡民走了进来。向他们了解以前高颐阙的情况时,长着一头卷发的壮汉赵文平告诉我,他们小时候这个汉阙还没专人看护,放学后他和小伙伴常爬到阙顶上玩耍,有时候跷着腿躺在上面睡觉,身子仿佛浮在半空中,阳光直直地射下来,很是舒服。那时候阙身间有个很大的缝隙,要爬上去比较容易。荒草很深,石阙里藏着一些蛇,不时会冒出来,因此,胆小的孩子是不敢爬这个石阙的。赵文平指着旁边精瘦的陈福全说,他长得像猴子,小时候爬得可快了,胆子又大,经常在石阙上捉蛇来耍。
和看护人陈嘉祥师傅聊得很投缘。黄昏时,他破例允许我们几个特殊的来访者在院子里吃晚餐,我们把小条桌和条凳从厨房里抬出来,放上几碟从远处餐馆里端来的菜,慢慢吃着。微蓝的天幕深藏着幽蓝的迷光,高高地淌下来,流到古朴富丽的高颐阙上,使阙身的红砂石浮现出蔷薇色的暗光。时光如此静好,静得似乎听得见一朵野花在神道遗址上绽放的声音。不久,一轮月渐渐升上来。好大一轮明月,它和约两千年前的建筑已曼妙地融合于一次共同的涌动中。
阙,《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阙,门观也。”《诗经·郑风》中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都邑》中说:“阙者,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阙是汉代遍布各地的威仪性建筑和纪念性建筑,分为城阙、宫阙、庙阙、墓阙几种。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东阙、北阙以及建章宫的凤阙、圆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阙,传说风阙原高二十余丈。这些巨阙除凤阙尚有夯土残址外,都已湮灭。中国现在遗存下来的三十个阙,都属于墓阙或庙阙。这三十个阙中,河南有四处,山东有三处,北京有一处,其余都在四川盆地,主要分布在渠县、梓潼、忠县、绵阳、德阳、雅安、芦山、仁寿等地;其中时代最早的梓潼李业阙(建于公元36年),许多专家认为并不是阙;发现时间最晚的,是2001年出土于忠县乌杨镇的乌杨阙。
除忠县的丁房阙有可能是巴王庙前的庙阙外,四川现存的汉阙都是墓阙。墓阙也叫“神道阙”,在汉代,一般情形下只有官阶在两干石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墓前立阙。四川汉阙大多是两汉时宫殿前木结构阙的模拟物,以准确的比例雕勒出当时木结构建筑中各种构件的形态。
四川汉阙的风格主要有繁复沉雄和简约清逸两种,前者的代表是高颐阙和绵阳的平阳府君阙,后者的代表是渠县的冯焕阙和沈府君阙。平阳府君阙是双阙的主阙、耳阙都保留完整的唯一汉阙。忠县丁房阙的形制颇有特色,与画像石、画像砖上众多的汉阙刻像极为接近。新都弥牟镇的王稚子双阙,是历史上著名的汉阙,始建于公元105年。阙身上的隶书气韵精简,法度劲古,深受历代文士推崇,宋代拓本更是无比珍贵。清代初年,到过新都的王士祯在《蜀道驿程记》中说:“王稚子阙,下方上锐,垒石如累棋。其颠如盖覆之,望之若率堵坡(塔)状。垒石凡五层,二层刻人物,三层象、虎、海马,五层狮子也。”可见当时阙体保存尚好。可惜不久后一阙倒塌、一阙严重裂开,谢阁兰前往新都考察时,在路边的一个寻常屋子内,找到一个砖龛,里面放着一截阙身上有文字的残体,屋子背后放着几块阙石(这些东西在“文革”中尽数被毁)。
从全国为数最多的汉阙遗存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繁多的汉阙图像,可知汉代时汉阙在四川是相当多的。据《华阳国志·蜀志》,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秦灭蜀后,张仪筑成都城时修造了城阙;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成都建了十八个城门,周围各地纷纷仿效,“于是郡县多城观矣”。秦、汉之际,全国战乱频仍;而富庶的四川则未受破坏,经济文教盛极一时。当时成都是人口仅次长安的大都会。以公元2年为例,长安人口为八万八百户,而成都是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户,所以《华阳国志》描绘汉代四川的风尚是:“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厢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所谓“染秦化故也”,指的是沾染了长安一带的风气——尚奢华尚厚葬。造石阙不但费资耗时,而且需要艺术品藻,它在四川大量出现正是“尚奢华尚厚葬”的一种具体呈示。另外,对于墓阙来说,本地固有的灵巫传统也是一个因素。根据这种传统中的灵魂观,三星堆时代的蜀人相信灵魂借助通天神树可以登天;到汉代,通天神树更多地衍化为了“天门”。“天门”的具体形态就是各种阙,往往有一只美丽的朱雀歇在上面。四川出土了全国最多的“天门”,充分说明蜀人在那个时代的灵性指向。
谢阁兰的考古队是在1914年4月21日抵达渠县的,旋即对六处七尊汉阙进行了仔细考察。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看出,谢阁兰的马队在崎岖的古驿道上行进着,长时间的野外之旅使他的胡子有些零乱,但他锐利的眼神在静穆中流露出淡淡雄心。这位内心将一切视作泡影的法国人似乎正站在人与神之间的边界上,他要用自己的一次冲锋,在时间深处找到被人们忽略已久的一种东方灵力。
2011年5月21日,我追寻谢阁兰九十七年前的足迹来到“汉阙之乡”渠县的土溪乡。细雨迷蒙,滚滚绿树与云气四合。坡地上不时能看到墓茔,一座连着一座,距生者的屋舍很近。当一个乡民荷锄从墓旁走过时,我感到生与死被裹挟在某种隐在的链条中。生,是死的阳面;而死,是生的阴面。在被当地人叫做“石厂湾”的王家坪,我见到了王家坪无铭阙。阙体上布满了各种神气活现的图案,其中最出名的是荆轲刺秦图。这个汉阙被围在围墙中。除了蒲家湾无铭阙,渠县的汉阙近年来都被围了起来进行专门保护。1914年时,这个被水田环抱着的汉阙已有所倾斜,谢阁兰很担心它不久后便会倒塌。如今,六十六岁的当地人李伟东告诉我,在他小时候,人们利用这个阙搭了个茅厕,保护是后来的事。渠县文博馆的专家肖仁杰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山崖说:石厂湾准确的位置就在那儿,到处是红砂石,汉代时很可能是汉阙的集中制作地,近年陆续发现了当年制作汉阙时遗留下来的石质构件。谢阁兰曾在王家坪的水田里发现三尊汉代神兽,头部都已失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四川红极一时的军阀杨森命人把这几尊神兽搬走。因太重,民工们只搬到了冯焕阙旁;然后神兽被当地村民埋了起来,直到2005年时才挖了两尊出来。第二天,我在渠县文博馆看到了这两尊长着羽翼的神兽,其中的一尊有尾巴。此类汉代神兽近来我看到了十余尊,这是唯一留有尾巴的。
著名的冯焕阙在土溪镇赵家村,因村东和村西的两个无铭阙,这个村已改名为“汉阙村”。一村三汉阙,的确天下无双。冯焕阙外,一个农夫牵着头牛慢慢离去,流动的牛背上浮着从汉阙飘下来的一点幽情。冯焕阙立于公元121年,原为双阙,现只存东阙;阙身由整块砂石制成;阙楼雕饰典雅,下部布满枋子和浅浮雕方胜纹图案,上部四周雕刻斗拱,两侧为曲拱;阙顶仿双层檐,檐石刻华丽筒瓦,勾头雕勒葵鳞瓣纹饰,可惜的是最高处的脊饰已失去。冯焕阙整体显得简练入神,朴素归真,敛含着典型的汉代风韵。谢阁兰赞其为“绝优美之物”,梁思成称它“曼约寡俦,为汉阙中唯一逸品”。阙身上用八分书分两排阴刻:“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这二十个字在书写上兼具汉隶石刻与简牍之妙,充溢着率真与灵性,左掠右磔,极尽飘逸之态,被许多人视为蜀派汉隶的典范。曾在土溪镇工作过多年的蒲鲸全告诉我,前些年常有日本人来参观汉阙。他记得曾经有两位七十多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来考察冯焕阙,被深深感动,竟跪倒在阙前哭泣不止。
汉阙,是汉风的凝结之物,是汉风本身,它让后人深切感受到汉代文化贯穿着的雄勃朝气和充沛威力——即使是在造墓艺术中,亦没有死丧消沉之气。当谢阁兰感慨“伟大的汉,所有朝代中最中国的一个”,他的话外音是此后中国文化广受以佛教为主的外来文化的浸染,生出了万千变化,而汉阙恰是佛教文化传入前的纯粹之物。在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二十九龛凿于南北朝时期(约在该时期中的公元531年)的小佛龛。仔细想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示现了汉文化“纯粹风范”的某种消殒。
死是另一个佛罗伦萨
芦山县城南一点五公里处,在青衣江青灰色的暮霭中,唐国富打开了王晖石棺所在院落的铁门。他戏称自己是“王晖石棺的守灵人”。2004年到2008年,他在这里做了四年多看护人;当上县博物馆馆长后,没事时仍会每天来两次,上午呆一小时,下午呆一小时。从博物馆到这里,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这已成为唐国富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他不来就感觉不舒服。他说,“在这里,找得到与世无争的感觉。只有我,才能每天静静地欣赏这尊石棺。上面的‘S线太妙了。我没文凭,全靠感悟,这尊石棺给了我很多启示。”唐国富在这里练习《曹全碑》《张迁碑》和《张黑女志》,他指着一摞习作和一堆墨汁瓶说:“这几年,每年在这里都会用掉二十八瓶墨汁。”
发掘于1941年的王晖石棺摆放在高处四面有飞檐的瓦亭里,全长二点五米,宽一点零一米,高零点八三米。棺体及棺盖分别用整块红砂石雕造,刻有五幅高浮雕图像;棺首为东汉时蜀地流行的半开门图像,右门半掩,一个衣带飘飘、腿胫上有鳞片的仙童探身作迎迓状,门上狞厉的长着双翼的辅首(饕餮)嘴里衔着门环;棺身上,一侧是长着双翅和腹鳞的修长螭虎,虎头之情状无邪如孩童,另一侧是长着背鳍和腹鳞的虬龙;石棺后端刻两尾相交、两首欲吻的蛇龟玄武图。这是惊世骇俗的天成之作。一种神秘的绚烂,在极静极动的大美中飘荡,浑朴瑰伟,元气充塞。自由曼妙的线条形成的无限力量,使万斤石棺看上去似在凌空飞升。这座凿成于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的石棺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建安风骨”。惊叹之余,我问唐国富是啥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王晖石棺
的;他答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知青”的时候,有天见一个老师在做王晖石棺的拓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芦山在蜀汉时曾由姜维镇守,唐国富就出生在姜维庙里,他和哥哥唐国臣是双胞胎。庙前有对雄沉的汉代神兽(现是雅安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小时候他和哥哥常常各自站在一尊神兽下面,喊一声“预备起”,然后比赛谁爬得更快。“我是骑着汉代的神兽长大的呀,所以和汉代有缘!”唐国富笑着说。天色暗下来,夕光变得朦胧,唐国富点燃了根蜡烛。烛光中,我想起了他开始时说的“王晖石棺的守灵人”那句话。
王晖石棺的图案,显然主要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个仙童是朱雀的变体。在四川汉代石刻上,石棺棺首上的半开门象征着重生,是“天门”的一种隐喻。在汉代的宇宙观中,天、地、人是本自一体不可分割的,人们顺从于天地施加给他们的命运,同时也把各种自身行为纳入到天地的自然结构中。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组成的“四灵”,既是天上掌管二十八星宿的神灵,也是大地上的四方方位神,同时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人们相信死亡仅仅意味着肉身的消亡,而灵魂会以另一种状态继续它的“罗曼蒂克”之旅。所以,作为“天门”的世俗化介质,墓阙上面大都雕刻着“四灵”图案(如渠县的七尊汉阙),这不仅仅是作为镇墓辟邪之用,也是为了护佑亡灵重生的仙途。
在四川博物院汉代石刻馆,我见到了另外两具出土于郫县新胜的精美绝伦的石棺。1973年前后,这个地方接连出土了六具汉代石棺。棺身由整块石头凿空而成,在纷呈的祥瑞中,刻着宴饮舞乐、渔猎采莲、车马出行、角抵擒虎、日月星辰的图案,掌管着长生不死之药的仙界领袖坐在龙虎座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对吻交尾托举着日月,一使者双手捧盾站在双阙组成的“天门”中央恭迎墓主人的到来。西王母在汉代四川受到了比其他地方更为热烈的崇拜,她呵出的仙气令这片土地上的子民陷入迷醉。在对永生的渴盼中,人们祈祷自己的灵魂能成为仙界中的一员——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相忘以生,无所穷尽。阴阳交合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化生万物,是吉祥的创生母源,因而是灵魂重要的庇护神,在各种画像石、画像砖上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汉代画像石通常刻画在汉代石棺、墓阙、碑石、祠堂、摩崖、墓壁砖石上。画像砖是集雕刻和绘画为一体的模印砖,出现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专为装饰墓室而用。1881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入川时,一块出土于新繁的吉语砖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用篆字刻着“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王懿荣“诧为异宝”,遂将其收藏。对画像砖的关注由此开始。1911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将四川一匹西王母画像砖偷运至伦敦,至今仍被列为大英博物馆藏品。据统计,目前全国收集四川汉代画像砖有三百多种、铭文砖有一百多种。在四川博物院汉代石刻馆,可看到情态众多的画像砖,题材有双凤、羽人、骑从、宴乐、锱车、轺车、渔猎、燕集、酒肆、乐舞、野合、习射、百戏、迎谒等等。生活在秘密的吉光中重新复活了!在传神的鲜活和真淳的热爱中,四蹄腾空的奔马大口喘着气,人物衣冠萧疏欲动,几乎可以听到活泼的古人在春野里摊开的声音。
四川发现的画像石裸体像、画像砖裸体像很多,主要是秘戏图、野合图等,有些仙境里的仙人也一派天然地裸着身子;甚至像高颐阙这样庄严的纪念物上,也有几个活泼嬉笑的全裸角神,性器官相当突出。同时代的中原很少发现此类图像。这一时期的四川画像中恰恰看不到后世浓墨重彩推出的烈妇。这说明了文化地区性的自由度,也说明儒家伦理尚未占领川人的精神阵地。在四川考察时,这种犷直之风引起了谢阁兰的注意,他看到一头长身的石虎:“柔韧的脊背弯成弓形,强健的肌肉紧绷着,阳物勃勃于旺盛的性力中:真实,总是充满自信。”
四川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比其他地方的更率性,更具有生活的醉意,主要题材可归结为长生升仙、生活情态、祈愿求吉、驱鬼镇墓四类,其中长生升仙是轴心。这些遥远的浪漫派造像,让我想起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那句意味深长的诗句:“死是另一个佛罗伦萨。”汉代人对死亡的认识与现在全然不同,他们坚信人与世界的同源性,这种同源性意味着世界的内部有着神秘的“永恒灵力”,该“永恒灵力”也贯穿了每个人,因而,死是生的尽头,死又是重生的开始——就像他们所喜欢的蝉,羽化是很自然的过程。墓葬地于是成了一个“生”与“重生”之间的中间地带,里面遍浮热烈的吉祥。
汉代人的生死观,让人想起洛夫乔伊说的那句话——“‘彼世,和我们所熟知的‘此世一样,依然是一个由变动、感性、多元与尘缘所构成的共同世界。所不同的只是尘世中的苦略去了,乐则提升了,以补偿人在生前所遭受的种种挫折罢了。如果人们所向往的‘彼世是这样,那么他本质上恰恰是对‘此世依恋的一种最极端的方式。”
画像石和画像砖细微地示现了汉代人死后的彼世镜像。正如古老的《礼记·郊特牲》说的“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按照汉代人普遍流行的信仰,灵魂是由魂和魄构成的。人死之后,亲人会登上屋顶,用死者的衣服为他招魂举行复礼,目的是“招魂复魄”。招魂不成则表明魂与魄已分离,生命已到尽头,于是用染成红色的裹尸布裹住尸体。死者的魂气早早离开,而形魄还在尸体当中,所以竭力保护尸体和善待它是重要的事情。于是人们流行用玉塞住死者的嘴巴,并且“事死如生”,大行厚葬之风。在四川,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崖墓,动辄成百上千,古人之所以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营造被后世称作“蛮洞”的原因,就在于认为崖墓更适合长久地保留形魄。使用仙气氤氲的雕镂石棺也是同样道理。正所谓“凿崖石以室兮,托高阳以养仙”。在彼世的新天地,亡灵延续着它的生活,尸体终将会腐化,而灵性将在后人的祭祀中踏上一条升仙之路。
在成都西郊青杆村的朱成石刻艺术博物馆,当我见到朱成时,水色漫开的空明中,他正于一棵麻柳树下静静地享受一杯普洱。他告诉我,最近正在组织人手从成都以前的所有老街道上找老砖,每条街找一块。“过去的泥、石、砖都是当代城市的殉葬物”,他要把这些殉葬物代表的“集体记忆”集中起来后做件有意思的作品。
聊起汉代图像,他带我去看他的收藏——几百件汉代陶房占满了一个大屋子,在幽光中像一大堆玩具。单檐式、重檐式、干栏式、悬山式……式样各不相同。这些陶房大都简约厚实,朴拙自然,有些分上下多层,可拆卸组合。屋顶瓦饰分四阿、攒尖、硬山、歇山、悬山五种。楼台间或站有不少陶俑,乐舞杂陈,弥散着醇酽的市井味。朱成说:“文化的基因都保存在建筑里,一代又一代。这些来自地下的建筑模式保留了当初的世俗生活,这是民俗化的世俗生活。”
朱成收藏了大量的四川古代石刻艺术品,各个时期的画像石达数千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汉代的。在他看来,四川画像石的高峰就在汉代,后世很少有这么浓郁的品味了。这些画像石密密麻麻地放置在库房里,整齐排开,一件连着一件。这么多天趣横陈的浑朴之作,让我感到汉代是一个跳动着童心的时代。几根彩色的绳子把一匹尾巴蓬起的陶马吊置起来。陶马身形英迈,臀部浑圆,优雅的步幅爆发出不可遏制的热情。朱成指着它说:“这是一匹汉代四川的冥马,供墓主的灵魂享用。骑着它,生死之路畅通无阻。”问及对库房内这些汉代四川石刻的看法,朱成说:“今天,如何把传统建筑精神延续下去,已成为一道难题。在汉代,四川的南方调性十足,很民间很自由。蜀人的想象力那时没怎么受到章法的限制,匠气很少。那是一个欢乐时代,蜀人显得很自信、生活艺术化。那时的石刻图像深朴沉雄,没受到外来符号的影响。”
连日来,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四川历史上的骄阳时代——事实上,我只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几束光和几瓢气息,心中却更加苍茫混沌。借着一些遗留下来的实物、图像和线条,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东方式生活,海市蜃楼般从遍地的马赛克大楼上掠过。那满是异趣的瑰丽,令我倍感历史的本质是神秘。当我站在三面被渠江环绕的汉代遗址城坝时,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乡民牵着头牛在水田里劳作,俨如汉代的农夫。三口汉代时的陶井已被使用了约两千年,现在仍在使用。不远处的农舍镶着些菱形纹、车轮纹汉砖,连猪圈上也镶有不少汉砖。一头白色的小猪用嘴抵住汉砖,发出几声怪叫。潇潇细雨中,天和地像上唇和下唇贴在一起,万象显得恍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