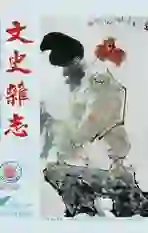《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2012-04-29蒙默
蒙默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髣(当为“髻”之讹),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其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纪》早已亡佚,引者文字异同至夥,上引二节虽大致相同,而“左言”、“左衽”之差则颇大,盖“左言”为语言之异,而“左衽”则服饰之异,虽仅一字之差而其意义则相去甚远。然旧日辑本如洪颐煊、严可均皆清世名家,则仅著“左衽”而舍“左言”,[1]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又仅著“左言”而舍“左衽”;以后王文才先生《蜀志类钞》虽两者并录,而不着可否之辞,其是其非,不可不辩;其余诸端皆姑置勿论。
经检诸书,其引《本纪》之文,作“左言”者远较“左衽”为多:
《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侮食来王,左言入侍”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名曰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此引最与刘渊林引相合。《文选》左思《魏都赋》“或魋髻而左言”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记》:“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此引与上显为同出一本而文稍省易,亦古人引书之旧习;其改作“左语”者,盖以“左语”释“左言”故。又案《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鱼凫治导江,逮蒱泽、俾明时,人民椎结左言,不知文字。”此虽未明言引自《本纪》,然自上下文审之,则亦显据《本纪》为说。益明《本纪》“左言”之说绝非误说。然《御览》引《本纪》之作“左衽”虽仅一处,当亦非向壁虚造。检《华阳国志·序志》言:
《本纪》既已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又言蜀椎髻左衽,不知文书,文翁始知书学。
是常璩之世(晋时)已有“蜀椎髻左衽”之说,唯常氏所见盖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之言,而显非扬氏《本纪》之说,是唐宋之传《本纪》者、清世之辑《本纪》者竟多舍“左言”而取“左衽”,诚皆鲁莽之甚者也。
“左言”者何?《文选·六臣注》载唐吕向曰:“侮食、左言,蛮夷国也。”此为释“左言”之最古者。谓之“蛮夷国”者,盖以蛮夷之饮食语言皆与华夏不同故也。且“左”字于古汉语中有卑、下之意。古代华夏之人歧视蛮夷,称之为“蛮左”,为六朝人常用语辞,如《水经·江水注》言:“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陈书·欧阳传》:“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陈书·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而王朝亦以招抚蛮夷所建立之郡县名为“左郡”、“左县”,如《宋书·州郡志》载:南豫州晋熙郡太湖左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南城左郡:“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边城左郡:“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南朝所立左郡、左县颇多,虽不必一一载其皆因“蛮民”以立,而其地之有蛮左则皆可考知也。蛮夷所居郡县既可名左郡左县,则蛮夷所操语言称为左言、左语,固亦其宜;故扬雄、左思、王元长并以写入篇翰,唐世王维犹有“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2]之句,故《辞源》释“左言”、“左语”为外国、外族语言,实为确解。蜀人“左言”为秦灭蜀前之蜀人;本非华夏之族,《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为实录。近世蜀地先秦出土文物并皆可证。唐卢求《成都记·序》言:秦灭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3]。秦言为华夏语之一支,是蜀在秦灭蜀前之为左言,唐人犹及知之。而自秦灭蜀后,秦、楚大量移民巴蜀,而蜀王又率其族人南迁,故《华阳国志》言蜀地“俗染秦化”,而巴地则“其人半楚”(见《蜀志》、《巴志》),及至两汉之世,巴蜀文化则几已与华夏不别矣。
巴蜀文化至两汉虽已丕变,然犹有古蜀之遗存焉。如出土文物两汉之画像砖石,其人物发式多作椎髻,当即“蜀人椎髻”之残留;又许慎《说文》、扬雄《方言》亦犹可见三数巴蜀梁益之异读语文,或亦蜀人“左言”之残余,唯皆单言支字而无连缀成词语者,难以考见其语言系属也。至《本纪》所载之蜀王名称无疑亦皆蜀之左言,故多不可以汉字之义释之。而近日学者或有以汉字形义相解者,宜其多扞格而难通也。如蚕丛,或以为发明养蚕之祖,夫“蚕丛始居岷山石室”,岷山在今阿坝州,汉为冉駹夷所居,据《后汉书·冉駹夷传》:其地“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此岂宜于桑蚕之土!若以“蚕丛”为汉字记音之左言,本与汉字之字义不涉,而以少数民族相近之音读校核,则似犹有可以疏释者。余尝以“蚕丛”、“冉駹”二词相校,案“冉”古音在谈部,蚕古音在侵部,两部古多通用,而“丛”、“駹”二字古音皆在东部,古本相通。是蚕丛、冉駹音读本通。(参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于岷山石室中”,《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应劭曰:“蜀郡岷山,本冉駹是也。”是蚕丛、冉駹住地亦同。《冉駹传》言“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亦与蚕丛“居石室中”之说合。据《太平寰宇记》,唐宋茂州“本冉駹之国。”[4]此茂州即今阿坝州之茂县等地,近世以来于茂县境内发掘数以百计之石棺葬,学者多以为即冉駹夷之墓葬,其时代略当战国西汉间。[5]此与《华阳国志·蜀志》言:“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相合。是蚕丛与冉駹之葬式同为石棺而其时代又皆在战国之际。(案春秋时唯周称王,楚自谓“我蚕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亦自称王;其他诸侯之称王者皆在战国时,周失纪纲,此为最甚。)近世茂汶地区所居为羌人,羌人称石棺葬非其先人之物,而为“戈基呷钵”(戈人墓葬)。相传戈基为纵目人。[6]此与《华阳国志》蚕丛纵目之说亦合。综上所述,故余以为蜀王蚕丛盖即冉駹之异写,亦犹开明王南迁印支而为安阳王,皆一音之转也。[7]或以常氏所言有异于《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之说(《蜀都赋》刘渊林注引),然据上所述,孰为可信,固不待辩也。
又如杜宇,校以南方民族传说,则亦有颇可申说者。《本纪》载古蜀王之名,或有杜宇则无蒲泽,或有蒲泽则无杜宇。[8]此蒲泽与杜宇之关系如何,仅据现存《本纪》佚文,不可得解。《华阳国志》言: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是杜宇之即蒲卑,犹鳖灵之即开明,一为人名,一为国名(或王朝名),故《本纪》之不同时并列也。然无论杜宇抑或蒲卑,并皆民族语之汉字记音,不可据汉义为释也。《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本纪》言:“朱提有男子杜宇,自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作“从天而降”,《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作“从天堕,止朱提”,其义并同。从天下降,显为神话。然此神话与贵州仡佬族传说祖先系从天庭而下之说相同。[9]仡佬祖先来到地上开荒辟草耕种田地,其功绩受到各族人民崇敬。有些民族尚有祭祀仡佬祖先之俗,[10]亦与《华阳国志》所言:“杜宇教民务农,……巴地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之俗相合。杜宇所自起之朱提,亦为一民族语地名。古朱提今云南昭通,据今可考者论之,其地自古即为濮僚民族所居。作于魏晋间之《永昌郡传》载:“朱提郡治朱提县,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11]是其地当有僰(濮)人;元李京《云南志略》载:“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12]《皇清职贡图》亦言昭通有土僚。朱提于唐宋后虽为彝族先民乌蒙部所据,彝人称其地为“濮窝”,即濮人所居之意。杜宇既起自濮人所居之地,宜其亦为濮人。“濮”为仡佬族之古称,至今贵州仡佬族某些支系自称中犹冠以“濮”音,如濮仡佬、濮偶、濮佬、濮告、濮尔等皆是。[13]杜宇国号蒲泽,蒲濮同音,蒲泽之名称格式亦与濮仡佬、濮偶等略同,而其祖先传说又与濮僚相合,因此,余颇以杜宇宜亦古濮人之一支,起于朱提而称王于成都平原。于此犹有可论者,先君子《巴蜀史的问题》尝考“蒲泽”当从常志作“蒲卑”为是。[14]盖杜宇始治郫邑,郫原何名,已不可考,以杜宇之国名蒲卑,蒲为族称,而地遂膺卑名;唯后世汉字孳乳,其为邑名者多增邑旁,卑遂写作郫,犹“丘”字后世多作“邱”,此为汉字常例,固无不可。后世不明“蒲卑”与“郫邑”之关系,遂乃讹卑为泽。然无论作卑、作泽,皆为以汉字记夷音,其义则不可晓,故后世字书释此郫字于地名水名外别无他解,而此字竟为生僻字。然此字虽释读为难,而郫邑之为蜀中古都则不可诬也。《本纪》言“望帝积百余岁委国授鳖灵”,“鳖灵即位号曰开明”。[15]《路史·余论》谓“鳖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案开明亡于秦惠王后元九年,[16]为公元前316年,则鳖灵即位略当公元前666年;而杜宇王蜀则略当公元前800年左右,时值西周宣幽之世,是郫之为蜀中古都略在3000年左右,较成都之为蜀都犹早四五百年,噫嘘,连续存在3000年之古都,是于海内实罕其匹!然而世之为政者竟有人因此“郫”字难于解读而拟废弃之者,此实欷歔可叹。试问“沃尔玛”、“麦当劳”、“伊藤”等名招其可以汉义解读乎?然群众固趋之若鹜。而此辈口中犹高唱尊重、保护历史文化,岂非梦呓乎?实令人忍俊不禁也。
《本纪》又言蜀开明之首为荆人鳖灵,然亦有引作鳖令者,如《事类赋》卷六、《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路史·余论》亦作鳖令。灵、令二字本音近相通,因有学者以汉义为释,遂以此“令”字为令长之令;而《汉书·地理志》牂柯郡又适有鄨县,于是遂生鳖灵为楚鄨县县令之说,鄨令北上溯江至蜀,为杜宇之相,治洪水,后遂受禅为蜀王。[17]案汉牂柯鄨县为今贵州之遵义,处贵州省中部偏北;而楚都郢,即《楚世家》“文王始都郢”之“郢”,系今湖北省之江陵,周成王始封楚熊绎地,在今湖北之枝江。(参宋翔凤《过庭录》卷九)鄨与郢都相去甚远,且有武陵山区相隔,唯有二路可通:一为自楚溯长江入巴,再溯乌江而上;一为自楚南渡洞庭,再溯沅江由黔东陆行至鄨。此二路亦即俗传楚将庄王滇之二路,然时已当战国晚期。[18]而以鳖灵当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国实不能有鄨地而置县令。上已言鳖灵为蜀王略当公元前666年,则其在鄨为时更早,而楚君之与鳖灵同时者略当楚武王、文王、堵敖之世,约为公元前740年—前672年,其时楚虽始大,而其疆域尚非辽阔,《左传》载沈尹戌言:楚“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古“方千里为圻”[19]。言楚之国土其时尚未及方千里也。廪君之巴,春秋时尚据有清江流域,至战国始为楚所灭而为楚之巫郡;[20]而庸国在春秋前期尚据有今鄂西北之竹山南至三峡奉节等地,至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灭庸,而庸地归巴,巴益强大,其后与蜀国联军攻取楚兹方之地(今湖北松滋),时在战国楚肃王四年。[21]是春秋之时楚不能溯长江、乌江而有鄨地也。自南路言之,楚之南为洞庭、彭蠡,其时为三苗后裔之国,至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吴起相悼王略在公元前382年前后,已是战国中期。[22]此时楚始有洞庭之地,是春秋时期楚亦不能南涉洞庭溯沅江而有鄨地也。楚于春秋时期尚未能有鄨地,又何能任命鄨县县令!且郡县制虽已起自春秋,然晋之县官为县大夫,楚之县官为县尹、县公,秦、齐县官固名县令,然已在战国时期。[23]是春秋时期楚虽已有县制之设,然绝无县令之官,而自鳖灵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实不能拥有鄨县之地,皆明鳖灵确不能为楚之鄨令。此不可信据说法之出台,实乃为以汉义释民族语言之所误也。
蜀中左言地名之可言说者尚有“湔山”。《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言:鱼凫“猎至湔山,便仙去。”此湔山或作“煎”(《古文苑》王褒《僮约》及章樵注),又或作“湔”(《尚书·禹贡·正义》引郭璞《尔雅音义》),皆为同音异写。此湔山即玉垒山,章樵已于《古文苑·注》中数言之也,盖湔为民族语名而玉垒则华夏语名也。此湔山北起茂汶,南至灌口,为江水、湔水之分水岭,后世亦称东岷。[24]湔水、湔县、湔塴、湔氐等名皆因此湔山而得名。《汉志》出玉垒之湔水,盖在玉垒东侧,今彭州之湔江是也。湔塴之名盖因湔山,晋刘渊林注《蜀都赋》云:“李冰于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灌溉平地”,言之甚明也。郦道元盖仅知湔之为水而不知其源在玉垒东,更不知湔堰之名缘于湔山,故在《江水注》中误以湔水在都安以上入江,江、湔互受通称,都江大堰遂得湔堰、湔塴之名,而不悟此显与《汉志》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之文不会。而杨守敬之流,不审道元之为误说,又从而为之辞,于《江水疏》中妄以“今灌县北有白沙河,疑即湔水”,造为“湔水导源玉垒,湍流赴江(在灌县西),又自江分派,乃得为湔水也(都江大堰为湔水所分,故又谓之湔堰。湔水又自灌分流,东径崇宁县、彭县为青白江,又径新繁、新都、金堂,至汉州东南会洛水,所谓于湔水合也)。[25]近世之编纂历史地名辞书者遂多以郫西之江沱[26]下合绵、洛者为湔之正流,而湔遂冒沱名,湔水之出玉垒东侧益不为人所知,此实妄中之妄,而湔、沱古义之紊遂更不可底止矣。(此当另考。)此皆止知湔之为水而不知湔之为山,更不知湔山所在、一切湔名皆自山出,故讹误累累也。
吾人既知古蜀人之为“左言”——异族语言,则更有可进而论者,即近世学者所热议探讨之“巴蜀文字”是也。《本纪》固尝言: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此当指蜀人上古之事,其后则渐有文字而礼乐渐兴也;此盖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亦为古文献及出土文物所明证者也。然而何谓文字?或文字之意义为何?此一基本知识则几为参与讨论者尽所忽视。经检《辞源》,其释“文字”为“语言的书写符号”。《辞海》则释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学专家向熹教授主编之《古代汉语知识辞典》释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此说拈出“体系”二字,其表述最符实际亦最完善。然此三说皆以文字与语言紧密相连而不可分,是为最要。如仅知其符号而不知其所表达语意为何,则是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其内容,是亦何有于我哉!对我有何意义?两者关系有如皮之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故欲释读此文字,必先通晓其语言,此乃必然之理。如仅有图像符号而不知其音读,遂仅据符号以揣度其意义,则头形之图可谓之为“头”,亦可谓之为“人”,然究为“头”抑为“人”,莫可定也;又如心形之图可谓之为“心”,亦可谓之为“爱”,然究为“心”抑为“爱”,莫可定也。此等猜谜式之释读,又皆无谜底可资核证,此等释读有何意义?虽连篇累牍又何益乎?即或已知其文字,又知其语言,然其文字系早已为失其传授之死文字,欲恢复其释读亦必须大费功夫。此埃及古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玛雅图画文字之能释读皆经数十百年探索研究之故也。又如殷商之甲骨文,虽有钟鼎篆籀可资参照,有古代音韵成果可供解读,现已研究逾百年,然犹太半不可识读,今日苟能多明一义、多识一字,已为重大发现,研讨古文字难度之大不言可知。而今之探究巴蜀古文字者,其有巴蜀古语言可供研读乎?吾固知其无有也,有后续文字之可供参照乎?吾亦知其无有也。学者仅就汉语汉文以供参考,可乎?不可乎;固不待多言也。综上所述,窃以为苟欲探究巴蜀古文字,首当探究巴蜀古语言;苟能于此有得,乃能有所参照,有门可入。余于巴蜀古文字尚在门外,以论蜀之“左言”,偶思及此,谨信笔写陈,刍荛鄙夫之议,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注释:
[1]洪颐煊辑《蜀王本纪》见所撰《经典集林》卷十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录洪辑以入其书之扬雄卷,仅增一条,而又未予说明。
[2]《王右丞集》卷五《送李判官赴江东》。
[3]卢书早佚,此序收入杨慎编录之《全蜀艺文志》卷三十。
[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八茂州。
[5]参见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第七辑。
[6]参见胡鉴民:《羌民之信仰与习为》附注②,文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边疆研究论丛》,民国30年成都印行。
[7]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
[8]《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本纪》、《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本纪》皆有蒲泽而无开明,《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有开明而无蒲泽。
[9]参见吴秋林等:《居都仡佬族文化研究》第352页~35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
[10]参见翁家烈:《仡佬族》,第4页、5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11]转见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第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2]王叔武校注《云南志略辑校》第9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13]参见另文《仡佬族自称的演变》(待刊稿)。
[14]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年第5期,后经两次重要修改补充,收入《巴蜀古史论述》。《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为最后定稿。
[15]此系节引《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本纪》。
[16]参见《史记·秦本纪》。
[17]皆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
[18]参见蒙文通:《庄王滇辨》,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1期,后收入《巴蜀古史论述》及《古族甄微》。
[19]并见《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三年。
[20]参见梁载言:《十道志》,载《汉唐地理书钞》。
[21]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史迹》。
[22]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吴起相楚》。
[23]晋为县大夫,见《左传》闵公元年、哀公二年,楚为县尹见《左传》庄公十八年,县公见宣公十一年。秦县置令明文见《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及《商君列传》。《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时已置县,在公元前688年—前687年;然是否置令,则不可知。齐置县令见《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时(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已是战国中期。
[24]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茂州汶川县载:“玉垒山:在县东北四里。”卷三十一彭州导江县载:“玉垒山在县西北二十九里。”唐汶川县治今阿坝之汶川县;唐导江县治在今都江堰市东导江铺;西北二十九里即今都江堰市西北郊之玉垒山,有玉垒关,今犹在。
[25]括弧内所引皆《江水疏》之文,盖以杨释杨也。
[26]《汉书·地理志》记蜀郡郫县:“《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