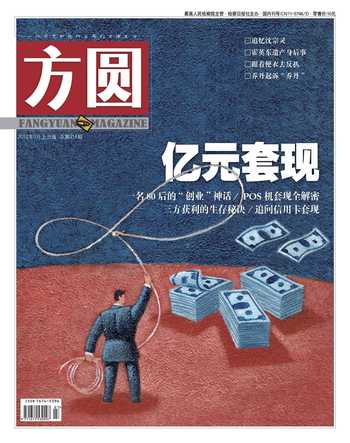追忆沈宗灵活得真活得善活得美
2012-04-29冯建红
冯建红


【√】回忆是片段的, 玉珠成串,但是编织起来,就是一个活得真、活得善、活得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2月16日,距离沈宗灵教授的九十寿辰还有9天,张骐教授正与同门为先生张罗着寿宴,先生却匆匆离去了。
儿子沈波说,父亲从送进医院到离开人世共13个小时,走得很安静。“沈老师终究是遂了自己的初衷,他莫非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最不能违背和质疑的方式告诉我们,尊重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意愿、选择最‘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纪念?”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齐海滨心痛地说。
最后的学术礼物
齐海滨是沈宗灵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跟先生感情深厚。这几年,他大多数时间在国外,不能常伴恩师身边,但时不时托自己的学生赵冬去看望先生。
2011年初,赵冬去看望沈宗灵时,因为身体的原因,沈宗灵说话很少,却总是面带微笑安静地坐着。他的夫人说:“沈老师年纪大了,听力差,不记得事,思维也跟不上,要是你们跟他说说学术,或许他能想得起来。”果然,当赵冬跟沈宗灵说起佩雷尔曼(沈宗灵专著《现代西方法理学》里有一章专门介绍佩雷尔曼的修辞学论证)时,他立即变得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还告诫赵冬要对这些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龙年大年初一那天,沈宗灵与赵冬通话时还曾吩咐,让其联系出版社将他去年再版的译著《人和国家》送些过来,等到过寿时好送给学生们。然而,书本正准备送往先生家时,他却匆忙离去,留下了遗憾。
沈宗灵翻译的法国思想家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影响了很多人。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马里旦的那句“国家是为人服务的,人为国家服务是政治的败坏”的名言印象深刻。苏州大学周永坤教授曾说:“它真正开启了我的心灵,使我得以能重新认识人与国家的关系,原本脑海中的国家主义受到清算,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确立了人本主义或曰自由主义的根基。”
这本《人和国家》最早在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霍宗彦”。很多人直到现在才知道,霍宗彦者,沈宗灵也!在当时那个年代,译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隐姓埋名。2011年此书再版,译者才换成 “沈宗灵”。
没有别的方式比这些著作更能表达沈宗灵的心意,可惜,他的很多学生没能亲自从老师手中接过这份厚重的礼物。
曾立志要“经国济民”
沈宗灵1923年出生于杭州,抗战期间搬住到上海租界,其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律学系,1946年毕业后获学士学位。沈宗灵生前曾说,在抗战那一冗长而极重要的时期里,当时唯一希望是抗战快点结束,幻想胜利之后,中国会变得如何富强,当时亦有了自己应该为中国变得富强贡献一份力量的狂热。
这种狂热,其实在沈宗灵中学时代的时候就已显露,当时他就已经立下了将来要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他对自己这种人生观的具体概念解释为,“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国搞好。”
所以,沈宗灵在读大学的时候毫无犹疑地选择了读法律,那时他已经想到法律是与从事政治事业分不开的,虽然他的父亲坚持要他学工程。
为了离自己“取得政治社会中最上层地位”的目标更近些,大学毕业后,他便去了美国留学。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系学习,次年获人文科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法”。
1948年秋天,沈宗灵带着一大套自认完整而高深的理论回到了祖国,他以为自己酝酿了多年的大抱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
在归国的旅途中,沈宗灵便安排好了回国后的计划。除了教点书,他把律师业务作为工作重点,当时他认为中国的律师也会像美国律师那样拥有政治前途。“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那时,沈宗灵就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沈宗灵回到了上海。然而,后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如沈宗灵想象的一样。彷徨过后,他转而继续走学术的路子。
沈宗灵最初在复旦大学教书,1950年参加了司法部主办的中国新法学研究院。“我觉得研究院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具体并不十分了解,也十分好奇。我那时二十七岁,也没结婚,没什么负担,就去了。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借用研究院负责人的那句话说:‘这儿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这里是搞思想改造的。我才明白过来,但一进去就出不去了。”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于1949年9月招生,是为了改造旧司法人员而成立的, 1951年末,该院和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一道并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沈宗灵生前每次跟来访者讲起这段经历,他都会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过程中,沈宗灵接触了另一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段时间,对沈宗灵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很大影响。在研究院第二期培训时,沈宗灵留院工作,任研究员。一直到1954年北京大学重建法律学系,沈宗灵被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工作,仍任讲师,兼任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连续三年主讲法学基础课程(当时称“国家与法的理论”),沈宗灵也因此成为北大法律系的元老之一。
之后的岁月,沈宗灵几乎都在燕园里度过,继续着他的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批学子。1993 年5月退休后,他仍旧继续承担对博士生的指导工作,直至2000年。
中国法理学的“沈宗灵时代”
沈宗灵是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推动了法学理论学科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发展为“法学基础理论”,再发展为“法理学”,并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主编的《法理学》系教育部国家重点教材,也是现在很多法律人的第一本法理学教材。
除了法理学外,沈宗灵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学领域也极为专长。他开创了现代西方法理学研究,撰写了建国后第一部详细的现代西方法理学理论著作《现代西方法理学》;他推动了比较法学科的建立和比较法的研究,专著《比较法总论》和《比较法研究》是比较法领域为数不多的必读经典。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这样评价沈宗灵:“沈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法理学的开拓者;是把西方法治文明介绍于我国并运用于我国的倡导者;是西方人权学说通向中国法学界的系统译介者;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早探索者。先生是中国法学在那个特殊时代连接与西方、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法治实践需要的桥梁。中国法学的那个时代可以称为沈宗灵时代。”
沈宗灵不仅个人在学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乐于将他的学识与社会分享。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的筹建及发展都离不开他的倾力支持。他曾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第一任总干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第一任总干事。
华南理工大学葛洪义教授第一次见到沈宗灵,是在27年前中国法学会的年会上, “给我的印象是,他的发言很沉稳,不仅讲话内容,而且说话方式甚至坐姿都是如此,从不激动,很有权威。”
“他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中国法学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如此评价先生,“他的《比较宪法》一书,以最准确和第一手的资料对西方20国的宪法作了系统化的研究,是宪法学进入2000年以后最好的一本教材,到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参考沈老师的书。”
他常劝人“莫学法理”
沈宗灵治学精神为同行所共睹,并被称赞为“最勤奋的学者”。他一生写作了多部法学著作,撰写论文110多篇,许多被译为英、日、葡文发表。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之后的二十年虽然只教授过12堂课,但其他时间仍然从事编译工作。平反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先生更加勤奋,笔耕不辍,先后译著了《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等名著。他说,自己在做学问上耽误了20年,要在有生之年努力弥补。
沈宗灵治学的严谨也是出了名的。“我刚从法律系毕业开始工作时,先生担任理论教研室主任,当时他30出头,年轻有为,教研室的工作抓得很到位、抓得很细。他对讲稿的审查非常认真,发现讲稿中的错误都要跑到资料室去查。”北京大学教授由嵘回忆说。
这股子认真劲,也表现在教育学生方面。沈宗灵有句口头禅,是“莫学法理”。他不鼓励学生盲目报考他的研究生,选徒弟也显得特别苛刻。
齐海滨教授曾撰文回忆先生:“我在一次课后向沈老师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师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沈老师还反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国际法或经济法这样实惠的热门专业?年轻人切忌心血来潮,何不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慎重考虑?”
“法学和历史学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可以集中研究一个人物,比如研究孙中山,但是法学不是这样。法学的东西,你看都看得懂,但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说得出,写得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沈宗灵生前曾对他的学生如此教诲。殊不知,他是在告诉学生,想在法理学研究上有所成就,须潜心积累,要耐得住寂寞。然世上真正想做学问或者做成学问的少,要么是急功近利,要么是天资所限。或许,是因为沈宗灵早就看得明白,才常跟人劝诫“莫学法理”。
在沈宗灵看来,如果要学,就一定要好好学。所以,他对自己的学生十分严格,最见不得学生对学问抱有狂妄态度。沈宗灵的高徒们记忆所及,师从老师期间多半都有被他棒喝的经历。
正应了那句,“严师出高徒”。沈宗灵从教50多年,毕生的精力几乎都在从事法学教育工作,为中国法学界培养了一批批法学大家,如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北京大学教授张骐等。
活得真善美的平凡人
在外人看来,沈宗灵不苟言笑,甚至有点古板。在香港大学李亚虹副教授的记忆中,“每次见先生的时候,都会高度紧张。因为他虽然彬彬有礼,一开门就让座,并让师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热茶,但他会在你的名字后加一个‘同志,然后很直率地对你的学业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加以批评。”
李亚虹还记得,毕业前,同学决定给每位指导老师送一个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谢师恩。当她和另一位同学将礼物送到沈老师府上时,他却拒绝接受,说她们不应该这样做。当她们说礼物上已经写了沈老师的名字时,他说那就将钱给她们。这让李亚虹她们不知所措,也无法理解,因为别的老师收到礼物都非常高兴,她们当时甚至怀疑是不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变得过分谨小慎微。
“老师就是那么一个耿直的人!” 沈宗灵的学生郑强回忆说,很多年前沈老师受邀参加一次研讨会,举办方发给与会嘉宾每人50元“车马费”。但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为其解释说是交通费,他却很认真地说“我坐公交车去的,回来打的面的,用不了这么多”。然后让我将剩余的钱寄回了举办方。
熟悉沈宗灵的张骐说,那是因为在沈宗灵看来,人活着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跟别人结交关系,说一些没有必要的嘘寒问暖的话。君子直来直去,这是一种真。沈宗灵虽然拙于社交,说不出来那些应景的客套话,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内心不理解不感激别人,他有自己的方式。沈宗灵的太太有次偷偷跟学生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误解他呀,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脸上严厉,可为你们是真操心,有时候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
在生活中,沈宗灵正直富有爱心的品格让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也充满了敬意。他回忆,读书期间,他从图书馆借过一本法理书,把家人的合影夹在了书中,还书时却忘了取出,没过几天,沈老也借了那本书,发现照片后交给系办,同时附上了一张纸条,“请找到照片里的同学还给他!”
回忆是片段的, 玉珠成串,但是编织起来,就是一个活得真、活得善、活得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评价沈宗灵说,沈宗灵的一生并非轰轰烈烈,但却树立了思想品德和学识学问完美结合的典范。“先生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学者。”季卫东如此评价他的恩师。他说,当下社会,能做到这几个字很不容易——潜心治学,淡泊明志。
沈宗灵,杭州人士,1946年复旦大学法律学系毕业,1947年3月赴美国求学,第二年9月获人文科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法律学系讲师。1954年北京大学恢复后,被调入北大法学系,主讲“国家与法的理论”等法学基础课程,是北大法学系的元老之一。1982年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1988年改任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93年退休,继续承担对博士生的指导工作,直至2000年。
作为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奠基人,沈宗灵推动了中国法学理论学科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发展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发展为“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主编的《法理学》系教育部国家重点教材,获得了多项奖励,至今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开创了现代西方法理学研究,撰写了建国后第一部详细的现代西方法理学理论著作《现代西方法理学》,同时撰写了专著《美国政治制度》,译著了《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庞德著,商务印书馆,1984)、《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凯尔森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等名著;他推动了比较法学科的建立和比较法的研究,专著《比较法总论》(1987)获首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
沈宗灵二三事
沈宗灵在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其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不无关系。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学术就是他的生活,学术就是他的生命。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齐海滨有一次去看望先生,注意到先生案头上还有一本翻开的英文书,问起来才知道先生每天依然是把读书和翻译作为生活内容。那是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荷兰学者克尔兹的《当代比较法》,先生从北图借来阅读,而且边读边译,当时已经差不多翻译一半了。“我对老师说,您如果以后不译了,我接着做剩下的部分吧。沈老师说,他只是随手译,习惯而已,并无出版意求。”齐海滨回忆说。
沈波回忆起父亲对学术的执着,亦深有感触。1998年,已经退休5年的父亲在随他去美国短住的一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一个月里翻阅和撰写相关法学研究资料,特别是关于法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法律和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生作了专门发言,并提出了法律全球化的两面性问题。
与学术上的严谨相反的,是沈宗灵的宽容。齐海滨回忆说,先生一生献身学术,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但从不在学生面前提起他自己的遭遇。“我在与法学院别的老师的接触中,偶有提到沈老师所遭遇的不公,包括沈老师的学术成果被人侵占等。所有这些,沈老师在我们面前从未提及一个字。有一次,沈老师到东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个学生,沈老师客客气气,没有任何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