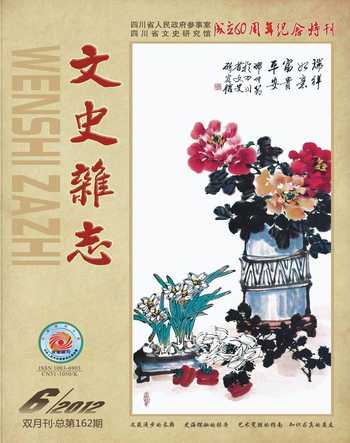“玄武门之变”新识
2012-04-29青子佩
青子佩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诗人杜甫结束了往鄜州省亲之旅返回长安途中,再一次经过昭陵,写下一篇五言长律《重经昭陵》: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
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
诗人这里讲:在隋末风起云涌的英雄群体中,最值得讴歌的是唐太宗。他手提三尺剑驰骋在沙场上,为夺取天下而身先士卒。尔后,他又在贤臣辅佐下躬行仁政文治,还谆谆告诫后代勿滥施武功。他的胸怀像蓝天一样深远广大,他那仁德的光辉长久照耀着国家的未来……
但是,后世也有人视唐太宗为假仁假义者,其提出最厉害的证据就是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害兄弟并抢班夺权。北宋著名的唐史专家范祖禹即在《唐鉴》里批评唐太宗“不顾亲”、“不知义”,说:“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太宗之罪著矣!”南宋大儒朱熹亦说:“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1]
实事求是地讲,范祖禹和朱熹们所揭露的确属事实,毋须隐讳。
蹀血贻讥的“玄武门之变”
原来,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起兵之初,“太宗时年十八”,已是一位战功累累、威震敌胆的骁将奇帅了。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为年轻的李世民开辟了一个施展雄伟抱负的广阔天地。在“隋祚已终”而群雄蜂起的时候,他用闪电之势迅速消灭了薛举、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和他的父兄们一道,终在公元624年完成了唐王朝的统一。李世民在兼并战争中位至尚书令,掌握了咄咄逼人的兵权,并组织了一个包括秦叔宝、程知节、李勣、尉迟敬德及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大批名将智囊在内的军事集团;政治上的羽翼也日渐丰满,到了“玄武门之变”前夕,已膨胀到极点而造成炙手可热之势,从而使太子李建成不得不生杀机以固其位。
在李建成周围其时也集合了一大群如魏徵、王珪、冯翊、冯立等文武名流以及诸多妃嫔内王,并联合拥有精兵强将的齐王李元吉,凭借皇太子的地位在政治上对李世民形成强大压力。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又进犯中原。李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领兵,代李世民督军北征,想借机把秦王府的精兵和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骁将划归自己手下,并得到了高祖的许可。这一消息,被王晊透露给李世民,情况万分危急。李世民赶紧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和杜如晦等商量对策,决定伺机先发制人。
这时,京城上空已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李建成、李元吉加紧联络妃嫔、内王,日夜在高祖左右谮陷李世民。李元吉还说:“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2]
对此,高祖没有表态。到了六月三日,高祖意欲让世民自识避祸,遂将建成、元吉揭发他私蓄八百勇士入宫图谋不轨的上表给世民看。世民情知形迹败露,于是反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
高祖决定次日审问兄弟三人。世民连夜布置,准备武力夺取权位。
翌日(六月四日)晨,李世民率八百勇士悄然通过玄武门(宫城北门)而伏兵临湖殿。玄武门的守将敬君弘和监门卫将军(掌勘验宫城出入证)常何原系李建成营垒的人,已被李世民暗中收买,成为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取胜的重要棋子。此时高祖正召集诸宰相泛舟于湖,商讨审问建成兄弟仨事宜,仓促之间不及反应,便被李世民置于控制之中。
不久,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由玄武门进宫。他们看到常何十分放心。可是,当他们进入玄武门后,常何却突然把门关上了,令他俩好生奇怪,但并未作过多考虑。兄弟俩西行至临湖殿时,才发现情况有异,似有伏兵;且李世民全副戎装,立马跃枪守候在那里。兄弟俩大喊不妙,急忙掉转马头逃命。李世民拍马赶来,一箭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射杀。
李世民一不做,二不休,即命尉迟敬德前往临湖殿索讨高祖手令。面对着这咄咄逼人的态势,以裴寂为首的股肱大臣默然不语;而萧瑀、陈叔达等则力劝高祖承认现实,将国事委与李世民,方可保无事。高祖无可奈何,仰天长叹一声,旋下手令,命诸军皆听秦王号令。两个月后,李世民接受高祖禅位,改明年(公元627年)为贞观元年,是为唐太宗。
按宋以后逐渐加强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来看,李世民制造的“玄武门之变”确实算不得善策,确乎是“不顾亲”、“不知义”的行为。司马光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3]而唐太宗则以玄武门的惊世之变,袭杀兄弟,抢班夺权,给后世王孙们的僭号越位,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司马光叹道:李世民“蹀血禁门,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4]
“大一统”历史观与唐三百年的历史走向
笔者认为,李世民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不顾亲”、“不知义”,与他在治国治世方面所提倡的“人本”、“仁政”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何况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兄弟阋于墙、家族相残的事情并不鲜见。较早的显例就有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景帝接连诛杀七国同姓弟侄的事件。
其实,无论是汉初与同姓诸王的斗争,还是唐初与李建成集团的斗争,都不应仅仅将其视作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如果放远来看,这实际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严峻问题。
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战国末哲学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稍晚成书的《吕氏春秋》,都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持积极态度,其中《吕氏春秋·八览》中“大一统”思想尤为突出。它们为秦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汉初成书的《公羊传》,其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大一统的重要性。以后董仲舒演化的“春秋公羊学”,在邹衍所论及《公羊传》基础上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对“大一统”的历史发展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们的指归却是宣扬“大一统”这种在当时说来无疑是进步的历史观。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一书里说,司马迁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它,形成《史记》所独具的“大一统”历史观。我们注意到,司马迁《史记》中的《淮南衡山列传》的大部分篇幅,叙述的就是中央与吴楚七国同姓诸王所展开的反分裂斗争。司马迁在篇末立场鲜明地指出:
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反映了汉初以来的民心所向,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还需说明的是,这种“大一统”历史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涵是华夏民族皆黄帝子孙。这种历史观认为,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的发展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这个国家一统、民族融合观念,应该说是当时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因此也成为司马迁架构《史记》的一个基本大纲。
迨入盛唐,刘知几著《史通》,对他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总结。他在“华夷”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可以说是远绍司马迁的大 一统观,近承魏晋南北朝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史学思潮。他希望中国境内各民族能像兄弟般和睦相处,长期一统,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利益出发,出于公心,捐弃前嫌,再也不要出现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兄弟阋于墙”的惨痛局面了。而刘知几有如此认识,还同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的政治眼光有着密切关系。那时的唐朝君主,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多摒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民族偏见,对各族“爱之如一”[5]。可以说,大一统的历史观是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它反过来又促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新的基础上的更高融合与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并且,分裂总是短暂的,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愈到后期,愈是如此)的根底也正在这里。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世民亲自导演的“玄武门之变”。如果用“大一统”的历史观来观照,用李世民后来在《贞观政要》里所表达出的人本主义情怀来观照,是不是可以说李世民所代表的正是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走向,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活泼开放的社会发展潮流;而李建成所代表的则与之相反——这从兄弟俩所依靠的、或者说背后支撑他的政治集团(站在李建成背后的主要是士族集团,李世民背后则主要为庶族集团)以及兄弟俩的意志品质和民心向背(《新唐书》说李建成“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新唐书》则议李世民“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魏徵在武德五年向李建成言:“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就可看出。
至于司马光、顾祖禹等对李世民“不顾亲”、“不知义”的批评,其实遵循的是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的陈腐古礼,不足为凭。因为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那样僭越礼数的大事件发生得并不少。远者如被李世民力逼退位的李渊,不就是以臣子身份取代隋恭帝而为唐高祖的吗?近者如司马光们本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所导演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建立宋朝),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打着“从母命”的幌子从亲侄子手中僭夺继承权(更有“烛影斧声”一类传说佐证赵匡义的僭越行为)。在这同样充满血腥与杀气,属于大逆不道的帝王面前,司马光们为何却佯装不知,不说一句话呢?
其实,在封建时代,不论什么人当政,也不论是以什么手段上台,只要他代表的是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实行的是“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大政方针,便对国家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其实也无须硬要去辨识“玄武门之变”的是非曲直;或者也可以说,这只不过是李世民当时在情急之中的无奈之举。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所识: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6]
明人李贽更是快人快语:“建成、元吉自家讨死。太宗杀之,不为过也。”“盖天下乃太宗上献之高祖,非高祖下传之太宗者也,岂与世及之常例乎!夫何俗儒不晓,尚有以长之说。”[7]
儒家人格和李世民的成功
我们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唐初宫廷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就其个人方面来讲,则完全得力于他较为完整的儒家人格。大家知道,通常讲的儒家人格(为原始儒家所阐述的人格)应当具备三个层次,这就是“仁”、“知”、“勇”。孔子讲:“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8]
《中庸》还将“知”、“仁”、“勇”称为“天下之达德”。如果说“仁者”是儒家人格的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知者”是人格结构中表征理智的因素,是实现理想人格的自觉意识的话,那么“勇者”则属于人格中的意志因素。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惧”。[9]可见勇是仁的必然要求,是仁的意志的升华。它源于“仁”,源于人格的内在力量。仁者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应当不折不挠,万难不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怕来自自然的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挑战或障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就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或“以身殉道”。
唐太宗正是这样的“仁者”、“知者”和“勇者”。(在这里,唐太宗无疑从原始儒家那里汲取了养料。)假若他在纷乱复杂、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面前没有洞若观火的能力和当机立断的勇气,也便不能从剪不断、理还乱的宫廷内耗中迅速脱身。假若他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惧怕各种流言蜚语乃至于身后的批评,他便不能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迅速结束动乱。假若他不敢实施僭礼越位、抢班夺权的“玄武门之变”,他便不能将国家迅速引上“大治”的局面,历史也便不会出现光芒四射的“贞观之治”。
倘使上述假设能够成立,那么,这样的唐太宗李世民才真算是一个假仁假义者。因为这位“唐太宗”至少欠缺人格中应有的“勇”,他的人格是不完整的。由此还会影响到对其“知”与“仁”的评价——因为这说明这位“唐太宗”不善于认识形势,辨识方向,把握时机;说明他心中无理想或缺乏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缺乏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说明他心中无天下苍生,唯有他自己!
幸而历史上并未出现这样一个“唐太宗”。
幸而玄武门之变证实了真实的唐太宗的仁者胸怀、知者风范和勇者气概。这以后,唐太宗又以“贞观之治”继续证实着他人格的完善。
唐太宗是一个真正的仁者、知者和勇者。他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这就是我们今天何以会在流传下来的各种官修唐史或唐史资料中看见有关“玄武门之变”的真实记录的主要原因。《贞观政要·文史》里有这么一段故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问房玄龄:“我经常阅读前代的史书,发现它们能彰善斥恶,足以规诫后人。但我却不理解,何以自古以来,却不让当代君王观看当代国史?”
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是好事坏事都要收录的,以此警诫君王不做非法的事。这样一来,有些记录恐怕就不合君王的心意,所以便规定不让君王本人观看。”
太宗说:“我的看法却不同于古人。今天我想看看当代国史,如果记载的是好事,当然无须多说;如果记载的是坏事,我就要引以为鉴,让自己不再犯错误。因此,你不必担心什么,可以把你撰写的国史抄录一份让我看看。”
房玄龄就通知许敬宗等将国史删改为编年体,有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抄送太宗。太宗看到关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记录,闪烁其词,颇多含混,就对房玄龄讲:“从前周公诛灭管叔、蔡叔而使周朝王室安定,季友用毒酒毒死叔牙而使鲁国安宁。我当时的举动,意义与此完全相同,即是为了安定社稷,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罢了。作为史官应秉笔直书,为什么躲躲闪闪,有所隐瞒呢?应该去掉那些隐晦敷衍的话,直截了当地照实直书出来。”
侍中魏徵知道后上奏说:“臣听说人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什么都不顾忌,只有国史可以警诫他改恶从善。如果国史记述不实,后代的君主又能从中获取什么教益呢?陛下今天要史官改削浮词,据实记录,是最好的大义大公的原则。”
唐太宗坦然面对历史,不回避,不推诿,不遮掩,勇于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表现出一个有魄力、有胆识的封建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应该说,对于玄武门之变他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以为正当的解释,这是他的权利,是不好予以指责的。而他敢想、敢说、敢干,并敢让人照实直书,这件事情的本身便令人肃然起敬,足令那些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者(新、旧《唐书》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叙上即有意回护唐太宗)汗颜。
注释:
[1]朱熹:《近思录》卷八。
[2]《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列传》。
[3][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6]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12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7]李贽:《史纲评要》卷十七。
[8][9]《论语·宪问》。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