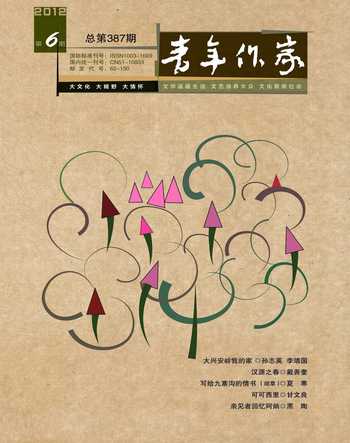夏日对秋天的怀想
2012-04-29宋晓达
2005年的一天,又是一夜的大雨。雨覆盖了大地、山野、房屋。整整一个夏季,皖南几乎都浸淫在氤氲的梅雨里。
我蛰伏在黄山脚下一个村落的老屋里,心情潮湿得快要长出青苔。窗外那棵柿子树依旧站在那儿,举着树叶,注视着我。秋痕无迹,鸟儿还没有来,秋天离我们还很远。
我时常留恋这山坞里的秋天,想那柿子树上的柿子红红亮亮坠满枝头的样子。
记得那时,我们攀枝花公路桥梁总公司刚来这里,参加安徽铜陵至黄山汤口高速公路的修建,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叫“苏坑”的小山村安营扎寨。村子四面环山,村口两股山溪潺潺流淌。村子里的人说,这就是风水上讲的“左青龙,右白虎”。
我们项目部四十余名管理人员,全部租用了当地老百姓的房子。原本给我安排的是一幢新修的、比较现代化的民房,我却偏偏选择了另一幢青砖黛瓦、马头墙、具有典型徽派风格的建筑。建筑看似老旧,其实非常典雅古朴,而且全是木质结构,楼板、楼梯、隔墙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料。一双燕子在堂屋里飞进飞出。
两层的阁楼,居室五十多平米。我把屋子一分为二,从中间隔开,里面睡觉,外面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椅的位置正好面对窗户,光线充足。推开窗,对面是一棵高大的柿子树。那时正是深秋时节,柿子红彤彤的,引来许多鸟儿啄食、舞蹈、歌唱,煞是喜人。
天色好的夜晚,有月亮从后山慢慢地爬上来,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半个,就挂在窗外那棵柿子树上。这时,我的小屋被月光灌得满满的。伫立窗前,风清月明,人淡如菊。整个身心都浸润在这如水的月光中,感觉自己就是一棵树,上面挂满了回忆、思念和牵挂。
记忆的枝蔓伸延至远方,伸延至成都,伸延至锦里那个秋日的夜晚:在锦里,一间两层楼的酒吧,我坐在临窗的一个位置。不是周末,酒吧里没什么人,我的对面是一个女人。不用说,她很美。我们呷着红葡萄酒,喁喁而谈。她说我像《廊桥遗梦》里的罗伯特·金凯——高、瘦、硬。我说:“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斯卡有足足四天的时光,而我们只有一个夜晚。”她诡秘地笑了,说:“一个夜晚已经足够了。”说罢,点燃了一支细长香烟,姿势优雅而迷人。她告诉我这雪茄是什邡产的。“知道雪茄名字的来历吗?”她问。我摇摇头。她说:“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上海会见徐志摩。泰戈尔是一名地道的烟客,他问徐志摩‘cigar的中文名字怎么叫?徐志摩想了想,说烟灰似雪,其形如茄,就叫它‘雪茄吧!”我大为叹服。若不是她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雪茄”这富有诗意的名字,竟出自徐志摩之口。
酒至微醉,花蒂半开。她白净的面颊,已爬满了春色。窗外的大红灯笼在风中摇曳,她的微笑在我眼前摇曳。萨克斯风曲子《回家》缓缓升起,我闻到了雪茄的味道,那是一种芬芳和女人的味道,越来越近,却瞬间又被窗外的风吹散了。夜有些深了,她伸出一只手起身告辞,没有言语,依然是诡秘的微笑。我知道,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她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消逝在那个小楼的酒吧,消逝在锦里,消逝在那个漫漫的秋夜。
好多年过去了,此刻,我在安徽黄山脚下的一个村落里,怀想秋天。那是我生命中的自留地上的美丽风景。
窗外的雨,依旧下着。阁楼里空荡荡的,没有月亮,没有红酒,没有音乐,也没有佳人。
只有桌上的一杯清茶、散落的书和墙脚蟋蟀的吟唱。
再过一年,我们就回四川,回到那个叫“攀枝花”的城市。
作者简介
宋晓达,祖籍辽宁彰武,出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曾在《诗神》《青年诗人》《星星》诗刊等二十多种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生命的歌唱》、诗歌散文集《炊烟是母亲栽的一棵树》、散文集《城市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