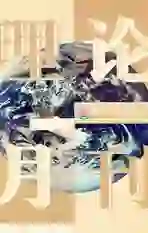论拉封丹《寓言集》中的互文性
2012-04-29王佳
王佳
摘要:法国17世纪著名寓言家拉封丹的《寓言集》由两百多篇寓言构成,每一篇寓言都有独立的故事和寓意。不过,《寓言集》是一个由寓言构成的有机整体,寓言和寓言之间相互关联,从寓言涉及的人物形象到寓言的故事情节,从寓言的道德训诚到作者的“旁白”,它们都在不同的语篇之间相互呼应,这种互文性关系改变了原本单一的寓意形成模式,也扩充了寓言这一短小文体的文学纵深,并对寓意生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拉封丹:寓言: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565.33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98-04
根据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所孕育的“互文性”理论,我们所阅读的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引用之前的文本,又为后来文本所用。文本间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相互指涉的网络体系。自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此概念后,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又分别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各自的注解,他们所诠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文本间的呼应和联系构成了文本与文本的“互动”。
寓言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文学体裁,它将深刻的寓意蕴藏在短小的篇幅之中,较为精炼的文字决定了每篇寓言有限的信息量,一篇寓言可以不需要详细的时代背景,也不需要过多的情节铺垫,寓言中的人物也可以毫无来历,甚至可以是由作者凭空塑造的主体。所以,从寓言阅读习惯上看,我们在欣赏寓言的时候,常常会孤立地去看寓言中的角色,去思考寓言所给出的故事,也仅仅只是依靠内容和现实生活的相似性来推断寓言背后所蕴藏的寓意。随着寓言的传承,很多寓言演变为成语,原有的寓言文本或许已经被遗忘。而脱离文本的寓言故事会失去很多原有的色彩,因为寓言的文本并不孤立,尽管某一篇寓言只有简要的背景介绍,但是,寓言和寓言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可以丰富寓言的人物形象,甚至会对寓意的获得产生影响。从动机上来看,这种语篇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寓言家的综合考量和创作初衷,理解这种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寓言。
法国17世纪著名寓言家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为后人留下了两百多篇寓言,都收录在《寓言集》中,该作品由十二卷组成,每一卷约有二十来篇寓言,它凝聚了拉封丹二十多年的心血。《寓言集》涉及领域众多,包括哲学、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主题也十分广泛,有讨论如何生存的,有讨论如何追寻幸福的,也有教育人们修行性格的。《寓言集》涉及面之广使得研究学者很难从中系统地归纳出寓言家的创作理论。然而,即便寓言间并无明确的逻辑关联,而且存在大相近庭的寓意指向,但如果将拉封丹的寓言割裂开,孤立地阅读某一篇,或某几篇寓言故事是不可能对《寓言集》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的,也就无法真正体会拉式寓言的价值和它得以经久不衰的原因。虽然每篇寓言都有独立的故事,独立的寓意,但可以发现,寓言间并非毫无关联,寓言间的诸多元素在语篇之间前后呼应,相互补充,人物形象在关系网络中变得更加丰满,寓意也变得更加充实,这种文本的互动使得整部《寓言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寓意的共生扩展了文本的广度和宽度,使得《寓言集》不再是许多小故事的汇总,而是一部宏伟的“寓言全书”。
具体来看,拉封丹《寓言集》中的互文性元素比较多,而能贯穿《寓言集》始终,并在寓言之间建立起关键性桥梁的主要有“寓言主人翁的互文”,“文本隐喻的互文”以及“‘旁白的互文”。寓言的主人翁多为动物。而很多动物在寓言间反复出现,从而扩展了动物在寓言中的单一性格特征,形象更为生动;文本的隐喻大多为生活的哲学,是“真理”的某个片段,而多篇寓言的隐喻能共同实现《寓言集》寓意的升华;“旁白”的互文则是寓言家参与思考留下的痕迹,是寓言家对某一具体故事的态度展现,但每篇寓言的“旁白”只能反映作者思考的一个侧面,只有通过语篇间建立的联系,才能观察到作者思考的全貌。
一、寓言主人翁的互文
传承了古希腊寓言家伊索的风格,拉封丹笔下的寓言多为动物寓言,即以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为主角的寓言。尤其是人类所熟悉的动物,更是成为了拉封丹寓言中被赋予使命的主人翁,在这些颇具趣味性的寓言中,主角的选择绝不是偶然,甚至可以说大多都具有不可替换性。各种动物在寓言中的粉墨登场成为了拉式寓言的一大特色,虽然拉封丹并不是动物寓言最早的创作者,但是拉封丹的寓言让动物成为真正文学艺术的主角,每种动物的出场不仅有它特殊的使命,更是具备了许多“人”的特征,通过话语和行为。主人翁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拉封丹让这些动物完全摆脱了在文学领域附庸性的地位,跻身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将动物拟人化虽然容易吸引读者,但也有一定风险,因为人的个性可以随意刻画,而动物的个性则会受到人类文化背景的束缚。拉封丹在确定动物形象时,实际上就是既考虑了它原有的文化属性,又强调它的相对性以及由该属性所延伸出的属性:例如,在欧洲文化中,狮子是“百兽之王”,受人膜拜也常常欺凌弱者;狐狸狡猾,擅于伪装,靠欺诈谋生;狼是丛林中的“硬汉”,蛮力有余,而智慧不足;驴子则是愚笨的代名词,偶尔故作聪明,也是“画虎不成”,可以说,拉封丹笔下的动物们基本具有大众文化视角中的属性。而另一方面,在动物各自属性的背后。又根据每篇寓言的需要,具备不同的个性,这些个性既是延伸也是补充,只有通读整部寓言集,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相互映衬,相互强化,共生、共存的特点。虽然拉封丹并未用太多的笔墨在某一篇寓言中详细地解释某种动物的性格特征,但这些寓言主人翁的特质在寓言间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展现,使它们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要提到的是“兽中之王”狮子。在拉氏寓言中,关于狮子的寓言很多,可以用两个形容词来归纳这一形象:威严、霸道。这两个特征在语篇间反复出现,前后辉映。在《狮子出征》一文中,拉封丹将威严的狮子类比“贤明的君主”,能根据部下的特点分配好每个下属的任务,从而发挥一个队伍最强的战斗力。而君主也有霸道的一面,在《小母牛、母山羊、母绵羊和狮子结盟》中,大家共同打猎,而狮子独享猎物,还言之凿凿“因为我的名字叫狮子”反映出绝对的强者若没有监管会有滥用权力的风险。为狮子证明的寓言数不胜数。拉封丹已经将其视为动物中的“王者”,整个寓言王国似乎就在狮子的统领下生存。不过,虽然狮子的“权威性”是它在《寓言集》中的主要特征,但狮子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一单一形象,如果把寓言中出现的狮子展示的个性相互关联起来,可以发现,这一寓言形象本身就能形成寓意。狮子的“威严”是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拉封丹从哲学的角度,以辩证地方法展现了一个生动的“丛林之王”:强者并非没有对手,在《狮子和蚊子》Ⅲ一文中,强大的狮子就在和蚊子的对抗中败下阵来。狮子可以失败,但王者的威严不可侮辱,尊严不能丧失。在《衰老的狮子》一文中,当强者不再强大,弱者欺凌它的时候,它仍然表现出“尊严高于一切”的姿态,他认为“谁都可以瞧不起自己,唯独愚蠢的驴子不行”,于是发出了“太过分啦!我愿意死,但受你的侮辱,我等于死两次。”的感叹。不同寓言故事中的狮子在保持一个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又各具不同,它们相互影响,并为在读者脑海里勾勒出了一个更为鲜活的狮子形象。它告诉我们,强者也是血肉之躯,强者也具有相对性,读者甚至可以将关于“狮子是什么样的”的思考看做《寓言集》没有写出的一篇寓言。而启发读者进行更深远的思考,也应该是作者本人的意愿。
另外一个在《寓言集》中反复出现,并让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主人翁是狐狸。寓言中狐狸的形象也符合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属性:狡猾,利用伪装谋生。这似乎在人类社会是一个受人诟病的性格,拉封丹在迎合这一一般性认同的属性前提下,给这一角色增添了一些“活性”,也就是一个更加真实,更具人性化,且并不被“一棒子打死”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符合拉封丹在作品中所认可的“适者生存”理论。在反复利用其特点展开故事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拉封丹让这一角色表现出了不同的一面。例如,狐狸的智慧不仅用来对付弱者,也能应付强者,为自己谋求生路。在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出现了两次《狼和狐狸》,面对丛林中强大的“恶狼”,狐狸也可以屡屡得手。而面对狮子,还要懂得献媚。在《狮子、狼和狐狸》一文中,面对狮子,既要保住性命,又要获得狮子的欢心,狐狸绞尽脑汁,达成愿望。不过,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狐狸也会失手。我们都读过的寓言《狐狸和獾》就是证明:“骗子。我为你写这些东西:同样的下场在等着你。”通过这些寓言。拉封丹试图改变“狐狸”在大众文化中单一的形象,也引起读者思考:“‘狡猾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是否也能成为有效的武器呢?”。这不仅丰富了读者对于“狐狸”这一角色特征的认识,还为我们应对生活中的“狐狸”提供了借鉴。
在拉封丹寓言中,还有许多诸如猫、鼠、驴等我们熟悉的动物,这些动物或因为外形,或因为本性,也都在人类的文化中形成了简单的与人类性格的隐射关系。不过,拉封丹在不同的寓言故事中为相同的角色赋予了多样的性格,它们在语篇之间相互呼应,使角色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而将这些形象更丰富的动物主人翁再放回到原有文本中,将会影响原有文本,进而创生新的寓意。
二、文本隐喻的互文
“拉封丹并不想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甚至害怕让人这么认为。”如果寓言成为了哲学家的道德说教场,那么寓言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这自然是作为一位寓言家所要竭力避免的。不过,拉封丹的哲学思考贯穿《寓言集》始终,它是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有些甚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而这些特点必须通过多篇寓言的阅读才能归纳,并得出结论。西方研究拉封丹的学者们都认为,《寓言集》中所展现的哲学思想比较零散,不易总结。不过,涉及面极广,极为丰富的文本隐喻却在语篇之间互为佐证,甚至产生共鸣。在涉及“人的本性”,“人的欲望”等方面所阐明的观点都必须超越单篇寓言进行理解,否则可能出现理解偏差、甚至是误解。批判拉封丹的人,如卢梭,拉马丁都认为他笔下的寓言过于血腥,不适合儿童阅读,甚至对儿童身心健康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判断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因为有些篇目,如《小母牛、母山羊、母绵羊同狮子结盟》,《狼和小羊》,就单篇寓言进行孤立地阅读,读者无法获得除了“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之外的任何其它的意义延伸。而只有把《寓言集》作为一个整体,将寓言看成相互依托的有机体,才会看到这些寓言具有价值的一面。通读全集就不难发现,拉封丹的“丛林法则”涉及的方面其实很多,他首先希望能通过最为简单的方式告诉人们如何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继续生存下去。《狼和小羊》虽然强调的是“强者的逻辑永远是对的”。但该篇只是展示了“丛林法则”中的第一条,拉封丹也塑造了诸如《狼和狐狸》这样的故事,强调强者狼也会在和智慧的狐狸斗争中败下阵来,智力也是“适者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寓言《狮子和老鼠》中,拉封丹又谈到强者的相对性,强者也需要帮助,狮子也会受益于老鼠,互帮互助有时也是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是通过某一篇或某几篇貌似血腥、毫无教育价值的寓言所能展现的。拉封丹笔下的这些寓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通过大量的寓言故事。编制出一幅隐射人类社会的“动物世界”的草图:“物竞天择”的世界是如何的残酷,为求得生存的众生又是如何“各显神通”,这都是读部作品之后的最终收获。批判拉封丹寓言的人没有将寓意隐射的范围上升到全集,也就看不到拉封丹笔下“动物喜剧”的魅力所在。
拉封丹用了大量笔墨来介绍“生存守则”,实际上,他除了希望告诉我们如何生存,也教育我们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追寻“幸福”的方法。而这些涉及“幸福”主题的寓言互为铺垫,互为补充,留给读者的是一本“幸福守则”。不过。如果只对寓言中的只言片语进行解读来理解拉封丹的“幸福观”,就不可避免地将其归为“自我放纵”或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行列。在《寓言集》中可以找到很多拉封丹宣扬“享乐主义”的佐证,例如在《狼和猎人》,他就很直接地表达“享受应当要及时”。这看起来像是“伊壁鸠鲁主义”信奉的格言,我们可以认为拉封丹本人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态度,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作品中谈论如何行乐,而只是通过寓言表达人需要摆脱束缚、为自己而活的观点。“自由”是幸福的根本,这也是拉封丹在《寓言集》中一再强调的,《狼和狗》和《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都展示了这一观点:宁可饥饿也不放弃自由的权利。快乐是自己缔造的。而自由常常会让我们忘乎所以,付出代价。寓言《两只鸽子》讲述的就是一只觉得生活无趣,不听伴侣的劝说,执意远行的鸽子,最后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重返家庭的故事。而该篇牵出的另一主题“爱情”,也是构成拉封丹幸福观的要素,“爱情”常常让人冲昏头脑,《多情的狮子》告诉我们,即便是强者狮子也会在情感中丧失理智,而失去理智即便获得爱情,也有可能并不幸福,在寓言《变成女人的雌猫》,男主人求神将自己的爱猫变成妻子,虽然如愿。但她妻子猫的本性难移,闹出一出出荒唐的笑话。读过《狐狸和葡萄》的人一定觉得它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然而,拉封丹的寓言结语“这样说岂不比发发怨言好?”说明其真实意图并不在此,与之相呼应的是《被人打败的狮子》,狮子认为人类画作中狮子被打败的场景是人类自己创造,如果狮子可以作画,情况将完全相反,由此看来,拉封丹主张的是用快乐的眼光来审视世间的烦劳和困惑甚至是不幸,生活就会频添许多乐趣。
寓言哲学观点的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使得单篇寓言中显得过激和突兀的寓意变得更加生活化和容易接受。我们可以从教导我们“追寻幸福”的寓言解码出一本生动的,极具辩证法的“幸福守则”,而这实际上也是拉封丹留给我们的又一篇隐形的关于“幸福相对论”的寓言。
三、“旁白”的互文
生活在“戏剧的世纪”的拉封丹深受戏剧创作的影响,十分喜欢在寓言中穿插作者的“旁白”,也就是以第一人称进行了评论,“旁白”不一定是寓意表达,它也会展现作者的个人情感,并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期望。在《寓言集》中,拉封丹并没有机械地对所有寓言给予自己的评价和观点,而是有的放矢地,有选择性地参与文本。
拉封丹希望借助寓言中的“旁白”和读者拉近距离,看似随意的表达散落在两百多篇寓言中,它们既是作者分别对某篇寓言的思考,也在整部作品中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如果把寓言家在作品中的思考进行汇总,我们将收获一部拉式“随笔”,它将是《寓言集》不可缺少的补充。寓言中的“旁白”常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总结式。一类是补充式。总结既有对本篇的总结,也有对其它寓言的总结。有的相互隐射,并强化寓意,有的概括性强,是对同类别寓言的综合评价,并将未表明观点表述清楚。例如,《变成女人的雌猫》所暗示的观点“不要盲目追求美的东西”在寓言《临水自照的鹿》中得到呼应“我们重视美,瞧不起实用,/然而美常常把我们捉弄”。这两句可以说是对前者精辟入里的总结。另外,我们在《农人和蛇》一文中能看到作者对之前许多“忘恩负义”的狡猾角色的明确态度:“慈悲为怀当然是好事,但对谁都慈悲却是问题。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到头来个个不得好死。”这篇寓言中的“旁白”也是对攻击拉封丹的人们的回应,实际上,揭示这个世界的“恶”,是为了劝诫善良的人们更好、更聪明地应对它。如果说,面对寓言《乌鸦和狐狸》,《狼和狐狸》中赤裸裸的欺骗,拉封丹选择了“中立”的话,那么通过这一则寓言则能看到作者鲜明的感情色彩和无可辩驳的立场。
“补充式”的干预在《患黑死病的动物》最后可以看到,“看你是有权势的人还是个穷鬼,法院的判决就会定你是白还是黑。”这一句总结是对《狼和小羊》的“强者总归最有道理”中“强者”的诠释。所谓的强者在弱肉强食的大森林靠的是力量,而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靠的就是“权势”和“金钱”了。这样的补充恰到好处,将寓意上升到社会层面,它不仅更为直接地鞭挞了拉封丹生活的“趋炎附势”的宫廷,更让读者理解到“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共性!在寓言《披狮皮的驴子》中,拉封丹讽刺的是“在法国颇有名气”靠“排场”来撑腰的贵族,不过,对于“狮皮”所起的“吆喝”作用,却是《托神像的驴子》中予以补充“穿官袍的人哪怕是傻瓜,那官袍仍是致敬的对象。”如此贴切的注解,反过来又能扩展我们对《披狮皮的驴子》一文寓意的理解。
拉封丹在寓言开始或结尾所作出的点评在《寓言集》中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读者需要全面而深入地阅读作品才能真正地欣赏到它,诗歌体写成的“旁白”相对精炼,如果不能以广阔的视角去探寻寓言之间由“旁白”所建立的思考网络,也就不可能看到《寓言集》较之一般寓言深层次的哲学价值,这正如拉封丹在寓言《猫和两只麻雀》所说:“我们从这桩事能得出什么教训?/没有教训,寓言就不是完美的作品。/我以为看清轮廓,但外表不足为凭。”实际上这已经暗示我们,寓言的内涵需要用心去体会,仅看外表是无法获得完整寓意的。
17世纪的欧洲宫廷还沉醉于戏剧中跌宕起伏的“天人之战”,而拉封丹已经悄无声息地将曾经被人忽略的动物寓言带入到上流文学的领域,寓言文学也由此成为法国文学不可缺少的力量。拉封丹虽然不是寓言的鼻祖,他笔下的寓言故事从内容上看也是继承多于创新。然而,拉封丹通过寓言的相互关联,塑造了一个宏伟的“寓言帝国”。对于一般读者,单独去阅读某一篇拉氏寓言收获不会很大,而通读整部《寓言集》却能感受整个寓言世界带来的心灵震撼。拉封丹在寓言和寓言之间建立起桥梁,使得寓言不再是短小的文学体裁,寓言的互文性让原本孤独的寓言“主角”反复活跃,让指向性单一的文本隐射交相呼应。让作者在文中留下的思考片段成为有无数论据的“哲理散文”。而寓言间形成的共鸣给了我们更多的理解寓言的角度,读者完全可以对寓言网络进行重新编织。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印象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原本单薄的寓意在互动中得到升华。每个时代和地域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文本进行再造。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全新文本,编撰属于自己的《寓言集》,从而让它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应该就是拉封丹寓言能够影响几个世纪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