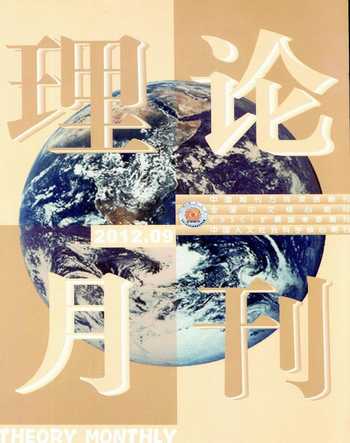数字艺术自由情感本体论
2012-04-29马立新马浩程敏
马立新 马浩 程敏
摘要:美的本质在于自由情感。艺术品较之自然的审美客体和其他人工创作的非艺术品审美客体更容易引发自由情感;而新兴的数字艺术较之传统的原子艺术更容易引发审美主体强烈的自由情感。原子艺术家的创作多缘于虚饰情感,这种情感在性质上属于必然情感的范畴,但其艺术品所激发的却是自由情感,这种自由情感可分为现实型和理想型两种。数字艺术系统特殊的数字技术机制使得艺术家表达本真情感成为可能和可行,本真情感隶属于美的情感即自由情感;数字艺术品除了激发现实型和理想型自由情感外,还能激发超现实型自由情感。另外,数字艺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网络情感,这种自由情感源于数字艺术系统特有的双重虚拟互动性机制。本真情感、超现实情感和网络情感构成了数字美学的核心和数字艺术的本质。
关键词:虚饰情感;本真情感;网络情感;超现实情感
中图分类号:J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76-05
美的本质在于自由情感。艺术品较之自然的审美客体和其他人工创作的非艺术品审美客体更容易引发自由情感;而新兴的数字艺术较之传统的原子艺术更容易引发审美主体强烈的自由情感。但我们尚未洞悉这种自由情感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数字艺术诱发的这种自由情感仅仅是比原子艺术所诱发的自由情感具有更大强度呢,还是在其中生成了某些美学新质,甚而至于发生了审美范型的革命?这是本文需要探明的新课题。
一
关于艺术的情感本质无论是现代的艺术表现论学者(以科林伍德、柯勒律治等人为代表)还是当代的艺术形式论(以弗莱、贝尔、苏珊·朗格等人为代表)学者都存在着部分交集,只不过前者视情感为艺术的原因,而后者则只将情感视为艺术形式的某种特有属性。例如贝尔把艺术的本质看做“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想参与两派之间的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学术论战,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两派跟他们都一直反对的传统的艺术再现论派一样,都在关于艺术情感的性质问题上犯了盲视症。不深入考察情感的具体性质,只空谈和泛谈一般的情感,对艺术来说是一种贬低和侮辱。我们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足以证明这种论调的极大危害。相信一般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永远都不会忘记2500年之前西方大哲柏拉图对艺术的攻击和蔑视。在他看来,艺术除了只能刺激起一般大众非理性的情感,让男人变成女人,让女人变为儿童之外,再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真理的成分。所以。在他的影响极大的巨著《理想国》中,他公然发出了把艺术家和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的倡议。显然,在他眼里,艺术不仅不能提供理性,即使其情感对公众也是有害的。这显然是柏拉图对艺术所持的武断和粗暴态度造成的,完全不符合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真实存在面貌。究其根源。我认为还是归咎于柏拉图缺乏对艺术情感性质的深刻认识。
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人类的情感有两种性质。即自由情感和必然情感,前者隶属于美的范畴,而艺术作为以审美为其合法性存在理由的本质就在于与自由情感而不是别的其他情感有关联。显然,数字艺术无论其血缘如何新奇、如何高贵、如何超越,只要它还是以艺术的身份与社会共存,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那么在追求自由情感、表达自由情感、传播自由情感和弘扬自由情感四个方面必须继续坚守。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但现在我们要对以上关于艺术和数字艺术本质的论断实施更加严格的CT探测,以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不实的成分和任何特殊的质素。
我们第一个要追思的问题是:原子艺术中所凝结或蕴含的情感是否真的就是自由情感?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原子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和追求的情感是否就是必然地归属于自由情感的范畴?看似合理合情的问题如果认真拷问就会感觉很有问题。这也难怪,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中,艺术家都是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天然就是情种,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创作出那些感动我们的作品呢?然而,天然的情感丰富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就情感丰富,也不意味着他所表达的这些丰富的情感就一定是自由情感。自由情感的本质在于没有实际的外向功利性的驱使。而这种实际的外向功利性对原子艺术家和数字艺术家来说都同样是无处不在的。有的艺术家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赚钱,有的艺术家是想借自己的作品而扬名,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还有另外一些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并没有这些比较世俗的动机,而是怀有某种高尚的艺术理想,如鲁迅写小说就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劣根,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也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如果鲁迅的文学动机是救国救民,那么中国古典文人长期传承的“文以载道”思想难道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吗?“疏导人性,教化人心”难道不是另一种社会功利性吗?再看看以求真为核心诉求的西方艺术传统,看看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的油画,读读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伯雷、但丁、歌德、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些被列入世界上最伟大作家行列的人的作品,谁能怀疑其共同的社会和人生改造的宏伟理想和社会担当?我们看到了,一种是基于世俗的功利性动机,一种是基于高尚的功利性动机,但其明显的外向功利性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
我们并不是就此指责这些伟大艺术家们的情感本身,我们只是想让诸位看清楚或者意识到,如果一个作家怀着这样一些动机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那么他所表达的这种情感还能算得上自由情感吗?如果说这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创作的。那么其他的那些艺术家能被指望基于其他别的动机吗?整个原子艺术世界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客观的说,原子艺术家们从生活中体验到的情感是包罗万象的,既有自由情感,也有必然情感,当他不怀有这些明显的外向的功利动机,而将自己从生活中所获得的真实体验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自由情感。可是不幸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将原子艺术家所刻意表达的这种情感归属于必然情感的范畴,但是原子艺术家们所表达的这种必然情感显然又不同于那种社会人司空见惯的见利起意性的必然情感,后者虽不自由但却自然发生,所以是一种自然情感,正因为这一区别,我们将原子艺术家的这种情感特称为虚饰的必然情感,简称为虚饰情感。虚饰情感实际上就是基于某种表现目的的人造情感。本来从生活中体验到的并非这种情感,但出于上述两种动机,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创作理想,在意志的驱动下,艺术家营造出一种或高尚或世俗的人造情感。这里有个绝大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这就是是否真的存在人造情感?人造情感是否具有普遍性?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无疑的。所谓人造情感显然是与自然情感相对而言的。自然情感也就是人类在与客体互作的过程中被激发产生的各种喜怒哀乐,每一种具体的情感都必然有一个相对应的刺激源。我伤心是因为我被好友欺骗;我激动是因为我工作上有新的突破或者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情人。但是,社会中的人也广泛存在着另一类情感。见了你的上司,本来心里憎恨他或者鄙视他,可是你还是强迫自己面带笑容跟他主动打招呼,你的强颜欢笑不是一种典型的人造情感吗?你的同事晋升了,你本来是充满了嫉妒,可你跟他说出的却是祝贺的话。你这样做固然是有违你真实的情感,可听到你祝贺声后,你的同事也未必真的从内心对你表示感谢,尽管他很可能口头上立即表示“感谢”,这样你和同事的这种互动情感都不能说是出于本心和真诚。据我观察,现实中的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所表达的都是这种类型的情感,这就是我所界定的人造情感或日虚饰情感。这种情感主要见诸于社会公共领域。所有这些情感的产生和表现都带有极其明显的功利目的,即为了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是基于个人本位或者自我利益的一种情感。这与原子艺术家们那种基于社会公共目的的虚饰情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无论是原子艺术家所表达的这种虚饰情感。还是一般社会主体所展现的那种虚饰情感,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公共性和虚伪性。
大部分古典和现当代美学家都没有洞悉艺术情感的本来面目。当代美学界影响较大的美国学者苏珊·朗格在探寻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关系方面造诣精深,而且与其他同类学者不同的是,她还进一步分析了艺术情感的性质,认为这种情感不是艺术家个人的私情。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普遍情感。”“音乐的作用不是情感刺激,而是情感表现;不是主宰着作曲家情感的征兆性表现,而是他所理解的感觉形式的符号性表现。它表现着作曲家的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着他对于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这些可能超越他个人的范围,因为音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符号形式。通过音乐,他可以了解并表现人类的情感慨念。”我们认为苏珊·朗格所谓的“普遍情感”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我们刚刚分析的虚拟情感。不难理解,原子艺术家在营造虚饰情感的时候,并非是没有任何审美尺度的。鉴于他已经放弃了本应该尊重的自我尺度,就只能从外部来寻觅。这个外部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具体的他人,只能是一般的社会大众。既然如此,这种情感从性质上讲就属于一种公共情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然而,苏珊·朗格所提出的这种“普遍情感”到底真实存在着呢还是纯属她自己的某种哲学构想?我们不能不细细考究。根据我们的论证和体验,凡情感都具有个人性、具体性、特殊性、当下性和现场性,其他场合不可能存在任何情感。所存在的只能是对已经消失了的那种情感的观念和理解。这就是说凡情感都是指具体的活着的某一个人的情感,这样,所谓社会情感、普遍情感、一般情感的说法难道不让我们费解吗?我的情感是具体和特殊的,你的也是这样,他的同样如此,那么社会的情感代表的是谁的呢?或者说谁才能体验到一种所谓普遍的情感呢?固然。面对同一客体,不同的人可能产生某种类似的情感,但我们之所以敢这样说,也是在事后彼此之间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的,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彼此谈论的只能算是一种对情感的理解和观念了。鉴于人性在社会交往中的求同存异性质,大家往往趋向于保留自己真实的体验,传达某种社会认同的观念,以免被社会孤立和隔绝。所以,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即使真的存在某种社会普遍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也是社会共同的虚饰情感,因此,苏珊的观点只是间接证实了我们对于原子艺术家情感性质的判断,并没有其他新鲜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原子艺术家自身所表达的这种虚饰情感物化为文本符号之后,就不再属于这种情感本身,而是由欣赏它的具体对象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鉴于那些功利性因素都不存在了,故而原子艺术作品所刺激起的接受者的情感则属于自由情感,只是这种情感的强度一般的小于数字艺术作品。
与原子艺术家相比,数字艺术家在审美诉求方面发生了重大嬗变。从迄今数字艺术所展现的美学景观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些迥异于原子美学的新质。最突出的一点是数字艺术实现了一种新型的自由情感——-本真情感。本真情感的实质是一种自然情感,就是一种存在于世俗社会中普通人心灵中的真实情感。真实情感存在于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原子艺术家之所以忽视真实情感而刻意营造虚饰情感一方面是囿于传统的原子艺术成规和教条,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原子创作的单向度线性模式。此外与原子艺术家本身固有的功利性的创作动机也难脱干系。
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彻底摧毁了原子艺术赖以生存的原子机制。把艺术家从上述这些精神和物质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自动赋予了数字艺术系统独立于原子艺术系统的特殊艺术机制,这就使艺术家获得了表达本真情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原子艺术的文化成规是讲究微言大义和“文以载道”,所以原子艺术家的本真情感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他们的日记和家书这些纯粹私人领域来表达。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越是到现代,艺术家们本真情感诉求就越强烈。所以,我们读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阿Q正传》也同样能产生那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其原因无非是其情也真其意也切。但是你读茅盾的小说、读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甚至读《红楼梦》我相信一般的读者都在感情上难以激起共鸣来。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原子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的目的要么是为了牟利,要么是为了扬名、要么是为了某种社会责任。要发表就要按照某种社会公认的艺术成规和审美心理来创作。因为发表权不在艺术家自己手里掌握,而是被大众媒介所控制,而大众媒介对作品的裁决机制又是等级森严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数字艺术系统中一去不复返了。数字艺术系统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的新媒介——互联网。这种媒介的特质之一是介入方式上的相对平等和极低门槛。只要遵从通用的国际互联网组织协议,任何个人都可以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自己全权拥有的网站上任意发表自己的艺术品。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艺术品在你自己感兴趣的别人的网站上发表而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这里任何绝对化的反驳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在这样的新型媒介和新型发表机制下,艺术家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完全可以写自己所欲写,书自己所欲书,而不必唯编辑的眼光是从,也不必唯受众的喜好是从。因此,数字艺术较之原子艺术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本真情感的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艺术系统对受众来说较之原子艺术系统具有大得多的互动性、开放性和民主性。对任意一件数字艺术品,接受者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借助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真实兴趣。对于很多直接诞生于互联网系统的数字艺术品而言,甚至这种诞生本身就离不开接受者的直接参与,比如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笼就是由包括很多接受者在内的作者们共同创作出来的。这些数字看客不必再像原子看客那样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审美趣味,更不必再一味接受或者尊重某些艺术精英的审美判断。他们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任一数字艺术品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基本上不太会受到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意见的压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他看到很多人都对一部数字艺术品叫好的时候,他依然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审美判断不动摇,并且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在网络上表达。所有这些在原子艺术系统内部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传播学中那个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理论。深究其原因。数字艺术系统特有的互动性、开放性和民主性归根结底是数字艺术所赖以生存的数字技术媒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传播机制的新型传播机制——私人传播。这种私人传播的基本特点是:第一。数字媒介为媒介拥有者和使用者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私人领域,一台电脑外接一根有形或者无形的网线立即就为主体生成一个独立的私人领域。第二。在这个领域内,主体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和保密权,他在这个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只有他本人才承担责任和义务。未经主体同意,任何他人都无法侵入这个领地其中。第三。借助于这块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媒介本身,主体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不受他人和外界干扰,基本上能做到随心所欲。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机制的存在,数字艺术系统表达真实情感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再来对比一下原子艺术系统。在原子机制下,原子媒介基本上属于一种准公共媒介。人们看原子电影听原子广播当然是在典型的公共空间进行;电视媒介虽把这个公共空间缩小到家庭或者办公室内部,但从性质上就这个空间依然属于公共领域。在这样的空间内活动,一个人的艺术趣味由于受到来自这共空间的群体压力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的真实的表达,所以就有了所谓“意见领袖”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区别。前者的审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消解和遮蔽了这个公共空间内其他成员的审美趣味。传统的报纸杂志看似不同于原子电影电视和广播的情况,但它们与数字媒介提供的那种纯粹私人空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跟原子电影电视一样都是单向度传播的,一般读者在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实现自己的审美自由,只能单方面地被动接受强势的审美信息。所以,唯有数字艺术系统才能提供纯然的私人领域。置身于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艺术世界,艺术主体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自由。当他们借助键盘和鼠标激扬文字、点击江山的时候,他们不必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们只要愿意就完全可以一览无余地宣泄自己的真性情。正是这种真性情构成了数字艺术的新的美学内涵之一。正也是这种本真情感的普遍存在,才带来了数字艺术系统自由情感的质变。
除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的真性情,在数字艺术系统里,人们还可以尽情地放松地交流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趣味。也就是说,数字艺术可以真正实现康德所谓的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数字艺术家在这里可以完全不必考虑通常原子艺术家们经常考虑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功能、人生培育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等这些外在的东西,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趣味。我们所看到的数字艺术极度多元化的审美景观就是这种审美趣味自由表达的自然结果。数字艺术特有的这种本真情感完全归功于我们上述所揭示的特殊物理和技术属性,这种因果关系在此无需再重申。
二
数字艺术在自由情感构建中的第二个优异表现就是大大开拓了这种情感的强度,将人类的审美经验提升到无限的深度和广度。艺术无疑在人类审美经验的社会建构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任。可以说,迄今人类业已形成的审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艺术的运动。原子艺术帮助建构人类审美经验的途径不外乎两条:即现实的途径和理想的途径。现实的途径比较地接近于人类的生活经验,因此这条途径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再现的艺术创作方式,将源于生活和现实的那些必然情感转化为艺术文本呈现出的自由情感,因此这种途径所实现的目的艺术文本因其最大程度地接近现实、历史和人生本身而容易诱发人们的以同情或移情为特征的自由情感。这种同情或移情机制源于自然人生,但强度超越自然人生。比如说,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经常见到这样的事情: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而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一辈子无怨无悔。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妇女,我敢肯定这样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个。可是当我们在现实中见到听到甚至亲身感受着这样的情感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受到强烈的触动。然而,这个主题一旦被纳入到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艺术中,就会产生出一种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我们就会深深地受到感动。这就是现实型艺术塑造人类审美经验或审美情感的一般方式。很容易理解,现实型途径主要是通过再现和揭示生活的真而达到美的终极追求的。
与现实型途径相比,理想型途径具有更宽广的艺术表现力,它通过运用一系列性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夸张、象征、通感、意识流、本质直观等来塑造区别于现实的艺术形象。由于这些艺术形象都与现实具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超越了一般人的审美经验,所以这类艺术实际上是对人类审美经验的拓展。如果说现实型艺术形象在审美效应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引起审美主体的情感共鸣即同情来实现的。那么理想型艺术形象则主要是通过引发审美主体奇特的情感体验来吸引受众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数字艺术大大超越了原子艺术的审美功能。借助于计算机超强的智商和其特有的属性,再加上创作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理论上讲数字艺术家可以创造出无限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景观,从而实现原子艺术难以企及的梦想。数字艺术的强大艺术表现力突出地表现在可以将理想与现实不受时空限制地任意组接、合成、转换和创造,这一点已经在方兴未艾的数字电影、数字动漫、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数字艺术上获得了有力的证明。在这里我们想重点分析一下数字电影为人们所展现的魅力景观。相信很多读者都观看过《阿凡达》,关于这部电影的审美体验尽管可能不尽相同,但在描述这种体验本身的时候,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个词汇“视觉奇观”。作为这部电影的观众之一,我也想不出更合适的其他词语来描述自己的审美感受,所以也接受了这一称谓。这种“视觉奇观”的性质当然是自由情感。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原子电影的那种自由情感,说它超越现实当然是毫无争议的,但将它归为理想型的自由情感也不合适,只要一想想诸如《红色娘子军》、《大闹天宫》等我们所熟悉的理想型的原子电影的画面和形象,再比较一下《阿凡达》的画面和形象,就马上会感觉出显著的差异来。前者的人物和环境的理想基本上囿于我们的想象之内。是与现实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比较近;而后者原则上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理想人物或理想性格,像其中的那些外星人从未出现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之内,类似的还有《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机器侠》中的机器侠、《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汽车人爵士、汽车人救护车和铁皮等,这些形象的功能完全不同于前者的象征或隐喻作用(原子艺术中像孙悟空、太阳、月亮、死水、甲壳虫这类形象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外形的理想,而在于外形背后的意义诉求的理想),没有承担原子艺术家所寄予厚望的重重的外向功利诉求,似乎只是作为叙事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吸引观众眼球、刺激观众情感的单元而存在的,但它又的确是生活现实中所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如果将其归人原子艺术中的那种理想型情感并不名副其实。为此,我们暂且将数字电影创造的这种“视觉奇观”情感称为超现实型自由情感。其他数字艺术如数字动画、网络游戏等类似于数字电影所激发的这种情感。显然,数字艺术派生出的这种超现实情感是原子艺术所没有的。是自由情感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一次质变,这是数字艺术情感属性的第二个特质。藉此,数字艺术在短短时间内就超越了原子艺术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奋斗才建构起来的美学大厦,将人类的审美经验导向了一个新的高地。
三
但是,并不是每一种类型的数字艺术都能诱发超现实情感。确切的说,只有那些主要诉诸于视觉的数字艺术才有可能,如数字动画、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绘画、数字图片等;而另一些数字艺术类型虽在这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却创造了不亚于这种情感效果的一种新自由情感——网络情感,这就是基于互联网虚拟互动性所派生出的那种自由情感。网络文学、网络游戏、QQ、MSN、博客、播客、微博,甚至包括一切基于互联网运行的艺术都能诱发这种情感。互联网所提供了这种崭新的互动性,是在计算机人机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人互动。这一特征是我们必须重点考察的,因为正是这一特质赋予了数字艺术超越原子艺术的另一情感力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互联网互动现场。关于网络文学创作和网络游戏的参与体验中的互动性,前面做了详尽的描述。这里我就再举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中的聊天室来考察。凡是上过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差不多都有通过各种聊天软件聊天交友的经历。根据我的观察,聊天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匿名注册,零门槛进入;二是必须互动,否则只能看别人聊,而聊天室这样的看客极少见,往往是因为找不到互动对象而退出;三是总是倾向于异性间进行。如果知道对方是跟自己同性后便会迅速降低继续交流的欲望;四是以情感为最主要的聊天诉求,但往往刚接触的时候不直接介入情感话题,等到一定了解后总会转入其中,最后又往往是因为在这个话题上出现分歧而中止聊天或者交往;五是一旦遇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聊天对象便会激起强烈的快感。并极容易降低对其他聊天对象的交往欲望:六是一旦有了固定的聊天对象极容易对聊天室产生强烈的期待和依赖心理,这种表现可能为焦虑、想象、不安、兴奋、紧张,严重的甚至产生幻觉等情感反应。
跟聊天室性质、参与机制相似的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品种还有MSN、QQ。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某些跟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那里同样的情况,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比原子艺术更容易刺激起审美主体某种强烈得多的自由情感。甚至让人们产生强烈的精神寄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瘾。鉴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为网瘾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心理问题。所以现在是到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追思的时候了。
较之原子艺术,数字艺术具有特殊的智能辅助,这让其平添了一支腾飞的翅膀,但是这支翅膀更主要的是赋予了它自身某些更具感官冲击力的元素,单凭这些客体本身的审美元素尚无法圆满解释上面的问题,因为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虽然让我们喜欢,却很难让我们上瘾,这正如我们对自己特别喜欢的原子艺术一样,喜欢归喜欢,却不能达到上瘾的程度。再根据刚刚对聊天室的分析,尽管这里完全没有《阿凡达》为我们提供的奇异世界,却能深深地让我们陶醉其中甚至不能自拔。这样一比较,再综合起来考虑。唯一的答案只能从互动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这一特质中来寻找。
那么,互动性真的就有这种特殊的作用吗?凡是有互动性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这种功能吗?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互动性并不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特有的,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情感的基本桥梁。通过这种正常的社会交往机制,每一个人都认识和了解了对方,让陌生人变成了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爱人,我们自身也被别人所接受。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人体验到的友情、亲情和爱情这些人类最宝贵的自由情感。当然社会中的互动性更多的情况下是直接的、公开的、甚至面对面的,而我们所获得情感也远非以上这些自由情感,不满、愤怒、鄙视、骄傲、自豪、憎恨、嫉妒、痛苦、幸运诸如此类的必然情感更为常见。因此,我们只能说,有互动就必然有情感,而不能说有互动就必然产生自由情感,更不能说就必然产生强烈的自由情感。
所以,为了揭示数字艺术的真正情感秘密,我们还得回到数字艺术现场去进一步考察那里的互动性是否跟我们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互动关系一样。我们发现。无论是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还是网络游戏的互动关系,抑或是聊天中的互动关系,都跟社会中的人际互动完全不同。我们观察到,在所有这些数字形式的互动中,当事人双方是互相隔离的。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在这里遇到你不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的动机,而是纯属偶然。我对你的作品感兴趣只是因为我喜欢它,对你本人究竟是谁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你对我的创作的意见比如说赞扬,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人的本性让我产生了一种关注你的欲望,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我更期望你从此更加关注我的作品。如果有几天你不来看或者没有你的评论。我就自然产生了某种焦虑和不安。在聊天室也是同样如此。在网路上邂逅一个人一开始多数情况下纯属偶然,甚至有种萍水相逢的幸运感。短暂的互动可能让两个本来完全陌生的人知道了彼此的兴趣、爱好。然后可能进一步知道身份、年龄。在互动中,对对方了解的越多,就可能越想了解更多的东西。每一次了解从理论上都降低了自己对对方的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会产生出新的不确定性来。而且,彼此之间因为有网络的天然阻隔。对对方提供的信息真实与否总是难以判断。即使借助于网络视频看到了对方的真面目,也不能完全确信对方的信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陌生性机制中,很快就让一个人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甚至暂时忘掉了世间的一切烦恼,让自己缥缈在无涯无际的网络空间中。在我看来,这正是数字艺术最特殊的最大的魅力所在。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数字艺术特有的网络情感性质归功于这种艺术特有的虚拟互动性。
网络情感的属性和原因都不同于超现实情感。其一。网络情感的强度未必很大;其二,网络情感不是直接的视觉刺激反应,而是源于虚拟空间的持续不确定性互动机制:其三,网络情感极容易产生依赖性。实际上,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本真情感、超现实情感和网络情感就是数字艺术特有的三大情感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数字艺术的本质规定性——数字美学。正是靠着审美诉求上的这一本质规定性,数字艺术与原子艺术划清了界线。
责任编辑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