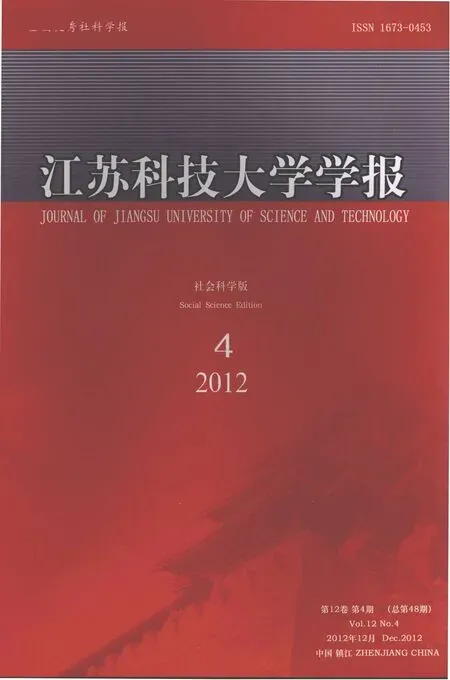孔子的乐论
2012-04-18黄子明
黄子明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
一、“乐者,乐也”——“乐”的含义
《礼记·乐记》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1]1074“音”和“乐”含义不同,“音”指的是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乐”则是表演出来的音乐,广义的“乐”包括诗、歌、舞。篆字“”,其下部分是一个木架,支撑起上面几个鼓。对于字的上半部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道:“象鼓鼙,谓也。鼓大鼙小,中象鼓,两旁象鼙也。”[2]265中国古代的鼓有形制的区分,小的叫鼙,大的叫鼓。这个字的上半部就是中间一个大鼓,旁边四个小鼙。
现代人会觉得,鼓在一个乐队中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乐器,但是在音乐形成史上,没有鼓是不可想象的。首先,鼓是体现乐曲节拍的重要乐器。原始部族的音乐曲调可能很简单,但是一定少不了明晰的节拍,否则就不成其为音乐。原始的音乐可能产生于击掌而拍带来的节奏感,后来就发明了鼓来代替。先秦典籍中非常重视鼓在乐队中的作用,将鼓视为最重要的乐器。《礼记·学记》中说:“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1]1070为什么鼓这么重要?因为击鼓可以调整音乐节奏,曲调是依附于节奏的,节奏一乱,再优美的曲调也不能成形。所以古人认为,没有鼓带来的节奏,五声就无法协调。其次,鼓是令人振奋的乐器。人在激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心脏剧烈有力地跳动,鼓声似乎是将这种内在的激昂外化出来,既加强了内在的情绪,又达到与他人的共鸣,形成群体性的亢奋。《礼记·乐记》中说:“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1]1128鼓声有振奋人心的效用,因而常用于古代战争,中国古人作战号令都是击鼓进军,鸣金收兵。鼓声能使群情振奋,适合于进攻性作战。一个好的鼓手会根据战斗情势调整节奏以鼓舞士气,这种作用是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鼓在乐器中地位特殊,也体现于汉语使用中。古汉语中“鼓”可做动词,表示演奏乐器,如“鼓乐”“鼓琴”“鼓瑟”等,其他乐器名词在语言中没有出现这样的使用情况。现代汉语中有“鼓舞”“鼓动”“鼓励”“鼓劲”“鼓掌”等,这些词都是用来表达对人的精神及情感的激励。
“鼓”可以激荡人的情感,与鼓相关的“乐”也和人的情感世界紧密相连。《礼记·乐记》中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1]1075音乐与情感的这种联系引申出与心情相关的含义,即快乐。《说文解字注》说:“乐之引申为哀乐之乐。”[2]265第一个“乐”是音乐的“乐”,后面两个“乐”则是快乐的“乐”。现代汉语中,表“音乐”的“乐”和表“快乐”的“乐”仍然是同一个字。“乐”这个字本义是音乐,快乐是引申出来的含义。《礼记·乐记》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1143
在先秦诸家中,道家偏重自然,法家偏重人为,儒家则介乎二者之间,它从两方面分别体现于“乐”和“礼”的精神。“礼”分出人的等级差异,对外在的行为加以规范;“乐”引起自然情感共鸣,达到内在的协调。《礼记·乐记》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典型体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1085“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1]1086。但是,先秦诸儒对待礼乐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这要归因于他们思想体系的差异。总的来说,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孔子是这三者中最强调内在和谐的。《孟子》一书对音乐的探讨非常少,孔子、荀子对音乐关注较多。荀子把“乐”与“礼”放在齐平的位置,“乐合同,礼别异”,强调现实的社会调节功能;孔子虽然认为礼乐同出于“仁”,但“乐”是高于“礼”的,看重个人的理想人格修养。荀子亲自著书,对音乐问题有专章论述,行文理性而冷峻;孔子坚持“述而不作”,《论语》只是追述他生前的只言片语,虽没有对其音乐思想进行集中而系统的阐述,却随处洋溢着孔子对音乐的巨大热情。
二、“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对音乐的挚爱
江文也先生在《孔子的乐论》一书中提出,“孔子是音乐家”。典籍中记录的孔子与音乐相关的轶事有很多。
先秦时期所指的“乐”往往包括了诗、歌、舞在内。可见,孔子的音乐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论语·述而》提到:“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3]97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果发现人家唱得好,就一定让他重新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子于是日哭,则不歌。”[3]87孔子在某一天参加丧礼哭过,于是当天都不再唱歌了。吉联抗的注释说:“反之,可以看作孔子平时每天都要唱歌。”[4]3《论语宪问》提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3]201孔子在卫国,有一天正击磬,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有心呀,还击磬呢。”最著名的一则故事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89人最直接、最容易获得的快感是饮食所带来的快感,肉又是所有食品中最容易让人产生快感的,孔子听到韶乐,三个月感觉不到肉的滋味。可见,对音乐的专注与沉迷使他完全超越了感官欲念的满足。
甚至在危难时刻,孔子也不离音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5]759《论语·卫灵公》中也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3]207的记载。孔子在陈国被暴民围困,师徒一行人粮食用尽,很多人病倒。《史记》上描写的孔子非常淡定,仍旧是授课讲学,弹琴唱歌。《论语》少了“讲诵弦歌不衰”的记载,没有孔子临危表现的相关描写,但《史记》的记载应该大致可信。“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在一行人生死未卜的危难关头,如果不是因为孔子表现得异常平静,以致让人怀疑他要么冷漠麻木,要么束手无策、故作镇定,子路又怎么会愤而责问自己的老师。《庄子·让王》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与《史记》相吻合:“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6]《论语》没有交代孔子的表现,就直接写子路怒气冲冲地责难老师,显得有些突兀。孔子对子路的回复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本来不免于困境,小人一遇危难就焦虑不安,行为失措。身处绝境依然能鼓琴而歌,不仅体现出他临危不乱的气概,也显现他对待音乐的深挚之情。音乐之于他,绝不仅仅是家常燕坐的一种娱乐手段、一种修养功夫或是一技之长,更是危难时刻的精神慰藉,是其精神世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孔子是否做过音乐资料的编撰工作,学界对此看法不一。《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5]762《诗经》三百余首都经过孔子一一配乐演唱,《六经》为其所编修。冯友兰先生则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孔子时代还没有私人著作[7],因而不可能对《诗》《礼》《乐》等进行编撰。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对《诗经》及其曲调确有精研。《论语·子罕》讲到孔子自述其“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118。他对音乐进行了整理修正,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原应有的曲调。
三、“乐则韶舞”——乐与仁的关系
礼乐本自西周以来“既是社会政治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也就是“礼乐作为社会制度层面崩坏了”。但是,它作为道德规范、教育思想和文化精神仍然活跃着,“礼乐之所以蝉蜕制度层面而成为纯文化,不仅是社会历史潮流使然,更是儒家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所致。”[8]音乐本来就与道德教化有关,《易经》道:“先王以作乐崇德。”[9]《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1081孔子将礼乐传统与自己的仁学思想结合,使乐与德的关系获得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孔子对音乐的欣赏是有其标准的。《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反对将礼乐作肤浅化的理解,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238礼绝不仅仅是一些礼节仪式,乐也绝非只是吹拉弹唱。《论语·八佾》记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0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内在的仁心,礼乐无从谈起。孔子反对空洞而形式化的礼仪,《八佾》篇表明了这种态度:“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3]30对待音乐,孔子看重的是从和谐的乐调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意涵。在《八佾》篇中,孔子将韶乐和武乐进行了比较,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3]45。“美”是就外在形式而言,指声音的丰盛悦耳;“善”是就内容而言,指音乐体现出的道德境界。孔安国注释认为,韶乐传为舜帝的乐舞,舜帝禅让天下,所以是“尽善”;武乐传为周武王伐纣而作,以征伐取天下,所以是“未尽善”[4]3。孔子赏乐不仅是从艺术的层面,更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层面着手。
孔子常和宫廷乐师探讨乐理。《论语·八佾》说:“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徼如也,绎如也。以成。’”[3]43-44孔子和鲁国的乐官讨论奏乐的道理,认为音乐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众乐器合奏,多种音调齐发,音容盛大;展开下去,呈现出高低和谐、节奏快慢分明、连绵不绝的气象,最终构成了一部乐曲。孔子体味的音乐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的故事。他对乐曲的掌握有一个渐进过程,先是“习其曲”,学会曲调;接着“得其数”,即掌握弹奏曲子的技法;然后“得其志”,领悟到曲子蕴含的情志;最后是“得其人”,参透曲作者的为人,并猜到“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5]756。《史记》甚至写到孔子操曲之后对文王外貌的臆测,这虽有些夸张,但将音乐的风格韵味与作者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却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高超的音乐技巧,更需要对音乐内容的悉心领悟,所以师襄子对孔子佩服不已,赶忙“辟席再拜”。
在《论语·卫灵公》中,颜渊向孔子请教治国安邦的道理,孔子在音乐方面提出:“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3]210-211孔子将放弃郑声与远离小人并列,认为坏的音乐使人放纵,就像阿谀小人使人受害一样。孔子将音乐品质的影响提高到国家管理层面来谈,这体现出儒家对音乐的重视。孔子对音乐的品评体现出一种中庸的态度,“郑声淫”的“淫”本意是过度,引申为使人放纵,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思无邪”[3]14。他在《论语·八佾》中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41《关雎》篇展现的快乐和悲哀都没有过度,因而得到孔子的肯定。
孔子主张“里仁为美”[3]47,仁是内在的“质”,礼乐是外在的“文”。“质”是根本,但“文”也并非不重要。《论语·颜渊》道:“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3]160-161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够了,何必还要那些礼节文饰?”子贡的回复是:“本质就像文采,文采就像本质,都是同样重要的。虎豹的皮革如果失去了毛的文采,就和犬羊的皮革一样了。”《雍也》篇有孔子对文质关系的表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78其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流于粗野,文采多于本质则不免虚浮,只有二者配合恰当,才是个君子。这里虽是独白,也可看做是孔子对于棘子成之类思想的回应。君子必须文与质两不偏废,音乐之于一个修养完备的仁者是必不可少的。
四、“成于乐”——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朱光潜先生曾说:“儒家本来特别看重乐,后来立论,则于礼言之特详,原因大概在乐与其特殊精神‘和’为修养的胜境,而礼为达到这胜境的修养功夫,为一般人说法,对于修养功夫的指导较为切实。”[10]谈“礼”主要是功夫论,而论“乐”则更多的是境界论;“礼”讲究外在行为的约束,“乐”强调内心情感的协调。在先秦诸儒中,孔子最重视内在情感的协调和人格境界的修成,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音乐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可以用《论语·泰伯》中的一句话概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104首先,人的学习开始于诗。诗本是歌词,诗教一般包含于乐教之中,但有时诗与乐分离而论,指音乐的文字内容。《论语·季氏》讲述了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的故事:“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3]230孔子独自立于庭上,见到孔鲤,就问他“学了诗没有”,并告诫说“不学诗,就不知道如何说话”。后来又一次见到他,又问“学了礼没有”,并教导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为人”。“言”属于理智的层面,学“诗”是教育的启蒙阶段,是传授知识。孔子是看重“言”的,《论语·子张》有子贡对孔子的评论:“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3]263子贡认为,君子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有知,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老师的高不可及,就像天是不能靠梯子爬上去的一样。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语言表达,平日说话很谨慎、很有分寸,具有智者风范。他对孔门子弟的教育是从“诗”开始的。
第二,礼使人立身处世。《论语·泰伯》中谈到礼对人行为的指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3]101恭敬而无礼则劳苦,谨慎而无礼则畏惧,勇敢而无礼则会作乱,直率而无礼则尖刻伤人。内在的良好品德必须依靠礼的指导,并通过恰当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如果行为不以礼为规范,就无法立世为人。礼是就道德实践层面而论的,较之理智的层面有所提升。
第三,理想人格的最后完成有赖于乐教。《论语·尧曰》中说:“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270“言”使人智,“礼”使人立,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孔子不满足于理智的澄明和行为的规范,他理想的人生境界是要打通自然本真与外在约束的界限,使二者浑然一体,无所区分。只有审美的艺术才可以让人达到这种境界,“成于乐”意味着教育和人格养成的最后环节。音乐是在冲突中求和谐,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人就能逐渐参透协调的精髓。在《论语·为政》中有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15孔子十五岁开始治学,首先当然是钻研“诗”,三十岁明白了“礼”才得以安身立命,以后就是境界的提升了,四十岁能不为外物所迷惑,五十岁算得上是一位“知天命”、懂得人生、穷通道理的君子,六十岁听到各种意见都不会觉得不顺,七十岁终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外在的约束与内心的需要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乐”的精神。《论语·雍也》中说:“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3]78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想做的一切都是自然合乎规矩的。反过来也意味着合乎规矩的也正是心中所想要的,这也正是“乐仁”的境界。“快乐”本来就是从“音乐”一义中引申出来的,“乐仁”也是通过审美的乐教达成的。李泽厚先生说,“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中国的传统……是由道德走向审美”[11],这在孔子的音乐思想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陈望衡先生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应理解为时间上的先后程序,而是逻辑上的环节[12]。诗教、礼教、乐教是同时进行的,它们分别从知识、实践和审美的方面对人格养成产生不同的影响,最高层次的乐教成为实现完美人格的点睛之笔。
通过对《论语》中乐论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孔子并非常人所想象的严肃刻板的道德说教者,而是颇具浪漫气息的音乐爱好者。他在潦倒的时候依然吸引大批弟子跟随,光靠博学是不够的,还与他那富有艺术气质的人格魅力有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并对其进行理论深化,强调乐与仁的结合,全面挖掘了乐在道德实践、个人修养、社会制度及风俗教化等各方面的意义,极大丰富了乐论的内涵。后来的儒家学说偏重谈论礼,对乐的推崇没有人及得上孔子。他视乐教为教育的最高层次,把理想的人格境界和行为规范都归结于音乐的精神,使伦理道德呈现出审美的特质,徐复观盛赞“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13]。
[1]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吉联抗译注.孔子、孟子、荀子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3.
[5]许嘉璐,安平秋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6]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981.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9 -50.
[8]聂振斌.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J].江海学刊,2005(3):16.
[9]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5.
[10]朱光潜.朱光潜谈美——东西方美学的经典阐述[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206.
[11]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54.
[12]陈望衡.论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J].求索,2003(1):210.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