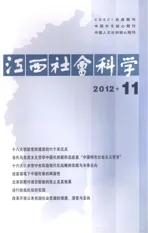地缘认同:客家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心理共识——以清末和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为例
2012-04-18肖文燕
■肖文燕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梅州是中国著名侨乡,更是广东省重点侨乡,有“华侨之乡”的美誉。梅州社会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梅州是客家的大本营,是客家腹地的中心,素有“五洲客家半梅州”之谚,被尊称为“客都”。本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全国著名侨乡——广东梅州为例,探讨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影响侨乡社会的心理因素——地缘认同。
在侨居国,华侨社会具有鲜明的特质,即保持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并按一定的原则形成不同的集团或帮派。华侨中,十之九为闽粤两籍人,而又以原籍乡土区别集团而分为五帮,即广府、客家、福建、潮州、海南。其中,客家帮为广东东北部一带出生之人,主要集中在广东梅州的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等县。[1](P113)可见,梅州华侨属于典型的客家帮。上面所指的“地方色彩”,即为本文论述的“地缘认同”[2](P55)。
地缘是指华侨因祖籍地域相同而结合起来的一种关系,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同乡”。它的范围可大可小,大而至一个省甚至扩大到两三个省;小的仅限于一个县或一个乡村,所以有“大同乡”、“小同乡”之分。海外华侨的“四缘”[3](P9),地缘、血缘、善缘、业缘,最先是由地缘关系开始的。所谓地缘认同,是一种对居住地区以及这一地区人文景观的归属意识。就此而言,海外华侨作为由中国迁出去的移民群体,其地缘认同必然会由中国祖籍地向海外居住地迁移。由于东南亚华侨地缘组织相当活跃,而且客家梅州华侨大多侨居东南亚地区,因此本文就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进行阐述。
一、地缘认同:华侨日常生活的逻辑
华侨的地缘认同从他们移居海外这一刻起就已经发生,不同时期其强烈程度不同。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心态处于“叶落归根”时期,此时华侨对祖籍地的认同尤为强烈。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华侨的身份和政治认同都由中国化变成当地化,华侨的心态开始由“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化,此时对祖籍地的认同逐渐变弱,进而转化为主要认同侨居国,对祖籍地只能是“宗族和祭祖之类的文化认同而已”[4](P170)。事实上,清末民国时期,华侨的地缘认同强烈而持久,并且已经渗透到华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下主要从组织、居住、行业、信仰四方面来阐述地缘认同的表现形式。
(一)组织地缘化
华侨社会有许多类别的组织,其中地缘组织非常普遍且大量存在。据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侨委会根据驻外使馆等提供的调查资料统计,到1942年,海外各地共有华侨组织3826个,其中亚洲最为突出,共有3213个,占其中的84%之多,亚洲地区又以东南亚国家侨团组织最多,共有3017个,占亚洲侨团组织总数的90%以上。而上述组织中,属地缘组织的有1008个,约占一半。[5](P82)由此可见,东南亚的地缘组织数量极为可观。
所谓地缘组织,又称同乡会、同乡会馆,它是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是指以中国国内原籍所在地的省、府、县、乡或村为名称和单位的组织,还有跨省的连省组织。如丰永大会馆是广东省的丰顺县、大埔县和福建省的永定县联合组织的社团。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它不仅有各地客属地区的客家人,同时还有江西、福建、广西、湖南等地区的客家人,分布在全马各州县,约有200多个属会。嘉应会馆是指历史上的嘉应五属(今梅州所辖)梅县、兴宁、蕉岭、五华、平远结成的组织,全马有嘉联总会,属下各地有24个嘉应会馆(含应和会馆、梅江五属公会)等。[6](P31)一般规模较大的组织都称为会馆,如应和会馆、福建会馆、琼州会馆等,同乡会则是规模较小的地缘性组织,如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福州关峰同乡会等。会馆最初的组织常称为公司,如丰顺公司、宁阳公司等。[7](P251)
客家人在地缘组织的创建方面最早并且最为活跃。在东南亚华侨史上,客家人最早创立地缘性的会馆。据载,1801年在槟城成立的嘉应会馆,它是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及平远客家人组成的,可谓新马地区最早的地缘性会馆,也可能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华侨会馆。[7](P252)无疑,客家人是东南亚华侨地缘组织的先驱和主体。这些地缘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为同乡移民安排住宿、介绍工作、组织宗教祭祀、恤贫扶弱、赈济家乡、调解纠纷、抵御外侮等,实际上成为各籍华侨的领导机构、联络机构、福利结构。其中,联系华侨与祖籍地的桥梁和纽带是其重要作用。
(二)居住地缘化
华侨社会多同籍聚居一处的现象,即居住地缘化。19世纪来自同一地域、操同一方言的新马华人,“引人注目地聚居一处”[8](P33)。陈达也指出:对于中国人在南洋的地理分布,有两点惹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其中一点就是“同乡聚居一处”[9](P51)。因华侨出国的路线,往往依照在南洋的同族或同乡的经验与协助,对于后来者大都有血缘、友谊或邻居的关系,或广义的同乡关系。因此后去的移民,大致跟着前辈所住的地域。因此,对于南洋的中国人的地理分布,其实可以按照华侨的家乡来划分。
对于客家人来说,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居住在爪哇的雅加达、三宝垄、泗水、万隆、梭罗;苏门答腊的占碑、巨港、棉兰、日里;加里曼丹的坤甸、山口羊;苏拉威西的孟加锡、摩鹿加群岛的安汶、邦加、勿里洞以及帝汶岛东部。在马来西亚,他们侨居在吉隆坡、马六甲、怡保、芙蓉等地为多。[3](P13-14)客家人在其他各国也多聚居一处。
客家梅州籍华侨在侨居国同样聚居一处。例如,印尼西加里曼丹以梅县人最多。从18世纪60年代起,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殖民者在西加里曼丹取得侵略据点以前,中国人主要为客家人凭借祖籍地域关系移入西加里曼丹的每年约在3000人以上。另外,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最南端的边佳兰埠右邻巴西高谷地方,居民有500多人,其中华人380多,而丰顺人又占90%,故有“丰顺之村”之称。印尼棉兰市西利勿拉湾镇,有“小汤坑”(汤坑是丰顺县一个著名侨乡镇)之称,因为在西利勿拉湾镇的百家商店中,丰顺县人开的就占30多家,大量丰顺人聚居在该镇。[10](P988、P996)可见,梅县、丰顺华侨聚居一处的特点。其他侨居国的客家梅州籍华侨也大多都通过地缘同乡关系的不断牵引,使聚居一处的华侨不断增加。
(三)行业地缘化
同乡加入一业,即行业地缘化。对于中国人在南洋的地理分布,陈达指出应特别注意的一点,即“同乡加入一业”[9](P51)。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行业(或职业)与地缘相结合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行业有超越地域方言之势,但由于存在着某一行业以某一地域方言群为主或为其垄断的现象,所以颇具有地缘的色彩。
二战前,侨居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各属(帮)均有其传统的行业。例如,20世纪初的荷印尼华侨中,福建漳泉籍华侨多从事批发、土产、贸易、布匹、制胶和榨油等行业;潮州籍华侨多从事农业、烟草业;广肇华侨多从事饮食、照相和土木工程行业,手工业诸如裁缝、制鞋、钟表修理、夹具制作及金银加工等。[11](P76)客属华侨也有其传统经营行业,在印度尼西亚,客家人商业中多经营杂货、酒类、鞋、首饰、缝衣、洗衣店及理发店,在工业生产方面华侨多从事锡矿开采[12](P60)。对于客籍梅州华侨而言,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侨乡梅州初期出洋的华侨,一般将原乡所学的手艺带到侨居国进行谋生活动,各县的华侨有各自的职业特点。如五华出洋者多以石业为主,兴宁华侨多以织布、藤业为多,梅县则以文员为多,大埔、丰顺以小商贩为多。[6](P26)
随着各行业的地缘化,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一些纯粹为某一地缘的业缘组织或大多数会员为某一地缘方言的业缘组织大量存在,如广府帮的北城行、鲁北行、广肇猪肉行、熟食行,潮州帮的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渔业公局、梨业公所、旅业工会,海南帮的琼侨汇兑公会、琼南客栈行、琼侨咖啡酒餐公会等。[7](P261)可见,业帮(同业公会)是带有乡帮性质的一种职业组织,这充分地体现了华侨社会行业与地缘相结合的特点,即行业地缘化。
(四)信仰地缘化
同地域供奉相同的神,即信仰地缘化。早期华侨社会,是以庙宇为中心,在神的名义下进行社会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对神的膜拜,使离乡背井的宗亲乡邻逐渐凝聚在一起,有助于培养地缘的认同感。华侨在庙宇中供奉的神祇,最普遍的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以及被作为航海保护者的女神天后 (又称天妃、妈祖)和商旅保护神关帝(又称关公)。例如,1673年建造的马六甲青云亭,据认为是各地华侨社区出现最早的庙宇。该庙供奉的中殿主神为观音,左殿天后,右殿关帝。1799年在槟榔屿建成的广福宫,供奉观音。该宫建筑费用由各籍华侨捐献,并由不同方言集团的代表共同管理。1838年新加坡各邦领袖共同设立的天福宫,主殿供奉天后,次为观音、关帝。这三个庙宇供奉的神祇,都是不分帮域,为华侨共同信仰和膜拜。[5](P76)
值得注意的是,华侨社会内部还表现出信仰地缘化。除了上述共同崇拜的神之外,他们还分地域供奉不同的神。在新马地区,福建人崇拜他们的地方神清水祖师、广泽尊王、圣后恩主、开漳和大使爷;潮州人崇拜他们特有的神玄天上帝、安济圣王和两位爱国者张巡及许远;海南人崇拜他们的地方神水尾圣娘和天后女神;广府人则崇拜三神侯王。[9](P14、P34)
客家人也有自己特别崇拜的地方神,那就是“大伯公”,如1884年客家人建立的丹绒巴葛福德祠,就供奉着大伯公。[5](P76)在马来西亚,有一位保护神“大伯公”张理。张理,是客家大埔籍华侨,“海珠屿”的拓荒者。他生前为华侨和当地人干了不少善事,所以被视为“保护神”,为纪念他,后人在“海珠屿”建起了“大伯公庙”。随着时间推移,客籍人士对这位开发“海珠屿”的先辈十分崇敬,于是一座又一座的“大伯公庙”,不仅在海珠屿,而且在马来西亚乃至于整个东南亚都建了起来,并有朝拜大伯公的风俗。人们有什么困难、灾难,都要祈求大伯公解救。[13](P313)
二、侨乡情结:地缘认同的合理延伸
对于华侨社会而言,地缘认同维持了地缘群体内部的生存和发展,保持了地缘群体与外埠环境的适当交流,以便从环境中取得群体发展所需的资源,从而推动了整个群体在华侨社会的发展。对于祖籍国来说,由于华侨的地缘认同已经渗透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必然强化着华侨对祖籍地侨乡社会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各项联系。华侨基于地缘认同而产生的对侨乡社会的情感,为华侨作用于侨乡社会提供了心理条件。
早期大多数移民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和愿望——“衣锦还乡”,返回埋葬他们祖先的故土,即华侨的祖籍地。强烈的祖籍地认同感使得华侨有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一种观念是“荣归故里”。发财致富后回去的华侨受到热烈欢迎,如果是从东南亚回去的,那就常常被吹捧为“南洋伯”,如果是从美国或澳大利亚回去的,则被称为“金山大老”。他们积攒下来带回去的钱不仅使他们自己,也使他们的家庭、亲戚和同乡普遍地感到荣耀。第二种观念是“叶落归根”。它表达出对故土的热爱,对祖籍归属之处的感情。这种观念通常适用于许多老一代华侨。[14](P3-4)老一辈华侨对祖籍地情思绵绵,怀念不已。他们有着强烈的爱乡热情,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华侨已逐渐成为侨居国公民,对家乡还有印象,在本人力所能及时,也愿意为家乡出份力。但是到了老一代华侨的孙辈们,他们对家乡的印象已经很淡薄了,只能是宗族和祭祖之类的文化认同而已。他们往往对家乡只存在好奇心,首次返乡后,因吃住玩都不尽如人意,便不愿重返。近几年来,侨乡梅县白宫镇侨联会,帮助华侨在故乡建造了十多幢中西合璧的别墅式楼房,旨在为华侨华人后裔回到祖籍地服务,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自觉回来的后裔寥寥无几。偶尔回来住上一两晚,便拔腿而走。[3](P30)华裔菲律宾人曾深情表白道:“中国当然还是我们的故乡,但是那是由父母继承而来‘籍贯的故乡’,而非我们感受中‘童年的故乡’。如果因此我们缺乏一份对中国深切的感情,这应该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在感受上觉得我们的‘家’在菲律宾,因为这是我们‘童年的故乡’……我们热爱这个国家。”[15]
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心态正处于“叶落归根”时期,大多数华侨是强烈地认同原籍地。辛亥革命后,经过革命运动和爱国运动,华侨的国家意识有所觉醒,然而绝大多数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基本还是停留在村县府省的“乡土”阶段而不是“国家”阶段。汇款回国,赡养家小,建造房屋,自然属于惠及族人乡里之举,即使是各地的学校,也大多是原籍华侨回乡捐建或捐助的。在新加坡,有些会馆揭示的宗旨即是“服务于桑梓”。在菲律宾,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乡会的工作和目的还在“故乡的公共福利事业上”[16]。
因而,华侨有强烈的地方观念,他们只对祖籍地的福利事业感兴趣,别的地方的经济规划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为筹建京汉铁路(中国记载多称芦汉铁路)在华侨中招股的失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和许多高级官员认识到铁路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因此,京汉铁路成为朝廷批准的第一条铁路。为了防止外资侵夺,它准备用华资建筑,禁止洋人入股。于是只得在华侨团体中集资,中国的外交官、华侨首领和特使都加入了这项活动。可是,反响非常令人失望。原因就在于华侨的地方观念。据说南洋的华侨根本不愿意购买任何股票,除非该线延伸到广东省,并附带建造一条从九龙到广州的支线。广东人占优势的美洲华侨也持同样的态度。在这些华侨的心目中,这条筹建中的铁路对他们家乡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毫无好处,因此不值得他们支持。这种地方主义在其后多年内继续影响了华侨向国内投资。[17]而梅县籍华侨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投资倡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商办铁路——潮汕铁路,正是因为可以照顾祖籍地社会经济发展而为。据铁路创办人张榕轩之孙张东沼回忆:“祖父当时选择这条路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汕头是一个港口有发展前途,其次是汕头离他的家乡梅县很近,可以在原籍起到发展经济的影响。”[18]而且,他们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伸到自己的家乡梅县。这有力地证明了华侨当时对祖籍地的强烈认同。
客家籍华侨这种对祖籍地的认同感更为强烈。客家人头脑中永远有着自己的故园,总忘不了“叶落归根”。他们节俭每一文钱,储存起来,一有机会,便托水客,带回家中,自己没有了,再去赚。[13](P324梅县籍华侨李权秀,他第一次领工资就把钱汇回家乡,其母收到儿子的钱,声泪俱下地说:“我的好儿子,真是百日禾,救了饿啊!”[19](P215)客家梅州地处山区,投资条件不是太好,但由于华侨爱乡之心甚强,稍有资获,多归国从事各项投资。此种投资,每缘于侨胞旅居海外,耳濡目染于现代文明,感觉故乡所缺乏者,正宜大量提倡,故投资者之初衷,“原非为利润之追求,且包含提高故乡生活程度之深意”[1](P209-210)。其动机可谓至真至善。
三、结语:地缘认同的当代价值
(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地缘认同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作为客家民系的广东梅州华侨,是一个很有旨趣的视角,其集客家、山区、华侨三位为一体的区域特色颇具典型性。有学者就指出:“客家现象本质上不是一个种族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20](P43)客家民系的形成应理解为一种“文化心理”的形成。同样,华侨的这种“地缘认同”也是以心理认同为主的文化认同,不是一种政治认同,而是文化上的归属感。华侨与客家相同的是,其所以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都有着长期饱受迁徙,一种谋求安居乐业、耕读传家、奋发进取的精神内涵,因为一个族群,需要荣誉感和认同感,尤其是在恶劣和不断迁移的现实环境中需要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总之,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心理“共识”就是这种文化归属感上的地缘认同,基于地缘认同而产生的对侨乡社会的情感,则为华侨作用于侨乡社会提供了心理条件。如何通过文化认同来达到强化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化向心力的作用,同样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课题。
(二)地缘认同下的侨乡社会资源
海外华侨之间的地缘纽带,是侨乡特有的一种社会资源。可以通过举办世界性社团联谊大会,以及依托于传统复兴,来实现它们的社会功能,同时依靠海外华侨、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三股力量的相互作用,并试图转化为当代客家侨乡梅州的社会动力。当利用传统的地缘纽带时,通过召开世界性的社团联谊大会,地方政府与海外华侨可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就为获取商业投资提供了可能,那么当招商引资成行时,就意味着政府与海外华侨的互动有了成果,并共同作用于当地社会。[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的实现,需要侨乡当地政府发挥关键作用,侨乡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即中央与地方政府。
(三)地缘认同下的华侨爱国心的准确把握
华侨基于地缘认同作用下的地方大资源,其作用的形成与绩效,主观上是因为广大华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们在血泪中艰苦创业,以人间最真挚的乡土恋、骨肉情回报桑梓。客观上是因为较为宽松的政策与环境。清末民国时期,各级政府虽时局动荡,但采取了有利于华侨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得力措施,制订了不少吸引侨资的政策。以史为鉴,综观作为地方大资源的华侨在侨乡梅州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其启示是深刻的。早在清末民国时期,广东地方当局与海外华侨尚能抓住机遇,迎来双赢互利的局面。而今,我们有新中国几十年来吸引侨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准确认识华侨的爱国心,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建一个真正公平、公开、诚信、高效的投资环境,显然十分必要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华侨志编委办,广州华侨研究会,广州师范学院.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 (广东):1[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2]孙谦.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3]罗英祥.飘洋过海的客家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4]龚佩华.侨乡社会文化的封闭与开发[A].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5]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华侨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6]梅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梅州市华侨志[Z].梅州,2001.
[7]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8](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M].粟明鲜,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9]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10]丰顺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丰顺县志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1]林德荣.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德研究 [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12]刘权.广东华侨华人史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3]谭元亨.客家圣典 [M].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14](澳)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M].姚楠,陈立贵,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5]周鼎.童年与故乡 [N].东方日报(菲律宾),1980-02-26.
[16]孙谦.战前东南亚华侨的地缘认同[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3).
[17](澳)颜清湟.华侨与晚清经济近代化[A].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8]黄绿清,杜佳.梅州华侨与中国的近代建设[A].梅州文史:第11辑[Z].梅州,1997.
[19]黄伟经.客家名人录:梅州地区第二大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20]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21]庄曙强.血缘与地缘:侨乡传统资源的当代运作——以泉港为研究个案[D].厦门:厦门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