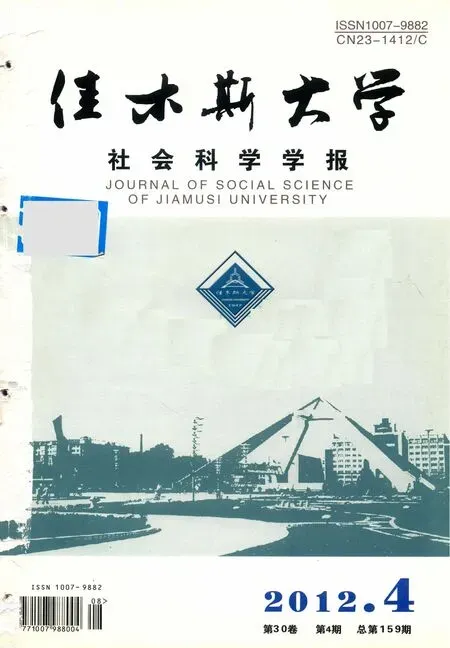关于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的探寻①
2012-04-18王威
王 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关于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的探寻①
王 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先民们经历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和多神崇拜等的漫长历史阶段,原始宗教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渗透到黑龙江三小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黑龙江三小民族在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被周围的主体性民族所同化,慢慢地开始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保护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是对三小民族的情感价值观、行为模式及传统文化的诸多方便所进行的保护。在保护的过程中,可借鉴近年来我国对汉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方法,对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护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一定要与迷信相区别。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只有从民族自身出发,充分调动本民族人们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保证其顺利地传承发展下去。
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文化主体
宗教信仰作为人类历史上特定阶段出现的产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方向,甚至对一个种族的存在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原始宗教信仰在一个群落或种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这个部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被视为这一部族发展方向的“指路明灯”。在原始社会中,原始人把其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不可理解而又找不到答案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为看不到也摸不着的“神秘灵魂”的指引。这一“神秘灵魂”可操纵包括人的生死在内的所有自然界一切事情的发展变化。人与自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原始人那里无法得到正常科学的解释,于是,原始人便把这种超己的“神秘力量”自发地发展成为最早的原始宗教信仰。
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自身思维意识的产物,也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宗教出现之初,人们往往能够通过这种信仰找到解决生产生活中所出现的“难题”的解决途径和解决方法,以此,宗教信仰才会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流传并保存了下来。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原始宗教信仰在其出现的若干年里,并不是后来史学家们所定位的那样,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当时所有人都将之视为真实可靠,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
一、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势保护在必行
黑龙江三小民族,从其出现的那天起,与其他民族一样,在信仰上从史前崇拜开始,原始宗教信仰对本民族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基本上都起到过“指引方向”的作用。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先民们经历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和多神崇拜等漫长历史阶段,原始宗教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渗透到黑龙江三小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
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随着人们对自己周围事物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科学,各种曾被人们奉为神秘不可解的现象逐渐被近现代的科学所破解,人们开始对先人们的宗教信仰弃之不用,更甚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过了时的宗教信仰被人们视若敝履。黑龙江三小民族在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被周围的主体性民族所同化,慢慢地开始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黑龙江三小民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不复当年那浓郁的渔猎氛围。我们说,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之为一个独立于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民族风俗习惯,而这些又取决于这一民族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黑龙江三小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曾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民族宗教信仰都以极快的速度在消亡,尤其是三小民族的宗教信仰——这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柱,基本已是消亡殆尽的状态。
萨满崇拜是伴随着黑龙江三小民族氏族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用它“万岁”的年纪“讲述”着北方少数民族悠远而又深沉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萨满崇拜作为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原始宗教和文化现象,渗透到古代北方民族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集北方先民的史前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诸文化之大成,既是北方传统文化的基石,又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如今,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趋同的挤压下,已经开始走向消亡,只能以文化遗存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它曾经的辉煌。
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涵盖了三小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曾是黑龙江三小民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每当重要的时刻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信仰活动相伴随,可以说从生到死,无论喜乐哀愁,宗教信仰已经浸润到黑龙江三小民族的每个角落。然而就是这个在黑龙江三小民族历史上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文化信仰,在今天却开始被本民族的人们所不熟悉。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是典型的渔猎民族。受季节性的影响,赫哲人除了捕鱼外,狩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因此,在赫哲族的图腾崇拜中,我们不仅能够找到非常普遍的鱼图腾,还存在着熊、虎、鸟等图腾。这些图腾崇拜向我们展示了赫哲人独具的地域特点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而关于鱼、熊、虎、鸟等民间神话、故事、传说、民歌、民俗事项,大量存在于赫哲族文化、文学及史志文献中。但是现在的赫哲人除了专门从事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无人能够说清楚这些图腾崇拜的意义所在了。“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文化多样性资源的宝库。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和多种生产生活方式蕴涵了丰富的传统知识和智慧。按照多样性促进创造性和多样性促进稳定性的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对这些传统和知识和智慧亦即民族文化多样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既是和谐社会创造力的源泉,又是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1]当我们今人在考察黑龙江三小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时候,原始宗教信仰作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必将进入研究者和保护者的视野,成为保护三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渐行渐远、大量缺失的三小民族原始宗教和传统文化,保护之责势在必行。
二、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任重道远
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是黑龙江三小民族十分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它渗透到三小民族的各个领域。保护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是对三小民族的情感价值观、行为模式及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保护。尤其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大力提倡“求同存异”以保存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在全球化的基础上保持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黑龙江三小民族作为世界众多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保护也是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
1.在文化“同质化”大潮中求同存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晓萍先生在其著作《全球化与民俗保护》中指出:“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即全球化的发展主义对民俗传承的消解与可持续节约主义对民俗传承的重视。”[2]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带动黑龙江三小民族不自觉地朝着全球的大方向发展而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黑龙江三小民族首先要面对的是国内主流文化的影响与同化,这种同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险些让黑龙江三小民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在原始宗教信仰的传承和保护上更是无人问津。但是正如董晓萍教授所说那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求同”,但更重要的是“存异”。一个完全被同化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而这个世界从出现那天起就注定是丰富多彩的。黑龙江三小民族特有的原始宗教信仰不仅是本民族存在的支撑点之一,同样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三小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就是在保护三小民族的文化独特性。
黑龙江三小民族虽地处偏远却历史悠久,当历史遗留与现实相碰撞时,融合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但是,如何在融合的过程中保存自己的特色,就成了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这里我们可借鉴近年来我国对汉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方法,对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进行保护。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属多神信仰。在各地进行传统汉文化的拜炎黄、祭孔子的时候,黑龙江三小民族也完全可以把自己民族对祖先及各神的崇拜、祭奠仪式以文化的形式在本民族内部开展起来,这不仅可以加深本民族人们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认识,更可使外来人了解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可为三小民族的传统祭奠仪式提供生动具体的范例。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同质化’,针对的是全球文化趋同的现象和趋势:普世的文化价值取代文化个性,削弱文化的自主能力,使主流文化失去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心理认同,逐步形成对各种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进整合化一的、依赖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文化’。”[3]在文化“同质化”的过程中,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在遭受着被削弱文化个性和自主能力的命运,如何在削弱中自强也成了学者们在探讨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问题时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原始宗教信仰,按照事物发生——发展——衰微的客观性,已经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我们在这里所要解决的也并不是把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如何发扬光大下去,而是让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本民族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得以长久地传承下去。在这方面,保护者和传承者完全可以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把那些曾经“一次性的”文化产品永久地保存下来并且在很广阔的领域流传、推广开来。信息时代,网络的广泛应用,大量的信息被共享,利用互联网和各种主流媒体,完全有可能把原本并不为太多人知的小民族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所熟识和了解,也有利于研究者在文化资源共享的同时相互交流研究所得,使研究向更加博大、深刻的方向开展,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2.破除迷信,将文化进行到底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生之初,“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4]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超人间力量的真实性。这里就出现了与封建迷信最本质的区别——封建迷信本身的虚幻性从一开始就是被从事的人所熟知的,但从事封建迷信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从事此种活动,并把它作为一种可盈利性的活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起来。简言之,宗教信仰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功利目的,而迷信恰恰与之相反。只有阐明这个问题,才能在研究中肯定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存在而非迷信。
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在其发展历史进程中被三小民族人们当作“信史”而加以利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衍生出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信仰文化和与其相关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包括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萨满)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是人本能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描写。”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宗教信仰活动是三小民族的人们对于自身认知的朦胧状态。以三小民族的鬼神巫术信仰为例,黑龙江三小民族信仰鬼神是因为他们认为“求神佑平安、鬼带灾祸”,因而他们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也全然相反,对神灵祭祀,以求保佑自己的宗族或整个民族能够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对鬼则用巫术驱赶、捉杀。从事祭祀的则是我们经常在研究中提到的萨满。萨满作为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能够帮助本民族的人民度过一道道难关。在整个宗教活动中,无论是萨满还是祈求的族人,都相信这一过程的真实可靠。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萨满文化则具备了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强势地显示出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如果这样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消亡,那么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保护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就是要保护这样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而在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与迷信相区别。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不会再把这样的宗教信仰当作“信史”,而是作为文化的一种加以保护。这种保护在很多民族内部已经产生。以赫哲族为例,在黑龙江省同江市的赫哲族聚居区已经开始在民俗生态村中,在固定的时间里举办以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宗教信仰活动。这一活动,不但能使本民族的人们了解、记住自己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文化,而且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使更多民族外部的人们认识了解赫哲族的宗教信仰文化。除此之外,三小民族的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记录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赫哲族的说唱史诗“伊玛堪”就是记录了大量的关于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文本。2011年11月23日,“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赫哲族伊玛堪”从此走出了本民族的囿于,走向了世界。对于鄂伦春和鄂温克两个小民族来说,这无疑是可供借鉴参考的最好形式。通过申遗等形式的世界性文化保护活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必将会得到世人的认可而更加长久地传承下去。
3.在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提升文化主体参与的自觉性
文化的主体既是文化的传承人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亦可称之为文化的主人。“文化主体参与是民族文化保护最基础最重要的方式和关键环节,他们的参与是文化多样性、活态性、连续性得以保存的保证,只有民族文化主体的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文化的原创力,创造发展民族文化。概而言之,文化主体参与是保护民族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容和环节,只有他们的参与才能最终使民族文化保护取得理想的效果。”[5]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保护只有从民族自身出发,充分调动本民族人们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保证其顺利地传承发展下去。
我国从建国初就开始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意在保证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创繁荣。好的民族政策需要有力的执行。民族的发展进步除了需要国家的积极性民族政策,更需要民族自身的自立自强。在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上,民族文化主体的参与更是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去留。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保护除了研究者的参与外,更是三小民族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保护好这样饱含民族文化底蕴和文化特点的文化形式,才能使民族自身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发展。
国家的积极政策不是让三小民族依附之上,被动地生存,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调动民族自身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为民族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贡献力量。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只有本民族的人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心灵深处领悟本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保证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性文件,文件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链条的基本图式,与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常态,对世界上不同的历史、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文化模式的国家人民来说,保持文化多样性,是现代人权的内容,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6]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主流文化趋同的大环境下,它的存在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保护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就是保护三小民族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就是保护三小民族作为文化主体的独立性,就是保护三小民族之所以称其为这一民族的主体性。
在大力提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保护黑龙江三小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不但是小民族自身的需要,更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由此,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责任将黑龙江三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这一特色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下去。
[1]叶建芳.文化主体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探讨[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1(2).
[2]董晓萍.全球化与民俗保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79.
[3]王真慧,龙运荣.网络时代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互动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104(2).
[4]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高兆明.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0).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K892
A
1007-9882(2012)04-0118-03
2012-05-08
王威(197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黑龙江伊玛堪研究中心成员。
[责任编辑:田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