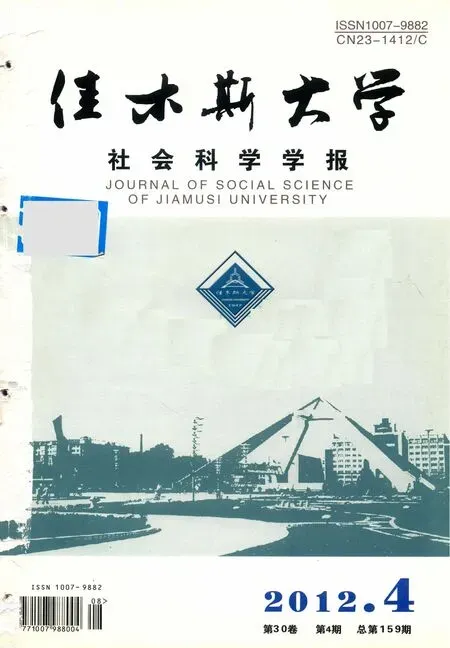我国古代社会乡村社区治理的政治艺术①
2012-04-18李雪彦
李雪彦
(安顺学院政法系,贵州安顺561000)
我国古代社会乡村社区治理的政治艺术①
李雪彦
(安顺学院政法系,贵州安顺561000)
维护既存政治秩序是每一代统治者的共同任务。但是,时代不同,他们在维护统治秩序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也会有所差异。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乡村地域极为辽阔,农民居住也相当分散,村庄之间亦呈相互隔绝之态势。面对此种情形,统治者们将司法、宗族及乡绅等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古代社会;乡村治理;政治艺术
政治艺术之一:司法控制
现代意义上,法律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由于这些社会规范具有超强的严谨性、惩罚性及制约性,且通常有外在的暴力机构来辅助其实施,因此在调停社会矛盾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法律具有其他一般规范及教化所不具备的绝对优势。正因为如此,法律被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及各政治权威奉为治国的经典术谋。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法律视为“最优良的统治者”,指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好是全无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使谁都难免有感情”[1](P163),“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上陷入了兽性的因素”[1](P171)。在这一方面,我国也不甘落后,在先秦时期便涌现出了一些推崇法治的思想家。如春秋时期的管子就用“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形势解》)的简单话语来概括了法的涵义,并进一步指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则民之父母也”《管子·论法》),强调了法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超强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法治”思考突破了理论争鸣之局限,而进一步向实践转化。结果,在政治权威的催促下,我国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古代法律体系,用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那么,在乡村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国家的这种法律体系有没有价值呢?笔者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官治行政以县级政权为终端,即所谓“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之广大乡村社会,统治者采无为而治之策,听民自为、自营。因此,对于乡村的社会成员来说,国家的法律基本不起作用。
笔者以为,从历史实践去考察,受行政成本、国家权力之分配模式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古代的政治权威确实将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当作农村管理的中坚力量。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国家法律在乡村管理中所产生的价值。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相关的记载中找到证据的。如山东费县赵氏家谱《家规》就明文规定:“凡本族不肖子孙私自砍伐祖坟林木者,逐出本族,死后不得入祖坟,并送交官府法办。”[2](P312)另,南海廖氏《家规》“禁淫秽”条分列三款:第一,服属内乖戾失伦,送官按例治罪,当事人永远革籍;第二,言语调戏妇女而生出事端,小则停三年,大则送官惩治;夜如人家,妄思无礼,或隐匿窥探,或恃酒胡闹,本人停胙三年。[2](P131)光绪休宁《葆和堂冠婚丧祭及扫墓差遣各仆条例》也规定:“朝廷号令甚严,于斗牌、打架、赌博、盗窃四事,法在必究,更觉凛然。尔等小心安分,庶可以保身家。设有犯此四事者,鸣官究治理。”湖北麻城宣统年间的《鲍氏宗谱》则干脆指出:“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媳者,免祀,送官治罪。”[3](P601)
可见,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法律对乡村进行控制的行为,即所谓的“鸣官”、“送官治罪”是存在的。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控制有其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简而言之,国家法律对乡村的调控主要以人为对象,对触犯国家法律的乡民进行制裁,进而达到维护乡村正常秩序的目的。然而,正如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人为了寻求指导和认可,通常是求助于这种法律之外的团体和程序,而不是求助于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4](P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法律对乡村的干涉、介入现象并不常见。若村民们发生一般性纠纷,通常他们也不直接寻求国家法律来解决,而是首先求教于宗族等传统性社会力量。只有当族内的权威人物和机构不能处理,或其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时候,才会选择“鸣官”。所以,同其他政治艺术相比,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乡村的司法控制只是一种“后位”选择。
政治艺术之二:宗族管辖
何为宗族?目前的学界无一致性的回答。综合各学人的观点,大概可以做如下归类:其一,对宗族进行静态的描述。如学者刘宗棠就给宗族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宗族组织是指世代聚居在一起的男性祖先的子孙,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财产为保障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5]。其二,用运动的观点来诠释宗族。如李锦顺、章淑华曾撰文,提出了“宗族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概念,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赋予了宗族新的内涵”。笔者以为,同其他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术语一样,由于立场、视角的差异,人们对宗族具体内涵的表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综合各类学术观点,我们又发现几乎所有对宗族有所研究的人都没有背离宗族组织的基本特性:其一,宗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其二,宗族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以最粗略的方式将宗族看做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的共同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共同体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乡村治理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发生过作用?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下述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教化及控制乡民
政治教化是每一个阶级社会都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统治阶级推行教化的手段却是有极大差异的。在我国古代社会,受地缘偏僻、通讯设施欠缺、经济发展滞后、行政体制安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统治阶级将农村地区的教化、控制权赋予了同乡民息息相关的民间组织——宗族。为了完成此目标,该组织通常先制定内容全面而复杂的行为规范系统,以为农人提供行事依据。盛行于我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各种族规、族约、家典、祖训即是证明。然后,再对这些家族法规进行宣讲。如黟县环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规》就规定:“每岁正旦,拜谒祖考。团拜已毕,男左女右分班,站立以定,击鼓九声,令善言子弟上正言,朗诵训诫”[6],另存在于家族内部的讲正、讲副即是负责宣讲各种族规家法的机构。最后,为了保证家族法规的权威性,宗族组织还被国家赋予了强制性的惩处权力,专门惩办那些违背了家族法规的个体。其方式有多种,常见的包括训斥、罚站罚跪、罚款、责打、出族、处死等。概而言之,在家族组织这种有软有硬的干涉下,我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男女老少的言行被普遍地限制在各种规则以内,很少有越纪现象。
(二)调处民间纠纷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方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设置具有诸多的不合理性。笔者以为,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地方行政权同司法权混同使用。地方公共权力的此种特性给地方行政官员带来了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不仅要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还要兴养立教,可以说“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在这种情形下,地方官吏要亲自去处理农村的各种纠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古代官僚体制下,政府通常将政权与族权相结合,利用宗族来调处乡村的各种纷争。这一点,有相关的史料可以明证。如江西按察使凌铸就实行过“族约制”,由地方官授予宗族牌照,以达排难解纷之目的:
凡有世家大族,丁口繁多者……地方官给予牌照,专司化导约束,使之劝善规过,排难解纷。子弟不法,轻则治以家法,重则禀官究处。至口角争忿、买卖田坟,或有未清事涉两姓者,两造族约会同公处,不得偏袒。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组织在调处各种民间纠纷时的重要角色。那么,具体一点,这些宗族组织是如何进行调处的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从三个层面予以论述:
其一,处理纠纷之主体。对此,经过梳理,笔者发现古代宗族内普遍设有族长、房长、家长等专门机构来处理斗殴、户婚、田土等一般性争讼。这可从一些家规、宗谱中找到依据。如庐江府何氏家记中就规定到:“族有念事,非奸盗人命重事,不得冒官司,须投房长、主祠,分剖是里”。(《庐江郡何氏家记》山阴华舍赵氏亦准许族人将不教不悌、凌辱尊长、欺辱孤寡、不务正业、霸田占产者扭送宗祠,而后由族长、房长会同族中执事进行会讯,然后决定是否请出祖宗的“家法”来加以处置。(《山阴华舍赵氏宗谱》卷首《家规》)另萧山管氏宗族也规定:族中“立通纠二人,以宗一族之是非,必选刚方正直、遇事能干者为之。凡族人有过,通纠举呜于家长”。(浙江萧山《管氏宗谱》卷4)
其二,调处纠纷之范围。在我国古代社会,宗族共同体对农人纠纷的处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调处财产继承买卖之矛盾。如蒋湾桥周氏宗族便规定“族内昆仲叔侄或因财产争论,应听族长及公正者调处,不得偏执己见”。(《蒋湾桥周氏续修宗谱》卷一《家规》)另,光绪年间,江苏句荣县民余人俊为其三个儿子分割遗产。余人俊的妻弟主张将全部遗产分为九份,两嫡子各取三份,一庶子取二份,余人俊本人留一份作“养赡之资”。房长余人龙出面干涉,主张三字均分。最后经县衙审理,同意房长余人龙的处理意见;第二,协调婚姻缔结之纠纷。如泾川万氏《家规》第十二条就指出,“嫁娶不拘贫富,惟择阀阅相当。若贪财贿以淆良贱,有玷门户多矣。吾族除以往不究,今后凡议婚纳配,须鸣族商议,果系名门,方许缔姻。如不鸣众或门户不相当者,合族共斥,谱削不书”。(《泾川万氏宗谱》《家规》)另,道光十一年李氏家族《宗归》亦规定“本房长、户首即宜苦谏力阻,或该妻实系犯出,亦必经鸣房长、户首,会同查议。公论无饰,方许从权,否则断乎不可”。(《李氏宗谱》卷二《家规》);第三,调处轻微刑事纠纷。
其三,调处纠纷之程序。在我国古代社会,对于因触犯族规家法而产生的案件,大多没有固定的审理程序和模式。但是有几点必须注意:其一,对于违反习惯法的案件,必须先向宗族组织投诉,而不能直接报官;其二,案件的处理绝大多数在祠堂内举行,由族长、房长会同族中有名望者一起负责;其三,族长对案件作出判决以后,即发生效力,他人不能提出异议,也不存在二审程序。
总之,凭借上述家族内部的调处,在国家法律难以延伸至乡村,乡村社区各类关系及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法制来协调的年代,中国农村社区的违规违纪甚至是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大大降低了因农人纠纷而导致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失控的风险。
(三)族内福利救济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民对土地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可以说,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生产物资,基本都自于农业生产所得。然而由于生产技术、工具及设施的落后,农民即使辛苦生产、勤快劳作,其收入也相当有限。扣除应缴纳的各种税收外,农民已所剩已无几。因此,农民必然成为传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客观上需要社会的救济与辅助。可惜的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的统治者均将征税、征兵以维护政治稳定作为自己最大的政治任务。对于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以促进社会福祉则保持着较为冷淡的情绪。
国家在救助乡民问题上的行为缺失导致了在农村社区中,出现了许多需要救助而得不到救助的贫苦穷人。这部分人的存在,对于乡村安全来说,无疑是危险地。这一点,宗族组织似乎也早已发现。因此,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了经济互助任务。在现实中,这种帮扶主要通过族内赈施来完成。对此,有相关的资料可以证明。如,(《樊重传》)《东观汉纪》就曾描述道东汉的刘般:“迁宗正,在朝廷竭忠尽节,勤身忧国,夙夜不怠,数纳嘉谋,州郡便宜,清静畏惧,受职修治,赈施宗族”。《后汉书·朱晖传》也指出,“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赢者,乡族皆归焉”。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领略到宗族在族员救济方面的重要作为。实质上,为了使这种救济正规化,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宗族普遍设有公产——族田,以为赈施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具体说来,族田通常被分为三类,其中祀田的产出用作祭祀,义庄田的收入用于赈济贫苦族人,书田则用于支付宗族学塾的经费。甚至,为了避免宗族公产的流失,他们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如义庄内就设有庄正、庄副职位,以负责收租、保管及出纳的工作。
总之,乡村社会的这种族内救济活动分担了穷困乡民的经济负担,抚慰了他们的失衡心理,舒缓了民间矛盾,为乡村秩序的稳定消除了隐患。
(四)传承乡村文化
乡村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在经济欠发达的小农社会,其所涉及的事务也是多维而复杂的。除了上述所讲的政治与经济层事务外,乡村文化的传承亦是我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问题上,宗族组织也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功能。概括起来包括:
第一,组织祭祖及修编族谱。祭祀是宗族最为重要和严肃的事情。为了更好地开展祭祖活动,我国古代乡村社区的许多宗族都建造了祠堂,并同时制定了一整套的祭祀规则,具体包括祭祀仪式、祭器祭品、出席人员、纠察设置、祭后议事、祭祠费用及对无故缺席的处罚等。另外,祭祀种类也较多,除祭祠外,常见的还有清明扫墓,忌日及节日祭祀等。族谱是宗族的历史,是宗族活动的记录,也是宗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媒介。因此,在宗族文化兴盛的古代社会,修编族谱便成为了宗族组织除祭祖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活动。
第二,制定乡规族约。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组织主要依靠家族法来规范、调节乡村的各种关系。因此,制定家族法规便成为了家族组织的一项主要文化活动。那么,这些族规祖训是如何制定的呢?对此,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宗族法规由族内有声望的“贤达”、“族望”组成临时机构来主持制定,族长与副族长则会参与到其中。宗族法规草案制定后,通常还要在宗庙、祠堂中宣读,通过即生效。为了增加族规的威慑力,有的宗族法规甚至还要以文本的形式进行公布。通常,这些生效的家族条例内容非常复杂,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职业选择、婚姻缔结方面的规定,也有纲常伦纪遵守、族人纠纷协调层面的条款,甚至连参与宗族、娱乐活动都有详细的规定。不仅如此,宗族组织还要相应地制定处罚措施,以保证其效力。
第三,登记族内人口。在我国古代社会,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家族势力的大小。因此,家族组织常将掌握族内人口数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许多宗族设立“纪年簿”一类的东西,登记所有的族人。对于那些新出生的人,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族长,以使之登录在册。此种登录,使得宗族能够将族人编制起来,以为自己的内部管理提供条件。
凭借着这些活动,我国古代乡村社会形成并沿袭了一种以宗族为单位,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特殊文化。在这种文化系统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道德感、归属感,对祖宗、祖法普遍怀有敬畏心理,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对宗族法规的绝对屈服,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今天人们对这种乡村社会文化的价值依然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家国同构的乡村文化为乡村社区秩序的稳固提供了心理基础。
政治艺术之三:乡绅有限自治
乡绅的含义,学界无严格规范的概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称那些有功名却居于乡村的人。从内容上看,乡绅又可细分化缙绅和绅衿两个等地。前者指退职的文武官员,以及封赠、捐买的实、虚衔之官。后者则包括有功名却未致仕的举、监、生、员等,他们常着青襟之服,以示同农人之区别。
作为科举制度及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特殊阶层,乡绅被国家赋予了一般平民所不具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特权。凭借着这些特权,乡绅比其他人更容易在乡村事务中抛头露面。而且,他们或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或者企图攫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或者兼而有之,也往往乐于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封建社会直接接近农村的县级行政单位,实行回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知县以上的行政官员基本不在原籍任职。因此,新上任的地方官对本地的情况很不熟悉,甚至不懂地方性语言。他们履行公务的时候,更多地依靠衙役、书吏和幕僚。而这些办事人员除了收税、稽捕等需要出勤以外,皆高居衙门,基本不同乡人打交道。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幕僚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与乡村社会、行政机构同平民百姓的大程度分离。而这对于一心想控制某种既定统治秩序的政治权威来讲,无疑是危险的。为此,他们也急需一个能够担当“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群体来连接已经分离的乡村与国家,以加强其对乡村社区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乡绅阶层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在乡村秩序的维护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一)沟通官民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古代,我国以官僚体制为载体的国家权力未有效地延伸至广大基层社会。可以说,在对乡村社会的统治中,国家权力是空缺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对地域辽阔的乡村,居住分散的农民以及散漫平铺的“蜂窝状结构”的自然社会,统治者要更牢固地控制乡村就必须培植一个既能代表国家又能代表乡村的中介性群体来为其对乡村的控制提供服务。乡绅便是这样一个群体。一方面,他们代表国家,替国家做事。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的变现便是乡绅协助地方官吏完成政务工作。而且,这种协助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实征派、政策宣传、治安、教化、乡村经济等诸多方面。甚至,他们还要充当官民矛盾的调节人。如清末时,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战争。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绅士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乡绅还是乡民的代表,代替乡人同国家进行一定的博弈,以更切实有效地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乾隆年间乡绅郎秀才率民冲击漠视乡里灾情的县官即是一例。
(二)献身地方公益
我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因此,乡绅作为一个接受过传统教育并有着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群体,其必然性地会被儒家思想所影响。实质上,在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中,忠、孝、仁、义这些儒家思想的道德精华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再加上其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乡绅必然性地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有实在的例子可以明证。如明宣德年间,江西普遍出现饥荒,地方米价腾贵。官府曾考虑开仓平粜,然库存有限,无法满足四乡的灾黎。正当官府踌躇之际,地方乡绅鲁希恭、新淦及郑宗鲁各出粟二千石助赈济,随后又有众多绅民献捐,暂缓了饥民的乏食之困。当然,乡绅们的公益举动远不止于此。实质上,除了上述民间赈灾外,在基层社会的修桥铺路、疏浚河道、修堤筑围等活动中均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三)振兴地域文化
乡绅是农村社区里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体。因此,在那个以文盲为主体的年代,他们必然性地在村级事务中的文化阵地上发挥作用。首先,他们在乡村兴办学校书院,以兴教化。对此,有相关的历史记载:邹守益,退职家居,邹守益,退职家居,以讲学善俗为事。“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则立书院、建祠、广乡约,以浚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则举清量、明户役,以正其始。其他如赈贷周族、睦邻施义、缮道桥、广陂堰,不一而宇”[7];其次,乡绅们还参与族谱、乡规民约及地方志的编写。如《柳亭山真应庙方氏会宗统谱.凡例》中就记载了编撰人员名单。根据此记载,参加编撰班子的共计70人,其中有功名的族人就占了23名,占三分之一。其他无功名者也都是读书人。可见,编撰族谱及乡规民约的权力实质上是掌握在知识精英,尤其是乡绅手中。最后,乡绅还通过讲会来控制地方。对此,也有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如“时阳明先生良知之学方倡,诸先生因佃以为萃和书院。月朔望,讲学其中。切磋之余,民间有难申之隐,则就是告理。豪强亦为之敛手,亦治化之一助也”[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乡绅都能伸张正义、扶危济困。实质上,也有不少的乡绅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家财力有限、国家权力无法直接进入乡村的年代,正是在乡绅的介入与配合下,宗族组织才能形成较为全面的宗族法规以调控乡民的行为及纠纷,国家的制度、政策、及意识形态也才能在闭塞、偏僻的乡村得到宣传、接受,原本处于隔绝状态的国家与乡村也才有了连接的机会与能力。正是在乡绅的作用下,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保持了长久的稳定。
[1]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孙盛运.清代家谱汇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吴强华.家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美]D.布迪,C.奠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刘宗棠.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6]环山余氏宗谱(木刻本)[O].民国六年,1917.
[7]罗洪先.明故南京国子监祭酒致仕东廓邹公墓志铭[M].念庵文集:卷十五.
[8]刘岵.寺院记.同治泰和县志:卷9(书院志)[Z].
D69
A
1007-9882(2012)04-0013-04
2012-06-28
李雪彦(1981-),女,云南大理人,法学硕士,安顺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从事政治学研究。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