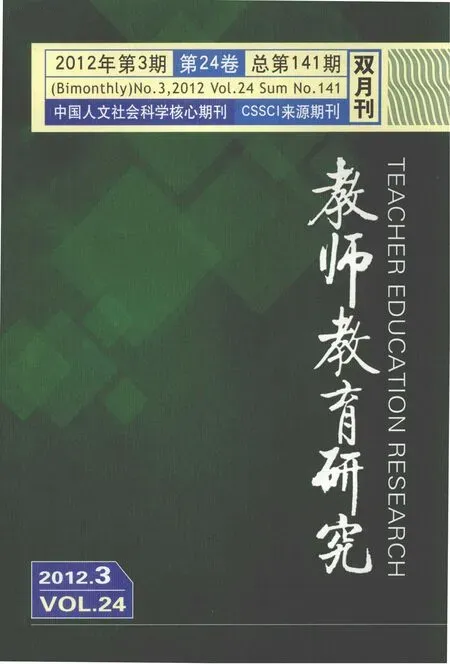中国传统社会 “尊师”制度的形成
2012-04-18叶菊艳卢乃桂
叶菊艳,卢乃桂
(1.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中国香港)
中国传统社会 “尊师”制度的形成
叶菊艳1,卢乃桂2
(1.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中国香港)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尊师”的制度化是精英儒士 (师)、统治者及民众三类行动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互动并形成典型化的、相互接纳的习惯性行动的产物。其中精英儒士 (师)对“道”(知识)的垄断及践行是其获得尊敬的合法性基础;科举考试则使“尊师”获得制度性基础和功利性色彩。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就当前如何重塑“尊师”氛围提供一些启示。
尊师;历史制度主义;传统社会
人们常常认为“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传统社会中到底是怎样的历史脉络和条件促使“尊师”、“师道尊严”这些理念的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人们想当然”的观念?在翻阅现有教育史及汉学界的有关文献后,笔者发现这个问题少有人回答①其中汉学界和中国思想史领域中有许多学者对“士”与皇权之间关系的分析,如余英时、张灏、葛兆光等人的有关研究。不过由于这些学者多栖身于史学界或文化研究领域,在他们的论述中直接旨向“师”研究的并不多。而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领域的有关研究,如萧承慎先生的《师道征故》,徐梓对明清时期私塾先生的一系列论述,吴智和对明儒学官的论述则侧重于陈述出传统社会中“师”的生存状况及地位是如何,但却很少对这些“是什么”及“如何”的现象进行解释,或提供一些解释框架。尤其是在看到许多文献纷纷描述明清时期私塾先生和儒官的悲惨境遇时,笔者不禁心生疑问:传统社会不是倡导“尊师”的吗?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私塾先生和儒学官员会如此落魄呢?那么到底“尊师”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呢?。但笔者认为这种梳理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重塑“尊师重教”氛围的政策脉络下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只有理清楚传统社会“师为什么受尊”及所需要的一系列条件,以及不同时代脉络对这一观念的影响,方可以更好地在当今时代采取相应的措施。
本文将借助伯格和拉克曼 (Berger&Luckmann)关于“社会现实是如何构建”[1]的有关论述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文章首先简要介绍所运用的理论视角和有关概念;接下来则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传统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下尊师如何得以制度化进行分析;文章最后对“尊师”制度形成的机制进行进一步总结并为当前国家制定有关“尊师重教”的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一、本文的分析思路:现实的社会构建
在伯格和拉克曼1967年出版的小书《现实的社会构建》中,两位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人类社会的一些习以为常的习俗或制度是如何产生并逐渐客观化为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现实”的。首先,他们回归到一个原始起点,即假设有两位行动者在进行互动。为了省力地再度操作某些活动,人类活动都会逐渐习惯化,形成某种模式。而互动的双方也形成了对彼此应该采取的行动的期待,这种互动的维持也有赖于双方彼此接纳对方采取的行动,即形成一种互惠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固定化下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具体行动,还有行动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仅是特定的某人做出该行动,而是处于相关的结构 (relevance structure)中的行动者都会做出该行动,此时,本来是某个位置上的具体的行动者该如何行动的知识就逐渐固化为任何处在该位置上的人都该如此行动的共享知识,某个位置上的具体的行动者可以泛化为该位置上的某类行动者。当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在参与互动中形成了相互接纳的典型化的习惯性行动 (reciprocal typification of habitualized actions)时,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就发生了。而就某个位置上该如何行动的共享知识则是社会学中所说的“角色期待”。
实际上,参与互动的双方之所以彼此接纳对方的行动,有赖于对对方行动赋予意义。然而,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参与互动的群体是多元的,到底谁的互动模式被制度化为一种共享的模式,即谁的意义被构建为一种主导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在伯格和拉克曼的分析中,语言在制度化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语言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和论证某种意义的正当性,为制度赋予认授性(legitimation),同时特定行动者的意义也可以通过语言和仪式等手段以客观化和外显化,或者说,制度在语言和仪式中晶化 (crystallized)。此时,制度对个体来说,成为一种外在 (external)和强加性的事实 (coercive fact),处于该位置中的个体也必须通过做出与该位置角色所需的行为 (role performance),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及的“合体统”,“合规范”。实际上,也正是通过进入到特定位置上的个体履行其角色期待,制度才被赋予了生命力。个体多大程度内化及履行这一角色期待,会直接影响制度的变形或延续。
本文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精英儒士(师)①实际上有能力与统治者进行互动的往往是精英儒士,但是“尊师”及“师道尊严”一旦成为制度后,则是对所有的教师都提出同样的角色要求。由于传统社会中只要有知识就可以被聘为人师,笔者在文章将儒“师”通儒“士”。、统治者及民众三类行动者在参与构建“尊师”制度。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这三类行动者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如何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进行互动②这一分析思路其实是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主要受Mary Douglas(1986)有关共享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延续的启发。她认为不同行动者基于个人利益进行互动的同时也具有“潜在功能”,最终会形成一些相互接纳的共享观念和行动规则,并且借助合法性机制使这种观念和规则成为一种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法则,从而被人们“想当然”地接纳,而得以延续。见Douglas,M.(1986).How institutions think.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及他们的互动如何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关键事件的影响,以探索“尊师”这一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出现及延续的。根据这三类行动者的互动模式的演变及一些历史关键事件,本文将历史时期上着力分析东汉以前、唐宋时期及明清时期。当然,这项讨论涉及一项制度在数千年历史中的演变,且涉及到庞大的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就本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纲要性的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东汉以前:“尊师”制度初见雏形
在我国,尊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但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教师享受高社会地位一方面是受到其官员身份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知识贫乏的影响。直至春秋时代,才出现了凭借自己知识技能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的“士”阶层,他们堪称中国第一代教师群体[2]。因而本文的分析起点为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出现。
此时兴起的“士”虽然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为普通民众提供教学服务的收入太低,他们更愿意成为占据社会资源的统治者的幕僚,以此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教学成为了他们传播自己思想、扩大自己名声以及暂时谋生的一种手段。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要从“士”那里获取知识 (但是需求并不高,只需满足日常生活,如基本的信件往来、写写对联请帖),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不从事劳动的人有些看不起。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以孔子为先师的儒士群体以重“礼”及“仁义之道”为主要信仰。这些儒士为了提升自己及所主张的思想的地位,纷纷运用所掌握的语言工具,撰文论述了作为“道”的代表者——教师的重要性。比如最早论述“天地君亲师”的荀子,认为“礼”是六经教育的基础,就将“师”作为“礼教”的前提,“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师的地位甚至盖过了礼本身。而“言不称师谓之畔 (判),教不称师谓之倍 (背)”(《荀子·大略》),学生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教师;在《学记》中,则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因为是求学于师,敬学也就意味着尊师。
在儒士的积极努力下,也是出于国家治理的考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道代言人的“儒士”正式获得了其合法化的地位。如葛兆光[3]先生的分析,“独尊儒术”实际上是统治者借“道”的统一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而儒士 (师)则一方面假借统治者之“势”获得权威①笔者注:根据翟学伟的看法,中国社会是一个“假借权威”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师”受尊实际上是因为其与王权的联系,可以假借王的权威[5]。金耀基则认为师受尊在于其成为官员的潜在可能性[6]。,另一方面则借统治者之“势”以树立自己所代表的知识的合法性,从而维护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4]。但儒士的这种对统治者之“势”的主动依附,接受统治者的庇护,实际上也为其后来独立性的逐渐丧失埋下了伏笔。
此时由于社会生产力仍然不够发达,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由于无知所产生的不确定感和被剥夺感会尊重掌握知识的人。而知识的掌握者则可以通过进一步激发或强化普通人的这种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以制造一种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情境,从而进一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7]。经过“独尊儒术”运动后的儒士由于其知识已经成为官方知识,也进一步获得了生产和传播这种知识的合法化地位。朝廷中只设五经博士②笔者注:“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齐、鲁等国,是官职名。如徐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故秦朝时的博士,是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人,他的职务就是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及书籍典章,以备谘询,充当皇帝的学术顾问。至汉代,博士为太学中教师的最高级别。并享有丰厚的福利待遇,但他们除了重点担任太学教授外,还保留了议政、备顾问、制礼、藏书和出使等共6项职责,并奉命巡视地方文教工作。而掌权的儒士也继续构建“礼”制社会,并将儒家知识构建为一种对指导社会实践有着极大影响的规范性知识。如在汉代,当时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皇帝下诏、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皇帝一有什么难以裁判的事情,也往往向五经博士咨询,而吏员们甚至用经书来代替法律③笔者注:如以《春秋》决狱的案例就是典型。。自然,此时的精英儒“师”也就获得了与皇帝“坐而论道”的优待[8]。但相对之前的游“士”而言,此时的博士已经是教职为主,政务为辅了。
三、唐宋时“尊师”的进一步制度化
至东汉后期开始,儒术逐渐衰弱。从魏晋开始,人们效仿的楷模是文人墨客,讲求词藻华丽,加之这段时间各种宗教的引入,特别是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的大力推崇,唐朝时儒家衰弱的态势更为严重。可以说,新的意义体系开始取代原来由儒士所主导的意义体系。儒家道统的衰弱直接导致了教师地位的下降[9]。一般士大夫议论拜师之事,辄“群聚而笑之”,于是人们更“耻雪于师”。面对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韩愈试图借教育的力量及儒家思想重新确立社会规范和秩序,矫正自魏晋以来形成的浮糜的社会风气,因而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代表“道”的师的职责为“传道”、“授业”及“解惑”,以让学生更好地领悟和体会儒道的精神博大。当然,在传统社会这样一个高度功能普化的社会,“师”所承当的社会功能远不及此,他们还参与乡土社会中一系列礼俗事件及社会教化。作为“道”的代表者,师为了获得受尊敬的地位,也为自己建构出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最集中的表现即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构建出强有力的道德要求,率先践行“道”,树立自己的“圣人”形象,以将自己区分于民众,如经历磨难,为了入“仕”以扬道可以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或锥刺股,可以执着于“道”及内心修炼,安贫乐道,克制物欲。这也即是如今我们所流传的“师道尊严”的由来。此时,师受“尊”的地位已开始和师自身的道德楷模角色紧密联系,并一直影响至今。
师受尊除了自身对道德的践行外,也与其自宋代起发展出的高度的主体意识及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有关。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社会中“师”的绩效精英 (meritocracy),或者说是“师”为维护自己之尊为自己提出的两大角色期待。而其对这两大角色期待的践履程度则是其获得社会信任和受“尊”的前提。虽然自隋唐起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然而此时的科举制度仍然受到门第的控制。直至宋代,“四民”才获得了更多的通过科考晋升为“士大夫”的机会,也正是如此,宋代的“士大夫”发展出对国家的高度的责任感和认同感,自认为自己是政治主体而不仅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10],希望能兼有外王事业和内胜功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秦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理念得以继续升华。儒师这种自觉的责任承担及内在问责 (internal accountability)[11]也为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儒家思想在诞生后,自身也有相对的自主性[12]。孔孟之道在宋代被宋明理学继续发扬光大,“尊师重道”、“师道尊严”逐渐被理学家纳入孔孟“仁义”之道并借科举考试而进一步成为合法性知识,被每位读书人所内化。而在一个缺乏社会分工的传统社会中,对于某个角色该如何扮演全社会都有着高度一致的共享知识,读书人从一接触知识开始进行初级社会化的时候,即已开始习得师生双方应该各自扮演的角色。而一旦不履行这种角色,就必须承担着高度的社会舆论压力,甚至无容身之处。由此,“师道尊严”已被建构为一种“议论”(discourse)①笔者注:根据费雪 (Frank Fisher)的界定,所谓“议论”,即指给特定的物理和社会关系赋予社会意义的思想和观念的集合体[13]。,凝结着传统社会中师与生、师与社会及师与君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除了运用语言文字将尊师制度晶化外,唐代也继续延续和发展了一系列上古时期的尊师礼节。如至盛唐时,学生拜师所行的“束修之礼”益发隆重。《新唐书》卷一十五《志第五·礼乐五》中就如下记载了开元年间皇子的束修之礼:
“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修一案,五脡②笔者注:实际上这些礼物并不贵重,但由于师生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共享观念即是“师”应该是安贫乐道的,因而生就觉得若多送礼反倒是侮辱了“师”的人格,而“师”则发自内心或是出于树立自己道德形象的考虑也不会表示出学生礼物过少的抱怨。。其日平明,皇子服学生之服,其服青衿。至学门外。博士公服,执事者引立学堂东阶上,西面。相者引皇子立于门东,西面。陈束帛篚、壶酒、脯案于皇子西南,当门北向,重行西上。将命者出,立门西,东面,曰:‘敢请就事。’皇子少进,曰: ‘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将命者入告。博士曰: ‘某也不德,请皇子无辱。’若已封王,则云‘请王无辱’。将命者出告,皇子固请。博士曰: ‘某也不德,请皇子就位,某敢见。’将命者出告,皇子曰: ‘某不敢以视宾客,请终赐见。’将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辞不得命,敢不从。’将命者出告,执篚者以篚东面授皇子,皇子执篚。博士降,俟于东阶下,西面。相者引皇子,执事者奉壶酒、修案以从,皇子入门而左,诣西阶之南,东面。奉酒、修者立于皇子西南,东面北上。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相者引皇子进博士前,东面授币,奉壶酒、修案者从,奠于博士前,博士受币,执事者取酒、修、币以东。相者引皇子立于阶间近南,北面,奉酒、修者出。皇子拜讫,相者引皇子出。”[14]
其他的太学学生拜师的礼数则同皇子。在这样一系列繁琐的仪式中,尊师行为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也通过附着于仪式而得以客观化和外显化,而师生双方也在这种仪式的体验中逐渐内化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唐代统治者还颁布了一些律令以惩罚不尊师的行为。如《唐律》中《名律例》和《门讼律》等规定,杀“受业师”者列入“十恶”之一;殴伤“见受业师”者,在量刑时,“加凡人二等”。这样的法律观也一直延续至清代[15]。
但与此相悖的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也让天下英雄尽入“王”之彀,中央集权开始加深。虽然在汉代“独尊儒术”,但此时儒师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算特别紧密,他们可以售才学于朝廷,也可归隐山林。统治者若要用才得亲自前往拜见,礼贤下士。但科举考试则强化了儒士 (师)对统治者的依附,师在自主性丧失的同时其实质地位也在下降。如唐朝始设“翰林院侍讲”给帝王讲学,“侍”为“侍奉”、“立”之意,也就是说,帝王之师在名称上从古典地位的“师”到汉代的“上公”及北魏的“三师”,而到唐宋时已开始变为“侍讲”,原来坐在讲学的如今则成为站着讲学。但与明代和清代相比,唐宋时期的侍讲除了讲文史学外,也会行帝王顾问之职,因而也仍享有与帝王“坐而论道”的机会。在北宋时期, “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一些士大夫主动向帝王要权利,试图与王共治天下。如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年),任经筵讲席的王安石连同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向神宗请赐讲者坐,神宗将此事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最后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方认为应该赐坐讲臣,使之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而另一方则认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并无师之实,应自知自重。两派相持不下,宋神宗只好问三朝元老曾公亮①笔者注:曾功亮 (998年-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北宋·泉州晋江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军火家。宋仁宗天圣二年 (1204年)进士,为官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意见,答复是自己给仁宗讲学时都是站立,言下之意是最好还是仿先王之例。后来宋神宗曾赐王安石坐讲,王安石却不敢坐,坚持站立②笔者注:故事原文见黄以周等.(2004).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卷3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顾吉辰点校本.。笔者之所以花笔墨来阐述这个事件,实际上也是想进一步表明尽管自唐宋时期尊师逐渐制度化,但当其落到实际中,尤其是掺和入君臣关系时,就变得非常复杂了,而对师来说,在帝王面前到底自居“臣”抑或“师”,依附于“王”还是维护“道”,以权利为先还是先“自我问责”(自己是否做到“师”的要求了?),这些都构成他们内心自我认同时的张力。
但总的来说,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至宋代,重建政治秩序、重开科举,选拔读书知理的人进入仕途已成为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共识。在这样的脉络下,许多精英士人都懂得采取各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行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声望,如争夺科举及学校改革的主持大权和主考官席位、著书立说,创办书院广招门生,主持地方社会的公益事业等等,设置一系列的洒扫应对仪式以将儒学之道进一步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精英士人的这些行动也进一步将“师道尊严”合法化为一种“似以为真”的社会现实。
四、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实施为“尊师”制度带入不稳定性
虽然在隋唐时期已有科举考试,但直至宋代,科举考试方真正地摆脱考生的门第之别,考试的录取率和公正性都大大加强。作为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统治者不仅借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且通过统一考试的内容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民众则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16]。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掌握科举考试合法性知识的儒师在统治者及民众之间的连结作用。原本只是教学生读书识字懂礼并担任社会道德楷模的教师,自科举考试开始,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训练学生通过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为民间的“尊师”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却使“尊师”多少带上了功利性的色彩[17]。而教师自己也由于获得了进入仕途实现抱负的机会,而开始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教化工作。
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的八股取士制度及一系列文字狱的实行,使皇权高度集中的同时也改变了统治者与儒士 (师)之间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的内涵。如果说唐宋时期一些开明的君主尚且考虑是否给老师赐坐的问题,自明清时,大臣在皇帝面前开始下跪,“士”与皇权的关系开始从原来的共存到共治降为奴役[18]。具体就教师地位而言,虽然出于借“道统”以维护“政统”的目的,尤其是在王朝刚创建时,统治者尚有励精图治之心,大力宣扬尊师,但明朝后期的君主多不好学,不仅不尊师,甚至辱师。如根据《明史》卷152《仪铭传》的记载:景泰元年 (1540年),明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恩典”,一些长者“俯伏不便,横莫能得一,他讲官拾以遗之”。(《明史》卷 152《仪铭传》)[19]。在祭酒、博士学官地位上,在明清时也有所降低。如根据高明士的考证,“国子祭酒”在晋陈时为“第三品”,至唐代为“从三品”,到宋明清三朝时则为“从四品”;而“五经博士”在陈时为“从六品”,到明清时则分别为“从八品”和“从七品”[20]。
与此同时,国家在对官学中教师的考评上也逐渐将重心放到其训练学生科考的业绩上。根据张学强的考证,明初对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进行考核时,如果教师考试通经,且在每个考核期(九年)内分别有9名、6名、3名学生中举人则为称职,可升等;分别有4名以上、3名以上及2名者为合格,可留原职;考试不通经,学生考中举人分别不及4名、3名及2名的为不称职,降黜。这种办法一直沿用至清代,但考核年限改为了6年。集中记载清代地方儒学教师传记的《碑传集》所记载的38位教师中只有9位有过升迁经历[21]。当时基本上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当教官升迁顺利时,可以吸引更多准备入仕者担任教官,而不顺利时,则教师的选拔也变得艰难。通常只有那些政治末阶的剩员才不得已而选择担任教官,而这种官阶的卑微也让教师更加不受尊重[22]。
也正是在这样无法“外王”的境遇下,明清的儒学精英们更加注重“内胜”之道,并且在自己的内心中仍将自己自居高位,如根据余英时先生收集的资料,清初文学家思想家廖燕 (1644-1705)在其《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续师说》中就写道:“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亲,五曰师。师配天地君而为言,则居其位者,其责任不綦重乎哉!”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儒师的这种自觉的责任担当也进一步被统治者所利用,如雍正上台后,为了获得儒师的支持以树立政权的合法性,雍正颁布上谕认为“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钦定国子监志:卷一)[23]由此,从帝王自民间均开始祭祀“天地君亲师”。
虽然仪式上如此,但在现实中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教师则并非都享受尊贵的待遇。对于那些任教于民间私塾的教师来说,若他们所通过的科举考试的级别越高,则被看作是越饱学 (熟悉经典)而被争相延聘,比如有秀才头衔的读书人总是会被争相延聘,并以轿子接到私塾中[24](骆憬甫,2004)。至于他们的教学能力如何,则很少有人关注。家长不会在乎他们的如何能够旁征博引的讲学,只在乎其能否帮助自己的儿子考取功名,当某位教师试图打破常规,增加非科举考试的内容,如唐诗鉴赏,反倒被看作教学不力①见舒新城.(1945).我和教育.香港:神州图书公司.,因为这与考试内容无关。还有一些状元在担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会撰写如何教学的实用锦囊。当然,里面的教学内容、流程和教学方法均深受八股考试内容的影响②笔者注:如清道观二十一年 (1841年)的状元龙启瑞在升任翰林院侍讲时 (1847年)就对家塾课程写了一篇指导,适用于十五六岁童子以下的蒙师。其中内容涉及教材选取、课堂中师生礼节、教学流程等等。见龙启瑞.(1872).家塾课程.出自舒新城.(1961).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p86.,而这种锦囊往往会被口耳相传。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读书人往往被自动看作会教学,而教学模式及教学内容却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学习经历来从事教学,以至于虽然乡间有众多私塾,但却采用同样的教学策略和教学内容,私塾先生如果有事告假,其它同行也可轻易地帮忙代课。而对于家长来说,他们也对这一流程有所熟悉,一旦有老师不严或者转变教学模式,则会以“教不严,师之惰”的理由来谴责。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25]所言,建立在功利性色彩上的制度总是不够稳定的。因此,尽管有“尊师”的道德要求,但在实际中,民间对教师的认同始终受到应试的牵引①笔者注:就比如家庭在私塾开学的第一日中,往往举行极其隆重的礼节。所有配备的东西,如状元糕、包着红枣的粽子 (取义“早点高中”),书包上刺绣的如意及放的锭子 (取义“必定如意”)都体现了家长对入私塾孩童的期望。而在拜菩萨时,享有丰盛祭祀品的并非孔子,而是掌管功名的“文昌君”[26]。,实际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此外,由于明清时考生参加考试都必须有担保人,考试级别越高,担保人的功名也需要越高②笔者注:如乡试时,就需要廪生资格或以上的人作保。而廪生的产生过程是:中了秀才的人每年都必须参加考试,若考的好,可获“廪生”的荣誉,不仅有米拿,还有权利招收童生为门生。门生若考中秀才,则需要孝敬廪生一笔钱。。考生往往拜这些担保人为“业师”。由于级别越高的担保人往往所拥有的人际网络越强,能拜入其门下并与其它考生结成同门,实际上也是扩大自己社会资本的方式,因而考生在考前都会“拜师门”并进行一些联谊。比如清末举人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描述了自己赴省试前就必须提前几天到省城拜师应酬。而一旦考取,往往要给这些“业师”孝敬一些银子[27]。而对于在民间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未获功名的教师来说,其生存状况则甚为凄惨。
由于元朝末年的战争使得全国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明朝时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和诏令,商业贸易有了极大的发展。社会世俗力量的壮大、出版业的发展及对经济资本的重视也多少使“道”统在民间开始动摇,这就意味着儒士 (师)对合法性知识的垄断地位受到动摇。一些儒士(师)转而投奔商界,试图通过增加自己的经济资本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纳捐制”的实行也为这些商人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商业的发展也使民众对教育的需求略有下降,尤其是清朝后期,由于连年扩招,却没有相应的官位,积压了大量功名获取者,聪明一些的家庭纷纷转而从商,因而在民间的教师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使得贫寒的落第读书人社会地位更加低贱。由于他们没有其他谋生的技能,只有带着考场失意的心情进入教学岗位,要么在自家设馆,要么则客居他乡,寄人篱下,无法照顾家人老小,还要受东家的百般限制和冷眼相待,有的东家甚至对塾师百般限制,如不得从事与教读无关的事情, “棋不容看,诗不许题”[28]。刘大棚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写道,“教书之人,抱远志者甚少”, “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于教学一途,“以多得几脩金为事”,“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读书原以求荣,今乃得辱”,若能寻得其他糊口之士,是不会从事教学工作的,“不但耽搁自己工夫,而且大损己德”[29]。可以说,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除了那些彻底对科举及官场彻底失望的读书人愿意将社会教化作为自己的事业外,一般读书人往往只是将其看作是暂时谋生的途径,尽管在从事教学的工作,但却没有“教师”的身份感。这些教书先生在自己边教学边备考的同时,也希望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能够考取功名。如果学生考中,作为开蒙之师的他不仅可以获得名声,也获得了就业机会及学生的庇护。当然,如果他们的教学没有帮助学生获得功名,要么他们会引咎辞职,要么则被东家开除。③笔者注:骆憬甫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上私塾的经历时就记述了一位曾经教自己两年的教师在这两年期间由于骆家兄弟考秀才失败,而他自己也连续两次失败,只好引咎辞馆的经历[30]。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实行后,“尊师”实际上是“尊官”。尽管如此,对于长期在孔子“仁义”道德熏陶下的读书人来说,守“志”及寻“道”仍成为其坚持生存的意义源,如刘大鹏就以“士”自居,因而在“士”自我问责精神的影响下,尽管东家对自己恶劣,学生学习又无任何天赋,却仍然要尽己之心,且拒收东家增加的报酬。也正是他们的这种责任担当,使他们得到社会信任的基础仍然存在。但19世纪末西学的传入对“道”统的冲击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彻底摧毁了士人安身立命之所,儒士自尊自重及受他人所尊的社会条件逐渐消失,一些士人转为现代知识分子,进入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成为专职的学校教师,也有一些仍然怀抱士人理想,试图参与政治,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撰述科举制度废除,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后,儒师如何进一步转变为全职教师以及其与民众和现代国家的互动关系。
五、“尊师”制度形成的机制及其政策启示
上文笔者分析了儒师、统治者及民众三者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出于个人利益进行互动以探讨“尊师”在传统社会是如何被构建为一种社会现实,笔者在此对这个机制进行进一步概括。
早期精英儒士 (师)出于经济和社会两大目标主动依附于统治者,接受统治者的庇护。在王权的庇护下,“师”一方面直接假借王权获得社会信任和尊敬,另一方面则凭借王权支持,将自己的知识建构为合法性的知识,并通过教学及参与及影响日常社会运行活动而获得社会尊敬。由于儒师所构建的知识主要是规范性知识,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师应受尊及师生各自应承担的角色的知识。作为回报,他们也生产并传播着有利于维护政统的知识,自觉执行统治者的命令,承担对上问责,并对统治者赋予了“庇护自己”的角色期待。
实际上,儒师获得其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道”的垄断权,即对合法性语言和意义体系的垄断。这种垄断一方面源于统治者对其的庇护,另一方面则在于“师”对“道”的自觉践行,自觉承担“上致君”“下泽民”的双重角色,这种双重问责精神及他们高度的责任主体意识为其赢来了社会信任。但科举制度的实行意味着统治者已经有一个确保官方知识的制度保障,儒师在与统治者博弈中的资本减少,因而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而科举考试制度也在原有师与民的信任关系中增加了一些功利性色彩,“师”被进一步赋予了“考试训练者”的角色,而当他们无法再帮助学生通过考试时,民众对师的信任会被减弱。
在统治者、儒士 (师)及民众三者互动的过程中,也有一系列的合法性途径使他们这种互动的行为及其中蕴含的对三类行动者的意义得以外显化及客观化,并得以延续。首先,皇权的长期存在以及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颁布律法等约束不尊师的行为,从而维护道统进而维护政统;而在长期的三者互动中,社会也形成了一系列尊师的礼仪和规范,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不尊师的行为;第二,蕴含“尊师”的文本长期都被看做经典的读书人必读的文本;第三,科举制度的实行直接使“尊师”的知识制度化为合法性知识,通过广大学子备考的过程而深深地印入他们的认知中,成为常识,这种规范性知识通过日常实践进一步在民间风俗化和稳定化①笔者注:近日看到葛兆光先生的一份访谈录,他对中国思想为何一直连续而超稳定的解释也和笔者这三点观察相似。见葛兆光:认识古代中国需要多面“镜子”.华夏经纬网,http://www.viewcn.com/zhwh/gxjd/2199659.html,最后登录时间:2010-2-11。。
而统治者、儒士 (师)与民众三者互动的行动模式及各自的角色期待经由上述历史演变历程逐渐得以建制。其中,统治者需要庇护教师,民众需要尊敬教师,而“师”则承担了“传道”、“授业”(包括帮助学生备考)、“解惑”及相伴随的“严”及“道德楷模”等角色。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方——统治者无需仰赖“师”的文化资本或考试制度得以废除,民间对教师需求减弱的时候,三者的实际发生的互动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教师的处境深受统治者对待儒士的态度及政策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上教师群体内部存在着很大分化,不同教师因为自己所考取的功名、所处的官学的级别及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而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断裂”的历史脉络下,“道”统的瓦解及科举考试的废除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教师的文化资本,教师也因此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地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撰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参与互动的人会通过自己的行动促使制度变形,但在制度变迁中,文化认知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尽管统治者、教师及民众三者在不同情境中的角色行为发生了变化,但各自对对方的角色期待的文化认知仍然存在。比如自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来,教师开始逐渐成为承担着具体社会功能的职业人,教师专业化工程也试图进一步将教师职业建制为一种专业,然而人们却仍然用传统社会中“功能普化”的“作之师、作之君、作之父”的师来要求现代教师;又比如当教师遇到当前考试及课改双重压力下,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及领导人应该负起责任来改变这种状况②笔者注:此为笔者在田野研究中听到的部分教师的观点。。但客观地说,这种文化认知一方面可以为社会重构尊师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则可以作为广大一线教师在繁重工作压力下维系自己工作的意义源。
由上所述,传统社会中教师受到尊敬有赖于几个条件:教师自身所拥有的“绩效精英”(对知识的垄断及道德践行)、全社会 (上至统治者,下至民众)对教师所拥有的知识的认可(“道”的统一)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师生各自对所承担角色的自觉履行。因而,如果要重建“尊师重教”的氛围,最根本的应该考虑“师”受尊的合法性问题,是否仍然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来对教师进行认可?如果废除了统一考试,到底当前应该从哪些方面建立教师的绩效精英?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出台的《教师专业标准》无疑对重塑尊师之风具有重要意义。
[1]Berger,P.L.,& Luckmann,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7.
[2]刘捷,谢维和.栅栏内外: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百年省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5.
[5]翟学伟.中国社会的日常权威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7]Bauman,Z.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M].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20.
[8][18]吴晗.论士大夫[A].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神权 [C].上海:观察业书,1948.66-74.51.
[9]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0][12]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 [M].牛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11]Sahlberg,P.Rethinking Accountability in a Knowledge Society[J].Journal of Education Change,2010.11,45-61.
[13]Fischer,F.Reframing Public Policy: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19][20]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 [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16]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J].二十一世纪 (网络版),2005,(10).
[17]阎光才.教师“身份”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及当下危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4):12-16.
[21]张学强.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6):78-83.
[22]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官 [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3]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2):99-106.
[24][26][30]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5]Douglas,M.How Institutions Think[M].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6.
[27][2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8]徐梓.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 [J].中国古籍与文化,2004,(4):64-70.
An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Respect for Teachers”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YE Ju-yan1,LU Nai-gui2
(1.Key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MOE,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China;2.Faculty of Educatio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SAR,China)
It argues that the“respects for teachers”was institutionalized when the three types of actors(the Confucian elite
(Shih),the rulers and the people)interac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formed the reciprocal typification of habitualized actions.The Confucian elite’s monopoly of the(normative)knowledge and their strong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provided the legitimacy base for their high social status and prestige,whil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rovided the institutional base for the“respect for teachers”,which also brought the utilitarian element into the“respect for teachers”institution.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the article also tries to gi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teachers in current China.
respect for teacher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traditional society
G40-092
A
1672-5905(2012)03-0054-09
2011-12-31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 (2009JJD880005)
叶菊艳,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育政策、教育与社会等。
(本文责任编辑:田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