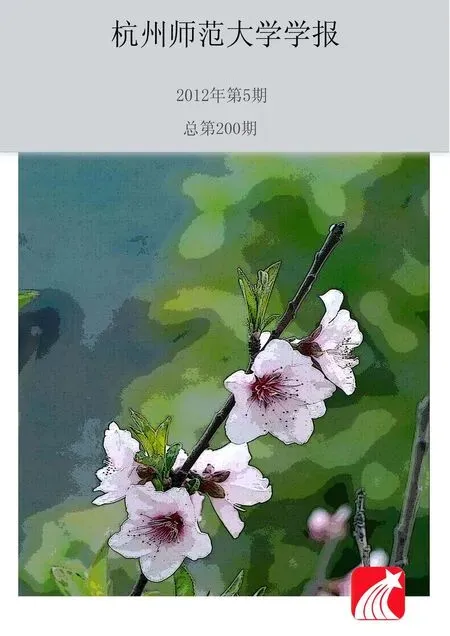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马华文学
2012-04-14陈思和
陈思和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马华文学
陈思和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马华文学的学科定位,采用王德威教授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纳入到比较文学学科视野,更具合理性。世界华文文学并存着三种文学形态:某国家或地区的完全主流文学;不完全主流文学;非主流的边缘性文学。相应地,华语文学在各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亦分三类:完全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不完全纳入教育体制;不具备纳入教育体制的条件。马华文学均属于第二类。应重视马华文学与在地国主流文学之间的交流融合,把马华文学放在国家文学的整体性结构中加以阐释和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马华文学;学科定位;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
2009年1月12日,由许文荣教授策划,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中协)和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马华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正式开幕。正不巧,那天我事先安排了去香港岭南大学访问,动身在即,匆匆地在开幕式上代表东道主中文系致词以后,就直接去了飞机场,把主持会议和接待客人的责任,留给了正在复旦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王德威教授。几年过去,我读到了许文荣教授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的整理稿,其中有一篇杨乃乔教授写的会议综述《第三文化空间:马华文学与比较文学——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1],里面提到了我的发言:
在开幕式的致辞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华人文学、马华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互文学科关系问题。陈思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旦因作者操用汉语走向外域书写,其就可能扩张为世界华文文学,其中包括马华文学;但是在学科的定义上,马华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无法归属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本质属性了。有人主张把马华文学带入外国文学,给予其学科身份的定位,但是在中国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马华文学又是长久的缺席,至少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空间中还不可容纳外域的汉语文学书写这样一种门类。所以,……我们不妨把马华文学置放于比较文学的领地,在此我们可以为其获取一种恰切的学科身份归属。
杨教授把我当时的一个即兴发言归纳得如此清晰,激起我对这个问题进一步阐述的兴趣。我读了这部论文集所收的论文,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马华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二是马华文学的教学实践;三是马华作家作品的深度分析。前两个问题都与我想谈的问题相关,我想借此机会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以弥补我缺席会议的愧疚。
一 学科回顾和辨析
在论述之前,我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学科的形成历史。在内地“文革”内乱结束初期,台湾在政治上尚未解禁,香港澳门尚未回归,内地在政治上已经开始了悄悄的解冻迹象,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成为基本国策。中国人要破坚冰走出去,第一站就是香港。那时台湾人还不能进入中国大陆,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或者从美国绕道回来探亲、或者建议到香港作为中介,两地人士见面。文学交流、学术来往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所以,第一批来到中国大陆的是海外的台湾作家和学者,最先与台湾文学界发生接触交往的地点都是选择在香港。这样,作为学术交流的副产品,港台文学研究和海外作家(当时也是归入台湾文学)研究就萌发出来。当时可能含有许多政治上的目的,暂且不去说它,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就出现了萌芽。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禁后,两岸的民间交流频繁起来,香港澳门已经有了回归的期限,作为工作目标的台湾的重要性,显然高于香港,于是这门学科遂改名为台港文学或者台港澳文学。那时海外华人文学还是附带着,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台湾去欧美各国的华人作家,一般都被视为台湾文学所派生的分支;到了1989年以后,随着内地出国潮汹涌而至,大批作家赴海外求生,他们基本上是用汉语写作,也很少在国外获得固定的职业。他们的身份依然是中国作家,发表作品的地方依然是内地的文学刊物,少数的发表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国家,影响所及主要还是华人世界,但也有部分作家开始影响到非汉语的国家(如严歌苓、北岛、杨炼、高行健等是最杰出的代表)。当时他们的创作还未被视为外人作品,国内文学界都以“海外留学生题材”“海外打工题材”等来命名这些创作。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海外作家声势渐大,对国内文学的影响日盛,特别是严歌苓的小说和电影几乎获得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内地学术界无法再把这部分海外文学的群体仅仅视为内地文学的附庸。这时候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包含了主要是从内地出国的华人作家。然而与此同时,先有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发起,后来普及到内地学术界,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逐步被人接受。从香港的立场出发,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布主要是北美和东南亚各国,基本上是从华侨文学延伸而来。从当年刘先生主编《香港文学》杂志编辑构思和理念,大致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就此慢慢形成。从大陆学界的立场看,它是综合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港台文学、海外文学慢慢发展至今的、内地文学作为其中心但并不包含其中的一个学科类别;另外一部分就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华工、再进而是华侨等移民文学延续而来的一个学科类别。这两个学科本来可以不相混淆,也不需要放置在同一个学科内,但现在被搅和在一起,构成了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特殊的位置。
如果我们仅仅从政治统战的目的出发来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那么内地所代表的中华文化是当然的中心,台湾和港澳地区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属于边缘性的分支,而以华侨文学为源头的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则更偏向边陲。如果我们仅仅依据独立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则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内地的文学能不能列入其间?现在主流意见是不宜列入,理由也是明摆在那里的,如果内地文学这样一个巨无霸占据了研究空间,其他地区的文学就无从显示其独立的意义。但是如果内地文学不列入其间,那么,台港文学也失去了列入其间的正当理由。因为华文文学的“世界”不可能排除中国内地而列入“台”“港”。这是该学科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这一理论困境,王德威教授提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是我深以为然的一个学科概念*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内涵有不同的诠释。杨乃乔在《第三文化空间:马华文学与比较文学——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一文中介绍王德威教授的这一观点时,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并且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归属其中。但本文还是以王教授的论文所阐述的内容为准。。根据王德威教授的解释,这个概念对应英语语境里的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文学,其“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如此,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文学、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语文学、巴西的葡语文学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语系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我们从以上两段引文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语系文学之间的差异,其相“同”是比较表象的,即在世界不同地区中取其相同的语言,来重新规划一个语言的乌托邦;但其相“异”则是本质性的,即在其他语系中存在着宗主国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在华语语系文学中则不存在,甚至相反,华语语系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历经现代性的残酷考验,中华文化不论在大陆或是海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的呼应,恰是华语语系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2]如果我们把这里所引用的唐君毅先生的话稍作修改,去掉“不论在大陆”部分,那么,它的意思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理解的华语语系文学的基本属性,即中华文学在全球的“花果飘零”与“文明传承”。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语系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帝国主义向海外殖民的强势文化产物,相反,它是在自身的漂移聚散过程中,被强势文学所压迫甚至摧毁的过程中,慢慢凝聚起来的语言文学。除了内地以外,台湾的华语受到过日语的摧残,香港以及东南亚英殖民地都受到过英语霸权的压迫,而海外华语在在地国也同样是弱势语言,常常到了第二代以后就慢慢消亡。在这样一种花果飘零的大趋势下,他们凝聚在中华文化的周边维持其文化生命势在必行。即使在今天,许多地区弱势语言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但其语言中已经融入了曾经有过的被侵犯和耻辱的记忆,同时也辩证地显示出语言的复杂内涵和变异特征(这一点在香港文学的语言中尤其明显)。
于是,根据王德威教授所阐述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内涵,似乎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印象:一,针对其他语系文学不包括宗主国语言的特点,华语语系文学则相反,因为华语语系文学本质上不是侵略性的语言殖民过程,而是在发散后不断被在地国的强势语言所压迫,它必须有一个文化返回源流的凝聚过程,使之有力量与在地国的文化环境相抗衡和争取生存;二,华语语系文学主要的研究范围是非内地的文学,研究汉语文学是如何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里传播、生存和发生影响的过程,同时它与各种在地文化相吸收融合后的语言、及其语言审美的特点;三,内地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作为世界华语语系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研究的对象,但一般来说,考察其本身的创作似乎不是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考察内地文学与其他华语语系文学之间的关系。四,华语语系文学其实是一个语言的乌托邦,其中各种华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国与国或者地区的关系,更不是中心与藩属、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是讨论一种同根同源的语言系统在融入了相异的在地文化风俗、语言(地方语、方言)以后出现的新的变异型态。五,从研究任务和范围而言,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更加接近比较文学的学科,而不是中国文学。
二 马华文学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的特殊性
杨乃乔教授在会议综述中分析了马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三者之间的学科联系,他把马华文学的“中国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性”以及王德威教授提出来的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作为三个关键词,意图深入探讨马华文学的学科定位。这个问题必然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马华文学与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马华文学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中国除外)之间的比较,由此再来理解马华文学在世界华语语系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组合的国家,宗教和民族的多元并置决定了马华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说,华文创作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情况与新加坡相似,我曾经多次参加新加坡的文学活动,每次活动都具备了四种语言:汉语、泰米尔语、马来语和英语。新加坡的国家语言是英语,用英语创作文学作品当然是主流,但是其他语言的文学创作也同样享有平等的地位;我有些羡慕他们,由此我曾经想到,中国也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们对于非汉语民族文学的阅读和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汉语阅读来完成的。我从未参加过一个中国的文学会议能够像新加坡一样,各族作家们能够同时用各自的语言进行交流,或者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朗读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对马来西亚的文学交流情况不太了解,我很少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情况。这可能是由具体的国情所致,我不想多加议论,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占马来西亚人口中24.6%(2010年,依据维基百科)的华族,其文学应该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失了华文文学、泰米尔语文学以及其他文学,马来西亚的文学将是一种不完整的形态。就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果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不包括各种语言写成的非汉语民族文学,它也是一个不完整的文学形态。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汉语文学/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的关系,与马来西亚的主流文学(马来文学)/马华文学的关系相比较,无论从写作阅读的人数比例,还是文学传统力量,马华文学在在地国的位置,都高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实际地位。
其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华语文学相比的话,它的特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现在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地区来看,中国内地、台湾、港澳地区除外,其他地区如北美、澳洲和欧洲国家,华语文学作家的主要构成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活动场基本上没有融入在地国,而是依托了原来语系的巨大的文化背景,他们用汉语写作的主要发表刊物、主要阅读者、主要影响都在他原来的生活区域:大陆或者台湾、港澳。除了个别双语作家外,他们的汉语写作对象不是在地国读者,而是故乡的读者。这样一种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仅仅是中国(包括台湾、港澳)在发展中掀起的出国移民潮的副产品,它的根在原乡,主要发展形式是依靠一代代的移民来生成的,而在在地国的环境下不可能有再生能力。所以,这一类华文文学,我们可以把它规划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一个特殊的类别。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人文学、华裔文学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语言的不同,更主要的差别是,移民第二代以后的华人(华裔)的创作已经使用了在地国的语言,他们的创作里或许有中国元素,但是其主要影响是发生在在地国,或者说它已经融入了在地国的文学多元组合(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研究世界华人文学、华裔文学的意义远比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要重要得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即华侨文学的延续,如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他们的作家可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一样,已经融入了在地国家,并且拥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社区,只是规模和影响不如新马,也没有新马那样成为国家主流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
这样我们就容易看出马华文学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的特殊位置了。它首先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在地国的影响与地位,马华文学的对象主要是本国的读者(主要是华族,但也不排除马来族和印度族等其他族群),同时又完全有可能走出国门,在华语语系世界各地区的读者群中发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他们可以完全不依靠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化力量来推动自己的文学活动,对自己的国民发生影响。作为文学原乡的中国文化传统,是马华文学的文化源头,也可以说是同宗同源,但是在历史发展中马华文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新传统以及和在地国的新关系。文化源头与文化中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因此,理论上把马华文学设定为中国文学在海外流布的边缘文学,是没有道理的。在以往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里,其实并存着三种文学形态:某国家或地区的完全主流文学(如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某国家的不完全主流文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某些国家中的非主流的边缘性文学(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如果再深入探讨的话,那么,完全主流文学和不完全主流文学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两个并置的中心,它们之间不是中心与边陲的关系,而第三种形态才是边缘性的文学现象,无论在在地国还是在原来国,它都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用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来讨论这三种文学形态,那么,各种语系的文学本身就应该是平等的乌托邦关系,就不存在什么边缘与中心。
三 马华文学与国民教育体制
三种形态的华文文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其划分的标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在在地国拥有的读者量和影响,以及文学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二是它在在地国有没有纳入正轨的教育系统。这后一个标准,决定了国家文学教育与文学本身的关系,正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即马华文学的教学实践。
一般来说,某国家或地区有没有深厚的文学传统,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良好的国民文学教育,其次是看它有没有与本民族风俗相关的文学因素。如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依靠基本的儒家教育体制,儒家传统包括了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等一整套完整的人文科学的雏形,儒家孔子定六经,其中《诗经》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集,如果没有《诗经》就不可能保留三百篇民歌,民歌终将会在动乱的社会生活变迁中消失。历代读书人阅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文学被直接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得以保存。其次就是民间风俗所拥有的文学因素,譬如说,中国传统民俗中有书写楹联、唱诗对歌等习惯,传统格律诗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遭到主流文学的排斥,却依然在民间被大量保存并且流行,即使在“文革”中,也会出现很多用旧体诗形式来表达的“革命内容”。“文革”以后旧体诗流行更广,尽管一般高校里没有旧体诗创作的课程,但这种文体依然通过民间教育流传下去。文学传统基本上是依靠这样两种途径来保存的,而现代文化市场上流行的文学读物只是满足读者一时的审美娱乐需要,它本身不可能成为传统的力量,但它可能产生延续传统的基础,有一些被人们所喜爱的文学精品就在千百万读者的辗转流布中获得提升、精致化和丰富化,慢慢地成为新的经典,然后被纳入教育体制,被研究、传授和学习。传统吸收了民间的力量,壮大了传统本身,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国民教育体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当然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如果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即使被国家权力硬性纳入教育体制,终究也是会被读者抛弃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说它。
华语文学在各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大致上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类,与前面所说的三种形态相对应:一种是完全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如中国内地、台湾以及回归以后的港澳地区。第二种是不完全纳入教育体制,即华语和华文文学是作为一种民族母语进入教育体制,并非是“国语”教育,像马华文学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由于马来西亚有大量的华校存在,华文教育依然得到很完备的保护。第三种就是不具备纳入教育体制的条件,如在欧美澳洲等,中小学基本上没有为华文开设的必修课程,唯有高校的外语教育(中文系)才可能涉及。教育体制中的不同地位,导致了华语语系文学未来发展的完全不同的前途和命运。
我指出这一点,正是想探讨马华文学的教学实践的最大可能性。这还不仅仅是指如何将马华文学作为一门主干课程在马来西亚教育系统里推行(关于这一点,许多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家都已经在出色地工作),我想强调的是,马华文学既然是马来西亚的国民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该推动马华文学与主流的国民教育亲密合作,加强两者的关系,扩大马华文学与在地国的主流文学之间正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可能。中华文学传统从来就有一种归纳百川的能量,不仅能够及时吸收来自边缘地区的异族文化因素来丰富自己,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比如元清两代)里,它甚至能够包容消化来自主流(包括国家权力)的异族文化,使自身内涵获得更加丰富的能量。这样一种特殊的能量,在当前马华文学的推动发展中尤其需要重视。这才是我把马华文学设定在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意图。
可能有的学者会以为,之所以把马华文学放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是指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存在着跨国家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更为深层的理由是,马华文学在本国教育体制的学科设置里,也应该考虑到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式。马华文学、泰米尔语文学和马来语文学,是同一国家文学属性而不同语种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跨民族跨语言,而且含有各自民族的古老文化背景,充分研究三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现状,有利于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尊重和融合,也有利于华文文学在在地国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项除了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外,很少有人能够胜任的学术事业。在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的学者不一定需要学习华语而华人学者则必须掌握马来语、英语或者其他几种语言,也就是说,马华学者已经得天独厚地拥有了研究和把握两个以上的马来西亚文学种类的能力。他们在研究和提升马华文学的同时,可以把马华文学放在国家文学的整体性结构中加以阐释和比较研究,吸引非华族国民对之发生兴趣,引起重视。这对于马华文学创作,可以不断吸收外族文化因素来丰富自身内涵;对于马华文学研究,也可以逐步地从渊源传承的垂直型思维研究转向多元比较的跨越民族文化的空间型思维研究。
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学者即使从本民族立场出发,他所思考的问题,也必然是有关民族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生存处境问题,必然是关照到全人类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世界文学”。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马华文学不可能走孤立发展的道路,希望它成为一种融合了多民族因素而突出普遍人性、并且在国民文学的整体格局里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华语创作。这是我对于马华文学的最衷心的祝福和愿望。
[1]杨乃乔.第三文化空间:马华文学与比较文学——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J].文艺争鸣,2009,(11):43-50.
[2]王德威.“华语文学研究的进路与可能”专题研讨——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J].中山大学学报,2006,(5).
MalaysianChineseLiteraturefromaComparativePerspective
CHEN Si-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ased on Professor David Der-wei Wang’s conc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make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om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co-exist three literary forms: complet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a country or region, incomplete mainstream literature, and marginalized non-mainstream literature. Accordingly,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completely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completely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onditionally unprepar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belongs to the second kind. Much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be studied with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ubject orientation;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2012-08-21
陈思和(1954-),男,广东番禺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I338
A
1674-2338(2012)05-0053-06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