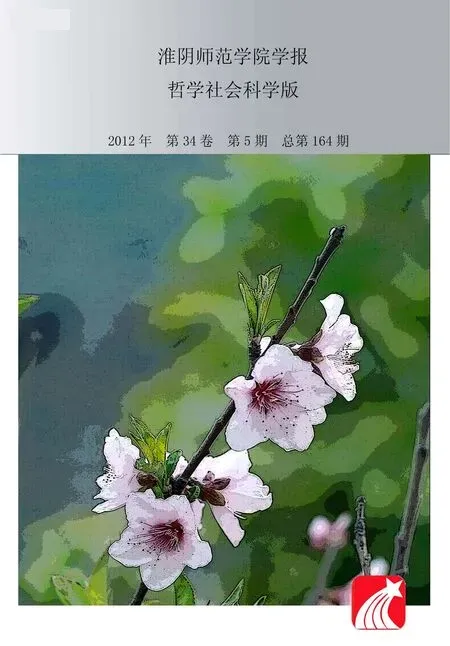对人类生存本相的探寻
——《小说的兴起》的文化分析意义
2012-04-13亢宁梅
亢宁梅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对人类生存本相的探寻
——《小说的兴起》的文化分析意义
亢宁梅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小说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体裁。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都是为了反映背后的本相。虚构的小世界是这个本相的“物质内容”,“真理内容”既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追问,也包括道德探索。同时小说形式的成熟也与资本的支持、媒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从哲学、社会学、文本考据等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个人主义;现实主义;社会转型;虚构;想象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小说这种文体充满好奇和敬畏。好奇的是,作为虚构的故事,也就是戴维·洛奇说的“小世界”,何以能反映背后的本相及真理;敬畏的是,它作为几个世纪以来最大、最沉重的体裁,俨然负载着古希腊史诗的使命,譬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近代以降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从黑格尔、勃兰兑斯,包括中国的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到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对小说的特征予以阐述,但都没能给我满意的答案。直到我读到了《小说的兴起》,长久以来的一些问题才得到解答。
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李维斯和威廉斯注重个体审美经验,突出强调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伊恩·瓦特早年在剑桥大学任研究员,对18世纪英国文学,尤其对笛福、理查逊、菲尔丁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是这个领域的权威。1938年他开始研究英国小说史,在“英国18世纪读者大众的增多和小说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基础上,开始深入小说文本,探讨小说的本体特征与小说的历史形成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他为此付出了十年精力,于1956年写成《小说的兴起》一书,把社会历史学运用于文学研究,从哲学、社会学、文本考据等方面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也许因为中国小说的形成背景、影响因素与英国迥然有别,国内虽然有学者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鲜有关于《小说的兴起》的研究文章。我尝试在相关作品阅读的基础上,对该著作一番粗浅的解读。
一、哲学基础的改变和人的价值的肯定
正如作者所言,“小说绝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文学表现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十分古老而又高贵的叙事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显然,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肃文学的例证。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它可以为包含了所有这类作品的各类形式命名。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也可以被说成是史诗”[1]274。伊恩·瓦特在这里肯定了小说与史诗的共同性,就是对既往事实的追述与肯定。通过文字对事实的记述,寻找背后的本相。这个本相,就是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真实。史诗、悲剧、喜剧是自古希腊时代就有的虚构体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韵律、情节、行动、人物、情感和措词”,史诗和戏剧的主人公都是神或英雄。通过记叙可能发生的事,从而反映出普遍性、内在本质和规律。
亚里士多德把模仿、虚构的艺术(tekhne)提到相当的高度,肯定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虚构故事在艺术有机整体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行动,都是必然的、合理的,具有普遍性的,这也就是后来典型说的滥觞。亚里士多德以知识和逻辑为基础,抛弃了命运和神性,反映了人类自我认知的进步。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终究是不彻底的,他把“认识、实践和创造看成三种分立的活动,既没有看出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也没有看出所谓创造还是认识和实践范围以内的活动”[2]。他仅仅把艺术放在知识领域内,用“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来“符合可然率或必然率”,这是时代的局限。因为人的主体自我还没有发展起来,艺术也刚刚起源。
到了古典主义时代,亚里士多德总结的艺术规律被贺拉斯抽象为“普遍的人性”和“理性”,也就是同类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永恒的标准,开了后世类型说的先河。虽然内涵有严重的倒退,但理论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保持奴隶主贵族的知识话语权力和审美趣味,抵制平民和工商业贵族的钱袋和趣味。可见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从来都是强烈的。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精神或真理慢慢隐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洛克的经验主义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两扇大门。“我思故我在”,对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的事,“我”这个“人”不再禀承神示,特殊的、具体的、感性的客观实体,才是真正的“现实”——“这种变化即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巨大变迁,它以另一种大有区别的图景取代了中世纪时对统一的世界的描绘,从根本上说,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发展的、而且是意外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特定经验的聚合体”[1]26。这种个体的主体改变了集体传说中的精神和英雄,也就摧毁了经典的史诗,促成了小说这种新体裁的生成。史诗中的直接叙述方法被用来反映“真正的真理或永久性的文学价值”。新起的个人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确立了绝对的自我中心,替代了宗教大一统的价值观,从而为个人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这种思想肯定每个个体天生有别于其他的个体,而且与被称为传统的过去时代的思想行为背道而驰,它被瓦特称为“哲学上的现实主义”,是小说兴起的哲学基础。
由经院哲学转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也由中世纪进入了近代社会。瓦特用细致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向我们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方方面面,即总体性的改变。
二、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学分析
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长达几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作过详尽细致的分析,给后辈学者树立了典范。瓦特在马恩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韦伯创立的社会学分析原则,进一步考证了这个转型过程的细节和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永恒的形式和理念这些终极存在瓦解了,变成了感性的当下。这些终极存在一直被认为是无始无终的。而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新的世界观认为时间不仅是物质世界关键性的一维,而且是人类个体的和集体的历史得以形成的力量。如此一来,当下的时间进入了文学,就打破了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永恒不变的道德真理的史诗,也使文学作品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古典主义的特定法则、著名的“三一律”就不再适用于小说。小说情节建立在个人性格逻辑的基础上,即过去的经验决定现实行动,并由此构成了小说情节基本内在推动力。
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宗教一统的社会结构转变成松散的世俗社会。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积聚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形成了经济个人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肯定了“经济人”的合法地位,把金钱视为“世界通用的徽章”,韦伯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征。瓦特查阅了1788年以来有数据记载的文献资料,发现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近40%,全国有大约一半的教区建有学校。占总人口近55%的下层民众处于赤贫状态,中产阶级中的商店主、零售商和文员的人数及财产大量增加。他们和上层贵族一起构成了18世纪读者大众的主要成分。
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还表现在工业产品的增多造成家庭劳动时间大量减少,城市妇女有大量闲暇时间用于阅读,比较贫困的学徒和家庭佣人也可以阅读主人的书籍,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阅读群体。与此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廉价的印刷品和报纸大量发行,登载传奇、犯罪故事、短篇小说和连载长篇小说,适应了读者大众的购买力和阅读要求。1742年,小说(novel)这一术语定型时,公共图书馆迅速增加,一便士就可以借一册图书,吸引了大量虚构故事读者。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明显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业人口,无力接受教育和支付阅读费用。中产阶级的相对低收入与对开本书籍的高定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了廉价盗版小说大量印行,小说的读者量远远小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观众人数。读者的世俗情趣有很大增长,小说作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使文本和古典的、现代的文学作品保持距离,增强故事内容的消遣性和趣味性。期刊杂志大量发行,宫廷和贵族的文学庇护势力开始衰微,市场上崛起了出版商,他们控制了舆论和广告,也控制了作家和读者。写作变成了商业行为,书商是老板,作家成为雇员,形成了著名的格拉布街雇佣文人群。笛福和理查逊都自觉地背叛了传统文学标准,把自己划归到体力劳动者的行列。他们的想象力和写作技巧极大地突破了先前的虚构故事,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强大和自信。他们制订了新的文学标准,也左右了读者大众的兴趣。
恩格斯在论述文学艺术发展问题时,一直强调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因素。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本杰明对此作了深入研究。瓦特分析了经济专门化对小说兴起产生的影响,肯定了技术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积极作用,“小说之所以可能出现,劳动分工起了很大作用;部分原因是社会经济结构越特殊,当代生活的特性、观点和经验的重要差异就越大,这是小说家可以描绘的,也是他的读者所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多,经济专门化提供了小说与之相关的大量读者;部分原因是这种专门化产生了小说才能满足的那种特殊的读者的需要……作为经济专门化的一种结果,日常工作的多样化和刺激作用大为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我们的文化中个人对印刷品,尤其是新闻和小说提供的代用经验的独特的依赖来补偿”[1]73-74。瓦特辩证地分析了经济因素的两方面作用,得出共同生活的丧失和想象力的缺乏是小说兴起的重要因素的结论,与本杰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他既不像本杰明那样为技术的进步大唱赞歌,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对艺术的发展持悲观失望的态度,而是把艺术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予以还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
第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转折。中世纪的阴影远去后,古典文化和拉丁文退回到学者的书斋里,民族语言文化大兴。同时兴起的是世俗趣味和消遣阅读方式的流行。当书籍报刊大规模地被商人、家庭妇女、学徒、佣人们阅读时,文字也就褪去了神圣的面纱,代之以市井故事和村字俗语,弥补了单调生活的不足。他们不再读布道词和优雅文章,只“快速地、漫不经心、无意识地消遣阅读”。由于他们在读者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的阅读趣味和出版商、传媒一起,强烈地影响了小说这种新形式的生成,代表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可以说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世俗的,有很大的反传统的因素,表达了这个阶级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
三、作家与文本分析
瓦特深受李维斯的细读理论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在文本分析上下了功夫。他详细论证了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三位作家对小说形式创立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摩尔·费兰德斯》、《鲁滨逊漂流记》、《帕美拉》、《克拉丽莎》、《汤姆·琼斯》几部作品不同的文本特征。
第一,从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反映方面看,小说堪称史诗。
时间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近代哲学家们多方面论述了主体与时间的关系。洛克把人的个性界定为长时间获得的一种意识的一致性;个体的人与他通过对以往的思想行为的记忆获得的持续的一致性相联系。休谟认为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概念,因而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而构成我们的自我和个性的正是这个链条。世界是哲学的基本范畴,理念与时空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不仅是物质世界关键性的一维,而且是人类个体和集体的历史得以形成的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时间成为构成小说形式的重要因素。小说打破了运用无时间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文学传统,情节也建立在对世界新的认识基础上。小说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密切关系直接依靠它对时间尺度的运用。在这一点上,小说与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迥然不同。
笛福在《摩尔·费兰德斯》、《鲁滨逊漂流记》中展示了一幅个人生活的图画,他虚构了真实环境和鲜明生动的细节,使宏大的历史进程与个人最短暂的思想和行为一一对应起来。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把叙述的所有事件置于一个详细的时间表中,使读者产生了连续不断地置身于情节之中的感觉。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虚构的事件都严格符合年代顺序。它们的共同点是:“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因此,出于一种义务,它应该用所涉及的人物的个性、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这样一些故事细节来使读者得到满足,这些细节应该通过一种比通常在其它文学形式中更具有参考性的语言的运用得以描述出来。”[1]27卢卡契研究小说得出的结论与瓦特一致:小说是被上帝抛弃了的世界的史诗。
第二,文体的确立与推进。小说这种文体的形成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有密切关系。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人天生地有别于其他的个人,而且与被称作传统的过去时代的思想行为的各式各样的忠诚背道而驰。资本主义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个人成为社会所依赖的有效的实体,开始独自扮演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第一次,绝对的国家正视了绝对的个人。”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点。个人主义削弱了公共的和传统的关系,它不仅促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生活,还促进了对人际关系价值的强调。经济个人主义使得宗教迅速世俗化,笛福小说的叙述结构方式体现了清教主义和根源于物质生产发展的世俗化之间的斗争。《鲁滨逊漂流记》开创了小说处理与忏悔自传相竞争的例子,他把自传体作为基础形式,实现了对主人公内心生活的接近。小说的文学语言具有数学式的明了,描写事物的形状、体积、运动和数量,这些都大大接近了普通人的讲话习惯和理解能力。
笛福小说中道德的连续统一性通常包括日常生活中道德选择的精神和物质论题的复杂关系,他的小说比以前所有的虚构故事都更加严密,是虚构故事史的里程碑,体现了形式现实主义的所有要素。理查逊解决了小说的情节问题。古典文学一般把命运作为主要情节,理查逊以求婚作行动线索,悄悄地把不可知的命运变成了普通人的世俗婚姻。18世纪初,婚姻基本上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优雅的、罗曼司式的爱情才与婚姻的意义相同。工厂的兴起使得家庭手工业衰落,劳动力市场上妇女大量过剩,婚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带有商业色彩,姑娘们被迫缔结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不般配的婚姻。这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反映在《克拉丽莎》和《帕美拉》中,构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使文学作品的内容从传奇向现实转换,从而增强了文学的现实性。同时理查逊以底层民众为小说主人公,就打破了古典文学“高等生活”和“低等生活”的分离状态,也打破了“样式分离”的等级外形。小说反映了中产阶级的道德优势,使个人的行为和性格代表宏大的社会问题,因此获得一般性的社会意义,这样的爱情就比传奇文学中传统情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丰富的心理内容。
第三,小说的美学原则的确立。近代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工业的兴起使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开始兴起,社会和职业的分工取代了宗教等生活共同体,城市的街道、商业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这种物理距离的接近和社会距离的疏远,正是城市化的典型特征。新型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每个人的活动范围都不能提供任何永久性的可靠的社会联系,这就产生了一种要在感情上把握和理解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的满足只能依靠对人际关系的隐秘的揭示。这种关系是不确定的,只有当下的意义,不保留永恒的记忆。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古典文学所追求的相式,作家从细节中挖掘有意义的性格和行为,试图对生活作出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书信体裁小说大兴,《帕美拉》、《克拉丽莎》都用书信描绘人物的心理和生活,书信“使关于人际关系的详细描绘成为可能,这种关系又为理想与现实之间、表象与实质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有意与无意之间的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对比所丰富”[1]189。“纸的虚假环境”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典型特征,文学形式再现现实,公众的声音转变为个人的声音,小说比以往任何文学形式更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从锁眼中窥视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小说集中描绘个人经验和人际关系,重点放在生活的私人性上,肯定了当代生活的正常欲望。而私人生活的社会性和欲望下的价值追求就在这种描绘中实现了,这就是小说的美学原则,完全不同于史诗,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文学。
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马恩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综合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在文学本体学和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比较大的拓展。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揭示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从诞生到成熟的长期艰难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清教主义有重要的影响,占社会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文化程度、经济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他的把社会历史学运用于文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具体分析中国小说的生成演变有很大的启示。
[1] [英]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上海:三联书店,1992.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1.
I054
A
1007-8444(2012)05-0669-05
2012-03-15
亢宁梅(1969-),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