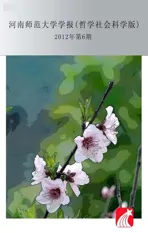一个作家的终结与永存
2012-04-13胡发云
胡 发 云
(武汉市文学艺术联合会 文学创作所,湖北 武汉 430010)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的清晨,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秘书长周文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卧室里。时年四十五岁的他就这样匆忙而又果决地结束了自己坎坷、艰辛、动荡、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说,他们夫妇俩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一个人最后的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他被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草草地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的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在我与文学接近的相当长的岁月中,我从未听说过周文的名字,直至我与妻子李虹相识以后,才知道她有一个姥爷,曾经是一个作家,因崇敬鲁迅而取鲁迅原姓为笔名——周文。知道了周文这个名字曾经和那么多重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鲁迅、胡风、冯雪峰、夏衍、丁玲、叶以群、聂绀弩、楼适夷、艾思奇、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而他的一生,又和我国那么多重要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对于我国的现代文化史还是现代革命史,周文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名字。然而,他却那么长久地消失了。
周文出身于川西古城荥经一户虽已衰落但尚还殷实的人家,他4岁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时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先后做过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等职务,20岁时就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环境里,他算是顺遂的。
周文的父亲是个懂中医的秀才,他开了一家药铺,乡下还有一点田产。父亲在周文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便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能早日成人成才,做家庭的栋梁。母亲给周文包办了一门婚事,随后又让周文到部队里任职。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军阀部队中那些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而又鲜活的素材。
周文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在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这些书刊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通过这些书,他知道了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名字。他由此逐渐看到了黑暗与愚昧,看到了不公与野蛮,并开始有了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的想法。
1930年,周文从母亲那儿要来了两百块银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骗来了两百块银元之后,便决然出川了。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在沿江而下的一路漂泊中,周文遇见了他的革命领路人叶以群,周文从他那里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到了叶以群用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在叶以群的鼓励下,周文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在完成了革命启蒙后,叶以群告诉周文安徽文艺研究会是左联的一个部分,他是左联的成员之一。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叶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从此,周文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养活,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对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同时,这种自豪感中也夹杂着由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所带来的伤痛感。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道德背景。
动荡的岁月总是青年人的节日。1933年4月,周文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与上海一所教会中学的女学生郑育之相遇,随后两人相恋、同居,并结成夫妇。在这一年中,周文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文学作品,将长篇小说《毁灭》、《铁流》,以及美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改编缩写为通俗本,并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雪地》。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收入由他们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中,并将《雪地》这篇小说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可以说,周文几乎是一步就踏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殿堂。
在上海的几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之外,还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譬如进入左联党组,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办刊物、印传单,举行飞行集会,筹备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联络员,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她到延安等。此外,周文还受鲁迅先生的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等物,将它们带到西安后转送给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联络斯诺去延安的采访事宜,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等等。值得提起的是,周文在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为他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周文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常想,如果让周文一直活下去,给他一个清明安宁的环境,他一定能写出许多奇谲瑰丽、惊心动魄的作品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是为鲁迅抬棺椁的16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是周文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们的安全。每逢鲁迅的忌日,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成都,或者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并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纪念文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同年9月,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这是他七年前乘风破浪下江南时的同一条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是逆流而上。离家七载,周文返川。船入夔门的时候,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永不还乡的誓言?七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七年后,他则以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的身份重返故里。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
1939年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早就想到前线去体验生活,然后写作。这一年的12月10日,周文带着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由于中共和阎锡山关系恶化,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转道延安。生活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样式——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以一种庄严、热烈、严谨、朴素并不可变更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
周文来到延安的第三天,便在延河边遇见了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他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毛泽东然后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长等职务。
1942年,高层一声“特务如麻”,边区顿时“坏人”遍地,大批党政文化干部,特别是那些从“白区”过来的知识分子顿时间陷于人人自危当中。周文的师友同道也一个个陷落,如王实味、丁玲、吴奚如、艾青、萧军、艾思奇等。数以万计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被揪出来,他们或被关押、批斗、肉刑,或者自杀、逃跑、痛哭流涕。这一切,都是周文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当那些师友同道历尽屈辱甚至丢了性命的时候,他内心又是何种状态呢。我一直想了解周文在这一段时间里真实的内心状况,曾经在他夫人那里翻寻他当年留下的种种文字,但是,一直都有记录自己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习惯的周文,居然没有留下任何这方面的文字,有几年间,甚至没有日记。
周文其实一直期望能重新去过文学创作生活,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希望如此。从骨子里讲,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位艺术家。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个优秀作家创作的序幕,当我们在为他青年时代短短数年间所迸发的创造力感到惊叹与骄傲时,同时也为他的文学生涯戛然而止感到一种深深的惋惜。
1951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由于马列学院运动的缓慢进展引起高层不满,中直机关党委中途指定周文负责学院的“三反”“五反”运动,并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于1926年入党,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最高领袖强力推进,“打虎”指标层层加码,时间紧任务重,不少单位沿用多年以来的关押、吊打、车轮战、逼供信等手段,“打虎”越多越光荣。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周文接手不久便进入了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但有人以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为由,开始追究打虎人,也由此开始了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两个月,周文陷于了无休无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着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任何人,宁愿让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回到房间,将卧室门闩插上了。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1980年,我第一次读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周文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卷本《周文选集》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两卷本《周文选集》。严格说,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周文,只在1932到1937年间存在过(这其间,他还做着许许多多文学组织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他那一百多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这短短四五年里创作出来的。那是一段清贫、动荡、危险又充满热情与梦幻的岁月。那时周文只有三十岁上下,无论从他的年龄还是从他的作品来看,哪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文都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的感觉、他的文字功力以及他对文学近于痴迷的爱,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作家中毫不逊色而且是极有潜力的一个。在其年轻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独特的、生动而丰富的人物与故事,留下了那么多强烈而真实的时代情绪与感受,今天读来依然是如此鲜活动人。譬如:浓郁的边域风情,古旧的边域民俗,雪山、栈道、小镇、军阀、挑夫、污吏,无谓而野蛮的厮杀,麻木而艰险的生存,茫然又痛苦的期求……周文给我们留下了一幅20世纪初叶川康边域的巨大风情画卷。说这些作品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我想也是不为过份的。它们生动地记录和表现了一段遥远的、已经逝去的岁月。我常常能从中读到黑暗与愚昧,也能读到苦难与壮美。这些都使周文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
我常想,如果周文一直作为一个作家,或许是一件更有价值的事。他的秉性、他的才华、他的情感,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作家,可以写出更多更成熟更优秀的作品来,甚至可以使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长久一些。但在那个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危难年代,作为一个左翼青年,一个党的秘密工作者,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周文是别无选择的。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了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的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一直担承着沉重浩繁的革命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行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革命运行的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