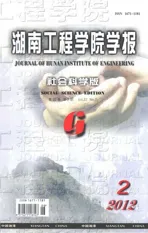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
——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2012-04-13周良发
周良发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
——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周良发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现代新儒家;五四观;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出卖我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北洋政府惩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径。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全民抗议运动,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罢免了曹、陆、章三人。五四运动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而且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作为五四时代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现代新儒家对五四运动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很难完全分开,而且部分现代新儒家学者在论述五四时亦以新文化运动为落脚点。故而,本文在行文过程中将二者揉合在一起,并未作具体区分。限于个人才学浅陋,笔者无力将现代新儒家诸人所有精彩的立论与卓越的观点完备呈现,谨以其开创者梁漱溟(1893—1988)、第二代唐君毅(1909—1978)、第三代余英时(1930—)三人为例,扼要剖析新儒家三代学人的五四观,以期厘清他们对此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深沉之思。
一 梁漱溟:以法律规约爱国行为
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师,梁漱溟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力倡儒家传统的现代复兴;在政治上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宪政建设。作为一位极富现实感的现代儒者,五四运动的勃然兴起不能不引起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的注意。在举国上下声援学生运动的浪潮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不为时论所移,撰写数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此事的观点。对于这场学生爱国运动,梁漱溟既同情学生的爱国之情,对三十多名学生被捕,“也同大家一样的气恼”[1]576,但他对学生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行为却颇有微词。
五四事件稍后,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从法律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言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1]576不止如此,梁漱溟还提出了解决之道。起初,他主张以总统特赦的方式解决:“我初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曲。”[1]577。但他最终还是主张依法处理:“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1]577。不难发现,此时的梁漱溟坚持法律至上的基本立场,认为学生应该做守法公民的楷模与典范,即便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也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
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其轰动效应不逊于两年后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为社会舆论大都站在学生一边,所以《国民公报》、《晨报》等报纸刊发了很多批评梁漱溟的文章。那么梁漱溟为什么在五四运动高潮迭起、方兴未艾之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法律置于学生的爱国热情之上?笔者以为,梁漱溟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知。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不同,梁漱溟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立而行道的社会实践家,并一如既往地将“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作为自己的一生职志。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养成了“除了仰脸的横行,与低头的顺受横行,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的痼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法治意识与宪政精神。所以,在扛起儒家文化大旗之前,梁漱溟是中国宪政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并认为宪政是实现个人安身立命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故而,他认为中国若要破除专制政体、消除军阀割据、实现民主自由,必须形塑国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平心而论,在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之中,梁漱溟对宪政思想的阐扬与持守如空谷足音般显得极不合时宜,但他那极富前瞻性的学术见解在中国法制史上却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时至今日,事过境迁,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时,只能通过他,而不能绕过他。
由于梁漱溟对五四爱国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所以在评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历史地位时,他似乎更看重前者的历史意义,只将五四运动轻描淡写地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插曲。[2]77-81在《蔡元培与新中国》一文中,梁漱溟如是说:“所谓民(国)八九年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则正是蔡先生长北大后所发生的东西。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3]74事实上,正因为新文化派对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才激起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以生命化儒学与快乐化儒学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构建“新孔学”体系,对新文化派形成真正的、有力度的挑战,从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五四运动的见证人与批判者,梁漱溟并未看到五四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二 唐君毅:力劝后来人不要效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老一辈新儒家留在大陆,开始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外,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等人远走港台及海外。面对一无寄托、一无凭借、一无归依之社会现实,他们以“天涯沦落儿”的凄苦心境,在困境中沉潜奋发,毅然承接了老一辈新儒家的未尽之业,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线生机。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首要人物之一,唐君毅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及未来走向作了周详深湛的研究,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国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等极富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现实困境的焦虑和未来走向的瞻念,折射出一个现代儒生的学术品格与人格风范。
面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儒家现实,唐君毅怀着“花果飘零”的文化心境写道:“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阴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4]23尽管只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十分精到地勾绘出唐君毅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立的文化意识。在唐君毅看来,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之所以“花果飘零”,可归因于两点:一是中国社会自步入近代以来,持续遭受东西方列强军事和文化的双重侵袭;二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过激行为,致使儒家传统再无栖身之地。相较而言,五四运动的兴起乃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再难续缕的主要因缘。
在《五四纪念日谈对青年之几个希望》中,唐君毅对青年学子提出五点希望:第一,做一个人;第二,做一个中国人;第三,做一个心灵开放的中国人;第四,做一个尊重中国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中国人;第五,做一个承担延续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之责任的中国人。在这五点希望中,唐君毅似乎更重视最后两点,因为他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缺乏了解和敬意”。他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祖先。如果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些坏东西,那么作为其子孙的我们决不会是好东西。所以一个人若侮辱其历史人物,侮辱其祖先,也就是在侮辱自己。而那些不尊敬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人物的中国人,绝不会真爱中国。这样以来,我们只会把他当作卖国贼,而不是中国人,“只如狂犬之对日月而乱吠,而同于禽兽之行。”[5]639故而,唐君毅力劝作为后来人的青年学子不要效仿:“千万不要学五四时期以来,若干刻薄文人,如吴虞等,轻易侮辱自己生命的祖先,侮辱中国历史上大家共同崇敬的人物,亦不要轻易贬低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价值,然后才配批评中国之历史文化的缺点,而补其不足。五四时代的青年知道反对政治上的卖国贼,现在的青年应当进一步的地方,即在更知反对一切文化上的卖国贼。”[5]640所谓“文化上的卖国贼”,是指陈独秀、胡适、吴虞、陈序经等批判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不难发现,唐君毅基于传统文化的立场,坚决反对五四运动,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旧传统、旧文化,提倡新观念、新文化,以及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种种努力视为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的根源。由此看来,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阐扬,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迷恋与膜拜,缺乏基本的理性思维,因为他无法割舍那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并未作客观理性的分析,而是汲汲于儒家道统的现代重构,所以唐君毅之论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的歪曲与否定。尽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走上“西化”的道路,但五四新文化除旧布新的理论方略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文化未作理性的分析而将之全盘否认的观点不免显得偏狭,它在国民新思维、新观念的传播与塑造上的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 余英时:主张心平气和论五四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余英时没有了第一代新儒家强烈的续统意识,也没有了第二代新儒家“花果飘零”的悲凉心境,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文化心态直视传统儒学的现实遭遇。在多元文化并存与共融的今天,他主张心平气和论五四,并先后写下《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兼论今后文化运动的方向》、《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三篇文章,对它的历史功绩、理论不足与当代启示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一)历史功绩
从历史上看,中西文化交流真正始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余英时将这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分成三个阶段:从明末传教士东来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为第三阶段,故而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转折点。因为五四运动以前,国人尚未自觉地意识到中西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国人只知道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未认识到中国文化需要进行彻底改造。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在这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正如余英时所言:“‘全盘西化’虽然是一种幼稚的错误,但这一概念本身已明白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只在科学、政治制度等枝节的革新,而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改造。仅此一点,五四的功勋便足以永垂不朽了。”[6]153
在余英时看来,只要心平气和地观察一下,我们必须承认五四运动具有两个基本精神:其一,反传统。所谓反传统,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据表现程度的不同,反传统可分成两个层面:彻底而全面的反传统和有保留的反传统。他一反学界之共识,打破学界之定论,认为五四运动的反传统是“有保留、有限度的,并且还是以承认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为前提的。”[6]155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肯定五四反传统的价值:“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一方面固然是要清除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罪恶渣滓,另一方面也正是要克服这种文化的保守性与排他性。在这样的特殊限制下的反传统运动,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6]155其二,文化自觉。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腐败无以复加,国力日呈颓废之势,中国与东西方列强的交战中一败再败,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下,国人才逐渐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就是文化自觉。虽然这种自觉五四之前在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已有所呈现,但直至五四时代才正式形成民族文化的普遍觉醒。
(二)理论不足
虽然余英时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但它并非完美无缺。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缺憾在于:一是缺乏理性认知。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已经探索到中国问题的文化根源并表现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觉醒,但它对文化问题本身的认识却并不深切,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强烈的怨恨之情,模糊了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视线。由于缺乏理性认知,五四时代才会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种非理性的口号,“全盘西化”的偏激口号也因过于伤害民族自尊心而无法为一般人所接受。二是有“破”无“立”。也就是说,五四只“除旧”而未能“立新”。现在看来,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破除旧礼教”都只是破坏性的,而白话文的提倡只是文体的改良,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至于民主与科学,在当时仍只是宣传口号,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更没有一种更高的精神来统摄它们,所以在现实层面的落实上难以展开。总之,五四运动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未能了解文化的再造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躯壳而在生命。
(三)当代启示
重新省察五四运动的是非功过,对我们今后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启示,即我们在追求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时,必须把二者放在新的文化运动的一般基础上才能生根发芽、发挥作用。而文化运动的成败最后系于它能否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根,尽管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外烁的”,但它的最终成就却“必须是内在的”。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中国应站在完成自己文化内在发展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而绝不能也不应走上“全盘西化”的路向,这一点已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倘若对中国文化根本性问题视而不见,一味向西方寻求灵丹妙药,妄想一夜之间重建一个崭新的文化,正表示出国人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不求甚解与急功近利。故而余英时认为,“我们的文化运动,不仅在横的方面寻求如何融解中西之冲突,在纵的方面要求如何贯通古今之变。”[6]161只有如此,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有“破”有“立”。
四 结 语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还催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尽管梁漱溟、唐君毅与余英时的新儒学思想有着许多共性特征,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三人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却见仁见智、各具特色。作为20世纪初中国宪政运动的拥护者,梁漱溟认为国人的一切行为应以法治秩序为重,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主义,对学生的激进行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寄居异地、归乡无望、四顾苍茫的唐君毅认为,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花果飘零”、“本根将斩”之现状乃是五四运动所致,故而坚决反对五四,奉劝青年学子不要效仿;作为第三代新儒家,余英时则立足当下,面向世界,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心态,直视儒学的种种困境,所以能够客观评价五四之是非功过。本文之所以对梁、唐、余三人的五四观作一扼要梳理与评析,旨在说明: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现代新儒家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折射出现代新儒家几代学人对民族前途与文化命运的深情关切与忧患之思,亦透视出新儒家新生代对老一辈“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价值体系”的政治诉求开始有所调适,进而逐步消解。
[1]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4[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高力克.陈独秀,胡 适,梁漱溟的五四观[J].浙江社会科学,2010(8).
[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6[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Viewpoints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A Case Study of Liang Shuming,Tang Junyi and Yu Yingshi
ZHOU Liang-f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not only a vital turning-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but also promoted the rise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modern Neo-Confucian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is students’patriotic movement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ntemporary issues.As a founder of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Liang Shuming dedicated law to statute students’patriotic action;the second generation,Tang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irmly opposed the May 4th Movement;the third generation,Yu had th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assessment to it.The differences reflected that the Neo-Confucian scholars had complicated attitudes toward this movement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modern Neo-Confucianism;viewpoints on May 4th Movement;Liang Shuming;Tang Junyi;Yu Ying shi
B26
A
1671-1181(2012)02-0056-05
2012-02-23
2010年安徽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培育基金“现代新儒家与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研究”(10357)。
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