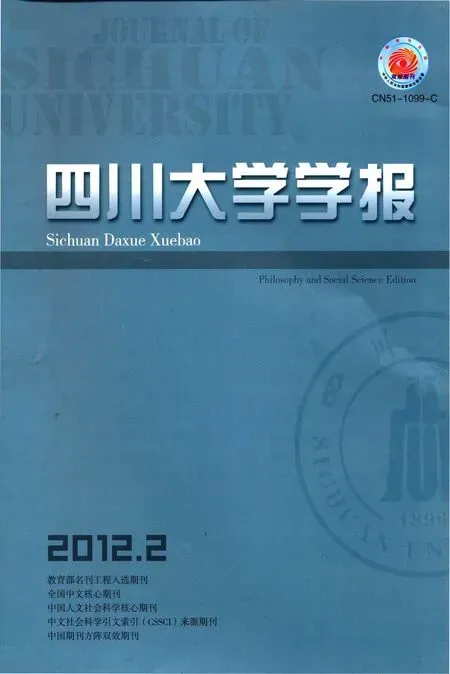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2012-04-12高小强
高小强
(四川大学 哲学系,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纯粹理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关于自由与自然的,其中正题肯定除了自然法则之因果性外还应设定自由之因果性,也就是假定自然之终极原因的绝对自发性,它使那个按照自然法则进行的现象序列由自身开始,因而是先验自由 (transzendentale Freiheit/ transcendental freedom),亦即自由的先验理念或者自由的宇宙论理念,没有它,甚至自然进程中的现象在原因方面的相续序列也永远不会是完整的。这里世界起源之绝对的第一开端不是时间上的,而是因果性上的。①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444-451/B472-479;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erausgegeben von R.Schmidt,SS.462-465,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1993(以下只注标准页码及德文本页码);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K.Smith,pp.409-415,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33(以下只注英译本页码);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8-383页 (以下只注李译本及页码);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4-379页,(以下只注邓译本及页码)。康德认为,自由的实践概念亦即实践自由 (praktische Freiheit/practical freedom)是把自己建立在自由的先验理念的基础之上的,后者在前者中构成了历来环绕着自由的可能性问题的那些困难的真正环节。实践意义上的自由是决意 (Willkür/capacity for choice or elective will or faculty of choice)对感性冲动的强迫的独立性。因为决意就其 (由于感性动因而)受到本能的刺激来说,是感性的;如果它能被本能所迫使,它就叫做畜类的 (arbitrium brutum[畜类的抉择])。人的决意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感性的抉择),但不是brutum(畜类的),而是liberum(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其行为成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固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因而对先验自由的取消就会同时根除一切实践自由。其实康德对自由之可能性的解释仍然着力于人及有限理性存在者,在人身上同时拥有经验性的品格 (einen empirischen Charakter/an empirical character),亦即一个这样的物在现象 (或现相)中的品格,和理知的品格 (einen intelligiblen Charakter/an intelligible character),亦即这个自在之物 (或本体)自身的品格。于是人同时拥有与服从自然因果性及其法则和自由因果性及其法则,两者在同一行为上可以毫无冲突地同时被发现。但终究来说,若两者发生关系,则应当是后者决定或规定前者,毕竟理知的品格、自由因果性及其法则才是决定与阐明人的行为的最高条件与根据。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533-558/B561-586;SS.523-542;pp.465-479;李译本,第431-445页;邓译本,第434-449页。至于决意与意志 (Wille/will or rational will or free will)、与更一般意义上的意愿 (Wollen/wish or desire)之间的关系,可参阅Immanuel Kant,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zen der bloβen Vernunft,Werkausgabe BandⅧ,SS.317-318,332,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t 1977;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Gregopp,pp.13-14,1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张荣、李秋零译《道德形而上学》,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221、233页;宣方译,载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322-324、337页。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单从第三个二律背反来看,先验自由不外乎为完整自然因果性的现象系列而假定的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前提,恐怕得不出“对先验自由的取消就会同时根除一切实践自由”这样的结论。揣摩康德的思路,他或者想表明:现象与自在之物乃至现象与本体之区分,乃是首先在理论理性的工作中确立的,而阐明人之自由的前提亦即人同时拥有经验性的品格与理知的品格,却需要依赖理论理性的确立,于是理论理性之先验自由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为实践自由奠基了。顺便说说,人的自由只能是实践自由!若说它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则说的不外乎是形而上学源于人类理性之超验的根本理想,这一理想植根于只有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人才具有的超验的本体品格,而这一品格就集中体现在自由的自因性之中。而自由的不可知性亦决定了我们对于自由的说明不可能是直接的,只能“绕圈子”。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证明自由的可能性,然后才能证明自由的实在性;只能在理解了“先验自由”之后,才有可能达到“实践自由”。也就是说,理解自由的消极意义是理解自由的积极意义的前提。②参阅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1、83、92页。
要先去说理论理性之先验自由,然后才说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康德在这里似乎是本末倒置或者说“多此一举”了。③康德在后来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却似乎没有秉承这里的说法,而是讲:凭借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从此也就确立了先验自由,而且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其中思辨理性在运用因果性概念时需要先验自由,为着当它要在因果联结的系列中思维无条件者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的二律背反里来挽救自己;但它只能或然地,即并非不可思维地提出这个概念,却并不保证其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为了它至少必须承认的可思维的东西,不因其所谓的不可能而令它在本质上受到困扰,从而陷入怀疑论的深渊。自由概念,就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法则获得证明而言,如今构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心石,而所有其他概念 (神和不朽的概念)原作为单纯的理念其实并无资格保留于思辨理性中,如今却因依附于自由概念而与它并通过它一道获得了存在与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因了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而自由这个理念正是通过道德法则以公示出自己。”“但如果仅仅除了那个普遍的立法形式外,并没有意志的其他规定根据能够充当意志的法则,那么,这样一个意志就必须被思想为在相互关系上完全独立于现象的自然法则,亦即因果性法则。但这样一种独立性在最严格的、亦即先验的意义上就叫做自由。”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Werkausgabe BandⅦ,SS.107-108,138,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t 1974;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Edited and Translated,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Lewis White Beck,pp.3-4,28,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3;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29页;李秋零译,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31页;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6页。以下简注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德文原本及英译本页码,韩译本、李译本、邓译本及页码)或许康德有他想要表达却没能表达出来的更大的思想,我们尝试结合康德第四个二律背反来看看能否找出这个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
二、神或天及天道
众所周知,若说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在寻求自然终极的一个理知的原因亦即自由的因果性的话,那么第四个二律背反就是要进一步地寻求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在康德乃至西人看来它当然就是神。于是康德又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作为“纯粹理性的理想”的神,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外乎是:人类既不能证实亦不能否定神之此在,惟有基于德性法则方能确信一个至上存在者亦即神之此在。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559-642/B587-670;SS.542-604;pp.479-531;李译本,第446-496页;邓译本,第449-505页。这样的“神”当有类于我们儒家的“天”、 “天道”或“天理”,譬如朱子在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时指出:所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而“止于至善”即“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再者, 《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此《大学》引用《尚书》的文字,对此,朱子解释道:“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而《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子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①参见《大学》、《中庸》,朱子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17页。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以下仿此。足见中国的天同万物之性尤其与人性紧密相关,人之德性,人性之必然的善即受之于天。人始终不渝地践履德行以充尽圆满地彰显自己的德性,此乃天之所命,因而乃人之天职。
这方面孔子当最为楷模。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②《论语·述而第七》、《子罕第九》。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后死者。言天若欲丧此文,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今我既得与于此文,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天既未欲丧此文,则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10页。《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见《中庸》,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5页。
此为孔子充分地体认与自信自己的天职与使命,有类于圣王尧、舜、禹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③《论语·尧曰第二十》,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93页。而“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④《中庸》,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25-26页。孔子亦赞美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⑤《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无为而治者,圣人德胜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重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62页。不过,到了孔子的时候,“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孔子深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此命,即天也,天命也。王道之起伏显隐,自有天命。但是,尽管王道不行,可道统绝不能因此而断绝。故孔子毅然决然开启儒家之学统,以令王道道统得以可能继往开来。此即“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之真意!因而他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⑥《论语·八佾第三》、《宪问第十四》,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68、157-158页。他深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然莫非天理之流行,而圣人自己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⑦《论语·阳货第十七》,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80页。此正是《中庸》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1页。所以人切莫欺天,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谓天,即理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但“非知至而意诚,则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无事,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⑧《论语·八佾第三》、《述而第七》,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65、112-113页。
具体如何知天,如何事天?孟子及《中庸》言之甚详:“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①《孟子·尽心上》,朱子注曰: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尽,固不知所以为仁;然智而不仁,则亦将流荡不法,而不足以为智矣。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
尽心知性知天,乃《大学》之“明明德”,亦即格物致知穷理之道。因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②《孟子·尽心上》,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而存心养性事天,乃《大学》之“新民”,亦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之道。如是为之,不疑惑,不动摇,无论命寿短长,皆能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③张载:《西铭》,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63页。如颜子虽不幸短命死矣,但却在短短卅载之生命当中,自始至终地好学, “不迁怒,不贰过”。如孔子之长寿而达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极善境界,却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如曾子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至死而后已。④《论语·雍也第六》、《为政第二》、《述而第七》、《泰伯第八》,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84、54-55、97-98、103页。尤其这“立命”,朱子讲:“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⑤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孟子言:“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程子讲:“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人有天所赋予或者通常说的命里注定的东西,首要的就是人性必然的善,由此而有人当向善和人之行善。此即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人人当为之,不得以任何托辞拒绝,更不得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必将沦为非人!其次,人有感官,有本能,有气血材质,有禀赋性格等等,基本上亦为出生所自然带出。人们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表达了个人的宿命是由它们所决定的。此即所谓“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不谓性”,就是可以改变。尽管禀性难移,但并非不能移,不能易。因而人的宿命或命运亦可因此而得以改变。关键在于人能否持之以恒地性其命,而不可须臾反之地命其性,以至于《大学》所谓“止于至善”。这正是多数人难以做到的,所以才有了各个人极难更改的宿命或命运。这也就是朱子的“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张子所谓‘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其言约而尽矣”。⑥《孟子·尽心下》,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69-370页。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⑦《中庸》,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28、31页。
为政、修身、事亲以及知人,皆首在于知天,而此又正回到了《大学》之道“明明德”上了。之所以知人以知天,知天以知人,是因为天人为一,天人合一。所以,若能充分地知人,也就意味着充分地知天。能够完美无缺地呈现人性人道,也就整全地呈现出天理天道。所以,此时的人性人道,因为充尽地体现了天理天道而与之为一、合一,而就是天理天道,也最是人性人道。而天理天道也因此就是圣人之道。圣人成就了人道之极致,所以为“诚者,天之道也”,亦即“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而我等“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1页。若人能够成就人道之极致,则亦为圣人。这就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以说《中庸》之主旨“在专以发明实理之本然,欲人之实此理而无妄,故其言虽多,而其枢纽不越乎诚之一言也,呜呼深哉!”②《中庸》,朱子《中庸或问》,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5页。亦如今儒唐君毅所言:“故有此诚之一言,而天德、性德、天道、圣人之道与学者之道皆备;随处立诚,而内外始终,无所不贯。是见此中庸之尽性立诚之教,为终教,亦为圆教。”③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5页。所谓圆教即圆实之教,圆教使圆善(至善)为可能;圆圣体现之使圆善为真实的可能。此为人极之极则矣。④参阅牟宗三著《圆善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305-335页。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之所禀受者皆在于天,而人独得天道或天理之全,此则宋儒所言:“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仁义礼智信)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⑤周敦颐《太极图说》,载《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页。这里人之所禀而独得其秀,可比康德之纯粹理知的品格,在儒家尤其明确其得之于天而又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亦即朱子所言:“‘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⑥朱子著《仁说》,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3279-3280页。其中,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出自程子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见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6页。所谓元亨利贞,亦即《周易》首卦“乾”。乾下乾上。“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者,奇也,阳之数也。乾者,健也,阳之性也。”“见阳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为天。”“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而所谓坤元,即《周易》次卦“坤”。坤下坤上。“- -者,耦也,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中略)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参阅朱子:《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一册,第30-31、32页。陈荣捷总结道:“仁是‘心之德’与‘爱之理’。此已成为新儒学的一句成语。其意即:作为体,仁是心之德;作为用,仁是爱之理。仁既是心之德,因此仁是每个人之性,也是普遍的性。”⑦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乃至到了船山还进一步发挥张子《西铭》“乾称父,坤称母”的思想,提出事天即事亲。不但“天人合一”,而且“天亲合一”,天道与孝道为一。⑧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314页。亦可参阅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296、299页。
三、自由、自律与道德法则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之奠基》中,也是从自由的消极阐明,即具有生命与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之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就是自由,它能够不受外来原因的规定而独立地起作用,论说到自由的积极概念,即“意志自由也就是意志自律,意志在一切行为中都对自己是一个法则,它所表明的仅仅是:行为所依从的准则必定是以自身成为普遍法则为目标的准则。而这正是定言律令的公式和德性的原则,从而自由意志和服从德性法则的意志亦即一个彻底善良的意志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自由的积极理念恰恰成就了善良意志选择的行为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的德性法则,亦即成就了人的德行。因而绝不能从人性中某些误以为经验的东西来说明自由,而是必须予以先天地说明。“每一位只能按照自由理念而行为的存在者,在实践方面就确实是自由的,一切与自由密不可分的法则就都适用于他”。因而必须把每位具有意志的理性者仅仅依此而行的自由理念赋予他,他的理性根本上就是实践的,“必须把自身看做就是自己原则的创始者,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这就是说,“必须把自身看做是自由的。其意志惟有在自由理念中才是他自身所有的意志,在实践方面,为一切有理性者所拥有”。至于自由与自律及道德法则的关系,康德的最后结论是:“当我们把自己想成自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知性世界的成员,并意识到意志的自律连同其结果——道德性;但当我们把自己想成是负有义务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同时置于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之中了。”①Immanuel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Werkausgabe BandⅦ,SS.81-89,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t 1974;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Transla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Lewis White Beck,pp.64-72,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Inc.1989;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108页;李秋零译:《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461页;李明辉译:《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75-84页。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更明确了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即:“自由当然是道德法则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因为假使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清晰地想到了道德法则,那么我们就绝不会以为自己有理由认定某种象自由一样的东西 (尽管自由并不自相矛盾)。但是,假使没有自由,那么在我们内心中就完全寻找不到道德法则。”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我们能够直接意识到的首先是道德法则而不是自由,是道德法则径直导致自由概念,或者说是德性首先给我们揭示了自由概念。亦即“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自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惟有在这个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实践法则相一致”。反之,先验自由“必须被思想为对于一切经验性的东西因而对于一般自然的独立性,而不论这自然是被视为单单在时间中的内感官的对象,还是被视为既在空间又在时间中的外感官的对象,没有这种惟一 (在其本真意义上)是先天实践的先验自由,任何道德法则,任何依照道德法则的归责就都是不可能的”。总之,“现在义务的法则,凭借因遵守它而让我们感受到的肯定的价值,通过在我们的自由意识中对我们自身的敬重而找到了更为方便的入门。一旦敬重确实奠立之后,当人们深感畏惧的莫过于在内心的自我反省中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是可鄙而无耻的时候,那么此时每一种德性善良的意向就都能够嫁接到这种敬重上去;因为我们的自由意识是提防心灵受低级的和使人败坏的冲动侵蚀的最佳的、确实唯一的守望者”。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SS.108,139,144,222,299;pp.4,29,34,101,167-168;韩译本,第2、30、34-35、105、176页;李译本,第5、32、36-37、103、168-169页;邓译本,第2、38、44、132、219页。
这种思想在儒家完全是自然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重复前面的论述,因为儒家之“初学入德之门”的著作《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新)民,在止于至善。”首先这“明明德”就在于明确、明澈与明达“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眛,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而之所以要明达之,是因为人之明德常常“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所谓“顾諟天之明命”,或《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就是在说天或天道与人之相通相合者,人之禀性得之于天,亦即人之所以为德者也。而人时时复其本性,也就是在与天或天道为一,以至天人合一。这就是人之德性!而对道德法则的体认自在其中,由此当然还有一番持之以恒的功夫,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等。格物致知,“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而“知至而后意诚”,说诚意为自修之首,关键在“慎独”,为善去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此“几”最是精微,“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①《大学》、《中庸》,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6-7、17-18页。。程子为夫子“非礼勿动”作“动箴”,即:“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②《论语·颜渊第十二》,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31-132页。因而慎独即自律,而且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自律。自律则择善而为,也就是人之自由。所以说我们正是在“明明德”当中最真实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的自由的。反之,我们也只有在慎独、自律与自由当中才可以真正地做到“明明德”。这正是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而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了。
四、结语:天道与人道
有着深厚的耶教一神论文明传统的西方,始终恪守神人之际,神人之别,人一旦逾越这一界线,那就是僭妄,后果就必定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于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抑制人成神的期望。其实这个传统早在耶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据说,罗马凯撒大帝出征凯旋而归,所有罗马人山呼万岁,却始终都有一位奴隶立在凯撒背后对他说:你是人或者你是有死者之类的话。古希腊罗马的诸神全能永生却并不全善,甚至《旧约》中的耶和华也很难被我们认同为全善,《新约》中的神与耶稣呢,亦难说。或许这是对神的臆测妄度,据说神是只需信仰而无须思议的,如此而有所谓天启神学;或者信仰而后思议,如此而有理性神学。前者对于天启只需忠实陈述和照办,像扫罗变保罗一类;后者却执意要思议阐说,于是不说不知道,一说成众说,纷纭杂陈,歧义重重。有人相信一个神;有人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神;有人相信一个道义的神,等等。大家都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神学乃至宗教都成为了纷纷扰扰的战场。但是西方人包括康德在内却执意一神教乃宗教信仰的最高形态,想起佛家虽不如此,而是破除一切执著,自然西方的所谓一神也在内,却到头来也要执著于“出世”,佛家尤其印土佛家对此也并不警觉,可惜可叹!
这样说来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之境界,看似平常,却远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就是表达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③《论语·微子第十八》、《里仁第四》,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185-186、71页。具体言之,则是:既不执意于出世,亦不执意于入世;既不执意于有神,亦不执意于无神;既不执意于一神,亦不执意于多神,等等,而是“义之与比”!正是因为孔子,把他之前譬如商周时的类似于西方一神或上帝之情识化解为与人道相通的天道以至天理,④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天命观具三义:第一义使中国古代之天或上帝,成为非私眷爱于一民族之一君或一人者,而天或上帝乃为无所不在之天或上帝。此为后代儒道思想,皆重天地之无私载私覆,帝无常处之思想之所本。第二义天命之降于人,后于其修德。此为中国后来宗教道德政治思想,皆不重对天或上帝之祈祷,而重先尽人事之思想之本。(中略)为中国人一切人与天地参、与天地同流、天人感应、天人相与之思想之本源。第三义人修德而求天命,及天命不已之思想,则为中国一切求历史文化之继续之思想,人道当与天道同其悠久不息,同其生生不已之思想之本源。简而言之,亦即:“天命之周遍义”、“天命与人德之互相回应义”与“天命之不已义”。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327页。高扬天道、天理,却并不孤悬之,人若能充尽地体认与领会天道与天理,则人道即天道,人理即天理。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易经·乾卦传》所说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而所谓大人,乃圣明德备者,其抚育万物,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同天地之覆载。其威恩光被,无远弗届,若日月照临于四方也。其赏罚严明,不僭不滥,顺乎四时之序也。其祸淫福善,与鬼神害盈福谦,其理一也。其行人事,上合天心,故“天弗违”。圣人之政,顺乎天时,故称“圣政”。其“惟德动天,无远弗届”,鬼神飨德,夷狄来宾,人神叶从,犹风偃草,岂有违忤哉。由此观之,君子之道即大人之德。君子惟能建诸天地而不悖,故能质鬼神而俟圣人。大人惟能先天弗违,故人与鬼神,幽明咸格而弗违。①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4-66页。
此乃儒家天人合一亦即天道人道合一之思想。据陈荣捷,此概念有四成份:其一,天人一道。其二,人为万物之灵。其三,人心能通天地之心。其四、天人一体。以至程氏兄弟云:“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②程颢、程颐:《二程遗书》,第六章。此处所谓合,乃二物之合并为一。若学者汲汲求仁,大其心,变化气质,存天理而去人欲,由是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自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同其明,不是与另一外物联合,而乃由尽己之心性经尽人之心性以至尽物之心性,则人与天同一。如是并非丧失个性,多为一所灭。而乃是个人之全德表现,其感化于天地同流也。③参阅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天人合一”辞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第147-149页。
反观康德,他沿袭西方一贯之旨,始终坚持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于是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其实康德所不明白的是,所谓理论理性的“先验自由”,所谓“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不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吗!而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不正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上达天道而与天道为一吗!况且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曾说过:“人的行为在那种完全不受其支配的东西里,也就是在一个与他全然有别的、他的此在和他的因果性的整个规定完完全全以之为依靠的至上存在者那里,有其规定的根据。”④康德《实践理性批判》,S.227;第105页;韩译本,第110页;李译本,第107页;邓译本,第138页。只是康德为论证实践自由的实在性必得去“绕圈子”,这又是为什么呢?照理,实践自由是我们每个人当下都能够真真切切地体证到的,何须绕圈子才能证实?⑤康德尽管认为“人们也能够通过意志对于除道德法则以外的任何东西的独立性来定义实践自由”,但是,“单单有效原因的自由,尤其是在感官世界里,就其可能性而言是根本洞察不了的;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自由的不可能性无法证明,并且现在又由要求自由的道德法则迫使我们,也正由此令我们有权假定自由,那就是万幸了!”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S.218;第98页;韩译本,第102页;李译本,第100页;邓译本,第128页。况且绕圈子所证实的还是实践自由,那又有什么必要非去绕圈子不可呢?康德哲学的整个探讨固然是从理论理性入手的,不过,如果他的理论理性的探讨仅仅是为了解决经验或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亦即仅属于“先验感性论”与“先验分析论”的主题),那么它能有多大的意义呢?顶多也就是把儒家所谓“闻见之知”说清楚了。它的意义应当超出与超越经验或知识的范围而上达形而上的领域 (此正属于“先验辩证论”的主题),而既然超出与超越了经验与知识的范围,当然就不可被经验与知识所证实与论证,也就是说它不当属于闻见之知,而当属于“德性之知”了。
形而上之天道惟有在实践理性中方可被亲证亲知,一方面,“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是主要说由天道下行而成就众物、众生以至人之性;另一方面,“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此是主要强调由人道而上达天道乃至与天道为一。对天道之下行与人道之上达的亲证亲知都首先离不开格物致知,亦即“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继而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①《中庸》、《大学》,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7、3-13页。诚如《中庸》所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子对此特有体会,他说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②《中庸》,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35-36页。所以我们说康德绕圈子来说先验自由乃至实践自由,其目的当是为此,可是康德为什么又说不出来,或者即使说出来又差之甚远呢?其原因也正是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