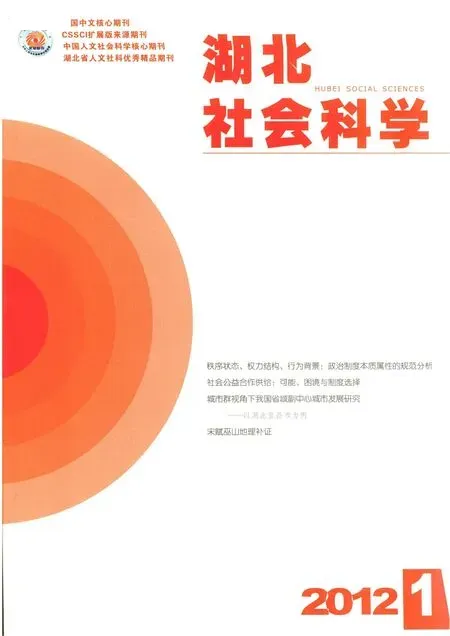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2012-04-12姚坦
姚 坦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姚 坦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其实质是一整套的社会主体和社会意识的意义、角色、规则的制定过程。媒介不仅是被国家或权力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构建权力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阶层。而作为第四媒体,网络一经出现,就从传播的渠道、内容、话语、乃至效果方面显示出对传统媒体意识形态的逆反,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效力,加强了主体自我建构中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反应力量,并最终会推动整体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网络
一、意识形态的媒介和意识形态工具的媒介
作为启蒙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理性概念而被提出来的“意识形态”一词,经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阶级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定制的,反映一定阶级意志的思想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p94)从而开启了“意识形态”的批判之路。
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2](p328)他将上层建筑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社会的权利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采取的是暴力形式;而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构成,以意识形态或舆论方式得以维持的。在这里,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促生、传播、维系着一个社会群里的同一性。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理论和国家理论出发,虚假性或者非真实性被认定为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通过制造虚假的幻想,美化和幻化现实,维护国家权力统治的合法化的基础。而媒介,作为知识和意识的传播中介,理所应当地为意识形态服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助长虚假意识的同时,又使人无法觉察这种虚假性,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最终成就单向度的人。他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3](p9)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则指出:“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4](p150)
更近一步讲,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是被国家或权力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媒介通过传播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赢得民心,为现实或现行制度做辩护。[5](p496-497)
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话语权和文化权依附强大的媒介系统而存在,媒介构造了介于真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之间的媒介世界,并通过揭示事件“真相”、指导分析模式、展示主流观点、提供思考结果等手段塑造并培育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观。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早已就专制统治下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问题作出质疑乃至批判,愿意接受传播上的说教式、强制型意识形态支配的受众越来越少,也使传媒这种支配的有效性越来越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有调查显示:当今中国受众普遍不欢迎传媒宣传,传媒宣传在当今中国受众信誉度越来越低。”[5](p496-497)可以确定的是,现今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开始进行缓慢转型,加速其过程的,是第四媒体——网络在当今生活中的大兴。
二、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意义、角色、规则的制定过程
在讨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构建作用时,阿尔都塞区分了“个体(individual)”与“主体(subject)”这两个理论范畴,并否认人道主义所说的纯粹的、纯净的“个体”存在。因为媒介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感染无处不在,作为个人的主体在进入社会的刹那起,就会受意识形态的“召唤(interpellate)”而成为主体,产生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或误认。换句话说,当个体进入人类社会时,就会接受这一整套的意义、角色、规则,并对自身进行定位和赋值。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其实质就是一整套的社会主体和社会意识的意义、角色、规则的制定过程。通过对传播5w过程的掌控,人们用以判断事物及自我的那些价值体系、审美标准和政治信仰等被媒介所普及。
现实生活中,鉴于媒介拟态环境的存在,人们觉得自我定位是由自己赋值,现实世界由自己掌控,思维和决策由自己制定,从而对意识形态的浸入缺乏察觉。
在阿尔都塞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想象”在起作用。“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关系。”[6](p33-34)
在传播的各个环节中,人只有使用通行于意识形态的固定框架,才能进行互动,进而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亦即是说,主体的社会的内化过程,伴随着个人的外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接触、使用媒介,使用统一的意识形态,从而找寻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旦人自身的意义确定,他就会对周围情境进行定义,即不断解释所见所闻,并赋各种意义于各种事件和物体中,而这种被人类赋予意义的各种事件和物体,会约定俗成为一个“社群”享有“共通的语义空间”的符号系统,他们会对符号含义的共同理解达成一种共识,这个过程是一种符号的互动,是个人自我角色塑造的过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巩固和更新过程。
虽然每个个体在不断塑造自我,但是自我也是社会创造的,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达。个体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才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处世行事。媒介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就是浸入到个体自我设计及互相沟通的环节,以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手段进行控制。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传播的内容、媒介语言和产品的规范化以及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媒介通过内容上的筛取和格式上的规范化,生产和传播着意识形态,最终通过媒介产品,散布到社会和个人。“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7](p329-330)
三、网络传播与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大众传播媒介是国家权力传导和行使的工具,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作为第四媒体,网络一经出现,就从传播的渠道、内容、话语、乃至效果方面显示出对传统媒体意识形态的逆反,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效力,加强了主体自我建构中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反应力量,并最终会推动整体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从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产生了什么效果的模式来分析网络传播的活动和网络话语的发生发展,其中“谁”指对信息的控制;“说了什么”指的是对内容的分析;“对谁”主要对接受者和受众进行分析。
(一)谁传播——主体意识觉醒。
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则绝大多数民众不会以公民的身份存在,难以积极参与本地事务,不能有效地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在传统的传播中,传播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造成媒介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分化出精英和平民两种群体,媒介资源和传播智慧集中在顶端,平民群体几乎没有掌握媒介资源,从而导致他们集体失语,不可能创造和传播自己的语言符号,形成对意识形态的补充和修订。
新兴媒体和网络的不断普及,网络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甚至有人说道,在网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美国著名的媒介理论家保罗·文莱森指出:“信息及其技术总体上是解放人,增加人的选择。主动和互动是网络传播主体的显著特征。网络使用者处于被解放状态,他们的思想丰富,言语具有创造力,主动的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展示自身对事件的看法和第一印象,那些事件中最为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话语或是动作,就是他们进行认识、评价和表达的切入点。此时网民是集传者和受众为一体的符号,他们不再受到传统媒体中“把关人”对信息的控制,有了最基本的表达自由和传播自由。作为网民,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话语内容和符号。如2008年“囧”的诞生,始于中文地区的网络社群间的一种流行的表情符号,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之意,指处境困迫,喻尴尬,为难,同“窘”一样表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极为窘迫的心情。囧字已成为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同时也脱离了网络本身,影响到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进入了主流视野和主流生活。
当网民把自己的看法发到网络上时,必须要能够引起足够多的受众的注意,才能成为流行,使大多数人都喜欢和欣赏,并愿意争相模仿,在此传播背后,是一个群体意见的接受和表达过程。当流行的传播达到一定规模时,它就成为社会舆论中重要的一环,体现出网民整体对媒介传播的自由,最终会对传统的媒介意见形成挑战。
(二)说什么——媒介内容的下端选择。
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网络使用者随心所欲的发言,既可以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与人分享自己的情感,也可以对国家的政策以及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事物进行评论,从而形成一种网络中的虚拟平等状态。在无名、无身份、无传统的背景下,任何言语行为和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传播的内容。亦即是说,区别于普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上端选择,网络媒介传播内容的选择由传统意义上的下端接收者选择。如“躲猫猫”传播的是官员故意掩埋事件真相;“打酱油”传播的是大众对“被”不明真相的反抗;“被就业”的传播反映的是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春晚中小沈阳的《不差钱》也被网友纷纷引用,一面显示了自己对生活困境的自嘲,一面也显示现在人们的炫富心理等,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内容展示了一种生活态度,是网民身份识别的符号资本,也是表达自我叛逆、向传统进行挑战的媒介和工具。这决定了网络传播具有反叛和戏谑的结构性、无序和匿名的创造性、狂欢与边缘的前卫性等文化特征。
(三)渠道——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
网络内容传播主要是通过各大网络的论坛、博客、以及链接实现。博客在文字表达的领域上,可以让每一个人可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我。其他的网民可以通过转载或是评论来扩大博客中某些言论的影响力。在论坛上发言、发帖往往会出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能使聚焦内容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如寂寞党的一句“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之后,逐渐形成一种固有的模式“不是……,是寂寞”的流行语。
同时,网络传播还影响于传统媒体,改变传统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各种各样当今舆论风潮,很多都是首先在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出现,其原因部分是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即时性,部分是互联网的匿名性。一旦某一事件在互联网上已经引起了较大规模的网民关注、讨论,传统媒体就会转载报道,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互联网舆论风潮的盛行,形成了该事件的马太效应。传统大众传媒必须介入到舆论风潮,才能起到控制舆论、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此时就成为了互联网舆论潮的放大器,媒介意识形态传播因而转向。
(四)对谁说——指向权利机关和政府部门。
网络话语会形成巨大的作用力施加于相关者和决策者,特别在一些重大事件、与民休戚相关的决策上更是如此。这在事实上说明,大众试图参与到意义、角色、规则的制定过程。
网络话语中虽然不乏一些自我调侃、自娱自乐、集体恶搞的成分,但是指向最多的则是政府权力部门的滥用职权,以及推卸责任等。如“70码”道出了网民对政府对公共事件的解释及处理不满意时的一种反讽;“这事不能说的太细”折射出了某些政府权力部门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钓鱼执法”暗含着假借道德和法律的名义,做种种聚敛钱财的卑鄙的公权力行为。网络传播是民众社会情绪的浓缩。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视察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五)传播效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网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民意的“晴雨表”,有利于国家机器了解舆论,体察民情。中国司法处理的一个新的路径是:网络媒体报道——社会关注——民间组织和个人介入——其他大众传播媒体的跟进——社会关注的升级——管理部门和领导部门的介入——事件重新调查和认定——对于司法体制的反思。[8](p198)
网络传播强化了舆论监督,引发大众对传播内容的思考。大众的意见对国家权力不但形成了制约,有时还形成了某种改造。压力迫使国家机器直面大众并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基于“想象中的大众”来发布各种信息。同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媒介如何“赢得民心”,又怎样生产“普遍赞同”从而维护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对此,葛兰西所认为的统治集团争取支配权靠的是“将对立一方的利益吸纳到自身”,这无异是说:媒介要赢得民心,要生产出“普遍赞同”,同样要靠传播对受众展示、承诺某种生活利益,或者说,同样要靠传播上为受众呈示“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5](p496-497)因而,媒介意识形态传播必须转向,转向生活,转向隐蔽。
四、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和网络传播的发展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观点。霍克海默早就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他曾说过:“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以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他说:“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结果“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9](p1-2)网络作为不同于纸质的和音视频的技术,代表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语言和传播产品等方面对媒介意识形态的传播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具体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可以孕育出“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首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的空间,[10](p32)尚待观察。大众媒介在构建统一标准和社会认同时,一向存在离心和向心两种趋势,换句话说,它具有在广泛大众中凝聚零散个体的能力,可以更有效和大规模进行社会整合,同时,也带有导致自由、个人主义和分裂的因素。而在网络媒介身上,两种因素都存在,并表现明显。网络一方面可以汇聚使用者的目光,形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网络全面超越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并吸收它们各自的优点,具备巨大的吸引力,在产生虚拟的联系感的同时,分流网民于不同的使用圈。因此,网络传播的具体发展尚不明朗。但不管何如,网络确实冲击了现有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带来了新的发展趋势。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葛兰西.狱中札记选[M].伦敦1971年英文版.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夏冠英.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生活化[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4).
[6]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4).
[7][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李良荣.历史的选择[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99.
G206.2
A
1003-8477(2012)01-0183-03
姚坦 (1984—),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郁之行